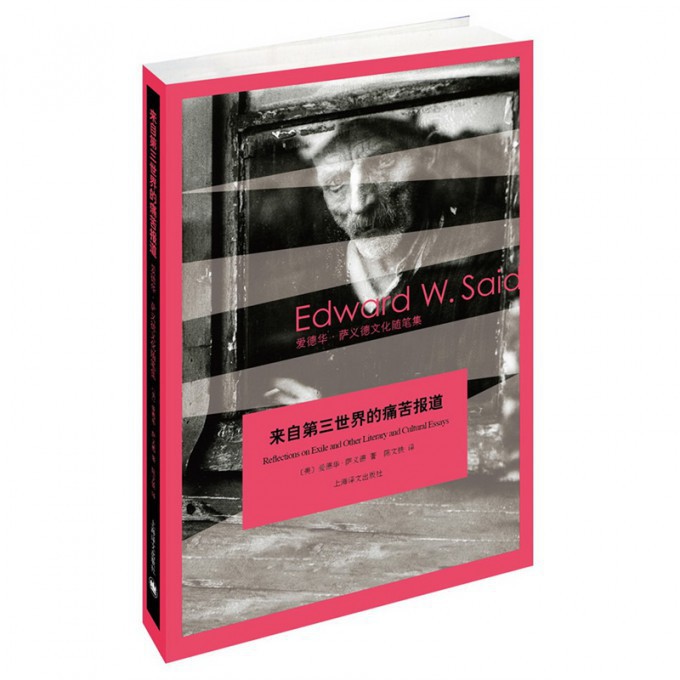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4.70
折扣购买: 来自第三世界的痛苦报道(爱德华·萨义德文化随笔集)
ISBN: 978753275835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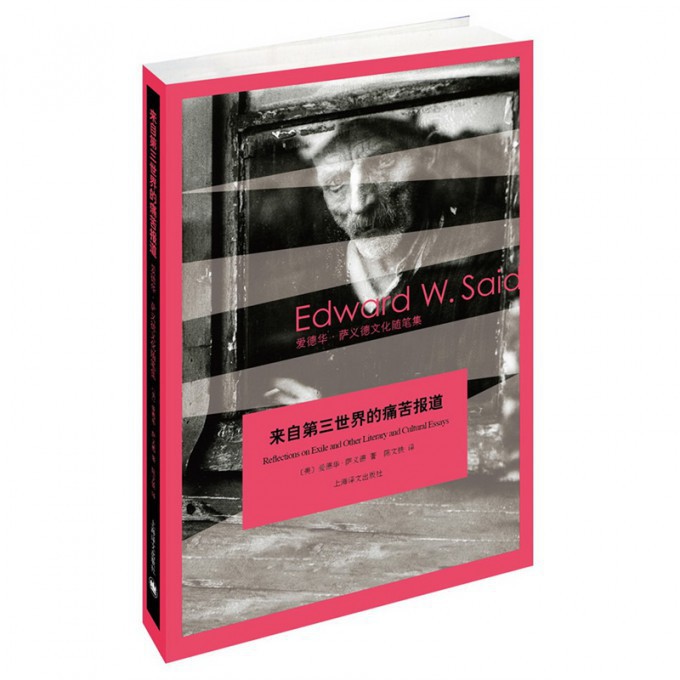
爱德华·萨义德(Edward W. Said,1935-2003),当今世界极具影响力的文学与文化批评家之一。生于耶路撒冷,在英国占领期间就读于埃及开罗的西方学校,接*英式和美式教育。1950年代赴美就学,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从1963年起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教授英语文学和比较文学,是享有声誉的文学和文化批评家,同时也是乐评家、歌剧鉴赏者、钢琴家。他的乐评、文学评论和他的理论著作一样,学识渊博,兼有清晰明快的行文风格。其主要著作包括《东方学》、《巴勒斯坦问题》、《报道伊斯兰》、《文化与帝国主义》以及《流离失所的政治:巴勒斯坦**的奋斗》等等。
赫什将文学批评分成两个阶段:**阶段是直觉 和表达深刻情感;第二阶段是反思和逻辑推理。批评 可能被当作艺术,也可能被当作科学。他在著作《阐 释的效度》中,特别关注的是第二阶段,虽然他似乎 不愿提及**个阶段如何影响第二阶段这一问题。不 管怎么样,他要求用一种逻辑的方法作为证据来衡量 话语,需要一种方法确保有效,这是合理的。这就需 要批评家关注要批评的作品,问自己一些问题,要么 使自己对于作品的论述合理,或者希望能够改正那些 批评。无论哪种情形,他都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赫 什认为,文学作品包含一种意义,既不是随意也不是 时刻变化的。值得称道的是,他认识到巨大困难不仅 在于阐释作品的意义,而且在于阐释意义的本身。所 以,在书中他不辞辛劳为这个不大张扬的词汇“现象 学”辩护。在现象学中,意图(用胡塞尔的话)或含 义,与意义相对,是我们常用的词汇,甚至废话都有 自己的含义,尽管是无法令人理解的含义。在文学中 ,意图的*广泛的范畴是题材,每部文学作品都属于 一种类型、完成一项任务,这样我们才懂得《失乐园 》是一部史诗,它总会实现某种特定的社会和历史的 期望。赫什其他的观点都不是很明确,因为他*制于 以下几点:(1)“没有既普遍又实用的普遍原则” ;(2)“没有概括观点的原则”。其余时间里,他 都致力于基础研究:区分含义和意义、批判实证主义 、对含义和可能性进行概括。 赫什的观点*有趣的是,他认为批评就是“因为 有必要理解才去理解”。我怀疑他的低调会让他把关 于一个批评家的逻辑工作的*后言论与海德格尔谈论 荷尔德林②的观点联系起来。在评价诗人时,海德格 尔在文章中说,他对荷尔德林的评价方式是“思想的 必要性”,是指头脑有必要执行一系列的行动。赫什 也许十分强调这项任务的有效性,可是当我们读普莱 ③或者布莱克默时发现,有效性只不过是他们欣赏文 学的必要的美而已,因为那是他们思想的核心。批评 常被冠以霸道恶名,以欣赏的名义对作品进行解读: 用方法生吞活剥作品,以辩论分而治之,以灵活多变 来占据潮流和“时代”。相反,普莱希望在批评中延 长文学的生命,布莱克默希望揭示文学绕着“现实之 外的大圈”(亨利·詹姆斯语)。因此,批评既要满 足文学的期望,同时又与之共生存在。文学与批评是 内部进行对话,不是公开的对立。我们可以说,这样 的批评距离艺术太近,然而,依我看,文学和批评越 迎合艺术,毫无疑问,批评就越不在意准确。小说形 成了自己的准确模式,但赫什对此丝毫不在意,因为 甚至在批评中也有两种文化。 只有在一开始阅读和欣赏布莱克默和普莱时,你 才会想起海德格尔。他们两人的作品大相径庭,各有 自己的特点,几乎自成体系(尽管还没有足够赞誉的 词语),很难归于普遍规则之下。他们的批评需要我 们给予艺术同样的关注,这点值得争议。除了几篇精 彩的文章外,**的还有,如希利斯·米勒和约瑟夫 ·弗兰克对普菜的评论,兰塞姆③对布莱克默的评论 等,多数批评家认为,这些评论尚不足以引起关注。 而且,很糟糕的是,布莱克默和普莱使用的习语让人 无法理解。两人都不习惯辩论,也不习惯用左手写的 “只言片语”。普莱的批评论,尽管被错误地丢进了 作为阐释方法的新批评中,但是它和布莱克默的批评 一起,似乎要强烈地激起读者的想象意识。因为两人 的批评就是一项事业,目的只不过是重新建立经历体 验,使人们从原始的起点到以文学或其他形式表现出 的方式来理解它。这样的事业,布莱克默称其为使文 学发挥作用,前提是假设*终有一个智者能接近生动 的经历,并融入文学中。希利斯·米勒谈到普莱的“ 静寂主义”进入作家的意识,约瑟夫·弗兰克谈到布 莱克默“情感概念化”的句子:两人的风格都有意保 留文学那种味道,尽可能既有差别又让人感到亲切。 (有趣的是,布莱克默的课堂模式,正如布莱克默在 普林斯顿的一个学生亚瑟·戈尔德描绘的那样,是证 明一个人和文学有多大的亲密程度。)尽管普莱和布 莱克默差异明显,但他们二人对作家的经历贡献** 大,在处理和表现那种经历方面具有**的才能。 这样的批评的代价是相当大的,也是必要的。布 莱克默躲躲闪闪,像有评论家说的那样,他好像在玩 掩球游戏一样,既不能**阐明一个观点,又无法放 弃它,这让他很生气。他的巧智是扭曲的,多变的, 他的始终如一是个谜。普莱的语气暗不文学本身的声 音,仿佛他评价的每个作家只不过是个概念,被庞大 意识瞬间照亮。不客气地说,布莱克默就是20世纪的 “兜圈子所”(CircumlocutionOffice),而普莱 是“趣味先生”(MonsieurTeste)。然而,还有比 这*大的价值。布莱克默的警句显示了一个作家旺盛 的精力,与众不同的才能,后者以“资产阶级人文主 义”的方式“把焦虑的潜意识技能与逐步亲近的过程 ”与深刻浸入结合起来,这种推理的能力从来没有对 “复杂无规律的事物”失去理解。普莱机智超群,选 择引言恰到好处,善于描绘一种意识来揭示事物本身 的“纯粹的瞬间”,把文章中不被重视的抽象概念这 种不寻常的东西与几乎令人吃惊的特性**结合在一 起。这两种情况都不属于布莱克默所说的“研究的游 戏”。每一种情形阅读文学作品就像阅读一边发生一 边创作的自传一样。 我想,让人永远惊奇的是普莱和布莱克默表达的 亲近或亲密的程度在语气上如此迥然不同。普莱的一 本名为《圆圈变形记》的书,是第三部被翻译的作品 。他的书总是关于一个主题:时间、空间、循环,这 些主题也是其他一系列作家关注的主题。一个作家自 我意识的初始时刻,他的笛卡儿式的“我思故我在” 思维,都会暗示他的内心世界,并从此继续按此方式 生存下去:普菜在《出发点》中说,人类被赋予瞬间 ,然后大脑创造持久,持久的“真正方向是从孤立的 瞬间到暂时的连贯”。普莱的方法就是把可以衡量的 维度归为一个作家的风格,这是作家的意识被转换为 语言的持久。这样,普莱可以研究时空内在的变化, 宇宙论风格及意识的变化,以此作为历史敏感度的证 据。在《圆圈变形记》中,普莱选择了圆圈当作康德 的物自体,它的完整和无懈可击为人类的思想提供了 一种疏远的模式。普莱认为,这种思想是为了获得完 美的内容、广泛的视野、中心的地位。(*新一期《 泰晤士报》文学评论副刊嘲笑他这些观点是“花哨” 的不现实的想法,但是我不难发现这种想法是对时空 感兴趣,甚至有些偏爱。)因此,在十八章中,其中 有四章是回顾整个时期,十四章是谈论单个作家,他 直接接触具体意识。P25-29
萨义德作为**的公共知识分子,在**拥有很大的读者群及知名度。**对于萨义德作为文学和文化批评家的角色,介绍得比较少。然而,萨义德在西方的学术地位,尤其是公共声誉,恰恰来自于这一方面。这本书精选了萨义德35年创作心血的文化随笔集,能让我们捕捉到一个区别于理论家的,*为渊博、开放、公共的知识分子形象.西方人文学科近三十年来的一系列核心话题和讨论都可以在这本随笔集中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