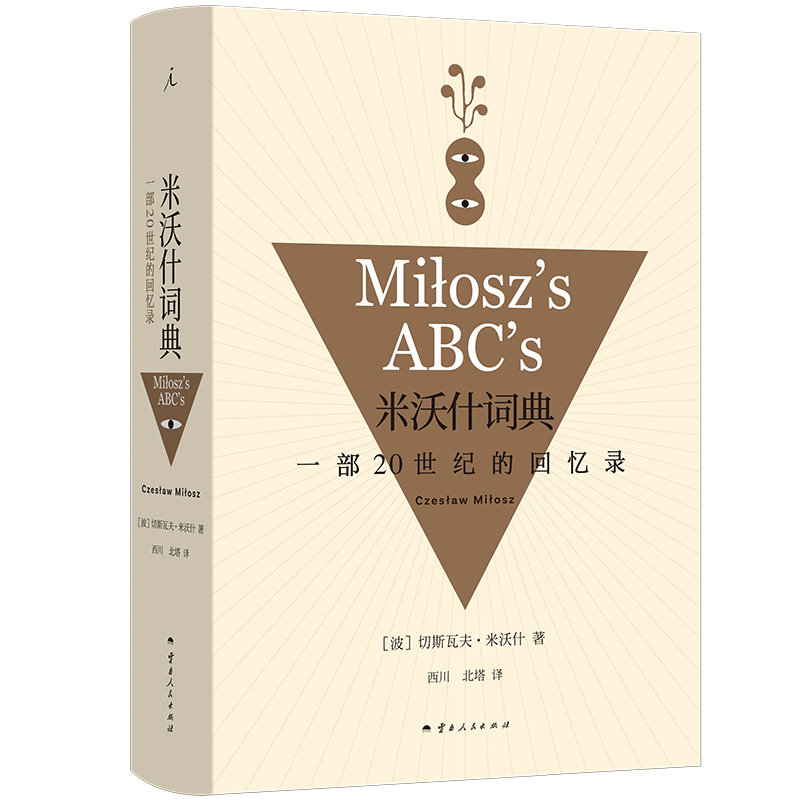
出版社: 云南人民
原售价: 82.00
折扣价: 50.90
折扣购买: 米沃什词典: 一部20世纪的回忆录(2023版)
ISBN: 97872222261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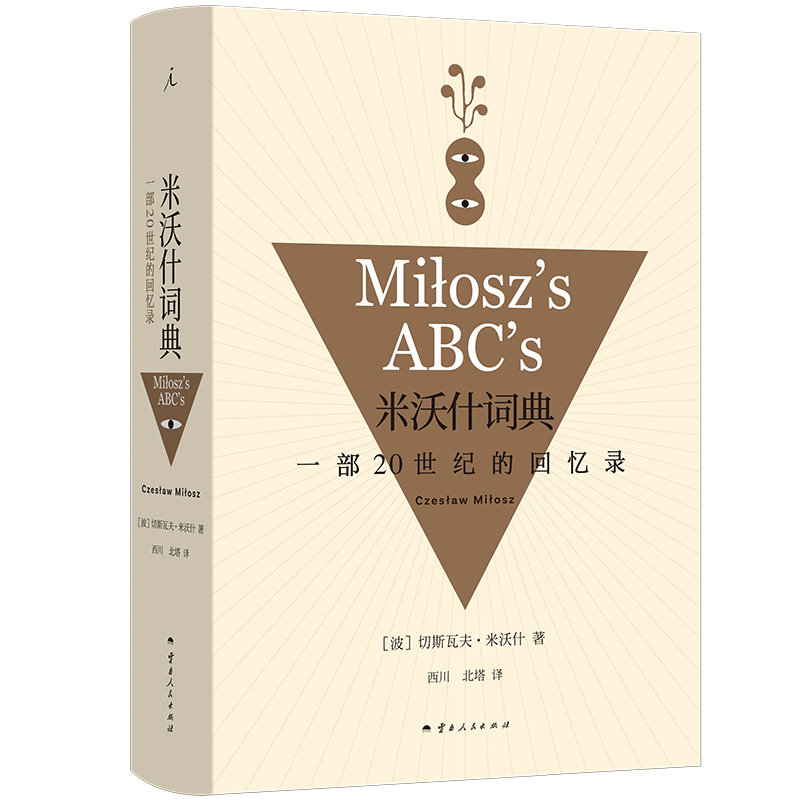
切斯瓦夫?米沃什(Czes?aw Mi?osz,1911―2004),波兰诗人、作家、翻译家,1911年出生于波兰第一共和国的立陶宛。1978年获诺斯达特国际文学奖,198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被誉为“我们时代最伟大的诗人之一”。著作宏富,主要作品有诗集《冬日钟声》《在河岸边》《三个冬天》《白昼之光》《日出日落之处》《无法抵达的土地》,自传体小说《伊萨谷》,回忆录《故土》《米沃什词典》,日记《猎人的一年》,政论《被禁锢的头脑》,文集《站在人这边》《在时间荒原上》,诗论《诗的见证》等。
ANUSMUNDI(世界肛门):世界的阴沟。某个德国人1942 年曾这样白纸黑字地定义波兰。我在那里度过了战争岁月以及战后一些年头,在许多年里,我试图理解一个人怀揣这样的经验度日,究竟意味着什么。哲学家阿多诺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在奥斯维辛集中营之后,写作抒情诗将令人厌憎。哲学家伊曼纽尔·列维纳斯将1941 年确定为上帝“抛弃”我们的时候。而我,明知在这世界肛门所发生的事情,身处这一切的核心之地,却写下了田园短歌《世界》及其他作品。我是否应该为此受到谴责?可能的话,最好写下一份指控状,或者一份辩护词。 ★ ANUSMUNDI(世界肛门):生命不喜欢死亡。只要有可能,躯体就会站在死亡的对立面,坚持心脏的收放,传布血流的温暖。在恐怖之中写下的轻柔的诗歌宣示了向生的意志。它们是躯体对于毁灭的反抗。它们是颂诗(carmina),或次第展开的咒语,让恐怖暂时消失,安宁浮现——一种文明的安宁,或者说得更贴切些,一种幼稚的和平。 ★ BEAUVOIR, Simone de(西蒙娜·德·波伏瓦):在女权主义者中,波伏瓦的嗓门最大,败坏了女权主义。我尊重乃至崇拜那些出于对妇女命运的体认而捍卫女权的女性。但在波伏瓦这里,一切都是对下一个知识风尚的拿捏。 ★ CENTER and periphery(中心与边缘):塑成我们文明的一切—《圣经》、荷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否均出自权力的中心?不总是这样。有比耶路撒冷更强大的首都,而小小的雅典很难与埃及一较高低。……创造的冲动从一国游走至另一国,是件极其神秘的事。由于缺乏明确的动因,我们便用承袭来的时代精神(Zeitgeist)一词指称它。 ★ CURIOSITY(好奇):崭新的发现会层出不穷。这就像一次穿越迷宫之旅,当我们穿行的时候,迷宫也在悸动,在变化,在生长。我们独自进行这一旅程,但同时也与全人类共同的事业,参与各种神话、宗教、哲学、艺术的发展,以及科学的完善。驱策我们的好奇心不会满足,既然它不会随时间流逝而稍减,那它便是对于死亡趋向的有力抗拒。不过,说实话,我们中的许多人在步入死亡大门时同样怀着巨大的好奇期待,急切地想去了解生命的另一面究竟是怎样一个世界。 ★ BIOGRAPHIES(传记):传记就像贝壳;关于曾经生活在其中的软体动物,你无法从贝壳那里了解多少。即使是根据我的文学作品写成的传记,我依然觉得好像我把一个空壳扔在了身后。因此,传记的价值只在于它能使人多多少少地重构传主曾经生活过的时代。 ★ BIOLOGY(生物学):由于以有机体果腹,每一生物都以其他生物为食。自然界就是由吞食者和被吞食者所构成。它的基本假设是冲突斗争,强者生存,弱者灭绝。基于科学数据,即便哲学对此也只能得出悲观的结论,但这还不是生物学发现的最残忍的一面。生物学最残忍的一面,是将强者供上神坛。 ★ DISGUST(厌恶):这个俄国革命时期的故事是约瑟夫·恰普斯基给我讲的。在火车站的自助餐厅里,一个人在吃晚餐。其服饰、举止使他有别于周围的环境,他显然属于战前的俄国知识界。他引起了坐在餐厅里的几个流氓的注意。他们走到他的桌子边,开始嘲笑他,最后还向他的汤里吐痰。这个人根本没有反抗,也没想把那几个闹事者赶走。场面持续了很长时间。突然,他从兜里掏出一把左轮手枪,把枪管插进嘴里,开枪打死了自己。很明显,他在此遭遇的事情,是往一盏已盛满厌恶的水杯中投下的最后一滴,那些丑恶行径在他心里引起的厌恶已达到极限。不用说,他细腻敏感,在一个温文尔雅的环境中长大,受到较好的保护,远离社会底层习以为常的残酷的现实。那种残酷和庸俗随着革命翻腾到了生活的表层,变成了苏维埃的生活品质。 ★ NUMBER(数目):当我们想到人类的总数,当我们想到这颗星球上每天有多少人出生,我们很容易陷入启示录所描写的那种惊恐境地。这样想的坏处在于:我们把过去的时代理想化了,认为过去的人们生活得比现在好。这种看法显然不对。不过,过大的数字会给我们的想象造成困难。因为只有神灵才能以这样的方式观察人性,人类自己没有资格。在一张俯拍下来的都市的胶片上,分布着千万个亮点,那都是汽车。那些坐在车里的人们小得像一些微生物。人类因为总数众多而变得如此渺小,这“一定让某些领袖和暴君感到很有兴味”,我在1939 年这样写道。换句话说,他们可以将芸芸众生看作恒河沙数的人群。多一百万,少一百万—那又有什么区别呢? ★ DISAPPEARANCE, of people and objects(消失的人和物):波兰文学中有些名字一直活跃在我心中,因为他们作品的生命力至今依然;有一些则不那么活跃了,还有一些拒绝再出现。但我所考虑的不仅仅是文学问题。我的时代,我的二十世纪,重压在我的心头,它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人们的声音和面孔所构成的,而现在,他们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待上片刻。 1. 一代知识分子中活到最后的人,一份20世纪的纪念与证言。将记忆与痛苦安排停当,为人物与往事登记造册——“我的20世纪是由一些我认识或听说过的声音和面孔所构成,他们重压在我的心头,而现在,他们已不复存在。许多人因某事而出名,他们进入了百科全书,但更多的人被遗忘了,他们所能做的就是利用我,利用我血流的节奏,利用我握笔的手,回到生者之中,待上片刻。”(米沃什) 2. 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人生之书,比《被禁锢的头脑》更为深邃广博的精神地图,揭示米沃什创作与反叛的源泉——在很长一个时期内,米沃什以《被禁锢的头脑》的作者而知名,获得诺奖之后,更多人才知道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大诗人与散文家。美国桂冠诗人哈斯称米沃什为“20世纪重要与恐怖事件的目击者”,本书是米沃什进入生命最后阶段的回顾与总结,将庞杂的事件、人物、地域、主题置于敏锐的审视之下。 3. 译文全面修订精校,中文版二十周年典藏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