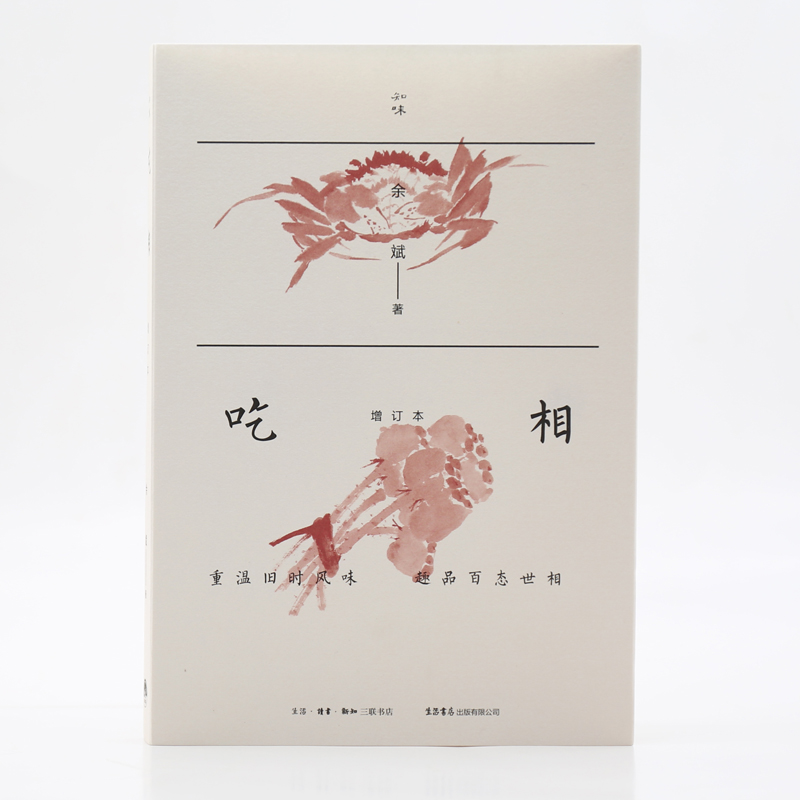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80
折扣购买: 吃相(增补本)
ISBN: 97878076839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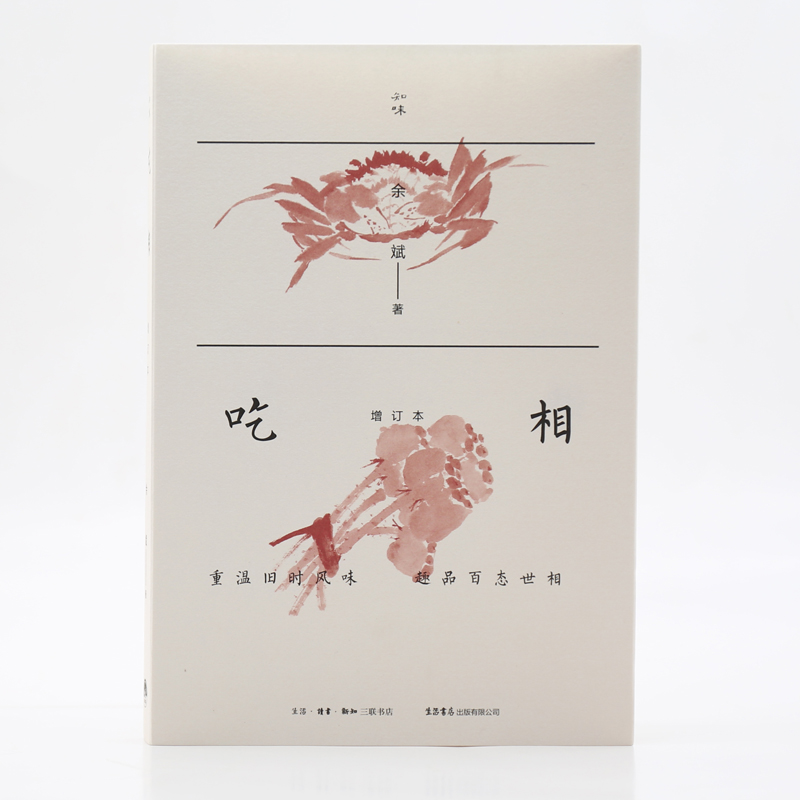
余斌 六〇后,南京人,现任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 作品有《张爱玲传》《事迹与心迹》《周作人》《提前怀旧》《旧时勾当》《南京味道》《译林世界名著讲义》与《一百年,许多人,许多事》(合著)等。
蟹 螃蟹,南方人北方人都吃。当然,是南方人先吃起来 的。所谓“第一个吃螃蟹的人”虽无从考证,却必是南方人 无疑。率先对无肠公子下口的人得有胆子,因其奇形怪状的 模样,再加被俘时的张牙舞爪,委实是拒人千里的。直到宋 代时,关中人仍有将螃蟹视为怪物者。沈括《梦溪笔谈》即 记有一桩趣事,说乡人不识螃蟹,有人收得一只干蟹,逢左 近有人得疟疾,便将此物借去,悬于门上,借以驱鬼——散 布疟疾者称疟鬼,疟鬼见门上怪物狰狞可怖,便过其门而不 入了。沈括甚至夸张地说,螃蟹在关中,“不但人不识,鬼 亦不识也”。 南方人对螃蟹自然见怪不怪,然“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要“前无古人”地将其视为可食之物,进而当作无上美味 ,却仍要有足够的勇气和想象力。此人是不是一位美食家, 不去管他,照古书上的说法,南方民间食蟹之风的大盛,与 口腹之乐的冲动没有一毛钱关系,其因由倒是螃蟹的泛滥成 灾:南方多种稻,螃蟹正是毁稻伤田的好手,元代史料里有 记载,这些家伙一度弄得稻不聊生,以致被形容为“蟹厄” :“吴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满,稻谷荡尽。吴谚有蟹(虾) 荒蟹乱之说,正谓此也。”故彼时的吃蟹之风大盛,其实是 农人的愤而食,是一种泄愤之举,大有食肉寝皮的恨意。 然而以螃蟹味道的鲜美,以南方人口味上的偏嗜,食 之后,转恨为爱几乎是必然的。事实上螃蟹早已被视为美味 ,吃蟹的“事迹”,亦可称“史不绝书”,最远的记到西周 ,往后隋炀帝的酷嗜此味不用说,东晋名士毕卓“右手持酒 杯,左手持蟹螯,拍浮酒船中,便足了一生”的豪语更是将 吃蟹定格为一桩韵事了。而到宋代,在位于北方的汴梁,食 蟹已成时尚。只是凡此种种,均限于宫廷或上层社会,平民 百姓不与也。没准儿元代江南农人的愤而食蟹倒是吃蟹之风 走向民间的转折点。(虽然食蟹既有悠久历史,江南又螃蟹 遍地,要到那时才走入寻常百姓家,似乎有点说不过去。) ………… 越是鲜美之物,越是要食其本味,这大概是江南人在 吃上面的一个原则。落实到螃蟹上,便是蒸,什么也不加就 上锅,端的是“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 其实大闸蟹其他季节也不是没有,但江南人吃螃蟹是 以膏蟹为目标的,这就须等到深秋才有了。所谓“膏蟹”就 是卵巢饱满的母蟹,卵巢俗称蟹黄,江南人对蟹黄的情有独 钟,从“蟹黄包”“蟹黄豆腐”之类以偏概全的命名即已可 见一斑了。于肉蟹以食肉为主,于膏蟹自然是以食黄儿为尚 ,故母蟹比公蟹更受人青睐。 掀开母蟹的壳,但见中央的部分有红黄二色,酱黄者 犹是粥样,橘红者色干硬,似鸭蛋黄,明艳照人。这都是“ 黄儿”,向来都是以干硬者为高的,我却好那粥样的,掰开 壳来且不动手,凑上去猛吸一口,妙不可言。蟹黄其实是螃 蟹的卵巢和腺体,既然称为“蟹黄”,蟹黄饱满的蟹不知为 何不称“黄蟹”而称“膏蟹”。这很容易引起歧义,因我们 通常都是将公蟹肚腹中对应于母蟹蟹黄的部分称为“膏”的 。字典里说“膏”:指脂肪或很稠的糊状的东西。——我觉 得公蟹腹中精华很符合这定义。蒸熟后它呈半透明状,似胶 重温旧时风味,趣品百态世相。 “吃相”一语,本义当然是指吃喝时的举止神态。但也时常挪作他用,说某人“吃相难看”,未必就是说他饭桌上欠斯文,有时是指其为人行事不够淡定,急吼吼缺少风度。再往大里引申,吃相之“相”也可通于世相之“相”,一个人有一个人的吃相,作为整体,人类有人类的吃相,一个时代则又有一个时代的吃相,在吃上面,也是“此中有人,呼之欲出”的。从吃相能看出的东西委实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