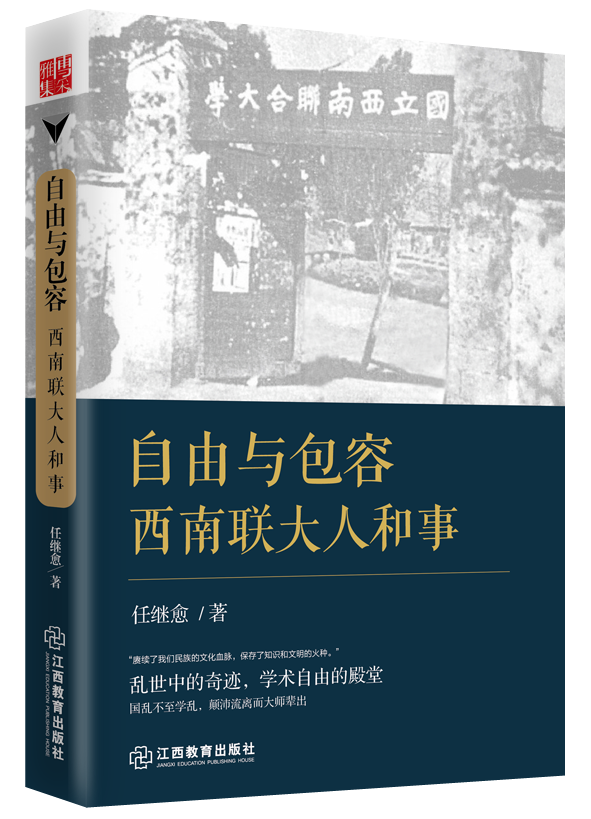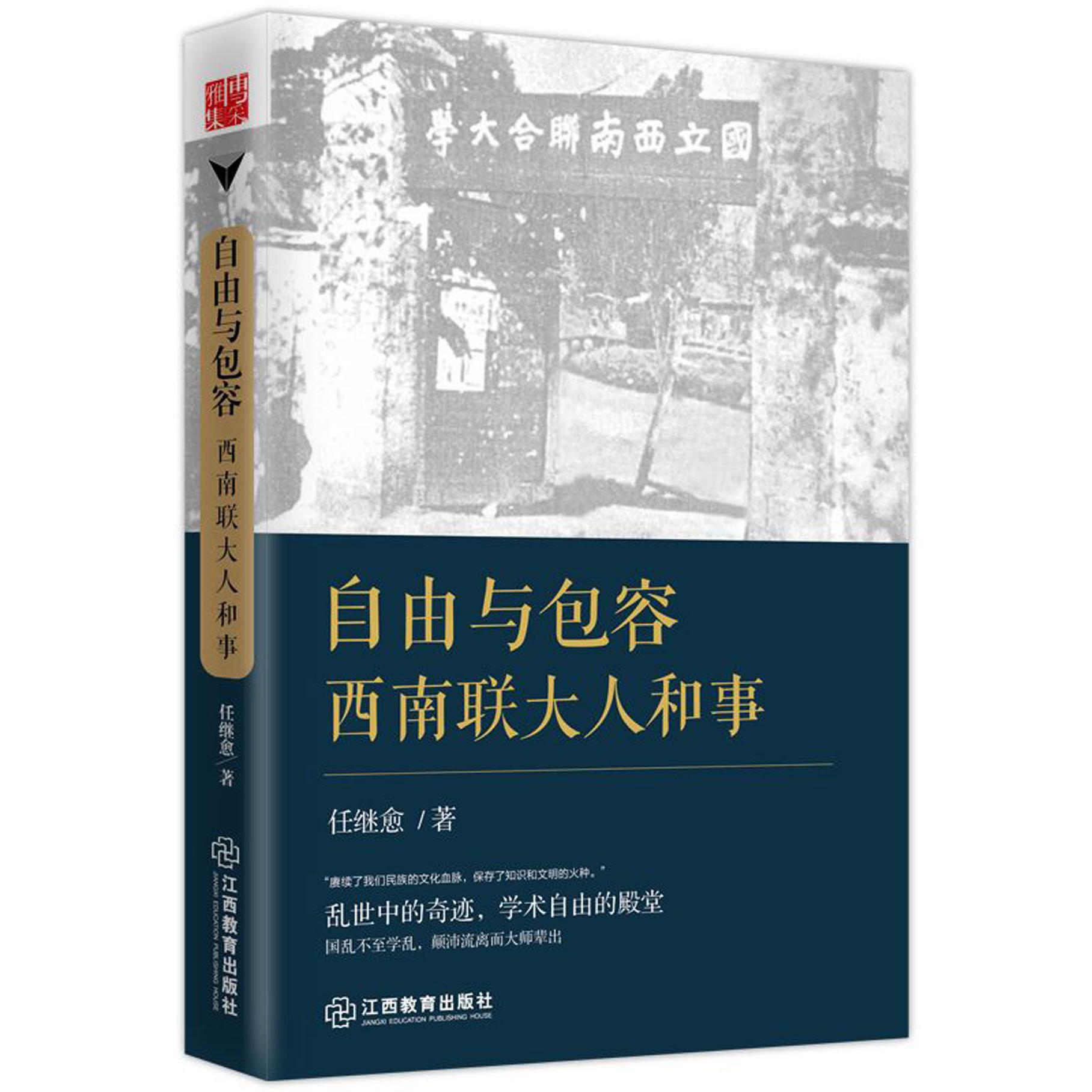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西教育
原售价: 36.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自由与包容(西南联大人和事)
ISBN: 97875392959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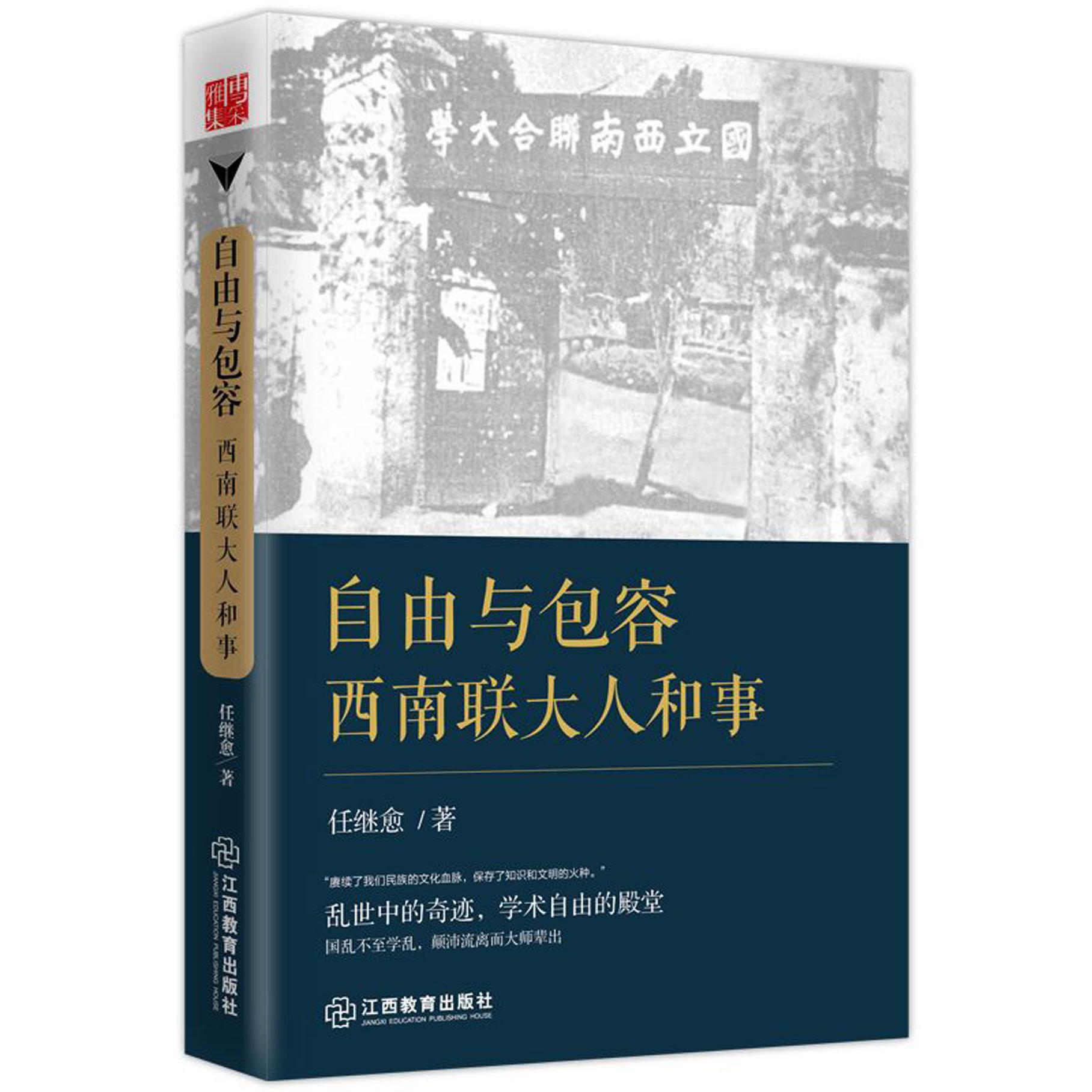
任继愈(1916—2009) **哲学家、**学家、历史学家,曾长期担任**图书馆馆长、名誉馆长。1939年考取西南联大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批研究生,师从汤用彤和贺麟教授。1942—19**年在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宋明理学、中国哲学问题、朱子哲学、华严宗研究、隋唐佛教等课程,并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史课程。19**年,负责筹建我国**个**研究机构——***世界**研究所,并任所长。著有《中国哲学史论》《老子全译》等,主编有《中国哲学史简编》《中国哲学史》《中国佛教史》等;此外,还主持《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中华大典》等的编辑出版工作。
精彩阅读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散记 *寇侵占华北,“七七”抗战开始。原在北平的北大、清华和天津的南开大学,奉命迁往湖南长沙,成立“临时大学”,临时大学在长沙驻有半年,又奉命迁往云南昆明。临时大学改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一直到1946年夏联大宣布结束,北方三所大学分别回到原来的校址办学,虽只有短短**年的时间,它在中国教育**却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的一段历史。 西南联大与我国抗*战争相始终。这所大学在颠沛流离中创建,在*寇飞机轰炸的间隙中上课,以极其简陋的仪器设备从事研究工作,即使在这样的条件下,不但办下来了,而且办得有声有色。这个大学在短短**年中为中国革命锻炼了大批革命骨干,为新中国的建设造就了大量**人才。西南联大的成就,在**外各学科前沿开拓了新领域,在**上也处在世界前沿地位。联大师生们的成绩是在半饥半饱的状态下完成的。 **流的大学,教学与科研并重,两者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西南联大不仅做到了,而且这两方面都处于各个学术领域的前沿。当时选送出国的留学生,到了国外也是尖子,这说明西南联大早已与国外**大学接轨。 1943年12月,林语堂从美国回来应邀在西南联大讲演,题目是《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他对联大艰苦的师生生活为之感动,说“不得了”。同时对联大师生战胜困难取得的成绩连称“了不得”。 西南联大理工科的成就,早已引起广泛的注意,很多人耳熟能详。像我国两弹一星的研制开发群体,联大人占了相当高的比例。诺贝尔奖获得者李政道、杨振宁,当年青年数学明星陈省身、许宝騄、华罗庚,物理学领域的周培源、吴大猷、赵忠尧,化学领域的曾昭抡、杨石先,植物学领域的汤佩松、吴征镒、戴芳澜,农学领域的俞大绂、娄成后,等等,已为人所共知,不必一一举例。 这里只凭回忆,说说西南联大文科的一些片段往事。 人文胜况 人文科学、社会科学方面,西南联大教师们的成就当年在全国也是**的。这一点似乎人们注意得不多,现在补充说一说。比如闻一多研究《诗经》《楚辞》,文献考证功力深厚,他后来利用西南地区民族、民俗的活化石,为他的学术造诣开了新生面。 语言学大师罗常培,利用西南地区的特殊条件(云南省就有22个少数民族)开辟了少数民族语言新领域,为我国培养了新一代的民族语言研究人才,如马学良、傅懋绩等人都成为**知名的专家。新中国成立民族语言研究所,这些青年学者成为骨干,为少数民族创制新文字,这批专家成了主力*,我国少数民族学的基本队伍是在联大时期培养的。 “西洋哲学编译会”,主持西洋哲学名著翻译工作,造就了不少哲学翻译人才。新中国成立后,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西洋哲学名著系列丛书,主要是西南联大时期的一批青年学者完成的。他还系统介绍了黑格尔哲学,新中国的黑格尔研究,贺麟有开山功劳。 金岳霖的《知识论》是他在联大的讲稿,他的哲学著作《论道》是他跑警报时在山坡上构思完成的代表作。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出版半个多世纪以来,**外还没有一部著作可以取代它的**地位。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语体文本)是这一时期完成的。洪谦是向**学术界介绍维也纳学派的**人。 钱穆的《国史大纲》出版的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抗战的百万将士”,这部中国通史成为各大学**的教材。历史系雷海宗讲授中国通史,他上课只带几支粉笔、不带讲义书本,能将历史事件、年代讲授得准确无误。结合他丰富的世界史知识,把中国古代史放在世界历史的大范围内来观察,使学生增加了知识、开拓了眼界。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选修课,上课时带了一包袱书,从不翻看,娓娓讲来,令听者忘倦。西南联大不采用当时***规定的作为全国通用的政治课《*义》教材,以《伦理学》取代***的“*义”课的大学,全国只有西南联大一家。 百家争鸣 百家争鸣成为西南联大的学风。北大中文教授罗庸讲“唐诗”课,第二年清华中文系教授闻一多也开“唐诗”课。闻一多讲选修课《楚辞》,第二年罗庸也开了《楚辞》课。两人讲授的风格、内容各异,同学*益很多。沈有鼎为哲学系开《周易》课,听讲只有三五个学生,闻一多也杂坐在学生中听讲。郑昕开“康德哲学”课,数学系教授程毓准也来听课。陈寅恪讲“佛典翻译文学”,中文系、历史系、哲学系的助教、讲师都来听课,本科生反倒不多,陈遂有“教授的教授”之称号。院址在昆明东南部、联大校本部,文、理、法各科都在昆明市的西北部,联大工学院的学生有的走好几里路听文科的课。学生中跨系听课现象蔚成风气。一年级国文课,全校文理及工科共同必修,共十多个班,讲课的教师中有李广田、沈从文、余冠英等十来位教师,讲课各有特色,这种气氛也只有在西南联大才能见到。 百家争鸣,学术**——不但在同辈中盛行,师生之间也不鲜见这种宽容求是的事例。历史系王玉哲在北大历史系二年级时,对傅斯年研究《齐物论》的观点提出不同意见,在刊物上反驳。傅斯年在西南联大担任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长,招研究生,王玉哲想报考研究生,又怕傅老师对他有芥蒂,后来壮着胆子报考了,并被录取,师生相处得好。 杨振声指导大学本科四年级学生写论文,这位学生写的是研究曹禺的题目,迟迟写不出,杨约学生谈话。原来学生的观点与杨先生不尽一致,怕导师通不过。杨振声告诉他,只要认真研究,掌握原始材料,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尽可写成论文,师生**一个样,学术怎能发展?学术面前,只重证据,不论资格。听说这位青年后来成了中山大学的名教授,并经常以此精神教导下一代。 北大文科研究所一年级青年研究生杨志玖研究元史,看到欧洲一位**汉学家著文说“马可?波罗没有到过中国”。杨志玖用过硬的原始材料驳斥了这位汉学家。迄今为止,关于马可?波罗在中国的活动,杨志玖的观点在**上已成为定论。 课余学术演讲会 抗战后半阶段,*本发动太平洋战争,美国派来志愿空*,在昆明建立空*的“飞虎队”驻昆明,经过几次空战,打下来*本飞机多架,使*寇飞机不敢再来空袭,上课时间比较正常了。中缅公路修通后,昆明成了对外交通的通道,联大有时邀请归国过路的名人讲演,我记得的有顾维钧、焦菊隐、徐悲鸿,美国回来的林语堂,牛津大学的Daods,出国作战、在缅甸密**城全歼*本侵略*的杜聿明,等等。西南联大学术空气很浓,学术演讲几乎天天都有,有时**还不止一场,有文艺的、学术的、时事的,还有如诗歌朗诵、音乐欣赏等,活动多在每天晚饭后,星期*则在白天,有不同爱好的同学可以有选择地自由参加。以上这些都是临时性的,联大师生经常举办的不同社团组织的歌咏、诗朗诵、话剧等也很活跃。师生们虽然物质生活艰苦,但是精神生活却十分活跃丰富。 徐悲鸿谈画 徐悲鸿先生由欧洲经苏联回国,经过昆明,联大学生邀请他演讲。他结识了不少苏联画家,还在苏联参观苏联红*卫国战争画展。他说苏联卫国战争调动了全国各界的爱国热情,艺术家也充分发挥了它的积极作用。苏联画展组织者动员了全国有名的不同流派拿出作品参展,其中大量作品是描写红*抗击德国纳粹的战争。也有些老画家,没有画过红*卫国战争的作品。为了使画展丰富多彩,表明全苏联不同流派一致的团结卫国精神,尽量动员艺术界*多成员参加。当画展组织邀请这些老画家拿出作品时,一位老画家生气地说:“没有,都给钉上木板了。”(因为当年苏联革命成功后,把不是直接表现革命的绘画作品封闭起来,教堂的**故事画用木条钉上谢*参观,这类**的行为曾引起一些画家的不满)经画展组织者一再劝说,这位老画家拿出一幅乡村风景画。徐悲鸿在画展会上看了这一幅画,题名“绿舞”,一棵大树屹立在田野上,树叶迎风飞舞,生动极了。恰好有几个青年参观者也在欣赏这幅画,问解说员:“这大树和房子很好,画上怎么不见红*啊?”解说员机敏地回答:“你不是看见树后这所房子了吗?红*隐蔽在房子后面啊!” 徐悲鸿先生在法国留学期间创作了一幅古代寓言画,画的是明清之际流行于社会上的一首歌谣,“他人骑马我骑驴,中怀怏怏恨不如,回头又见推车汉,心下一时稍舒齐”。大意是说,有人看到别人骑马、自己骑驴,心中不平衡,回头又看见推车汉子大汗淋漓地推车上坡,心中的不平衡又缓解了好多。这首歌谣在于说明每一个人的生活水平,总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教人安分守己,并没有什么“革命性”。苏联的画家同行们看到这幅推车图,他们虽不懂汉文,却很欣赏画中的推车人两臂肌肉丰满凸起,很有力量,称赞把劳动人民的精神画出来了,要求赠给**美术馆收藏,徐悲鸿先生答应了。新中国成立后,有一年我去苏联,参观苏联美术馆时曾向有关方面打听徐悲鸿的这幅推车图是否还在,他们说,展品有千百件经常轮换,一时很难查找了。很遗憾没有亲眼看一看徐悲鸿先生的这幅“推车图”。 刘文典先生 刘文典,字叔雅,安徽人。清华大学教授,早年加入同盟会,在*本东京与孙中山相识,又是章太炎的学生,他的治学路数与章太炎不同,没有走文学训诂的道路。我*先读他的书是《淮南鸿烈集解》和《庄子补正》。陈寅恪为此书作序,说不但可以补前人注解的缺失,还可以恢复《庄子》旧貌。我读过刘先生的书,觉得陈先生的称赞未免过头了。 抗*战争时期,后方物价飞涨、民不聊生,工薪收入者*子过得十分拮据。闻一多靠治印(刻图章),联大教授在中学教书,借以贴补家用的大有人在。刘先生的文名早为滇人熟知,在昆明期间,滇省富绅多以请他撰写碑铭、墓志为荣。润笔丰厚,远过教中学,对经济困难的刘先生不失为一种经济生活的重要补充。 我旁听过刘先生讲《庄子》《文选》。刘先生上课时,香烟一支接一支,手指熏成黄褐色,衔着香烟说话很难听得清楚。先生有一爱子五六岁,上课时跟他同来同去。有时正讲到精彩处,小孩子跑到教室外面捉蝴蝶,刘先生一眼瞥见,不免喊一声“快回来”。如果把刘先生的课一字不漏地记下来,凭空插入这三个字,就无法理解,因为出现得太突兀。 刘先生不修边幅,头发散乱,一件长衫总是皱皱巴巴。他为人直率、纯真,具有庄子的洒脱。有一次在雨中,刘先生一个人打着伞慢慢走着,长衫后襟湿透,鞋子沾满泥水。同学黄钺指点说,刘先生像庄子“曳尾于涂中”。 昆明气候温和,号称“四季无寒暑,一雨变成秋”。虽说四季如春,冬季还是比较冷。一般健康人有一件毛衣或一件皮夹克,即可应付一年,刘文典、陈寅恪两位冬天要穿皮长袍。陈先生和我们研究生同住一所小楼,冬天怕风,窗户缝隙用纸糊得严严的,不准透风。**,刘先生访问陈,两人互争谁的身体*差,相持不下。刘先生说,我穿了两件皮袍子,可见我的身体*差,自得之色溢于眉宇间。陈寅恪不再争,服输了。 刘先生欣赏称赞南北朝时已提出的关于“诗”的定义,他在黑板上写了“诗缘情而绮靡”,认为超过后人的任何定义。他还讲,文学作品贵在以正写反、以实衬虚,用华丽的词藻写荒凉,以欢快的词藻写悲哀。杜甫《秋兴》八首中就用了这种方法,十分成功。讲晚唐温李诗时,咏牡丹,不用那些常用的香艳纷华字样,把牡丹的神态写活了,非一等手笔办不到。 他还讲,中国古典文学经常利用汉字象形的特点,引发读者的想象,从而增强了读者的想象力。《海赋》中用“髣髴”二字(而不用“仿佛”),好像海怪蓬头乱发在水中出没,可以增加大海的神秘气势。 刘先生平时对学生、对同事,礼貌待人,彬彬有礼。他看到他不喜欢的人,也真是当面让人家下不了台。抗*战争初期,***力量小,*本*用飞机经常到昆明轰炸、骚扰。联大北墙外是大片荒山、坟地,听到警报声,师生到校外后山隐蔽。有一次刘先生躲警报,在后山遇到他平时很不喜欢的一位先生,他当面指责他:“我躲飞机是为了保存中国文化,你怎么也来躲飞机?”那一位先生很有涵养,对刘先生也很尊重,没有和他争辩,换了一个地方,离得他远远的。魏晋时,阮籍用青白眼对待不同的客人,刘先生在这一点上有点近似。 刘文典先生经常讲文学造诣与人格修养不可分,为人与为文是一回事。他驳斥周作人的主张。周作人说,读者读作家的作品,并不必了解作者是什么人。比如吃包子,只要包子做得好吃,不管制作包子的厨师是否**过他嫂子。(周作人的这段话,我不详其出处,刘文典确是对同学这样讲的。)刘先生接着说,“文学作品是**精神产品,不同于制作包子。一个**过他嫂子的人能做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来吗?” 刘先生魏晋风度太多了、太任性了,联大结束迁回北京的那一年(1946年),他应云南绅士的邀请,去滇西一个县里为人撰写墓志,对方盛情挽留,请他游山玩水以助文思,一住四个星期。学校对他不按规定上课、长期请假缺课,提出了批评。三校迁回北平时,他没有随同大家北返,而留在云南,应聘为云南大学教授。云南大学能请到刘先生,喜出望外,求之不得。从此,我再未见到刘先生。 刘先生精考订,哲学、文学修养也很高。他曾赴云南西部滇缅战线慰劳前线将士。刘先生回来,在课堂上说起在宋希濂*部,即席赋诗祝捷,他吟诵了其中的两首。他习惯于叼着香烟讲话,有些字句听不清,有句云: 春风*塞吹芳*, 落*荒城照大旗。 海外忽传收澳北, 天兵已报过泸西。 刘先生讲,杜甫有“落*照大旗”之句,这里古典今用,写出了*营气势。他得意地念了两遍,所以记住了。 我钦敬的陈岱孙先生 抗*战争前,北平市有五所大学(其他高等学校,如工学院、医学院、女子文理学院、法商学院等都属于专科学院,不称大学),即北大、清华、燕京、辅仁、北京师大。其中,北大、清华两校地位相当,性质相近,都是国立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清华比北大多了一个工学院,历史较短;北大历史较长,文科师生人数较多,两校师资多为****学者,这两校的关系较亲密。我在北大哲学系读书,清华大学金岳霖、闻一多、张申府先生都在北大兼课。哲学系与经济系少交往,陈岱孙先生没有在北大兼过课。 抗战开始,北平沦陷,在长沙成立临时大学,半年后,临时大学迁往云南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临时大学的**年,昆明的校舍未建成,文法学院在云南蒙自县,借用蒙自海关旧址上课。租用歇业的一家法国洋行作为单身教师及学生的宿舍。我们有较多的机会看到久已闻名、未得谋面的老师们的生活片段。 在学校网球场上,有四位教授的身影经常出现。这四位是金岳霖、陈岱孙、赵乃博、浦薛凤。陈先生风度翩翩,赵乃博先生穿中式短裤褂。他们的球艺很娴熟,特别是陈先生打网球,频频上网拦击制胜,引人注目。在蒙自半年,昆明新校舍建成,文法学院同在新校区域上课。 我未读经济系,听到经济系老同学传来的一些陈先生的轶闻,引起人们的兴趣。 一、讲课条理清晰,时间掌握准确,为全校**。上课前一两分钟陈先生已站在黑板前(西南联大新校舍没有讲台),上课铃响,他开始讲课。这一点,别的老师认真去做不难办到,难得的是陈先生讲完*后一句话,恰恰是一定段落,下课铃也响起来。同学们对他的讲课艺术既惊叹又欣赏,这一点是任何老师无法比得上的。陈先生讲课并不念讲稿,听课者只要手头勤快,记下笔记,这一节课就是完整的一章一节教科书的一部分。这种出口成章的才能,西南联大教授中只有两位,一位是陈先生,另一位是冯友兰先生。 陈先生讲课认真,以身作则,给同学做出榜样,同学们听课从未敢迟到。个别同学去迟了,不好意思进教室,就站在教室窗外听讲。好在西南联大的新建校舍有门窗而无玻璃。昆明气候温和,无狂风暴雨,有似热带雨林气候,阵雨过后,雨过天晴也无须玻璃挡风遮雨。站在靠近讲台的一端听讲,比坐在后排还听得清楚,只是没有扶手椅,记笔记不方便。 二、陈先生还兼任经济系主任,经济系是大系,每个年级有一百多人。学年开始,选课同学拥挤在他办公桌前,他能不假思索地处理每位同学所选的课,有重修的、有复学的、有需补修课的。陈先生都毫无差错地处理得妥妥**,几乎不到一分钟就在一张选课单上签了名,从未发现差错。(选课单系主任当面看过,签字后,才能交教务处正式登记。)在规定时限内,可以加选,也可以退选某门课程。陈先生执行起来十分认真。有一位同学,过了学校规定选课时限,来要求加选课程,抱着侥幸心理,企图碰碰运气,写了一个申请,说了一些延误的理由。陈先生看过他的申请,一言未发,把信推在旁边,接过下面另一位同学的选课单。这位同学看到碰运气没有指望,也一言未发,悄然退出。陈先生办事一丝不苟的精神在同学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讲这件故事是一位西南联大的老同学任继亮,今年已八十多岁,记忆犹新。 三、陈先生在经济系开过《财政学》课程,有一次学年考试,考题是“假如我是***长”。这个题目等于对《财政学》的全面测试,不光考记诵,还要考联系实际的措施。可以想见陈先生教学的学风,很注意理论联系实际(闻自西南联大经济系黄)。 新中国成立后,1952年,全国进行院系调整,原清华的文法学院大部分师生并入北大陈先生调到北大经济系。全国上下一面倒地学习苏联,全盘接*苏联的大学教材。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学一无是处,对西方学者的经济学避之唯恐不及,对西方的学说故意置之不理。中国自我封闭了近二十年,形成了人才断层。“***”清除后,拨乱反正,西方资本主义各种流派大量涌来,学术界有一批趋时者刮起不讲马克思主义、唯西是从的风。 陈先生不愧为一代宗师。他通晓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学也有长期深入的理解。在**思潮时期,陈先生没有公开发表评论苏联经济学的机会,但是他对马克思主义有深刻的了解,他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也有过系统研究。以他毕生的精力,辅以深邃的学识,加上他多年的学术积累,虽然年事已高,但在十年内仍然发表了著作《从古典学派到马克思》,主编了《政治经济学史》,还参加了许多政治活动、学术活动。《庄子》说:“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他的学术活动、学术著作,*非十年之内从头起步可以完成的,这是他多年蕴藏的能量爆发出来的硕果。 在**思潮时期,学术问题不能讲透,政治棍子动辄到处飞舞。一些学者仗义执言,如马寅初、孙冶方,遭到意外横祸;有些“识时务者”,随风篷转,不顾事实,昧着科学良心;有的甚至落井下石,以牟个人的富贵。陈先生屹立不摇,保持二十年的沉默。陈先生写文章、发表著作和他不写文章、不发表著作,都彰显出爱国知识分子的人格风范。 陈先生一丝不苟的认真精神,表现在治学方面,也表现在为人处世方面。他的门生弟子遍及海内外,有声名显赫的,有学术**的、有在职的、有退休的,也有出于各种机遇默默无闻的。凡是来请教、送文章请提意见的,都*到春风般平等的接待,虚而往,实而归。学识渊博如陈先生,比一般专家*懂得科学的严肃性和治学的艰难。他常对来访者说:“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我不懂。”其实,即使是他自称“不懂”的某些领域,也比自以为“懂了”的人懂得还多,真正实事求是的学者都能从中*益。 改革开放以来,商品经济活跃,市场上出现一些假冒伪劣产品,文化教育界也出现了某些伪劣的专家教授。再加上“**”之后,文化教育这个重灾区元气大伤,大学里能正确无误地传授知识的教师已经算上乘。学识渊博、贯通古今中外的大师已十分难得;品重士林,行不言之教,影响深远,为同行钦仰,陈先生是我所认识的少数前辈学者之一。 从陈先生一生言行中,可以看到多灾多难的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爱国主义精神和中华民族雍容宽厚、博大深沉的民族性格。 钱穆先生 钱穆先生,字宾四,江苏无锡人。我大学一年级时听他讲中国通史,这是文科、法科的共同必修课,听讲者甚众,在二院大礼堂上课,座无虚席,初听时不大适应他的无锡口音,听了几次习惯了,很感兴趣。 钱先生讲课生气活泼,感情充沛,声音洪亮,听者忘倦。 他善于利用地下考古材料,结合文献,开头讲上古殷商史,利用王国维甲骨文的研究成果,内容显得十分充实而有说服力。 钱先生还开过“近三百年学术史”课,是历史系高年级选修课。清代学术界汉学、文字考据学占主流,钱先生讲清代思想,虽涉及汉学,并未纠缠于当时的考订、训诂。他讲顾炎武,很推重他的《天下郡国利病书》;讲颜习斋,肯定颜氏的重实行、反空谈精神,却又指出颜氏太重狭隘实践而轻视理论,也有弊病,与胡适一味推重颜习斋的观点不同。 钱先生在北大历史系教授中,他是**没有出国留学的教授,在当时崇洋的情况下,也遇到一些小的不愉快。有一年,系主任陈*颐休假,有人提议系主任是否由钱先生接替。胡适(当时任文学院长)说:“钱先生刚来北大时是副教授,现在已是教授了。”没有往下说,这个建议就搁浅了。这是历史系高年级同学传闻之说,可能有据。 钱先生在西南联大时,讲课喜欢讲中西文化的异同,对中国文化情有独钟。当时,姚从吾先生对他说:“讲中西文化的异同,*好听听莱茵河畔教堂的钟声,这里有西方文化的精神。”钱先生没有听过莱茵河畔教堂的钟声,所以似乎没有资格奢谈东西方文化比较。姚从吾的话是我亲耳听到的。 钱先生治学勤奋,搜集资料十分认真。30年代没有影印设备,只能用手抄录。钱先生家里用了三个毛笔字写得好的书手,给他抄写。钱先生有天赋,又勤奋好学,令人钦佩。 钱先生通史学年出题目也新颖。有一道题只有六个字,拟旨“批红”“判事”“封驳”,意在考查学生对唐的政治制度及其机制的掌握情况。考试下来,同学张锡纶(现已离休)对我说:“试题出得真棒。” 七七事变后,钱先生与同学们一齐到了湖南长沙,又转到南岳衡山脚下。前方抗战,同学们难以安下心来读书,都要到前方参加**线工作。记得有一次欢送离校到前方的同学会上,有一位同学讲:“我渺渺茫茫地来到学校,我又渺渺茫茫地离开了学校。”钱穆先生针对这位要离开的同学的发言说:“我们这个时代非同寻常,每一位关心**兴亡的人士,都要有清楚明确的目的,万万不可渺渺茫茫。前面有艰难的前程等待大家去开拓……” 学校迁到云南,文法学院设在云南蒙自县,租用了一个快倒闭的法商洋行(哥鲁士洋行),又租了蒙自海关的一部分房子,安顿下来。钱穆先生继续整理他的“中国通史讲义”,后来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书名为《国史大纲》,扉页上写着“谨以此书献给前线百万将士”,钱先生爱国主义的精神跃然纸上。 钱先生在蒙自与哲学系的沈有鼎同住一室,沈有鼎为人古怪。抗战时期,***靠大量发行纸币维持行政及一切开支。每月发工资,都是新印的纸币。沈有鼎每月把工资码放整齐,放在一个旧皮箱内,上课、散步从不离手,每天晚上数一遍,以此自娱。有**检点钞票,发现少了一摞,他怀疑钱先生拿了他的钱,就问钱先生。钱先生平时待人和气、彬彬有礼,对沈有鼎的无礼质问,不仅大怒,还要打沈有鼎的耳光。这件趣事在蒙自流传颇广。贺麟先生向我转告这件事时,我觉得沈有鼎真是个怪人。 联大文学院迁回昆明,因一时没有教授宿舍,一部分教师住在昆明以南100多里的宜良县,汤用彤先生、钱穆先生都租住宜良岩泉寺,下寺是和尚主持,上寺为道士主持。他们先住在下寺,和尚吃素,承包房客伙食,房客可以吃荤。有时钱先生买一只*煨汤,办伙食的和尚不吃肉,却喜欢偷喝*汤。后来从下寺搬到上寺,跟道士搭伙。道士不吃素,好吸鸦片,有一定的文化素养,相处融洽,直到在昆明市找到住房,他们才离开宜良岩泉寺。 1946年,西南联大结束,三校各自回到原来校址。我将回北大。从重庆经成都转西安,回家探望老父。汤先生嘱托,过成都时看望他的两位老朋友,一位是吴宓先生,一位是钱穆先生。吴先生在齐鲁大学,钱先生在华西大学。钱先生住的地方比吴先生的好得多。钱先生知道我未到过成都,告诉我可以游游青城山、灌口,峨眉山、乐山比较远,且不是一个方向,如急于回西安就来不及了。还指点我每处花多少时间,途中费用也大致说了说。 我虽然多年听钱先生的课,过去有过接触,也多属于问问学问,这次见面只谈了生活方面的琐事,娓娓而谈,亲切如家人,对钱先生的为人*增加了一层理解,如坐春风中。 一代大师,因小见大 我在北大读书时,没有听过罗莘田先生讲课。抗战时期,我报考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批研究生,那是1939年。北大研究生考试前先送交论文,论文通过后,才能报名。笔试后,还要参加口试,考试委员中有罗先生,这是**次与罗先生见面。毕业时,答辩委员中也有罗先生,罗先生参与了我读研究生的全过程。我算是一个及门弟子,只是未曾入室。 一、密切的师生关系 当时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有陈寅恪、向达、姚从吾、郑天挺、罗常培、罗膺、杨振声、汤用彤、贺麟。 师生们共同租用了一幢三层楼的宿舍,在昆明靛花巷3号。师生们同灶吃饭,分在两个餐厅,因为房间小,一间屋摆不开两张饭桌。 师生天天见面,朝夕相处。郑天挺担任文科研究所的副所长(正所长是傅斯年先生,后来兼任“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常驻重庆)。罗莘田先生戏称,我们过着古代书院的生活,郑先生是书院的“山长”。当时同学周法高是罗先生的研究生,周戏编了一副对联: 郑所长,副所长,傅所长,正所长,正副所长; 甄宝玉,假宝玉,贾宝玉,真宝玉,真假宝玉。 对仗不大工稳,在同学中流传,后来传到罗先生耳中,把周法高叫来,要他把心思用在正道上,不要逞歪才。 二、课余的学术报告 西南联大的学术空气很浓,课外、晚间的学术讲演,百家争鸣。文科研究所罗先生组织的讲演,我记得有:汤用彤先生讲“言意之辨”;向达先生讲“唐代俗讲考”;冯友兰先生讲“禅宗思想方法”;贺麟先生讲“知行合一新论”;化工系教授陈国符先生讲“道藏源流考”。这些讲演有的收入论文集,有的拓展成专著。陈寅恪先生每天九时入寝,不外出,从未参加过学术讲演。这些不同学科的讲演,罗先生都有兴趣。罗先生四十多岁,却不会世故,同大家在返回靛花巷的途中,有时也参加同学们的评论,有青年人的兴致。 三、生动活泼的课外生活 靛花巷导师中,好静的多。罗先生性格活泼开朗,组织“昆曲社”,以中文系青年教师为主,经常参加的骨干有浦江清、沈有鼎,生物系的崔芝兰教授,还有云南大学中文系的青年教师,罗先生也是常客。在罗先生影响下,我也去听过几次昆曲清唱,居然坐满一间小教室。我还和罗先生共同看过联大中文系师生演的话剧《风雪夜归人》,男女两位主角都出自中文系。罗先生发动中文系专*古音韵学的讲师用唐韵读唐诗,与近代读法很不一样,使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还和姚从吾先生、罗先生听过中央大学黎东方教授讲三国历史,回来的路上罗先生评论说:“这是另外的学派,可听而不可学。” 四、安贫乐学 写联大的历史,经常提到联大师生面临物价飞涨的局面,不得不在校外兼职,以贴补生活,这是实情。却也有一些教授靠那点固定的收入,不兼职,专心做学问。据我所知,文科研究所的导师,没有一个在校外兼职的。有时收到一笔稿费,罗先生总忘不了邀几位同学一同到附近北方人开的小馆子吃一顿北方饭,中文系以外,罗先生忘不了也邀我参加。 五、热心助人 学生毕业后,初次教书,心里不踏实,罗先生就告诉学生不要胆怯。说他自己刚毕业到外地(西安)教书,主要依靠钱玄同先生的讲义,再逐渐补充,教到第二遍时补充自己的材料,逐渐充实,教学内容有所提高,自己信心也增强了。学生们有什么困难,或者请他介绍工作,他总是热心帮助、从不推辞。有一次四川某大学请马学良去做教授,许以副教授,马不去。罗先生知道了,对马学良大加称赞,说研究少数民族语言,不能离开了云南这块宝地,坚持下去必有大的成就。罗先生对他的弟子中,到结婚年龄尚未成家的,他也关心,愿意做媒。他说我将要刻一方图章——“百梅馆主”,以纪念做媒的成绩。据我所知,经罗先生介绍的,虽未达到一百对,的确也组成了好几对新的家庭。 六、仗义执言 罗先生性格开朗,看不惯的事,认为是不合理的,他就直言不讳地批评。抗战时期,由于物价上涨,工资不变,文教人员难以维持生活。当时***规定,除固定的工资另外增加“米贴”,按人口多少给以补助。这一办法,缓和了一部分工资低、家庭负担重的职工的困难。中文系一位教授填表时,子女栏目内填了七八个子女的名字,备注中说明“前妻所生”。罗先生对这位教授很看不起,说,平*断*与前妻子女来往,发米贴时才想起前妻所生来。 七、罗先生的住室 抗战时期,西南联大师生都很艰苦,有一间宽大的住室,就很不错了。 罗先生住室正中墙上高处挂一镜框,照片上写着“恬厂四十自造像”。下边挂着两幅字,一幅是叶恭绰写的大字行书,豪放、有气势,而内容一般,抄自成语,事隔多年,没有印象。另一幅是沈尹默写的条幅,是沈氏自己的诗。沈的诗比他的字要好些,我记得有:“年来容我且徐徐,小病深思亦启予。竖起脊梁*倾欹,放开腹笥着空虚。”“腊梅枝头雪未消,东风吹雪绽山桃,北人莫道春常晚,为此**岂易遭。” 字画旁边有个面盆架,有时浸泡着衬衫、袜子。罗先生利用读书余暇,自己洗衣服。有时罗先生正洗衣服,学生来了,帮着拿到室外去晾晒,回来再继续谈学问。 八、读音要准确 有一次,有人谈到唐代医学家孙思邈,罗先生说,现在很多人都念错了,念孙思秒(miǎo),应当读孙思莫(mò)。还说起唱歌、唱戏,不能念倒(dǎo)了字。抗战时期流行广泛的《松花江上》,“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九一八,九一八”,这两个“九一八”都念成“揪尾巴”了。他又说,有修养的演员,即使天赋好,念倒了字,也会使他的艺术减色。 九、《临川音系》 罗先生的《临川音系》《厦门音系》是他早年成名之作。我对罗先生涉及的领域未入门,不敢赞一词。但从罗先生对中国方言的研究,给我以启发,方言是地区性的语言,一个地区的山川、水土、文物、风俗,自成体系,越是古代,地区的特点越明显。 由此我想到,文化、文学也和方言一样,也不能没有地区性。中国地域辽阔,风俗及传统文化,东部、西部有很大差异。同为明末清初人,浙东的黄宗羲、湖南的王夫之的思想很不同。地区文化对他们的影响不能忽略,离开地区性,不能把黄、王二人的思想讲清楚。 十、不服输的性格 罗先生所治的语言学,沿袭清代朴学传统,把这一学科归到中文系。实际上,近代语言学这一学科*需外国语文的基础。西方语言基础不深不厚,就难以超过乾嘉诸大家,有所前进。中国语言学界的开拓者,人们**三位大师(李方桂、赵元任、罗常培),李、赵二位都在青年时期在西方学习过,接*过西方近代科学训练。唯有罗先生,未出国门一步,也达到**水平,成为现代语言学奠基人之一,他要比别人付出*多辛劳,这是不言而喻的。罗先生没有在美国当学生,却在美国做了教授,而且成了一位**的教授。罗先生的勤奋好学,给他的学生们树立了榜样,这种精神启发了不少学生。 在靛花巷文科研究所,有三位先生,汤用彤、郑天挺、罗常培这三位导师熄灯*迟,都在十二时以后,导师如此,学生也不敢懈怠,也算导师们言传以外的身教吧。 十一、庆双寿 旧社会,夫妻二人同年生的,遇到过生*,两人合并举行一次庆寿家宴。亲朋好友也前来祝贺,热闹**。罗先生与郑天挺先生恰好同年同月同*生,只是时辰不同。罗先生曾对人戏称:“我的八字和郑先生的差两个字,所以命中注定做不了总务长。”(郑先生当时任西南联大历史系教授,兼作总务主任)中文系章廷谦教授,字矛尘,五四时期老北大的学生,鲁迅文章中称为“一撮毛哥哥”的。此人善交际,爱起哄,每年快到罗先生生*时,他到处喧嚷:“罗、郑两位过双寿,要请客,请大家别忘了参加。”罗、郑两位对这种起哄式的被迫请客很反感。有一次,罗先生在院子里发话说:“明年过生*,谁都可以请,就是不请章矛尘。”章廷谦倒不在乎,不请他也会到场的。 十二、建所逸闻 新中国成立后,胡乔木到东厂胡同几次找罗先生,提到**加强语言研究,要成立研究机构,希望罗先生主持工作,提出建所方案。*初未允,后来罗先生对他的学生说,新中国要建语言所,这是件大事。当前,李方桂、赵元任都不在**,我不能再推辞了。提出建所方案,对罗先生来说不难。他胸有成竹,很快拿出方案。当时不知是谁给罗先生出了一个主意说,现在要学习苏联经验,苏联正流行马尔语言学派,应把学习马尔学派放在**条。后来知道马尔学派主张语言有阶级性,是错的,在苏联已遭到批判,随即把**条删去了。因为这一条是作为标签贴上的,**条以下都是罗先生和同事们仔细推敲、论证后写定的,**条拿掉,丝毫不影响原来章程的完整性。 西南联大是中国教育**的珠穆朗玛峰,文有陈寅恪、闻一多、钱穆、冯友兰等,理有华罗庚、杨振宁、李政道等。“不仅是中国教育**的奇迹,也是世界教育**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