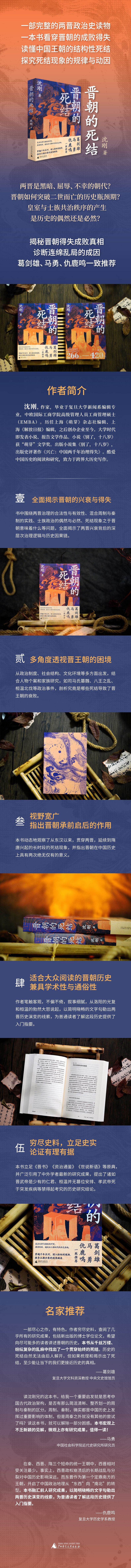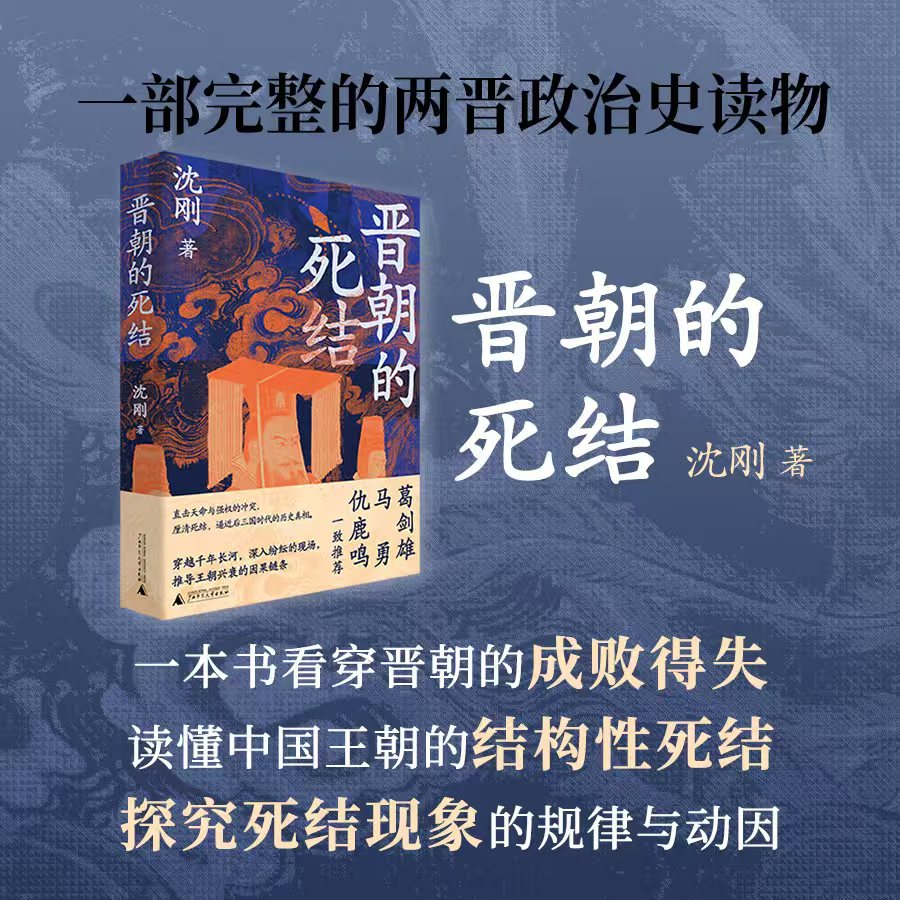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2.80
折扣购买: 晋朝的死结
ISBN: 97875598701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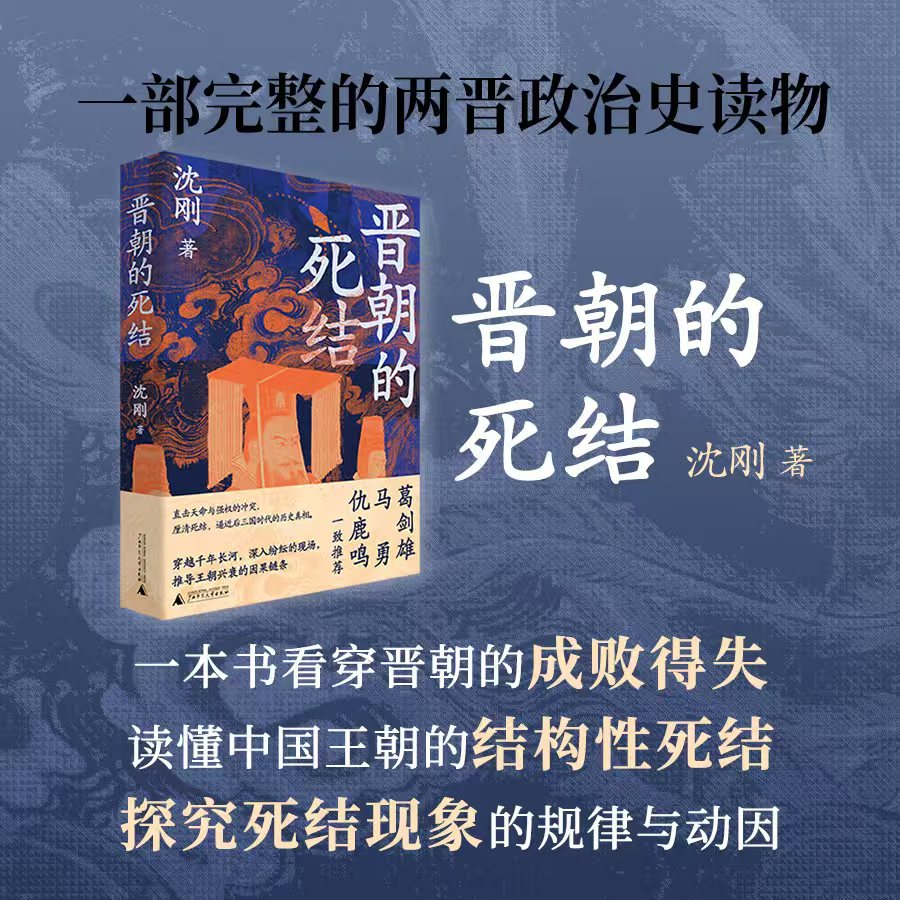
沈刚,作家,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编辑专业,中欧国际工商学院高级管理人员工商管理硕士(EMBA)。历任上海《萌芽》杂志社编辑、上海《解放日报》编辑,之后创办企业至今。大学时代即发表小说、报告文学作品。小说《别了,十八岁》获“萌芽”文学奖。出版小说集《别了,十八岁》,出版史评著作《兴亡:中国两千年治理得失》。酷爱中国历史的阅读和研究,致力于跨界大历史写作。
光武帝刘秀中兴之后,统治国家的儒学理论、中央集权君主专制下的皇权和汉政权的天命完美统一,共同构建了士民对于东汉政权合法性的高度认可。即使皇帝短命、早夭,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汉室仍然维持一个世纪以上。黄巾起义以后,天下出现了武力割据的局面,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血腥政治逻辑,与天下士人“心存汉室”的价值观念之间,形成了结构性的尖锐对立。曹操“挟天子而令诸侯”统一北方,既是暴力权谋现实政治逻辑发展的结果,又充分利用了汉室正统的价值思潮。曹魏代汉,没有解决政权“受之于天”的合法性命题。 党锢事件之后,朝野“清议”一方的士大夫固然受到极大冲击,但也进一步推动了士大夫阶层自主意识的觉醒。部分党人名士或隐居或转入地下,在县乡、郡国乃至全国,清议的舆论继续存在,各级在野名士层出不穷。抨击时政的言行遭到禁止,品评人物的德行却成为清议的主要内容。经过宦官势力残酷镇压,在野的名士群体反而更被戴上了儒家思想制高点的光环。普通士人想在郡国乃至全国扬名,必须得到相应的郡国级、天下级名士的评论认可。这相当于在国家朝廷的政治权威之外,另外产生了一种价值取才的评判体系。 特别是在中原核心区域的豫州颍川、汝南等地,以及大儒郑玄所在的青州北海,几大名士家族担当了核心的角色。其中,汝南许劭、许靖兄弟创办的每月初一发布的人物品论活动,以“月旦评”品牌而著称,几乎拥有认证天下级名士的权威。士人如果经“月旦评”品题肯定,立即身价百倍。《后汉书·许劭传》中记载,曹操未发迹前,多次备厚礼要求得到好评,许劭鄙视其人而予以了拒绝,后来曹操寻机威胁,“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操大悦而去”。 公元 184 年,东汉中平元年,黄巾起义爆发。张角利用东汉社会价值认同混乱的时机,自创太平道,以咒语、符水为工具行医、看病和传道,对底层无依的贫农进行宗教动员。十余年间,发展信众数十万人,势力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和豫等八州之地,连东汉政权一些官吏、宦官也成为信徒。灵帝不得不下诏大赦党人,各地世家大族、名士被迅速动员起来参加平乱。十余年来受到迫害、冷落的士大夫群体,重新回到了东汉的政治舞台。 汉灵帝接受皇族刘焉建议,改巡视、监督性质的刺史为州牧,即在郡县之上新设州一级的行政单位,以朝廷重臣出任首长,授予地方军政实权,推翻了光武帝郡县不置武装的制度安排。灵帝去世后,朝廷中外戚、宦官与党人发生斗争,外戚、宦官势力几乎同归于尽,凉州军阀董卓进京控制局面,废除少帝刘辩,毒杀何太后,改立灵帝次子刘协为帝,是为汉献帝。随即汝南大族袁绍率十八地方首长起兵讨伐董卓,虽未获成功,但实际形成了各地武力割据的局面。 在多个地方军政集团中,除部分由武人军阀主导以外,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和刘璋等人,均为当时的世家大族、名士或皇亲。其中个别如袁术异想天开,以为得到了传国玉玺,即得到了天命的授权,随即登基称帝,结果遭到各方强烈的谴责,被迅速攻灭,传为笑谈。其他多数人以掌握的政治、军事资源为后盾,既不愿继续忠于破落的汉献帝政权,也不敢违背汉王朝乃天命所系的价值正确,从而再受命另建新的王朝。对于天下危局束手无策,无法提供适当的解决方案。 相比较而言,曹操的政治眼光明显高于同时代的群雄。他主动将献帝迎至许昌,以东汉政权正统的名义平定各方。先后击败袁术、吕布、张杨、眭固和张绣等割据势力,在官渡之战中,一举击败袁绍军政集团,北征乌桓、南伐荆襄、西讨凉州,尽管在赤壁大战中,败于孙权和刘备的联军,但是,基本重建了北方中国的治理秩序。在曹操进行统一战争的进程中,出现了相当值得关注的有趣的现象。作战中对立的双方都将忠于汉室作为号召的旗帜,曹操方面以汉献帝的名义发布诏令,自居为汉中央政权,将地方势力视为叛逆予以讨伐;而曹操的对立面,则痛斥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贼”,进行尊汉反曹的全面动员。 《三国志·武帝纪》记载,曹操“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以法家严刑峻法的霸道方法论,力图振作中央政权的专制权威。他三次下达求才令,强调唯才是举,“明达法理”被作为进入组织体制的依据,而对于以名节、德行为核心的儒教征辟标准不以为然。曹操依照法家农战的思维,大规模推行屯田制度,直接把失地的劳动者组织起来,将其置于独立的郡县体制外的屯田官员管理下,解决国家物力、财力资源缺乏的困境。 曹操同时以汉政权的名义,先后招徕大族名士至其麾下效力,在重建中央政权威望、整合华北社会的过程中,这些大族名士给予了充分的合作。川胜义雄先生考证,贡献最大的是荀彧,堪称第一功臣,其次是则为荀攸。从祖父一代开始,两人所属的颍川荀氏便不断产生汉末清议之途的领袖人物。钟繇、陈群的先祖钟皓、陈寔与荀彧祖父荀淑同为颍川清流集团领袖。此外,如华歆、王朗、崔琰等也都属于北海清流集团,同进行著名的汝南月旦评的许氏之门交往甚密。 不过,曹操雄才大略、文采风流,却始终难以得到世家大族、名士内心真正的认可。曹操的父亲曹嵩,曾是宦官曹腾之养子。阉人养子之后,成为曹操入仕后难以抹去的污名。他长期担任东汉政权丞相,兼领冀州牧,越来越表现出对于献帝的极不尊重。曹操处死了孔融、崔琰等多位与之产生矛盾的名士,两次和汉献帝身边近臣亲属发生冲突。参与倒曹行动的车骑将军董承等多位大臣,除刘备事先出走外,均被灭族。怀孕的献帝妃董贵人,伏皇后和她所生两位王子,以及伏后之父伏完等家族数百人,全遭杀害。 公元 213 年,东汉建安十八年,曹操被封为魏公,以邺城为都,公然立宗庙而祭社稷。三年后曹操进爵魏王,出入服饰礼仪与天子无异,不仅成为事实上的最高统治者,还相当于自建了和东汉政权并行的政治系统。曹操被封魏公时,远在成都的刘备、许靖和马超等人上书献帝,痛骂曹操“窃执天衡”“剥乱天下”,他并不以为意。曹操称魏王后,孙权上表劝他称帝,曹操却哈哈大笑,“是儿欲踞吾著炉火上邪”。他不可能再做忠贞的汉臣,但他也相当清楚,天下士人不可能支持他打着兴汉的旗帜代汉。 曹操最信任的首席谋士荀彧,因此忧愤而死。荀彧是迎奉献帝的主要策划者,经他推荐的人物,后来都成为曹魏政权的高级官僚。荀彧晚年因劝阻曹操不要加九锡、称魏公,遭到了曹操的忌恨。 陈寿在《三国志》中,认为荀彧“机鉴先识,未能充其志也”,即未能及早识破曹操代汉的意图,充当了曹操改朝换代的帮凶。范晔写作《后汉书》,仍将荀彧视为忠贞的汉臣。唐人杜牧全面否定了荀彧的行为,批评荀彧“教盗穴墙发匮而不与同挈,得不为盗乎”?帮助盗贼挖墙破柜而不与盗贼分赃,难道他不是盗贼吗?司马光反驳了杜牧的观点。他在《资治通鉴》里,给予了荀彧相当的理解:“且使魏武为帝,则彧为佐命元功,与萧何同赏矣;彧不利此而利于杀身以邀名,岂人情乎?”高度赞扬了荀彧坚持汉统价值而牺牲生命的儒者之仁。 历史学家对于荀彧的不同评价,反映了荀彧选择的矛盾之处。为了实现匡扶汉室正统的理想,荀彧不得不帮助最有能力统一天下的曹操,当曹操暴露出代汉的野心,荀彧其实处于极其两难的境地。这不仅是荀彧个人的痛苦所在,也是整个儒生士大夫阶层无法选择的痛苦所在。尽管大多数官僚最终保持了沉默,一些趋势者表达了劝进,但是,被动地服从政治权威与主动地忠诚于价值理念,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心理状态。 同样,这也不仅是曹操个人的困局,而是当时整个汉魏时代的困局,即坚持儒学、天命和汉统的核心价值,与实力至上、胜者为王的现实政重背离。国家治理体系形成了死结。 网络上曾热议:如果能穿越,最想去哪?晋朝似乎总被忽略。历史课本中的晋朝,混乱且难以理解。但《晋朝的死结》一书,却让我重新审视这个朝代。 这本书以“死结”为线索,清晰地梳理了晋朝150多年的历史,涵盖关键时间点、人物和事件。但它并不只是局限于人物与事件的演绎,而是深入历史肌理,注重分析隐藏在表象背后的原因、联系和规律,让读者在轻松阅读中深化认知。 书中的视角不仅限于晋朝,还扩展至东汉、三国、南北朝乃至隋唐,揭示了古代王朝在天命与强权间的挣扎。晋朝的故事,让我们感受到历史的悲怆与无奈,体会到“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这本书还有一种独特的魅力,那就是能让你冷峻观望历史盛衰的同时,不知不觉中对其中的历史人物深深共情。这既归功于作者的笔触平和,没有夸张的渲染;又可能是本书揭示的“死结”现象是一个万古同悲的命题。司马炎好不容易称帝,却改变不了继任人是个傻子,没法坐稳皇位的命运;永嘉之乱后,司马睿被拥戴重建晋政权,与王导共坐,不过是一个没有实权的国家象征;能人桓温三次主持北伐,却被疑狼子野心,晋都洛阳得而复失,终究竹篮打水一场空。 那么,再回到最初的那个问题,假如可以穿越,你有勇气选择到晋朝,去解开死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