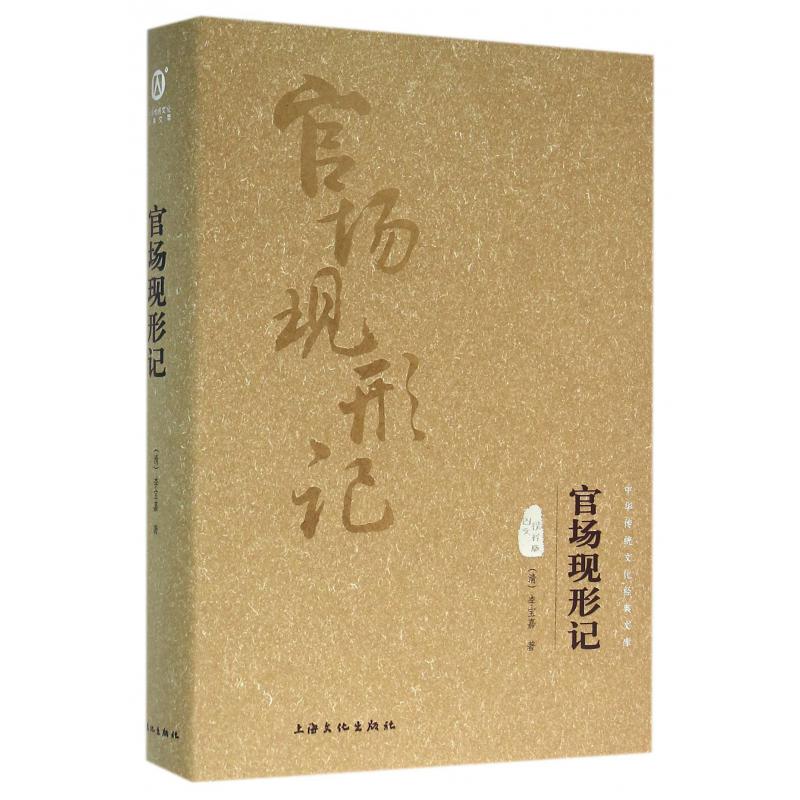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化
原售价: 59.00
折扣价: 31.87
折扣购买: 官场现形记(图文精释版)(精)/中华传统文化经典文库
ISBN: 97878074078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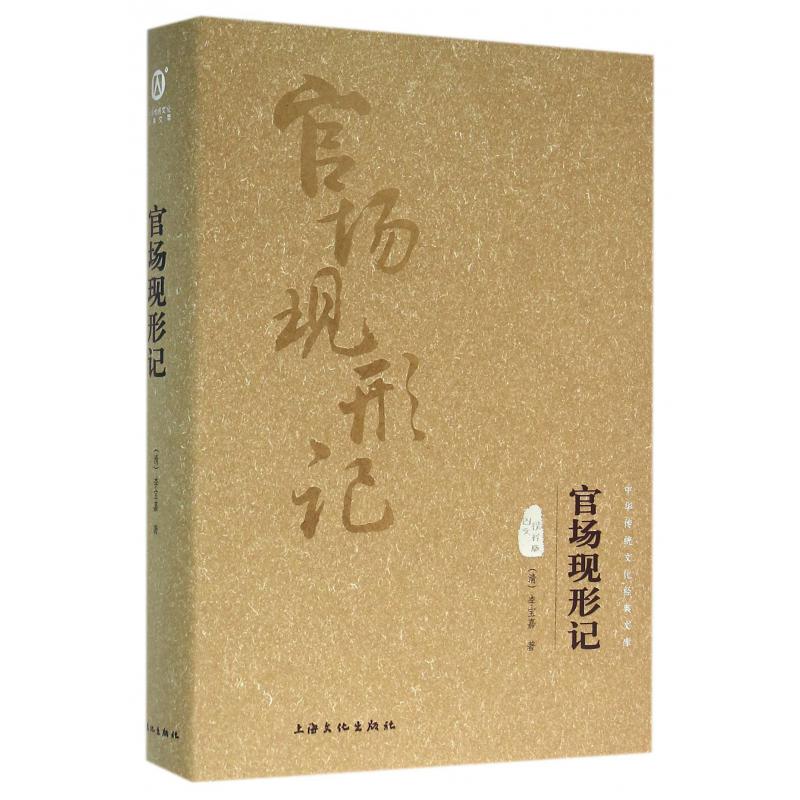
这方必开是从来没见先生发过这样大的气,今儿 明明晓得是他儿子的不是,冲撞了他惹出来的祸,但 是满肚子里的痰越发涌了上来,要吐吐不出,要说说 不出,急得两手乱抓,嘴唇边吐出些白沫来。老三还 在那里叽哩咕噜说:“是个好些儿的,就去中进士, 做官给我看,不要在我们家里混闲饭吃。”王仁听了 这话,更是火上加油,拿着板子赶过来打。老三又哭 又跳,闹的越发大了。还是老三的叔叔听见不像样, 赶了进来,拍了老三两下。又朝着先生作了几个揖, 赔了许多话,把哥子搀了出来,才完的事。按下不表 。 且说赵老头儿,自从孙子中举,得意非凡。当下 就有报房里人,三五成群住在他家,镇日价大鱼大肉 的供给,就是鸦片烟也是赵家的。赵老头儿就把一向 来往的乡、姻、世、族谊开了横单,交给报房里人, 叫他填写报条,一家家去送。又忙着看日子,祭宗祠 。到城里雇的厨子,说要整猪整羊上供,还要炮手、 乐工、礼生。又忙着拣日子,请喜酒,一应乡、姻、 世、族谊都要请到。还说如今孙子中了孝廉,从此以 后,又多几个同年人家走动了。又忙着叫木匠做好六 根旗杆:自家门前两根,坟上两根,祠堂两根。又忙 着做好一块匾,要想求位翰林老先生题“孝廉第”三 个字。想来想去,城里头没有这位阔亲戚可以求得的 ,只有坟邻王乡绅,春、秋二季下乡扫墓,曾经见过 几面,因此渊源就去送了一份厚礼,央告他写了三个 字。连夜叫漆匠做好,挂在门前,好不荣耀。又忙着 替孙子做了一套及时应令的棉袍褂,预备开贺的那一 天好穿了陪客。赵老头儿祖孙三代,究竟都是乡下人 ,见识有限,哪里能够照顾这许多。全亏他亲家,把 他西宾王孝廉请了过来,一同帮忙,才能这般有条不 紊。当下又备了一幅大红金帖,上写着“谨择十月初 三日,因小孙秋闱侥幸,敬治薄酒,恭候台光”,下 写:“赵大礼率男百寿暨孙温载拜”。外面红封套, 签条居中写着“王大人”三个字,下面注着“城里石 牌楼进士第”八个小字。大家知道,请的就是那王乡 绅了。另外又烦王孝廉写了一封四六信,无非是仰慕 他、记挂他,届期务必求他赏光的一派话。赵老头儿 又叫在后面加注一笔,说赶初一先打发孩子赶驴上城 ,等初二就好骑了下来。这里打扫了两间庄房,好请 他多住几天。帖子送去,王乡绅答应说来,赵老头儿 不胜之喜。 有事便长,无话便短。看看日子,一天近似一天 ,赵家一门大小日夜忙碌,早已弄得精疲力尽,人仰 马翻。到了初三黑早,赵老头儿从炕上爬起,唤醒了 老伴,并一家人起来,打火、烧水、洗脸、换衣裳、 吃早饭,诸事停当,已有辰牌时分。赶着先到堂祠里 上祭,当下都让这中举的赵温走在头里。屁股后头, 方是他爷爷、他爹爹、他叔子、他兄弟,跟了一大串 。走进了祠堂门,有几个本家都迎了出来。只有一个 老汉,嘴上挂着两撇胡子,手里拿着一根长旱烟袋, 坐在那里不动。赵温一见,认得他是族长,赶忙走过 来,叫了一声:“大公公。”那老汉点点头儿,拿眼 把他上下估量了一回,单让他一个坐下。同他讲道: “大相公,恭喜你,现在做了皇帝家人了。不知道我 们祖先积了些什么阴功,今日都应在你一人身上。听 见老一辈子的讲,要中一个举是很不容易呢。进去考 的时候,祖宗三代都跟了进去,站在龙门老等,帮着 你抗考篮。不然那一百多斤的东西怎么拿得动呢?” 还说是文昌老爷,是阴间里的主考。等到放榜的那一 天,文昌老爷穿戴着纱帽圆领,坐在上面,底下围着 多少判官在那里写榜。阴间里中的是谁,阳间里的榜 上也就中谁,那是一点不会错的。到这时候,那些中 举的祖宗三代,又要到阴间里看榜,又要到玉皇大帝 跟前谢恩,总要三四夜不能睡觉呢。大相公,这些祖 先熬到今天,受你的供,真真是不容易呢。”爷儿两 个正在屋里讲话,忽然外面一片人声吵闹。问是什么 事情,只见赵温的爷爷满头是汗,正在那里跺着脚骂 厨子,说他们到如今还不来,“这些王八崽子,不吃 好草料的,停会子告诉王乡绅,一定送他们到衙门里 去。”嘴里骂着,手里拿着一顶大帽子,借他当扇子 扇,摇来摇去,气得眼睛都发了红了。正说着,只见 厨子挑了碗盏家伙进来。大家拿他抱怨,厨子回说: “我的爷,从早晨到如今,饿着肚皮走了三十多里路 ,为的那一项?半个老钱没有看见,倒说先把咱往衙 门里送。城里的大官大府、翰林尚书,咱伺候过多少 ,没瞧过他这囚攮里的暴发户,在咱面上混充老爷。 开口王乡绅,闭口王乡绅,像他这样的老爷,只怕替 王乡绅捡鞋还不要他哩。”一面骂,一面把炒菜的杓 子往地下一掼说:“咱老子不做了,等他送罢。” 这里大家见厨子动了气,不做菜,祠堂祭不成, 大家坍台。又亏了赵温的叔叔走过来左说好话,右说 好话,好容易把厨子骗住了,一样一样的做现成了, 端上去摆供。 当下合族公推新孝廉主祭,族长陪祭,大众跟着 磕头,虽有赞礼生在旁边吆喝着,无奈他们都是乡下 人,不懂得这样的规矩。也有先作揖后磕头的,也有 磕起头来再作一个揖的。礼生见他们参差不齐,也只 好由着他们敷衍了事。一时祭罢祠堂,回到自己屋里 ,便是一起一起的人来客往,算起来还是穿草鞋的多 ,送的份子倒也络续不断,顶多的一百铜钱,其余二 十、三十也有,再少却亦没有了。P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