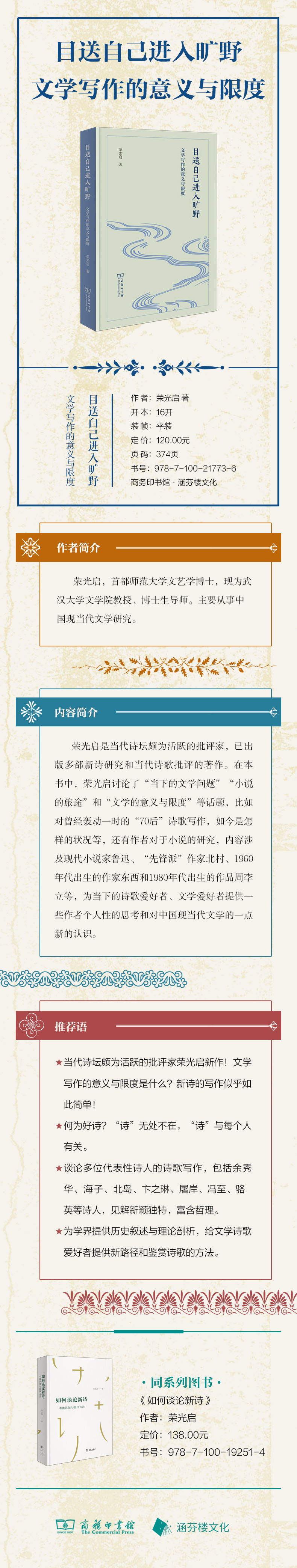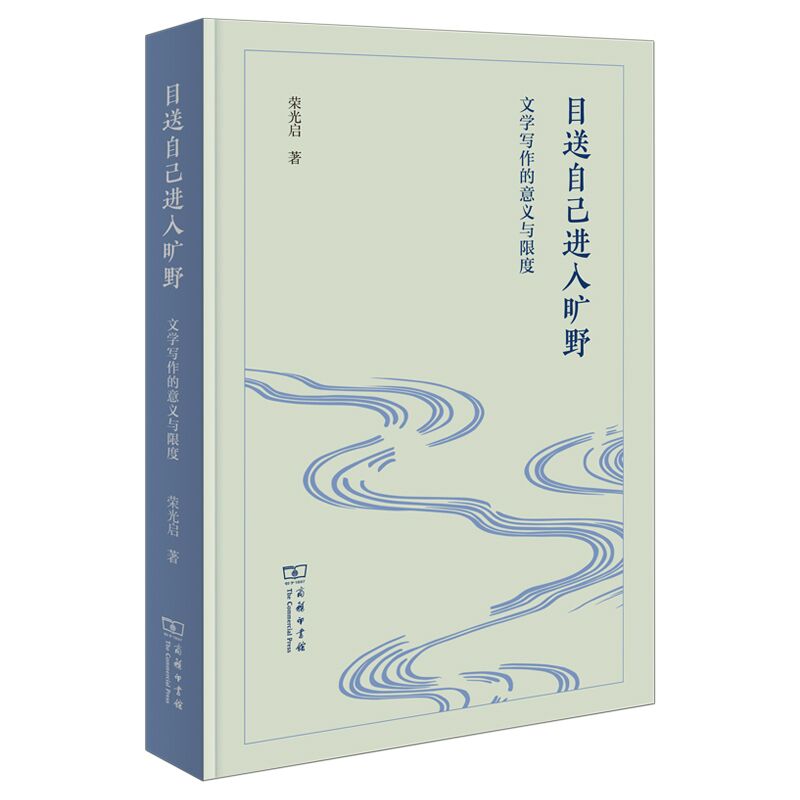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原售价: 120.00
折扣价: 84.00
折扣购买: 目送自己进入旷野——文学写作的意义与限度
ISBN: 97871002177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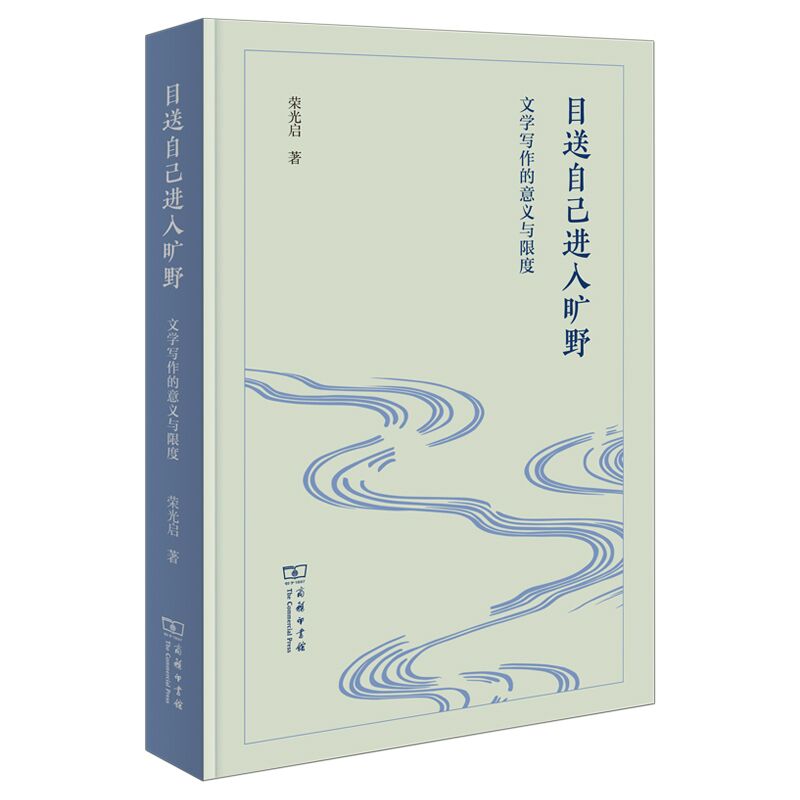
荣光启,首都师范大学文艺学博士,现为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诗”,无处不在;“诗”,与你有关 一 当我们说到“诗”,一般人脑海里会马上浮现出许多经典诗歌文本,习惯性地认为那些文字才是“诗”。但通常的情况是:“诗”/“文学性”,从发生学的角度,首先是一个人的说话方式的特别及由之带来的效果。 人很多时候,为了表达内心的真实的或复杂的状况,会寻求一些区别于平常的交际性、工具化的说话方式。比如,他会组织自己的语言,诉诸情绪、感觉、经验、想象和记忆的叙述,试图传达出日常交际语言无法传达的内容。这样的话,这种言语活动就有可能带来某种表达的“新鲜”,其中有趣味性,或者有某种深刻、感人、恸人的意蕴。人的言语活动所带来的意蕴之“新鲜”,才是“诗”/“文学性”之开始。 我们通常说的“诗”/“文学性”,其实首先是言语活动所体现出的一种别样的意趣、意味。从作者来说,他是主动的,他希望能够表达出一个真实的自我,为此他会运用与日常交际语言不同的说话方式;而从接受角度,作者所呈现的语言活动之特别,会让读者在“异样”的接受中意识到另外的内容,通常是获得关于人、关于生活或生命的某些新的感知。当然,这种感知不是概念推演、在严密的逻辑性叙述中的哲学化的“具体”,而是蕴藉在文学性的“具体”之中。这种“具体”由对情绪、感觉、经验、想象和记忆的叙述构成。这样的“具体”叙述其目的是为了作者所体会到的存在,能在最大程度上被某些读者“具体”感知。如同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所言:“正是为了恢复对生活的体验,感觉到事物的存在,为了使石头成其为石头,才存在所谓的艺术。” 艺术的目的(也是“诗”之目的),首先不是让人思虑“石头”意味着什么,而是让“石头”作为“石头”本身被人感知。这里的“石头”,当然可以指代我们的生活。 二 当我们有这种认识,我们可以获得两种益处:一是不苛责他人的写作。如同我们经常做的:以我们自己认为的最杰出的最经典的作品为标准,来评估我们面前的作品,轻易地说出其中的问题与缺点。这种态度其实很容易让我们忽略作品的创新性与艺术性。这是对“诗”的一种合理的批评态度;二是意识到“我”自己也是“诗人”。在言语活动中产生“诗”,并非只是他人的事、一些所谓著名诗人的事,也是“我”的事。当人有这种意识,最终的效果不是他有没有成为“诗人”,而是其语言表达能力的提高。这是对“诗”之功能的合理认知。 从原初的意义上说,“诗”是特定生活状况中自我心灵的一种语言表达,对“诗”的思忖,其实是对生活、自我与语言之关系的一种思虑。这样讲的话,“诗”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现象,“诗”无处不在。同时,“诗”是一个有语言自觉意识的人的一种表达能力,“诗”与每个人有关。 三 “口语诗”的流行,已经是当代汉语诗坛不可回避的问题,无论是读者眼目所见,还是诗人的作品呈现,口语化的写作,都相当普遍。有意思的是,读者对口语诗的态度也非常极端。支持的人竭力高举之,反对者觉得这种写作方式不值一提。 “口语”这里指的是现代汉语中与书面语相对的语言形态,我们在日常生活中的交谈,一般来说,普遍使用的是口语。这样的语言注重交际功能,其声音和意义具有普遍性,在表达时尽量避免歧义、多义和复杂性。而语言的“诗功能”恰恰相反:它要求表达效果具有隐喻、象征意味,指向更深更广的意义领域。以口语为“诗”,其中语句通俗易懂,明白如话,这可能吗? 新诗自发生以来,一直有以口语为诗之传统,在白话文运动中,以白话、口语、俗语、俚语为诗,乃是“革命性”的,新文学也由此面对许多敌对阵营的挑战。新诗诞生之后,随着对诗的艺术性的追求,口语化的诗作,不能说是主流。当代文学阶段,尤其是“第三代”诗人的写作,口语化的作品在其中极为引人注目,但在纷繁的流派与主义中,仍然不能说是诗坛主流。但在我们这个时代,情况似乎大为改观。翻阅诗歌杂志和浏览诗歌网页,你会发现:新诗的写作似乎如此简单!最直接的现象就是口语化的诗作铺天盖地。无论是读者所见还是作者正在进行的实践,新诗的口语化现象都相当普遍。与口语相对的是书面语,为什么没有“书面语诗”?为什么要单独列出“口语诗”概念? 了解新诗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口语诗”一直有强烈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其诞生往往产生于一个争夺话语权力的场域。白话文运动,反对的是旧诗词、文言文写作的权势;当代的口语诗,其发生的语境也相似。口语诗常常与“革命”相关,它要去除的是既有的笼罩诗歌写法、统摄诗歌写作的某种意识形态。新诗发生初期,诗歌作者因惯用旧诗词而产生许多陈言套语、陈词滥调 ,陈独秀、胡适一代人极为反对。当代口语诗的历次勃兴,也有此类状况。“第三代”诗人的反对“隐喻”、反对“文化”;“70后”诗人竭力倡导“感性”的“下半身写作”,都有颠覆既有诗歌意识形态(诗/诗歌语言,应该是这样的、诗意,是如此产生的等等观念、内在成规、审美“程式”)的革命意图。 也正是这种革命性,使人们对口语诗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与认识:第一种态度——支持者认为,口语诗才是新诗之正道。在世纪之交的中国语境里,它反对的对象正是广泛流行的“知识分子写作”特征,那种习惯以有异域文化特征的、书面语特征的、“西方化”的、从翻译作品中来的语言与意象进行诗歌写作的方式。第二种认识——口语诗写作的反对者则认为:口语诗差不多是“口水诗”,大白话、“废话”、缺乏“诗意”,难登大雅之堂;口语诗写作没有难度、口语诗均通俗易懂,不值得深入研究;好诗人不太爱写口语诗、常写口语诗的作者中,难有好诗人大诗人。 对形态各样的口语诗的理解,检验我们对新诗的包容度和理解力。 四 在2022年8月下旬一次媒体的电话采访中,记者问到为什么今天大众对新诗的意见这么大,仿佛每一次新诗被大众所关注,都是因为什么丑事(在他们看来的“烂诗”,却获得某些殊荣),然后记者说“胡适、郭沫若写的第一代新体诗”好像大家觉得还好…… 我当即否定:“大众也读不懂胡适、郭沫若,很多人也骂他们,不知道他们写的是什么,这种东西怎么能叫诗呢,一样的……”然后接下来我有一个解释:“普通的读者是不能够鉴赏这样的诗的。因为我们还停留在唐诗宋词那个标准,不太理解现代诗是怎么写的,我们仍然是以古典诗歌评价的那个标准,去看待新诗”。 这个解释,由于缺乏我和记者对话的语境,被单独摘出来,听众很不能接受:一是认为我贬低唐诗宋词,看低古典诗歌,这大概算我的无知以及诋毁传统文化……二是我太不尊重“普通读者”,竟然说他们“不太理解现代诗是怎么写的”,甚至“不能够鉴赏”在他们看来是“烂诗”的东西,这,简直是侮辱。 事实上,我一直期待新诗能够被理解。这种理解倒不是为了新诗写作者或者新诗研究者的利益,而是觉得新诗在被误解中,普通读者最有损失:诗不光可以欣赏,也可以用来自我表达,每一个有语言能力的人,都可以尝试去写诗,或者说在语言中创造“诗意”。但现在的情况就是,由于对“诗意”的认知仍然停留于旧诗的“阅读程式”(读者对不同文类的期待意图、内在的文学能力),体察不到新诗的诗意,或者不认同新诗的诗意,导致了许多人对新诗的鄙视、远离了一种可以言说内在自我的艺术方式。 我非常尊重诗歌的读者,我希望诗歌写作能够回到普通人的意识之中:诗,不只在典籍或旧时代之中,也在我们的日常言语活动之中;诗人,不只是李白、杜甫、徐志摩、海子、顾城、狄金森,你也可以是。 当代诗坛颇为活跃的批评家荣光启新作!新诗的写作似乎如此简单!“诗”无处不在,“诗”与每个人有关。诗人,不只是李白、杜甫、徐志摩、海子、顾城、狄金森,你也可以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