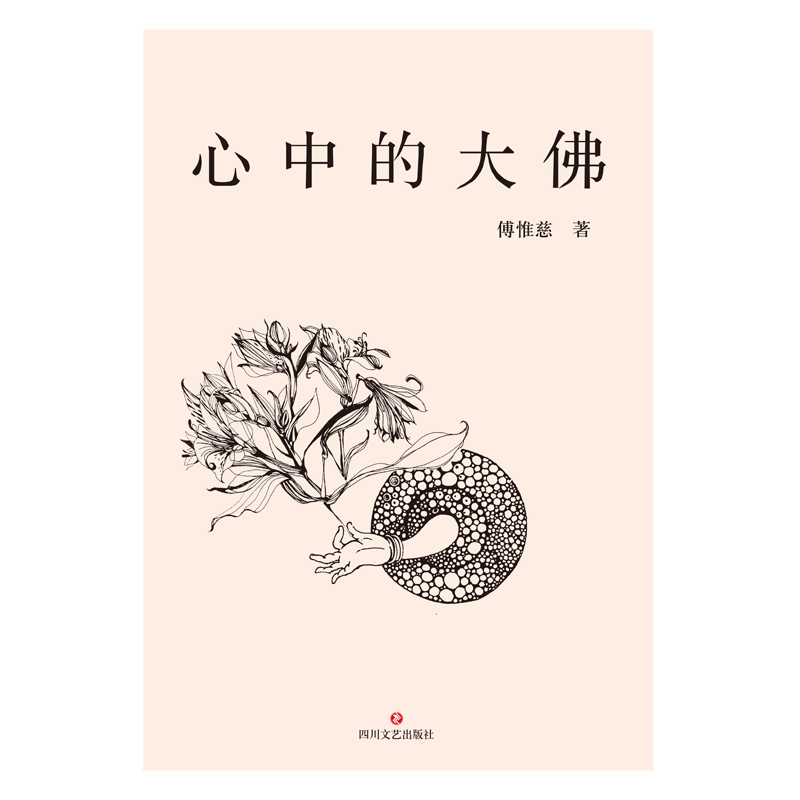
出版社: 四川文艺
原售价: 38.00
折扣价: 24.70
折扣购买: 心中的大佛
ISBN: 978754114397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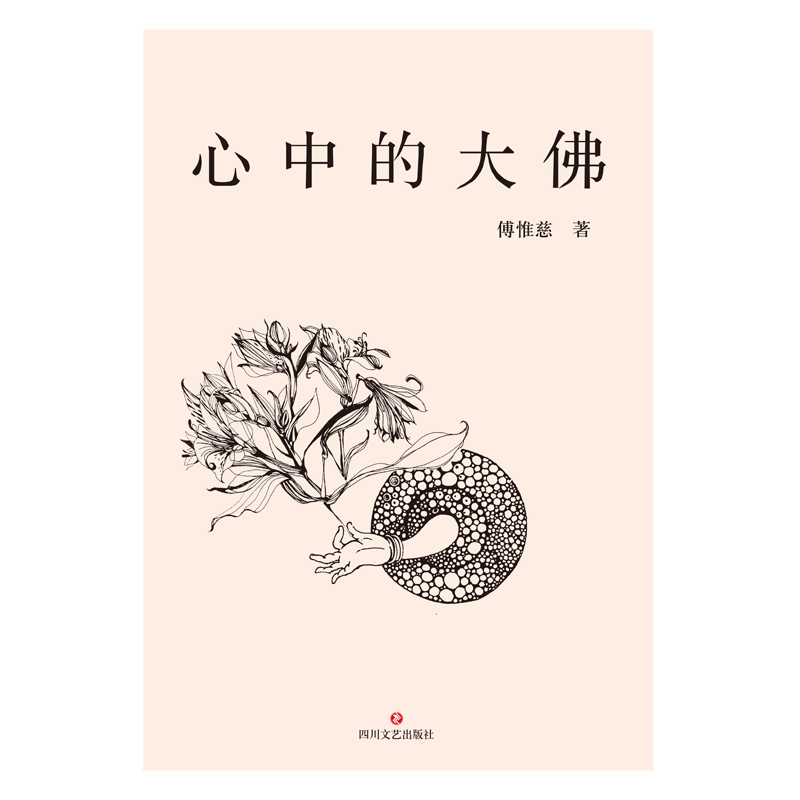
傅惟慈,著名文学翻译家、教育家,钱币收藏家,也是一位旅游和摄影爱好者。 他的一生充满传奇。1923年生于哈尔滨,曾求学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讲授语言、文学课。20世纪80年代赴德国、英国教学。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有近四百万字的译著,较有影响的有:卢森堡《狱中书简》、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亨利希·曼《臣仆》、毛姆《月亮和六便士》及格雷厄姆·格林多部作品。
千里负笈记 一、告别大学生活 日历翻到1943年,我已经在沦陷于日寇之手的北 平(那时北京还叫北平)生活了十余年。在日寇铁蹄 下,物价飞涨,百姓生活越来越困难。最困难的是粮 食,一般人家,吃饭不得不搭着“混合面”,一种用 豆饼、高粱、花生壳等磨制成的粗粮。我家在我父亲 去世后,幸好留下大小几处房子,靠“吃瓦片”(出 租房屋)还买得起细粮,生活尚能温饱。1942年秋季 ,我考入天主教会办的辅仁大学西语系,这时第一学 期已近尾声。我在大学学习还不错。英语在上中学的 时候就有些底子,一有闲暇,我就到图书馆去看英文 书。我喜欢文学,耽于幻想。在西语系一年级的几门 课程中最爱听的是文学界老前辈李霁野讲授的世界文 学史。李老师早年参加过文学研究会,同鲁迅有过交 往。课堂上他为学生开启了一座座文学宝库,从荷马 史诗、希腊悲剧讲起,一直到中世纪薄伽丘的《十日 谈》和但丁的《神曲》。开英国文学选读课的英千里 老师是辅仁大学创办人英敛之的长子。英家全家人都 信奉天主教,英千里十几岁就由一位神甫带到欧洲, 后来在英国伦敦大学毕业。他精通英、法、拉丁文几 种语言。用英语讲课,语音纯正,征引繁富,充分显 示出他的博才多学。给我更深印象的是他在课堂上毫 无顾虑地抨击日本对华侵略,并不时传达一些抗战信 息。在敌伪严密控制下,英老师这样做需要很大勇气 。在他选读的文章中,有一篇HG威尔斯写的《盲 人国》,引起我对科幻小说的兴趣。《隐身人》《时 间机器》和《莫洛博士岛》日后都成了我爱读的小说 。“四人帮”倒台后,我译了英国温代姆的《呆痴的 火星人》,阿西莫夫的《低能儿收容所》几篇科幻小 说,同早年爱读科幻不无关系。 我有一批喜爱文学的朋友,有时聚在一起,谈天 说地,也大言不惭地谈论各自的抱负。我想当个文学 家,平常也胡乱写些东西。那时候我正痴迷于施特劳 斯的圆舞曲,曾借用他的几首曲名,练习创作。《南 国的玫瑰》写的是一个中国留学生和一个意大利少女 的短暂恋情。《蓝色的多瑙河》也是写中国留学生, 假期中这个中国青年沿着多瑙河漫游,经历了种种奇 遇。若干年以后,我读毛姆的小说《刀锋》,发现书 中主人公在德国浪游的某些情节,竟和我的虚构很有 几处近似的地方。我深知自己的幻想式练笔文章一文 不值。我对社会现实毫不了解。艾芜的《南行记》, 高尔基的《在人间》《俄罗斯浪游记》强烈地吸引了 我。我渴望走出家门,在外面广大的世界混迹于千百 万普通人中间。抗日战争烽火连天,中国人正在受难 。在战场上经历一次战火洗礼,如果幸免于死,倒也 是难得的经历。不管怎么说,我对大学生活感到有些 厌腻,我渴望走出去看一看外部世界,看一看中国的 另一面——一个真实的中国。 早在入大学前我就开始盘算出行计划,如何离开 敌伪统治下的北平。我同少数几个知心朋友也常常议 论此事。一个在北平师范学校念书的同学介绍给我一 个同重庆方面有联系的地下工作者。这人的公开身份 是小学教员,我常常同他约好在北海公园见面。他每 次都给我讲解抗日战争形势,青年人奋斗的方向,等 等。后来见面的机会多了,自然也谈到青年人渴望离 开沦陷区,参加抗战的事。我问他有什么路子可以去 后方。他说有,但要冒风险,而且要等待时机。他告 诉我有两条路离开敌伪统治区:一条走东线,经河南 商丘;一条走西线,经河南沁阳。前一条是通商道路 ,来往人多,行路的时间长,花费大,有时还会碰上 盗匪滋扰。后一条路程短,但要轻装上路,还要事先 安排,找向导带路。我对是否辍学出走,很长时间犹 豫不决。这一话题在同那位地下工作者会面时虽然还 不断提及,但一直没有深谈。直到最后我去意已定, 而且大致定了行期以后,他才透露给我上路的一些细 节:具体路线,何处换车,下车找何人联系,直到行 路的一些注意事项——该带什么(后方缺少的物资) ,不该带什么(书籍、文具、证件和一切可能暴露学 生身份的东西)。他还给我讲了一些“那边”的情况 ,好的和坏的,希望和困难。“那边”一词是指我国 未受日本人蹂躏的领土,是指人民可以自由呼吸的地 方。我渴望光明,渴望自由。在北平大学里念书,生 活虽然还算惬意,但却感到窒息。更何况这里到处插 着太阳旗,国土已经变了颜色,叫你随时随地都有生 活在屈辱中的感觉。除了我的书,这里还有什么可留 恋的呢?1943年春节前十几天,学校马上就要放寒假 了。我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卖给同学,又从家里要了 些钱,提着简单的行李,登上了一趟南行列车。火车 驶出车站,我向灰色的古老城墙和角楼挥手告别。未 来等待我的是什么,是个未知数。我只知道自己将要 走进一个陌生而又新奇的世界。山水、人物、粗劣的 饮食、鸡毛小店……或许还有枪林弹雨。什么我都准 备迎受,也愿意迎受。虽然有些忐忑不安,甚至有些 恐惧,但新鲜感支撑着我。想到我的那些可怜的同学 正在吃力地背诵课文,准备期终考试,而我却坐在火 车上旅行,我感到宽慰,甚至幸福。上帝给了我眼睛 是叫我看东西,给了我双腿是叫我走路。我现在就在 使用它们。我刚刚迈出生活的第一步,今后我还要看 得更多,走得更远。当时我的思想虽然还模糊不清, 但在潜意识里,已经逐渐定出终生遵循的生活准则了 。P14-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