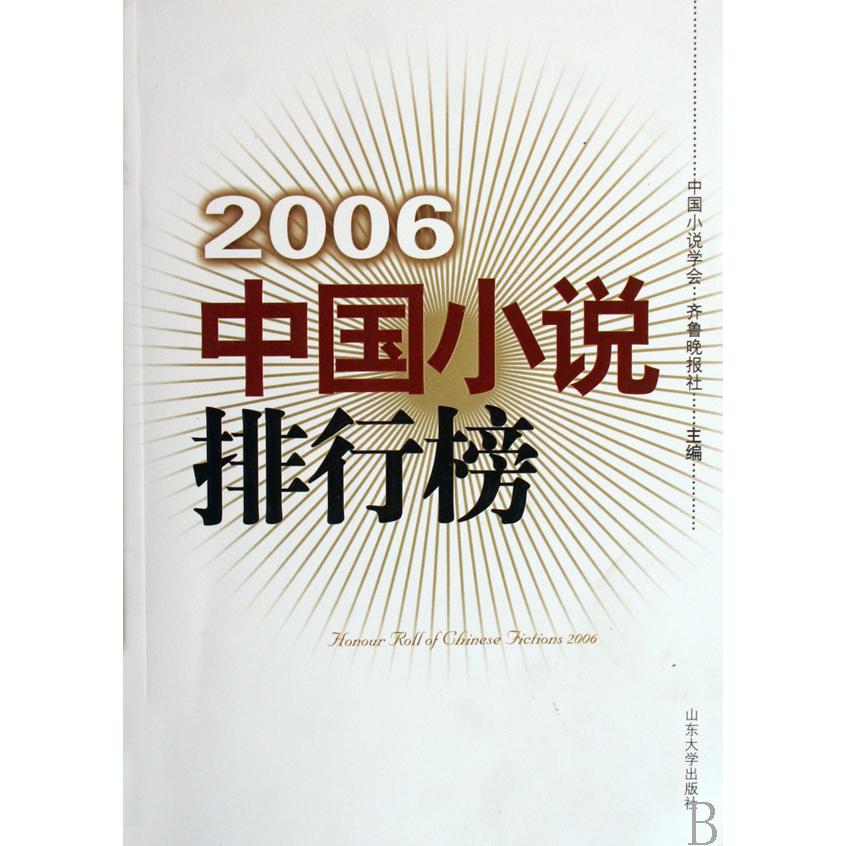
出版社: 山东大学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44.60
折扣购买: 2006中国小说排行榜
ISBN: 978756073467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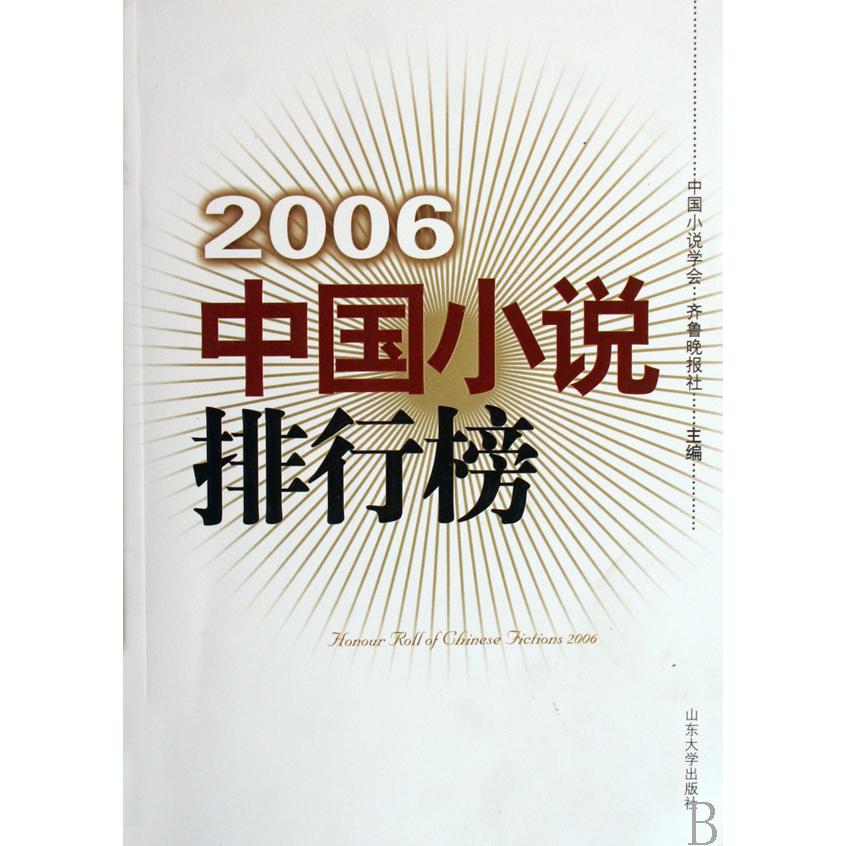
“自由”的小说——评《生死疲劳》 吴义勤 在我看来,《生死疲劳》无疑代表着小说写作的一种难能可贵的境界 ——一种完全没有任何束缚和拘束的、随心所欲的自由境界。这是一种能 让作家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发挥到极致的境界,环顾中国文坛,能达此境界 者,大概唯莫言一人耳。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作家无不渴望、追求着“自 由”,但是“自由”却从来都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国家、民族、启蒙、救 亡、战争、政治等宏大词汇无时无刻不在压抑、阻隔着中国作家通向“自 由”的“道路”。无论是鲁迅等“五四”一代作家,还是巴金、老舍等三 四十年代的作家,抑或赵树理等解放区作家,或者周扬、郭沫若等新中国 语境中的作家……历史从来就不曾给他们提供过“自由”的机会,他们总 是背负着沉重的负荷,新时期以来,改革开放、思想解放的潮流为中国文 学赢得了走向“自由”的绝好机遇,但“自由”对中国作家来说却仍很奢 侈。从意识形态写作到反抗意识形态写作、从现实主义到反现实主义、从 历史主义到新历史主义、从精英主义到民间立场、从宏大叙事到个人叙事 、从西方化到本土化、从共名到无名……文学的每一次解放,似乎都同时 伴随着一次新的束缚。拿先锋派来说,他们的形式主义写作似乎很“自由 ”了,但刻意的“形式”却分明是一道枷锁,牢牢绑住了他们想象的翅膀 。更重要的是,中国作家难臻“自由”之境的原因还在于他们的“心魔” ——他们的思想、观念、思维和精神,他们的文学目标总是太具体、太直 接,总是能让我们看到他们在追求什么、思想什么,因此,思想的深度、 精神高度、现实的广度、形式的创新程度等等反而都成了他们走向“自由 ”之路的拦路虎。在当代中国作家中,很难说王安忆、余华、韩少功、贾 平凹、张炜、张洁等作家的成就与莫言孰高孰低,但从“自由”的程度来 说,恐怕他们谁也无法与莫言相提并论。莫言敢于不要“思想”,敢于反 对“高雅”,敢于宣称“作为老百姓写作”,敢于不要规范、不讲语法… …在他这里,新与旧、雅与俗、美与丑、实与虚、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分 已经没有了意义。换句话说,他的小说似乎是没有追求的,他真正做到了 “无执”,一切只是因为需要而进入他的小说,并成为小说必不可少的部 分。也许某些语言过于粗糙,也许还有语法错误,但这就是其语言的独特 性,一旦你把他变得文雅了、语法正确了,也就没有莫言的味道了。这就 是“自由”,既在不断地超越和打破规范,又在不断地创造新的可能与规 范。毫无疑问,《生死疲劳》就是这样一部“自由”的杰作。 许多人都承认,莫言是一个艺术的精灵,他的小说从来都不会僵死在 一个模式中,而总是会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刺激。《檀香刑》中的“猫腔” 如此,《生死疲劳》中的“六道轮回”更是如此。对于小说来说,“六道 轮回”是一个伟大的艺术发现,是莫言的生命体验、艺术灵感与中国民间 一种根深蒂固的生活态度的奇妙遇合。对莫言来说,生活的边界相对于他 自由奔放的想象力而言本来就是虚幻的存在,而“六道轮回”更是赋予了 莫言自由突破生活边界的巨大现实性与可能性。在《生死疲劳》中,莫言 以“动物的视角”来叙述土地和农民,叙述两个家族、几代人、一个小镇 成为中国农村1950至2000年间风云历史“标本”的毛茸茸的过程,中国农 民大爱大恨、大喜大悲的生命体验由此得到了极致化的表现。小说的书名 来自佛教偈语即小说扉页中的“生死疲劳由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 ”。莫言借助“六道轮回”的思想,让主人公在循环的生命中一世为驴、 一世为牛、一世为猪、一世为狗、一世为猴、一世为人,人畜无界,彼此 呼应,既是对世界的奇观化,又使小说有了统一的视角和统一的情怀,而 超越生死的道德力量也是莫言的特殊追求。 所谓“六道轮回”是佛教中关于人的生存境遇的一种哲学化思考和救 赎方式。莫言的目的并不是为了阐释、宣扬佛家思想,而是借用这个奇特 的框架去阐释他对于中国农民的命运以及其与土地关系的思考。某种意义 上,“六道轮司”正是莫言“想象中国”的一种方式。有人说,对“六道 轮回”的发掘和使用,是莫言回归传统的表现,是对中国古典叙事资源的 再发现,这当然没错,但同时我们又要看到,莫言的“六道轮回”又是一 个超越了古典文化语境的“六道轮回”,是一个打着鲜明的莫言印记的想 象世界的方式,其中既有着传统的因素,又更有着现代性的内涵。莫言借 助这样的方式彻底打破了生活的边界,生与死、人与自然、人与动物、3B 界与鬼界、此岸与彼岸的界限完全消失,其对中国社会、中国农民、中国 农村、中国历史的解释也自然地进入了一个自由的境界。首先,“六道轮 回”是一种奇幻的时间模式。它与中国人的宇宙观、自然观、生死观密不 可分。其次,“六道轮回”又是一种奇幻的叙事模式。莫言的叙述一向诡 异多变而充满质感,《生死疲劳》则再次展示了他的叙事天才。“六道轮 回”本身便意味着数种不同的生灵对自己一生的叙述。它使活人、死人、 动物、鬼魂在小说中都具有了平等的话语权。世界的形象区此变得复杂而 神奇。可以说,正是借助于“六道轮回”,莫言为我们呈现了一个精彩奇 幻的艺术世界。这是一个人的世界与动物的世界、现实的世界与虚幻的世 界、历史化的世界与当下性的世界水乳交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主体当然 是人,莫言把不同时代、不同命运、不同个性的人放在一个似乎共时性的 “空间”里面进行观察,把人的表演、人间的传奇与历史和时间之间“轮 回”的错位呈现给我们,既揭示了历史的荒诞,又解剖了人性的复杂与黑 暗。 莫言对现实世界的认知方法和表达方式是奇妙的,他从不追求对外部 世界的真实摹写,而是追求奔放自如、随心所欲的大写意性的体味。在他 的艺术世界中,感觉是最重要的,如烟雾弥漫于天空,碎片布满于大地, 感觉在文本中无处不在。正因为对感觉的尊重,莫言对小说的技巧之类一 直不以为意。哪怕是写实性的小说,莫言也总是以感觉和想象力的释放为 大目标,他不愿成为一个“工匠”,他想摆脱的是真实性、技巧之类的“ 雕琢”工艺对个体想象力和艺术感觉的压迫。但在《生死疲劳》中,我们 似乎看到了一个更为细腻、更为精致的莫言,虽然变形、夸张、荒诞的描 写随处可见,感觉的碎片四处飘扬,但是象征性的场景、诗性的段落、精 致的技巧,等等,在小说中也是令人印象深刻。 对莫言来说,《生死疲劳》对叙事现代感的追求首先体现在“复调叙 事”和“多重文本”结构的营构上。小说的开头、结尾都是同一句叙述语 式:“我的故事,从1950年1月1日讲起。”小说的事件时间、叙事时间和 阅读时间竟然诡异地完全一致,它使《生死疲劳》的叙事模式由此幻化出 五彩缤纷的奇丽景色。而从叙事视角上来看,小说的叙述视角又是多重视 角的复合与重叠,这种复合性视角经由莫言超乎寻常的感觉的整合,就形 成了一个集狂欢化、广场化、戏剧化于一身的奇妙艺术世界。在这个世界 中,人的内心、动物的内心、叙事主体的内心,与大地、自然和社会律动 遥相呼应,营造出了一种复杂而混沌的艺术效果。某种意义上,小说后半 部让主人公“加速度”死去的“疯狂的杀人表演”,其实又何尝不是莫言 对后现代社会的一种狂欢化想象。莫言通过一幕幕狂欢化的图景,力图在 小说中建构一种原始的语境,从而使人(生物)的本能得以释放。在这里, 民间、土地的永恒价值代替了一切虚伪的东西,贯穿五十年的政治性活动 被推到反讽的层面之上,小说呈现给我们的恰是历史的丰富性和毛茸茸的 现场感。 关于《生死疲劳》,“章回体”的形式也曾是文学界热议的一个话题 。李敬泽兄说莫言是“向中国古典小说传统致敬,是中国传统最亲切、熟 悉的大音,是东方式的魔幻现实主义”。但我觉得,似乎没有必要把“章 回体”看得如此重要,更没有必要跟“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进行直接的 比附。《生死疲劳》中的“章回体”不过是莫言创造的一种小说形式,它 与中国传统的“章回体”小说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最多只是形似而已。这 个形式已经完全莫言化了,莫言赋予了它崭新的内涵,与其说是“古典” 的,还不如说它是现代的,至少它是古典和现代的融合,其本身的现代感 是非常强烈的,而这同样也是莫言创造力和想象力的一个证明,在他这里 ,所有的艺术形式只有“自我”和“非我”之分,而没有了东方与西方、 古典与现代的界限,换句话说,他已远远超越了这些界限而进入了一个艺 术创造的自由境界。 (本文作者系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