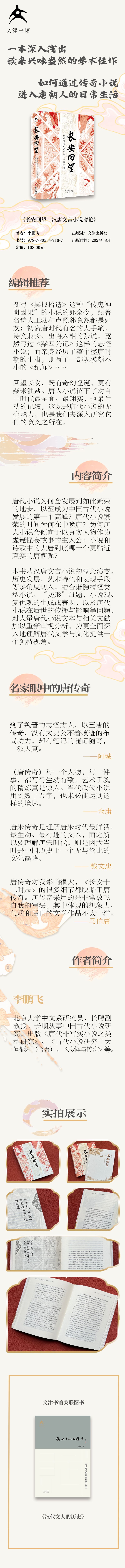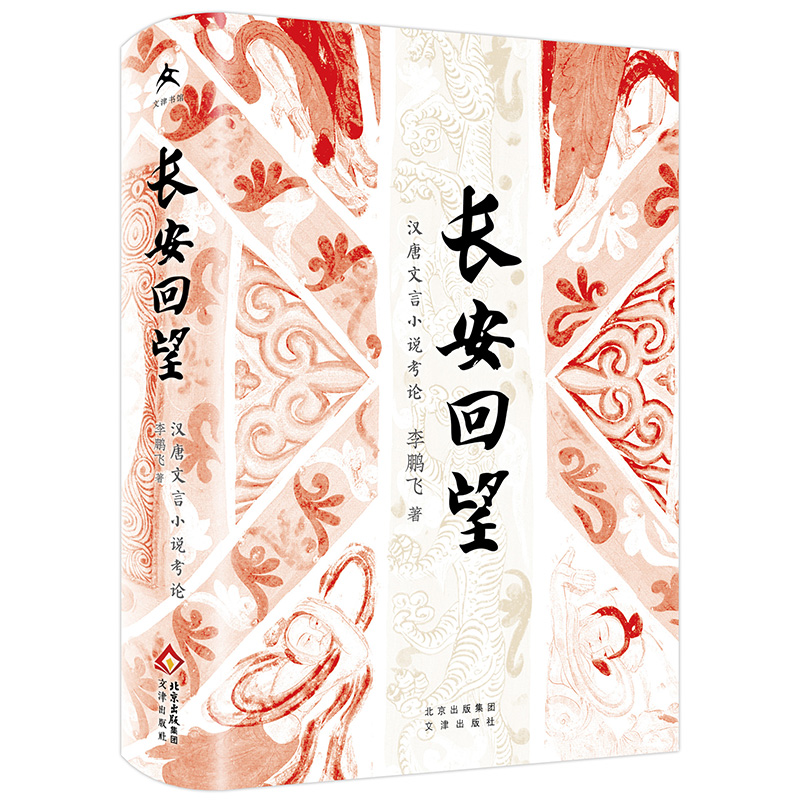
出版社: 文津
原售价: 108.00
折扣价: 63.72
折扣购买: 长安回望 汉唐文言小说考论(精)
ISBN: 97878055491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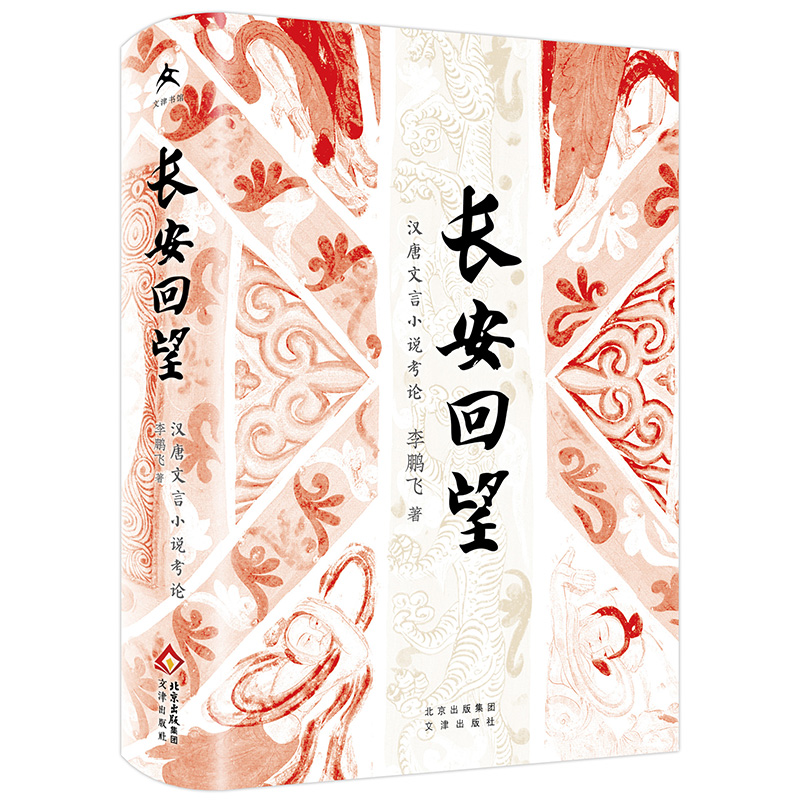
李鹏飞,1972 年生,湖南益阳人。文学博士,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员、长聘副教授。长期从事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出版《唐代非写实小说之类型研究》、《古代小说研究十大问题》(合著)、《志怪与传奇》等著作或论文集,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
唐代小说繁荣的原因新探(节选) 关于唐代小说繁荣的原因,以往学界有过一些笼统的但是很有影响力的说法,这些说法因为由一些著名学者提出,虽然年代已经很久远,但迄今仍被学界普遍接受。因此,我们有必要先对以往有关这一问题的观点予以回顾和梳理。 概而言之,以往关于唐代小说繁荣原因的讨论,有宏观与微观层面两大类。 宏观层面上主要是从唐代的阶级矛盾、阶级结构、经济背景、文化风气的变化等角度来展开讨论,这以刘开荣完成于1945年的《唐代小说研究》(1947年出版,1955年修订)为典型代表,后代的很多小说史(比如吴志达的《中国文言小说史》)都受到此书观点之影响,基本观点也大同小异。这一类讨论往往是受到当时流行的文艺思潮或社会科学理论的启发而出现的,并未从唐代史料中获得多少具体的、直接的证据,因此他们所认定的这些因素对唐代小说的影响其实都是似是而非、没有经过深入论证的,其失误也是很明显的,在此也没有必要对这些说法进行详细的分析。 微观层面上最有代表性的一些看法是由缪荃孙(1844—1919年)、郑振铎与鲁迅等人所提出。 缪荃孙的《醉醒石·序》提出“进士行卷说”(指唐代举子以小说投献名公或主司,冀其称誉,以求在科举考试中获胜),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第八篇、《且介亭杂文二集》中也提出相同的看法,后来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第二章、程千帆的《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第八节都专门阐述了进士行卷风尚促进唐传奇勃兴的观点。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中则明确指出:在大历、元和年间开始繁荣的唐代传奇文是古文运动的一支附庸,促成其生长者,古文运动“与有大力焉”。刘开荣的《唐代小说研究》第二章也持同样的看法。 缪荃孙、鲁迅、刘开荣、程千帆的看法分别来源于北宋钱易《南部新书》甲卷与南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所提到的唐人以小说行卷之风的记载。但实际上,这些说法之错误,早已有一些学者进行了有力驳斥,已经一再被证明是难以成立的,比如王运熙的《试论唐传奇与古文运动的关系》认为:唐传奇的语言、风格与文体是上承汉魏六朝志怪,同时受到同时代的民间通俗文艺(如变文、俗曲)之影响而形成的,而跟韩、柳所提倡的古文有很大不同,因此传奇文体不是受到古文运动之影响而出现的,古文运动也不是传奇兴起的动力。吴庚舜的《关于唐代传奇繁荣的原因》也驳斥郑振铎、鲁迅等人的观点,该文指出:早在唐代古文运动兴起之前,小说创作就已经蔚成风气了。虽然吴庚舜所理解的“小说”跟郑振铎、鲁迅等人所说的“传奇”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指出在“古文运动”发生之前已有很多小说出现,这一点还是符合历史事实的。吴文同样也反驳了“行卷说”之谬误:他首先指出赵彦卫《云麓漫钞》中的那一段记载本身就是不符合事实的,既不符合当时进士行卷的历史事实,也不符合唐代小说本身的实际情况(因为大多数可以考知创作时间的小说都创作于作者考上进士之后,而不是在考进士之前。他也顺带驳斥了陈寅恪对这一段材料的误解),其实这一段记载反倒足以说明当时拿小说行卷是不会获得应有的效果的(因为曾有举子拿小说行卷,但被驳回了)。在吴庚舜之后,当代著名唐代小说研究专家李剑国先生在其《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的长篇序言《唐稗思考录》中也专门深入地驳斥了“行卷说”,其看法与吴文基本一致;李剑国也反对古文运动是传奇繁荣动力的说法。吴庚舜与李剑国也反对了一些其他的意见,比如社会经济状况、诗歌发展、宗教观念对唐传奇发展的推动等等。可以说,经过很多学者的深入讨论之后,我们可以认为:“行卷说”与“古文运动说”这样一些长期被学界普遍接受的观点其实是站不住脚的,应该完全放弃,或者至少应该重新加以批判性的审视,而不要当作定论予以引用。但是,在以往关于唐代小说繁荣原因的讨论中,也有一些意见是颇具启发性的,或者是可以被我们所认同的。对这一些说法也应该加以总结,作为我们进一步深入讨论这一问题的前提与基础。 周潜发表于1936年的《论唐代传奇》一文的第二节“传奇之来源及其背景”简要概括唐代传奇兴起的背景为:“唐初承六朝之弊,士尚清谈,此其一也。其后天下承平,帝皇恣于淫乐,艳迹秘闻,民间羡称,此其二也。天宝以后,藩镇开府,奇人术士,如川归壑,各以技术干禄,于是剑侠之事,津津乐道,此其三也。小说之动机,不外乎感触,唐代思想极为自由,且贵族与平民,时有接近之机会,而宫廷间对于民众娱乐之需求,亦较前代为多,……或感于盛衰之靡常,借小说以寄其感喟;或感于阶级之殊异,借小说以发其咨嗟;或假托鬼神,寓其惩劝;或摭拾谑浪,恣其侃调。文不一体,意不一途,分道扬镳,各树一帜,此其四也。当时达官如褚遂良、牛僧孺;文人如韩愈、柳宗元;诗人如杜甫、白居易等,皆有小说之述作。是小说已为一般文学人士所垂青……传奇作品,已为一般人所乐道,此其五也。综观上述五原因,传奇之来源及其凝成之背景之梗概略真矣。”虽然这一段论述涉及的一些基本事实不免有些失误(如褚遂良、杜甫作小说之说就不知其何所据),但其第三、第四、第五等三个原因的归纳很有启发性,虽然其表述极为简略,也未作任何具体论证,但这些意见基本上都是可取的,也比较符合唐代小说史的实际情况,有的观点还被后代学者的研究所进一步证实了,比如他指出中唐时期的藩镇开府对于小说发展的影响这一点,即可谓极富见地,后来戴伟华教授的研究即证明了周潜的这一看法。 李剑国的《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之序言《唐稗思考录》也对唐代小说繁荣的原因进行了深入讨论,提出唐代小说繁荣的根本原因应当从小说本身去找,从小说的传统中去找。他认为唐代以前,小说就已经积累了丰厚的传统,而唐代文人对这一传统具备非常充分的了解与较高的认同。其次,唐人继承了六朝的“剧谈”“说话”风气,并因为唐代社会思想活跃,言论自由,更加强了这种风气,唐代很多小说便都是经由口头传播进入书面记载或文人创作而产生的。唐代实行科举,官员调动频繁,士人流动性极大,导致他们见多识广,也有利于故事的交流与搜集。此外,唐代民间俗讲、说话风气的兴起也加强了文人之间的剧谈与说话风气,并促使其质量的提高,这成为唐代小说繁荣的重要基础。而在小说创作环节上,与传奇小说的兴起发达密切相关的因素则是人情化、兴趣化、诗意化、情绪化等美学因素的出现。而在小说观念的层面,唐人尽管一方面继承了汉魏六朝的小说观念,但是同时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即从以功利为核心的观念转变为以审美为核心的观念,一些优秀的小说家已经以真正小说家的心态来进行创作了。李剑国先生的讨论虽然主要瞩目于唐代小说中符合近现代“小说”标准的那些作品,但他提出的这些原因都更为具体,更贴近小说本身,因此大都具有说服力或启发性。但是,其中也有一些说法不够深入,缺乏具体论证,尚有继续讨论之必要,比如人情化等美学因素的出现恐怕并不能说是小说兴起的原因,而只能说是小说兴起后的结果或表现。我们需要追问的恰恰是这些新的美学因素何以会在唐代发生? 周勋初的《唐代笔记小说的崛兴与传播》一文对笔记小说(主要是史料笔记以及有关的小说)这一特殊文类在唐代的兴起作出了一番很有见地的解释,他指出:唐代笔记小说的创作其实主要是从开元、天宝盛世以后才开始的(笔者案:这一说法虽然有些绝对,但大体上是可以成立的),其原因正在于大唐盛世由盛转衰这一历史转折所引发的人事沧桑之感,在在触动士人心弦,从而产生一系列稗官野史。这种围绕一个中心而出现的创作盛况,前此从未出现过。该文列举了一系列笔记小说与传奇小说,诸如《次柳氏旧闻》《明皇杂录》《开天传信记》《东城老父传》《长恨歌传》等,都跟这一段历史密切相关。周勋初的这一观察虽然主要是针对某一类特殊题材的史料笔记与小说,但这一发现其实可以进行一定范围的推广,亦即在这一类笔记小说之外,还有很多小说的出现也都与开元、天宝盛世的衰落有关。此外,大量其他题材小说的出现虽然不一定都跟这一因素直接有关,但它们主要也是出现于盛唐以后,尤其是出现于贞元、元和之世,这一点周先生没有提到,当然也未能进行任何解释,但这一问题若能得到透彻解释,或许就能说明唐代一大部分小说产生的原因了。 最后值得重点提及的则是戴伟华先生的有关研究。其《唐代幕府与文学》(现代出版社1990年版)与《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都对唐代小说的兴盛与节度使府这一机构的密切关系进行了讨论,尤其是后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更为全面深入。唐代小说的繁荣与藩镇节度使府的设置有关系,这一观点民国时期的周潜曾极其简单地提到过(主要提及侠义类小说跟使府之关系),但未作任何论证。李剑国先生也注意到唐代官员、士人的流动性大大增强与小说的兴起有关系,但也没有进行任何论证。还有更多的学者都注意到很多著名的唐人小说都是在旅途中“征奇话异”的结果,但也只涉及少数名篇,而未能说明这一结果之所以发生的原因。戴伟华先生的研究则从藩镇使府机构的设置与其用人制度入手,详细深入地说明了这一制度在“安史之乱”以后的普遍推行如何导致士人与官员的流动性大大加强,也说明了他们如何因此而被大量集中到一些藩镇使府之中去的具体过程与具体情形。正是在人员的流动中,发生了大量故事的传播、交流、搜集与写作,也正是在藩镇使府的特殊生活方式(如大量的宴饮活动)的推动下,出现了在特定时空讲故事或记录故事的风气。《唐代使府与文学研究》一书列举出十二种著名唐代小说或小说集,其产生都跟上述的因素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戴伟华先生的这些结论因为建立在实证研究的基础上,所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可以用来解释相当一部分唐代小说与小说集产生的原因。当然,我们还不能以这一结论来解释全部唐代小说出现的原因。因为唐代小说其实是一个复杂的整体,这一复杂整体中的不同部分的产生原因可能都会有所不同,我们应该分别加以考察,才更为合理。 读唐诗进入唐朝人的精神世界,读传奇小说进入唐朝人的日常生活。 撰写《冥报拾遗》这种“传鬼神明因果”的小说的郎余令,跟著名诗人王勃和卢照邻竟然都是好友;初盛唐时代有名的大手笔、诗文兼长、出将入相的张说,竟然写过《梁四公记》这样的志怪小说;而亲身经历了整个盛唐时期的牛肃,则写了一部规模颇不小的《纪闻》,其中所载的神异故事大都发生在开元、天宝时代;还有从盛唐进入中唐的戴孚,写了一部专讲怪力乱神的《广异记》…… 唐人小说留下了对自己时代最全面、最翔实,也最生动的记叙,这既是唐代小说的无穷魅力,也是我们去深入研究它们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