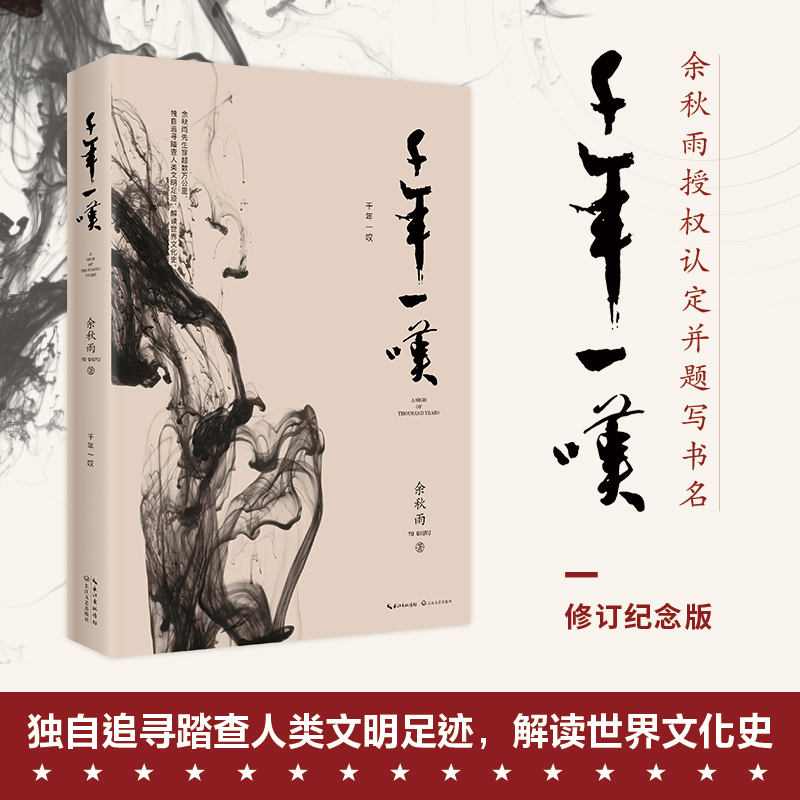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出版社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15.50
折扣购买: 千年一叹
ISBN: 97875354619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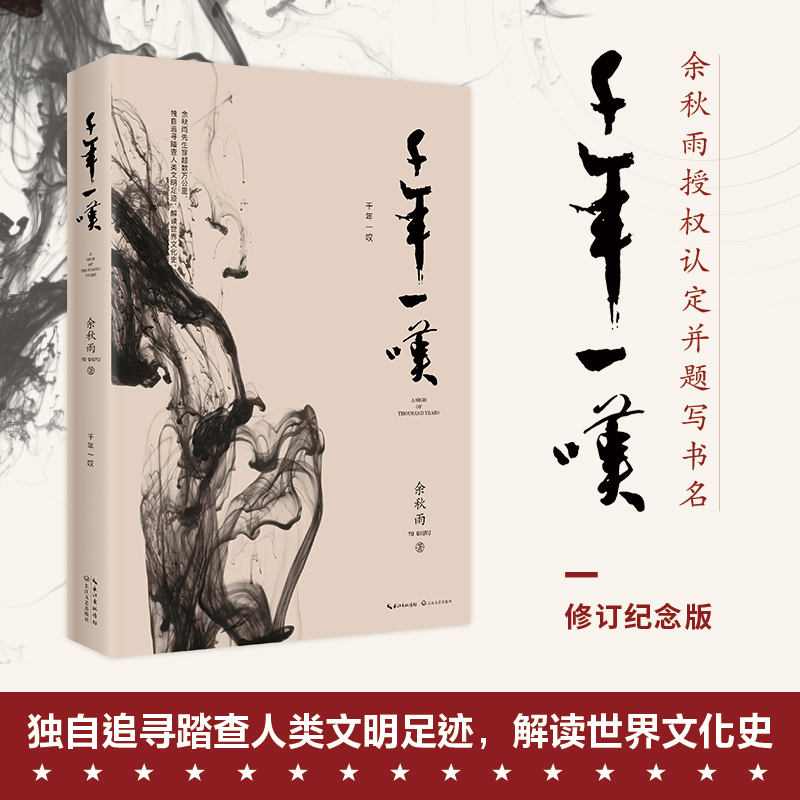
余秋雨,一九四六年八月生,浙江人。早在“文革”灾难时期,针对当时以戏剧为起点的文化极端主义专制,勇敢地建立了《世界戏剧学》的宏大构架。灾难方过,及时出版,至今三十余年仍是这一领域唯一的权威教材,获“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同时,又以文化人类学的高度完成了全新的《中国戏剧史》,以接受美学的高度完成了国内首部《观众心理学》,并创作了自成体系的《艺术创造学》,皆获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被推举为当时中国内地最年轻的高校校长,并出任上海市中文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兼艺术专业教授评审组组长。曾获“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十大高教精英”、“中国最值得尊敬的文化人物”等荣誉称号。 二十多年前毅然辞去一切行政职务和高位任命,孤身一人寻访中华文明被埋没的重要遗址。所写作品,既大力推动了文物保护,又开创了“文化大散文”的一代文体,模仿者众多。 二十世纪末,冒着生命危险贴地穿越数万公里考察了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克里特文明、希伯来文明、阿拉伯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等一系列最重要的文化遗迹。作为迄今全球唯一完成全部现场抵达的人文学者,一路上对当代世界文明做出了全新思考和紧迫提醒,在海内外引起广泛关注。 他所写的书籍,长期位居全球华文书排行榜前列。仅在台湾一地,就囊括了白金作家奖、桂冠文学家奖、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有影响力书奖等一系列重大奖项。 近十年来,他凭借着考察和研究的宏大资源,投入对中国文脉、中国美学、中国人格的系统著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大学、《中华英才》杂志等机构一再为他颁奖,表彰他“把深入研究、亲临考察、有效传播三方面合于一体”,是“文采、学问、哲思、演讲皆臻高位的当代巨匠”。 自二○○二年起,赴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大学、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联合国中国书会讲授“中华宏观文化史”、“世界坐标下的中国文化”等课题,每次都掀起极大反响。二○○八年,上海市教育委员会颁授成立“余秋雨大师工作室”。现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秋雨书院”院长、澳门科技大学人文艺术学院院长。(陈羽)
哀希腊 看到了爱琴海。浩大而不威严,温和而不柔媚,在海 边炽热的阳光下只须借得几分云霭,立即凉意爽然。有一 些简朴的房子,静静地围护着一个远古的海。 一个立着很多洁白石柱的巨大峭壁出现在海边。白色 石柱被岩石一比,被大海一衬,显得精雅轻盈,十分年轻 ,但这是公元前五世纪的遗迹。 在这些石柱开始屹立的时候,孔子、老子、释迦牟尼 几乎同时在东方思考。而这里的海边,则徘徊着埃斯库罗 斯、索福克勒斯、苏格拉底、希罗多德和柏拉图。公元前 五世纪的世界在整体上还十分荒昧,但如此耀眼的精神星 座灿烂于一时,却使后世人类几乎永远地望尘莫及。这就 是被称为“轴心时代”的神秘岁月。 现代世界上再嚣张、再霸道的那些国家,说起那个时 代,也会谦卑起来。他们会突然明白自己的辈分,自己的 幼稚。但是,其中也有不少人,越是看到长者的衰老就越 是觊觎他们的家业和财宝。因此,衰老的长者总是各自躲 在一隅,承受凄凉。 在现在世界留存的“轴心时代”遗迹中,眼前这个石 柱群,显得特别壮观和完整。这对于同样拥有过“轴心时 代”的中国人来说,一见便有一种特殊的亲切。 石柱群矗立在一个高台上,周围拦着绳子,远处有警 卫,防止人们越绳而入。我与另一位主持人许戈辉小姐在 拦绳外转着圈子抬头仰望,耳边飘来一位导游的片言只语 :“石柱上刻有很多游人的名字,包括一位著名的英国诗 人……” “拜伦!”我立即脱口而出。拜伦酷爱希腊文明,不 仅到这里游历,而且还在希腊与土耳其打仗的时候参加过 志愿队。我告诉许戈辉,拜伦在长诗《唐璜》中有一节写 一位希腊行吟诗人自弹自唱,悲叹祖国拥有如此灿烂的文 明而终于败落,十分动人。我还能记得其中一段的大致意 思: 祖国啊,此刻你在哪里?你美妙的诗情,怎么全然归 于无声?你高贵的琴弦,怎么落到了我这样平庸的流浪者 手中? 拜伦的祖国不是希腊,但他愿意把希腊看成自己的文 化祖国。因此,自己也就成了接过希腊琴弦的流浪者。 文化祖国,这个概念与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 国不同,是一个成熟的人对自己的精神故乡的主动选择。 相比之下,地域祖国、血缘祖国、政治祖国往往是一种先 天的被动接受。主动选择自己的文化祖国,选择的对象并 不多,只能集中在一些德高望重而又神秘莫测的古文明之 中。拜伦选择希腊是慎重的,我知道他经历了漫长的“认 祖仪式”,因此深信他一定会到海神殿来参拜,并留下自 己的名字。猜测引发了好奇,我和戈辉都想偷偷地越过拦 绳去寻找,一再回头,只见警卫已对我们两人虎视眈眈。 同来的伙伴们看出了我们两人的意图,不知用什么花 招引开了警卫,然后一挥手,我和戈辉就钻进去了。石柱 很多,会是哪一柱?我灵机一动,心想如果拜伦刻了名, 一定会有很多后人围着刻,因此只需找那个刻名最密的石 《千年一叹》提供给我们的是对于那些古老文明的直接肉眼观察——也许仅仅是走车观花的观察。这样的观察也许不如统计数字的客观和全面,但就其揭露一个文明,一个社会的真实状况而言,有时也可以更为入木三分。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余秋雨先生的眼光还是挺深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