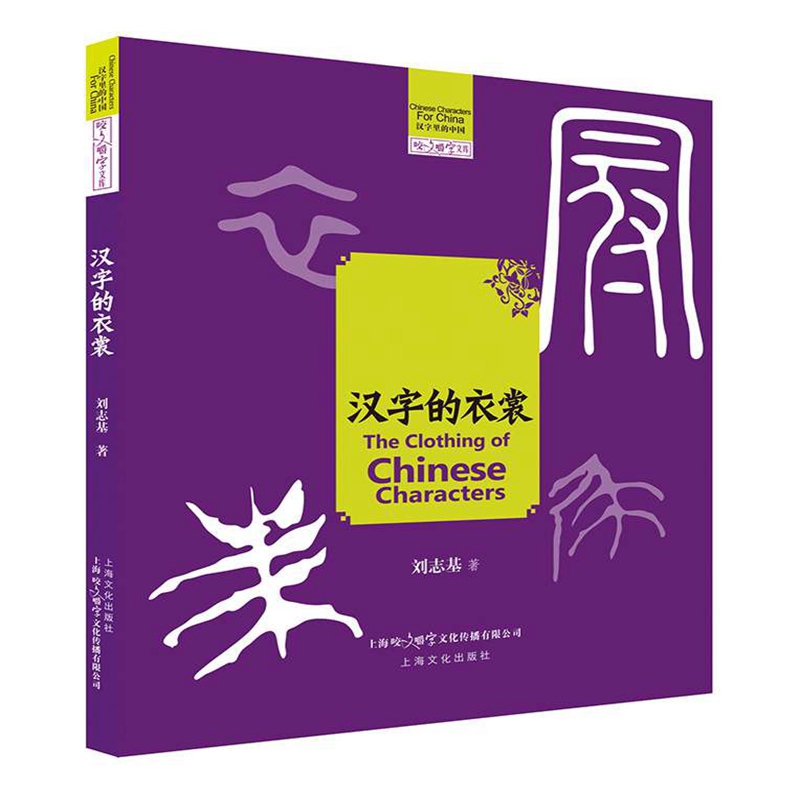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化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6.90
折扣购买: 汉字的衣裳
ISBN: 97875535311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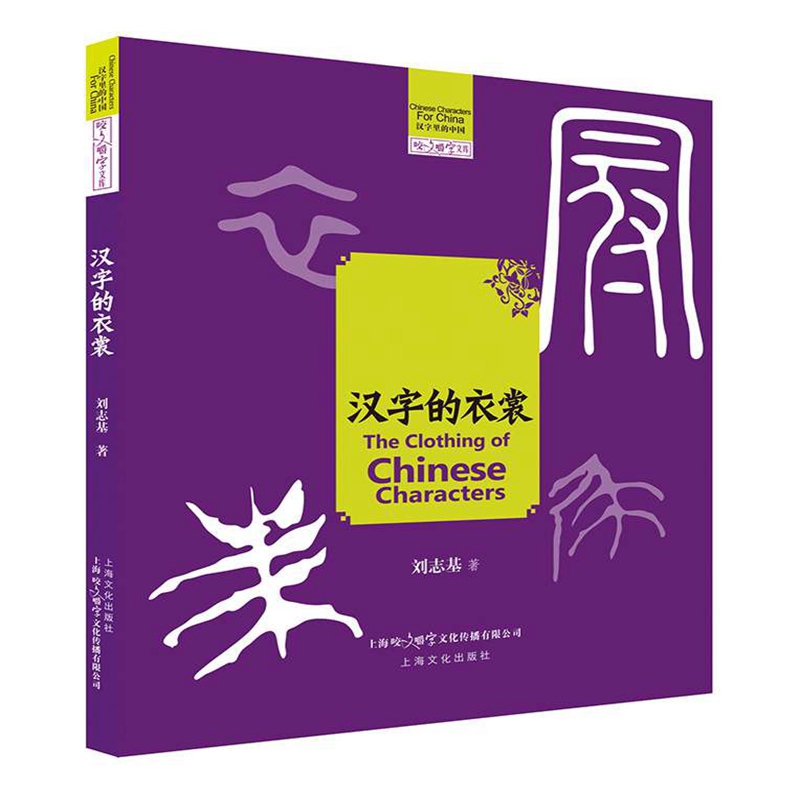
刘志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上海市高等学校教学名师,主要从事文字学理论、古文字数字化研究。
“黑衣人”的前世今生 一说到“黑衣人”,人们或许马上会联想到巴里·索南菲尔德执导的那部同名经典科幻喜剧电影。影片中的黑衣人是专门对付入侵地球外星人的特殊警察,肩负着保护人类的特殊职责。虽然影片《黑衣人》中的穿黑衣者出现在未来世界,但是我们穿越历史隧道,却可发现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国大地已经出现“黑衣人”,而他们同样担负着特殊的使命与职责。 《战国策?赵策四》记载,赵国大臣左师触龙替幼子向赵太后求侍卫一职时说:“愿令得补黑衣之数,以卫王宫,没死以闻。”其中“黑衣”,就是王宫侍卫的代名词。这种黑衣人是专门护卫国君和朝廷的,在担负特殊职责这一点上,与未来世界的“黑衣人”有类同之处。 无论是保卫地球人还是保卫王宫,“黑衣人”的基本特征就是“有用、有益”。“黑衣”包含的意义与前文所述“黔首”所用“黑巾”的意义显然并不相同。中华文化从来就是多元的。“黑”的象征意义分成两路演化,齐头并进,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 “黑”字作为颜色词在传世文献中首次出现于《尚书·禹贡》,其中提到大禹治水后,人们去兖州耕作,而那里的自然环境是“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所谓“厥土黑坟”,就是那里的土壤地高、色黑、肥沃,因此草木丰盛,即“厥草惟繇,厥木惟条”。由此可见,从土地之黑色中获得的感受,与从墨刑之黑色中获得的大相径庭。土地肥沃,对于人类生存而言无疑具有最大的“有用、有益”特征,所以用黑色来象征此类意义也是很自然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与“黑衣”一职近似,又出现了被称为“皂隶”的人群。“皂隶”指的是一种穿黑色衣服以表特定身份的人,最初是指奴隶,如《左传·襄公十四年》:“庶人工商,皂隶牧圉。”后来多指衙门中的差役。《聊斋志异·皂隶》中记载了一个诡异的故事:明朝万历年间,历城县令梦见城隍向他要人去服役,他就从自己衙门里挑选了八名差役,将他们的姓名写在文牒上到城隍庙烧了。当天晚上,这八个人就都死了。这八个可怜的差役,就是所谓“皂隶”。皂隶是封建社会的统治体系中最下层的权力执行人群。明人陈士元《俚言解》“皂隶”条记皂隶的服装是盘领的皂衫。虽然皂隶护卫的不是王宫,职责也更加繁杂,但他们也是穿黑衣的人,这种性质,从“皂隶”两字中即可窥见。 “隶”表示奴隶类的贱役,而“皂”也就是“黑”的同义词。将“皂”与“隶”相连缀,这显然是因为黑色为衙门贱役的专有服色。显然,黑色的服色意义由“黑衣”到“皂隶”,虽然传承了官府执事意义,但尊卑地位却有了变异。说来也巧,“皂”字表“黑色”的意义,也经过了一番曲折的变异。 今人看到“皂”字,一般就会想到洗涤用品之名,诸如“肥皂”“药皂”“香皂”等等。这种用法的来由还是很清楚的:“皂”可指“皂荚”,“皂荚”是一种落叶乔木,它结的果实即荚果,富于胰皂质,可以去污垢,所以古人用它来洗涤物品。现代的制皂,虽然未必再用皂荚,但是制成品也称之为“皂”却是很自然的。 “皂”还有一种意义,指“皂斗”,即壳斗科植物栎树(又名橡树)的果实。皂斗因其富含鞣质,可以制成深浅不一的黑色染液。于是,“皂”又有了“黑色”的意义,这也正是“青红皂白”之“皂”的意义。关于这一点,《说文解字》徐铉校定本说得很清楚:“草:草斗,栎实也。一曰象斗子。”“臣铉等曰:今俗以此为艸(草)木之艸(草),别作皁字,为黑色之皁。案:栎实可以染帛为黑色,故曰草。通用为草栈字。今俗书皁,或从白从十,或从白从七,皆无意义,无以下笔。” 其实,“皂”的前身是“草”字,它最早出现在石鼓文中,用“茻”“早”两个偏旁组成,前者是“草莽”的“莽”的本字,用以表义,后者则表音。秦简文字和小篆将“茻”简化为“艸”。 “草”为何被《说文解字》释为“草斗,栎实也”?这当然可以用“借用”(《古文字谱系疏证》第653页)即通假来解释。但是,梳理相关文字演变实际状况,似乎还有更复杂的原因。 “草”中表音的“早”从“日”从“甲”(古文字“甲”写作“十”),甲是天干第一位,因此“早”是个表示日始出的会意字。然而,该字却是被更早用来表示“皂”的。就出土文献来说,有学者认为,在睡虎地秦简(《秦律五·杂抄三十》)中,“早”的意义正是用为“皂”的(《古文字谱系疏证》第644页)。就传世文献而论,《周礼·大司徒》“其植物宜早物”的“早”也是表示“草斗”的(强运开《石鼓释文》)。据此可以认为,先有“早”字因通假而有了“草斗”义,而“草斗”是植物,所以加注“艸”旁也可视为营造后起本字的行为。当然,这种演变,客观上造成“草”既表“草木”又表“草斗”的兼职现象,为免除文字交际中的误会,用“从白从十”的“皁”或“从白从七”的“皂”去分担“草斗”义是汉字记录汉语精密化的必然趋势所致。值得注意的是,“皁”或“皂”的表义偏旁为“白”,“白”是“黑”的反义词,而白物正是染黑的对象。在汉字偏旁对字义的表达方式中,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如“日”作义符可以构成“暗”“昧”等。因此,“皁”或“皂”两字的结构,也并非如徐铉所说“皆无意义”。 在“皂”字来龙去脉的梳理中,其“黑色”之义的来由也得以说明了。但是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浮出水面:“黑色”本有“黑”字来表达,那么,根据语言文字的经济性和区别性原则,“皂”是没有必要出现的。所以,我们不禁要问:“既生黑,何生皂?” 要解答这个问题,可以审视一下由表“黑色”的“皂”所组成的词:“皂衣”,指的是黑衣,秦汉时官员所穿,后降为下级官吏的服装;“皂服”,旧时小吏所着的黑衣服,亦借指小吏;“皂裘”,黑色的皮衣;“皂巾”,古代受墨刑者所戴的黑色头巾;“皂带”,黑色的衣带;“皂领”,黑色的衣领;“皂履”,黑色的鞋子……以上释义,皆出于《汉语大词典》,应该可信。由此可知,“皂”所表示的是专表服装颜色的“黑”,而不是一般意义的“黑”。因此,这种“黑色”,用一个本表黑色衣服染料“草斗”的“皂”来表示再合适也不过了。更需要注意的是,从汉字发展史的视角来看,用“皂”表服装颜色的“黑”并非是一个孤立现象。 早期汉字(殷商甲骨文、西周金文)中很少有表颜色的字。但在战国时代的出土文献里,“红”“绿”“紫”“绯”“缟”等从“糸”旁的颜色字纷纷出现,到《说文解字》中,这种“糸(纟)”旁的颜色字多达几十个。这种文字现象,需要从文化的层面加以解读。 人类学家曾对人类颜色概念的产生做过相当深入的调查,结果他们发现:“色调的数量随着文化的复杂程度增加而增多……越复杂的社会所需要的颜色词可能越多,这是因为他们拥有更多的可以由颜色区别开来的装饰品,或者是因为他们有更为复杂的制备各种染料和涂料的技术。”(见《文化的变异》,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32页)。由此我们再来思考“糸”旁颜色字在战国秦汉间大量涌现的问题,或不难领悟其中缘由:“糸”就是丝,乃是服装原料,用它来作为众多颜色字的表义偏旁,表明人们对服装染色具有很高的关注程度。显然,用“糸”旁颜色字涌现的因由来解释“皂”表黑色服色文字现象的发生也是合适的,差别仅仅在于:“糸”旁字表颜色,表义的焦点在被染色的对象;“皂”表黑色,表义的焦点在于“草斗”,也就是服装的黑色染料。 那么,服装的颜色染成皂色为什么会得到充分的重视,进而导致“皂”发生了上述那些颇不寻常的字词现象呢?这又与古代社会把服装颜色与人身份地位相联系的服色制度不无关系。由“黄袍加身”一语,可知黄色是帝王之服色;由“朱紫尽公侯”的诗句,可知朱和紫是古代高官的服色;由“戴绿帽子”一语,可知绿头巾原来是古代娼妓家人的帽子。而“皂”作为服色,也有类似意义,这种意义正体现于“皂隶”一词。 由此可知,“皂”之“黑”,与“黑墨”“黑煤”“黑天”“黑云”的“黑”是有所不同的,这也是它在汉字字符集里存在的理由。而我们也可以对“青红皂白”一语的奥妙有着更深切的领悟:也许正是因为“皂”的“底细”更加复杂,比喻“底细”的这个词语才没有说成“青红黑白”,而是用“皂”来替代“黑”。 “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其中“衣”排首位。《汉字的衣裳》,说的就是蕴藏在汉字本体之中的穿衣打扮之事,包括整衣、穿衣方式、衣料、头衣、足衣及衣上之饰、服装颜色等。“衣”字从何而来?“垂衣裳”如何“天下治”?“袜”的原初模样是怎样的?围裙是如何咸鱼翻身的?何为“红得发紫”?……这些问题都可以在这本书中获得答案。文字本身就能讲故事,这正是我们使用的表意汉字不同于表音文字的最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