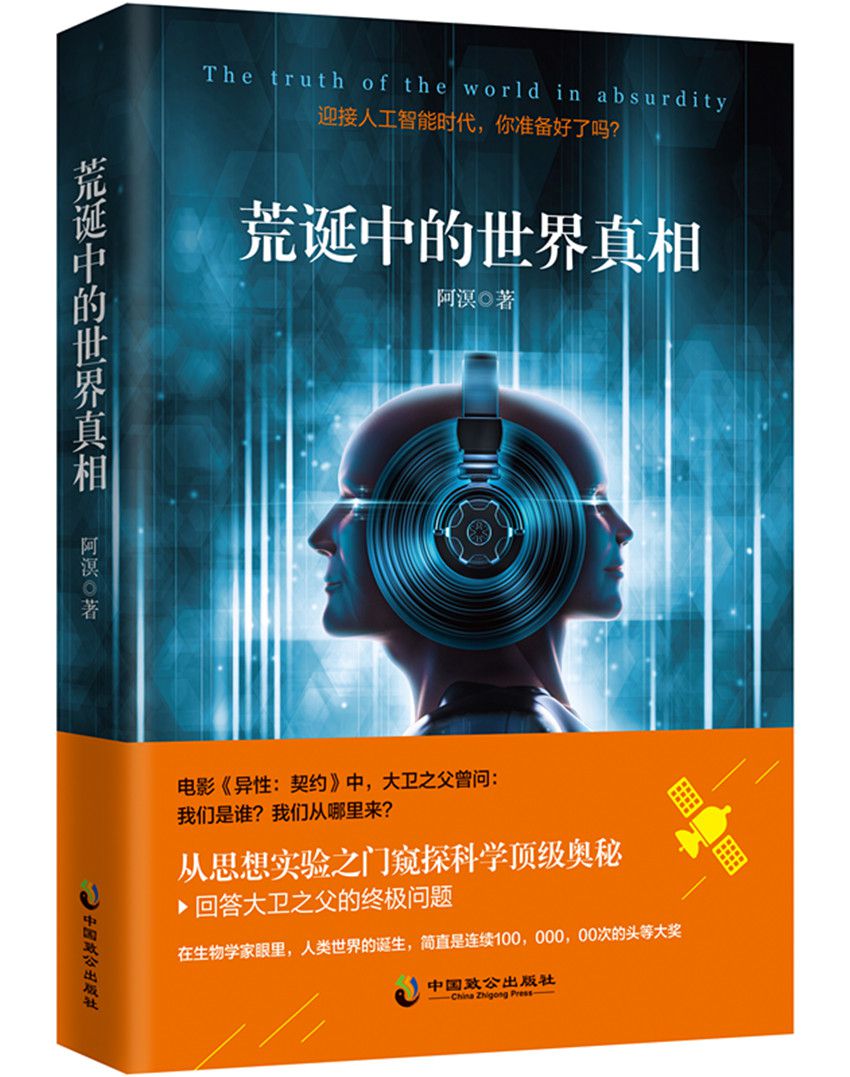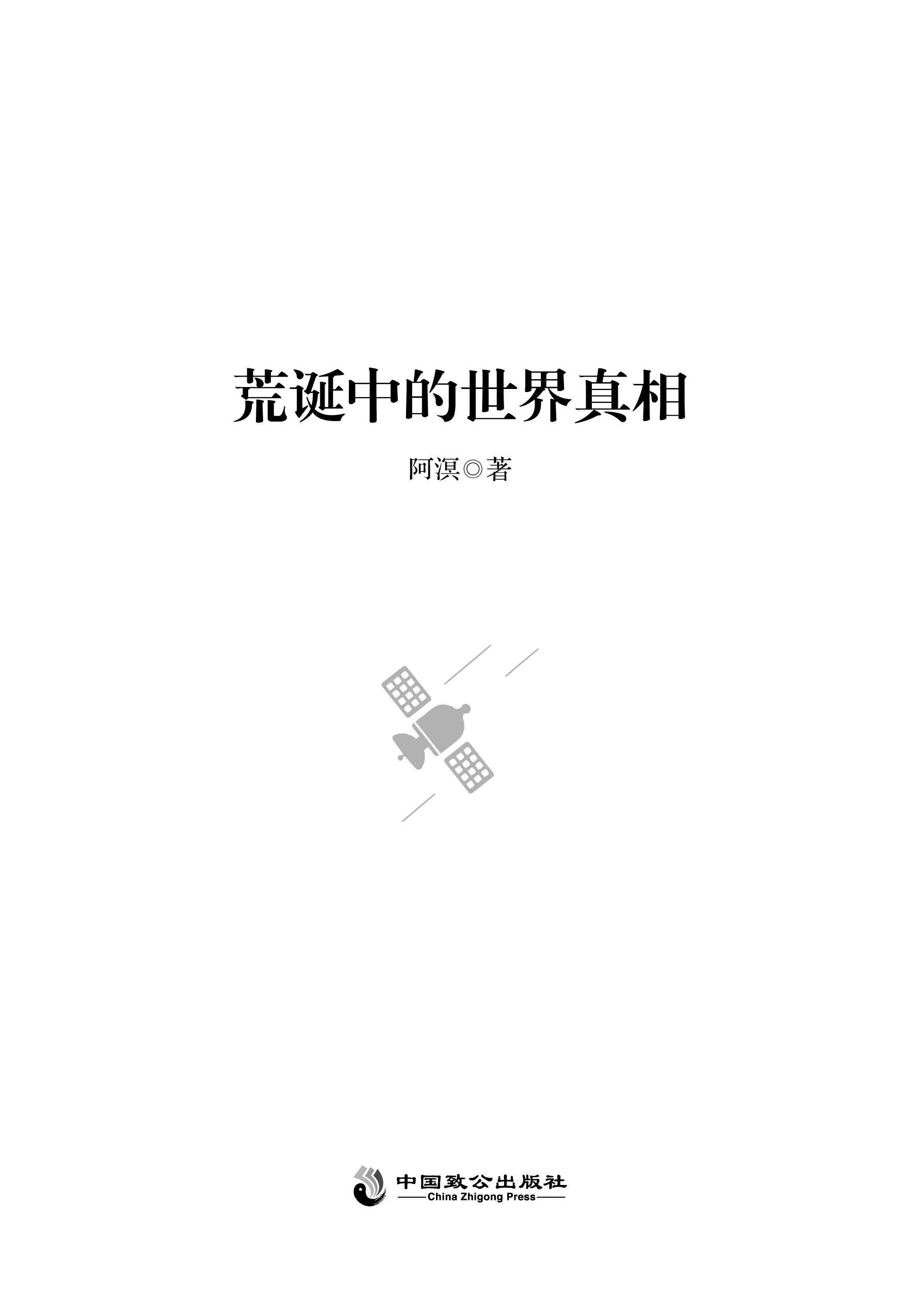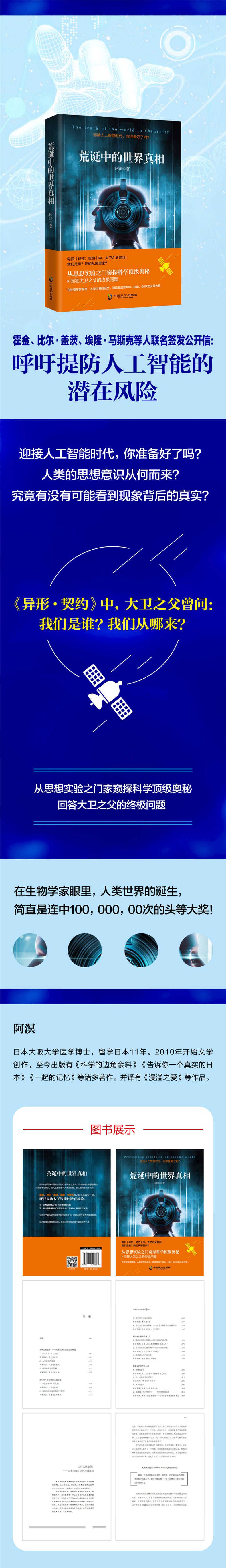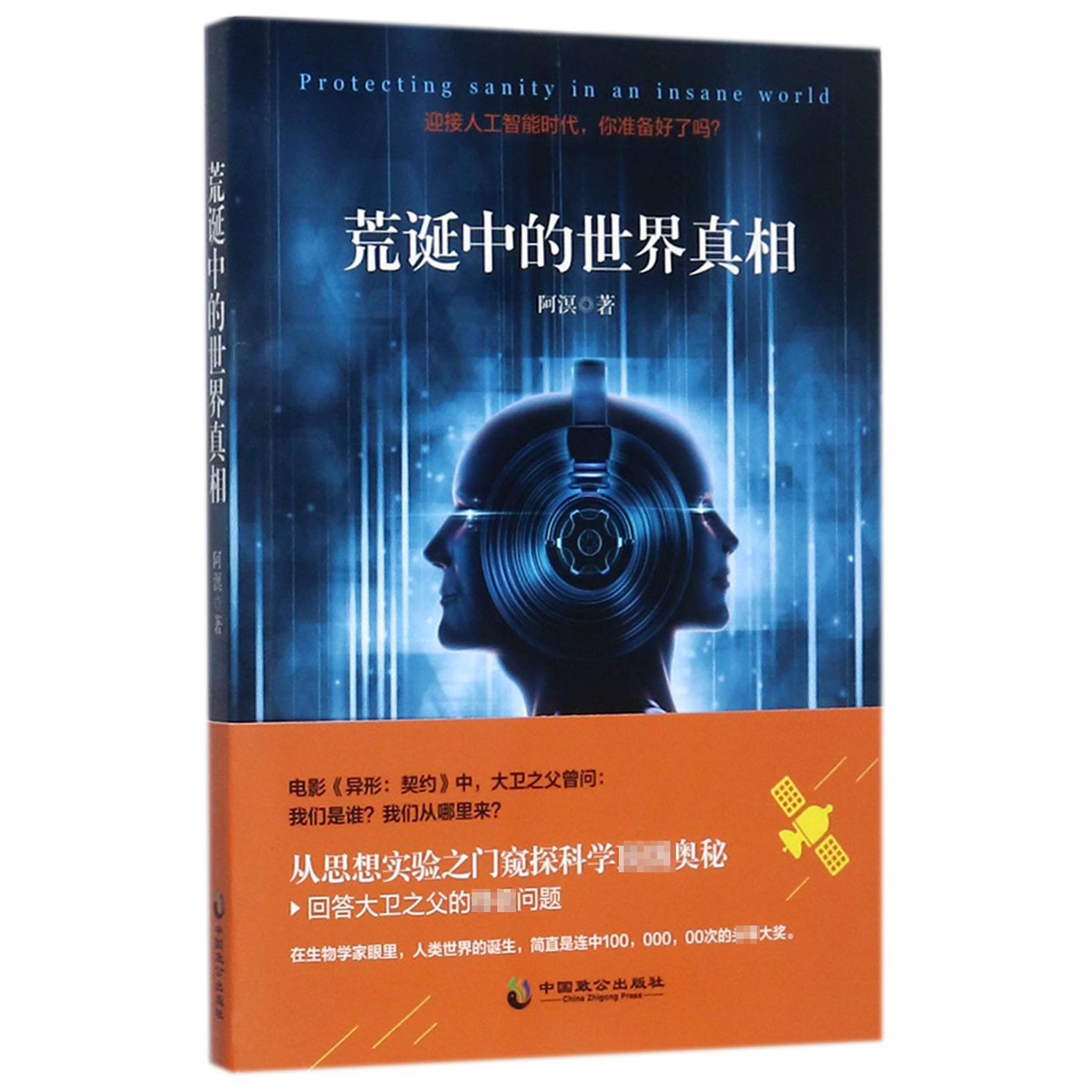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致公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0.80
折扣购买: 荒诞中的世界真相
ISBN: 97875145106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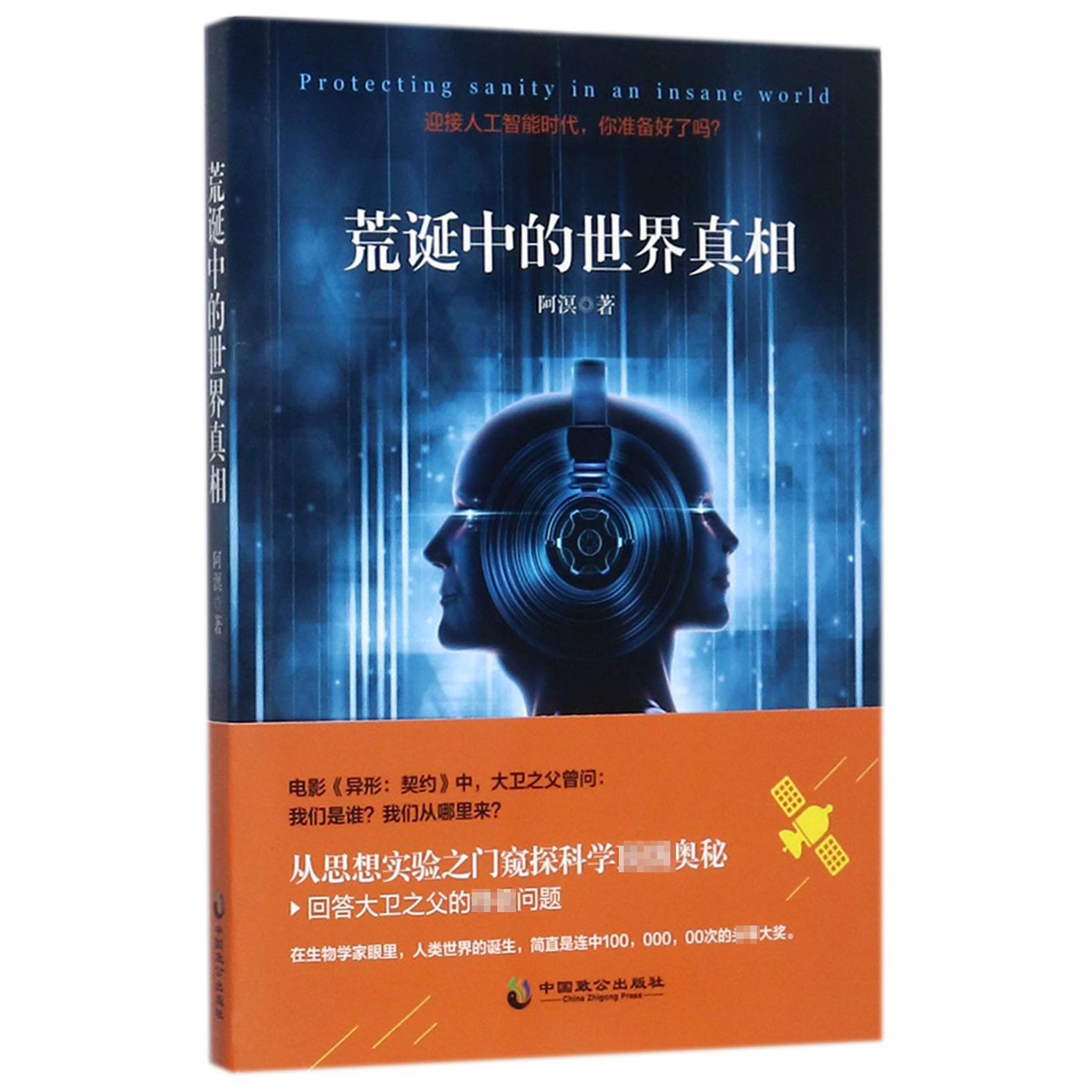
*本大阪大学医学博士,留学*本11年,2010年开始文学创作,至今出版有《科学的边角余料》、《告诉你一个真实的*本》、《一起的记忆》等诸多著作,并译有《漫溢之爱》等作品。
试读 为什么我是我? ——关于自我认定的**难题 *简单的问题通常都是这个世界*难以回答的**难题。比如何为生,何为死,世界的边界又在哪里?又比如人为什么是人,我又为什么注定是我?关于自我的认知,是形而上学*核心的拷问。和猫狗不同,灵长类是**可以对自我产生存在意识的动物种群,虽深刻却又不足以让人类能够对镜中映射出的那个自我进行一个清楚而**的判断。如何定义自我,决定了我们将如何理解这个世界。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尽管人类的发展走了这么远,却可能还没有跨出真正意义上的**步。 1、什么决定“我之为我” 近代科学的兴起,曾经一度成为人们期待了解自我认知**秘密 的**。灵魂存不存在,内心和自我意识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不仅 是人类生命中*为神秘的一环,也是科学可以借此一举*破千百年来 由神学构建的世界终结命题。然而,尽管解剖学、微观生物学将人体 组成的探究发挥到了**。可人们*终发现,就算把人类研究到分子 级别的大小,也仍然没有找到什么是决定了“我之所以是我”的** 答案。相反,当科学将人类的组织结构研究通透之后,面对复杂的人 类组成部分,却对“*终将复杂的人体组织调动起来,形成一个完整 人格的核心部分究竟是什么的”问题变得*加无从下手。 科学的视角下,灵魂是不存在的。一切人类的活动、思想、情 绪、感*,都不过是冰冷的生物化学反应和生物物理学规则的综合结 果。将人类的身体组合起来,那就是一个人,拆分后,不过是毫无生 机的有机物。但这样的结论并不能使人信服,这超出了人类理解自身 的思想维度。我们即使可以接*关于计算整个宇宙的复杂公式,也无 法接*自身的丰富感*力和思想都来自那些由于不同目的而组合起来 的化学分泌物和细胞活动。而*耐人寻味的问题则是,科学的结论如 果成立,将留下另一个问题,如果将组成人体的器官或组织取出任意一部分,显然都无法代表这个人;而如果仅仅将拆分的人体组织器官 堆放在一起,就真的可以说这就是那个人了吗?如果不算,一个人的 人格和身体之间究竟还有什么是不曾被科学纳入视角的呢?科学让我 们对于自我的定义变得*加扑朔迷离。 在古老的时代里,尽管近代科学还没有兴起,还是有一些哲 学家设置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这就是**的思想实验——特修斯之船。 特修斯之船(Ship of Theseus)这是*为古老的思想实验之一,*早出自普鲁塔克的记 载。它描述的是一艘在海上航行了几百年的船,中间经历过无 数次的维修和替换部件。木板一*烂,就会被替换掉,以此类 推,*后所有的部件都不是*开始的那些了。那么,*后这艘 船是原来的那艘特修斯之船,还是一艘**不同的船?如果不 是原来的船,那么在什么时候它不再是原来的船了? 这个古老的思想实验诞生之时,还没有诞生近代科学。思想实验 中的“船体”不存在灵魂,因而在描述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的 参照物上并不会产生*进一步复杂的问题。但当近代科学对人体进行了充分的研究之后,人类自身同样面对这样一个问题,究竟什么代表了我?随着科学的进步,特别是细胞工学突飞猛进的发展,利用每个人自身的细胞生产出**不发生任何免疫反应的器官和组织只是时间问题。尽管未必有人会*换全部器官和组织,但特修斯之船中所描述的那种情况,是可以切实发生的。一个崭新的我还是不是原本的那个我,将是未来人类需要直面的真实问题。 其实,不需要细胞工学的新进展,一个正常健康的人体本身,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新陈代谢,人体的所有细胞*新一遍大概只需要 6-7 年。也就是说,现在的你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在过去 6-7 年中被逐批*换为了*新的一代。人体本身就是一艘特修斯之船。只是,这个*新换代缓慢大部分时候我们无法意识到这个问题。特修斯之船的问题一直不曾远去。 哲学家大卫·刘易斯(D**id Lewis)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解开这个**难题的思路。他是从形而上学的统一性上出发,认为任何事物都需要从四维的元素来认定,除了形态、质量、决定一个事物的还有它所在的时间和空间。一个连续性的事物本身在时间和空间上有着前后因果的影响力。正如,一个***换了零件的特修斯之船尽管从本质上和原本的船**不同,但显然在时间轴线上前后互为因果,没有原本的船体,也谈不上出现新的船体。尽管*换零件可以让它面目全非,至少旧有的一切都随着*换而荡然无存。但在四维的角度来看,新的部件建立于旧的本体,即便*终**取代旧有本体,它们依然是同一艘船。 其实刘易斯的理论如果从反面观之,倘若我们不从四维的角度来认定统一性,那么,不仅仅只是*换器官的人体,连流淌的河流、四 季变化的山峰都存在统一性的问题。因为它们的内部构成都不是恒久 不变,但显然我们不能说因为河水的变化,山峰中*木的*替,河便 不是原本的那条河,山也不是原本的那座山了。这个世界所有的存在 便都成了可疑的不确定。 这也是为什么,哪怕当一个人苍老或者*换了身体器官,他依然 可以认为自己还是曾经的那个自己,是因为他和之前任何一个时刻的 自己在这样的一个时空中始终保持着因果联系的连续性。除非这种连 续性被打破,那么,这种因果关系就是存在不变的明证。 当然,四维角度的说法也并不**,因为虽然特修斯之船中所 描述的情形,可以通过因果联系的连续性来找到前后者之间的关联, 但事实上,这种说法只能帮助我们解决一部分的特修斯之船的“困境”。 试想,假设当一座沙丘改变了形状,或增减了重量,我们可以根据刘易斯的理论来证明它还是原先的沙丘。但如果我们将这个沙丘一分为二呢?或者取出其中的一把沙子,我们可以说这一把沙子也是那座沙丘吗?那剩余的沙丘呢? 这就是哲学家托马斯·霍布斯后来对特修斯之船的延伸。他假设如果用特修斯之船上取下来的老部件来重新建造一艘新的船,那么两艘船中哪艘才是真正的特修斯之船?的确,当特修斯之船不断*换零件,刘易斯的解释可以通过前后的因果关系来证明特修斯之船没有改变,但用*换掉的零件去组装另一艘新船,*终我们将得到两艘符合大卫·刘易斯理论的特修斯之船,而且两艘都是同样的,没有办法证明其中哪一艘才是原来的那艘。因为毫无疑问,两艘船都和*初的那艘特修斯之船有着时间和空间的因果关系。尽管大卫的解释并不能**解决特修斯之船的困境,但至少,他给我们一个方法,让我们可以去理解我们自我存在的证明,并不仅仅依赖于肉体的感知。它可能*接近那个浪漫的说法,我们都曾 经存在于某个时代里。 其实,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特修斯之船”的诡异现象都不曾降临于人类自身。尽管这个思想实验的内容令人困惑不解,但先人们显然不曾设想过自己的身体便是一艘不断航行和*换零部件的“特修斯之船”。因为,在近代科学兴起之前,人类不仅对自己的身体没有一个直观的认知,对他人的认知也始终依赖于模糊而笼统的感*系统。当我们认为自己认识一个人的时候,我们的脑海中所依赖的“数据”通常只是他的外部形象和交际风格。这既缺乏明确的判断依据,也没有具体的数据分析。一切都只是一种印象。 尽管如此,这样的人格认定,在近代文明前的漫长岁月里仍旧不 存在任何问题。虽然笼统的印象不可能全面地定义一个人的真实情 况,但作为观察者,这种印象稳定而富有个人意识色彩,反而相当牢 固。而另一方面,人类的人格和形象毕竟不是轻易改变的事物,或有 偏差和改变,但因为是基于模糊的判断准则,被观察者恰到好处地忽 略不计了。除非是精神失常或人格分裂,人们才会承认其人格的剧烈 变化,但仍然不会联系到可怕的“特修斯之船”,因为肉体仍旧维持着 相对的形象。并不会有人认为一个人“疯了”之后便不是这个人了。 而近代文明兴起之后,这一切都改变了。如前文所述,人类对自己的身体有了充分的了解,并且逐渐具有“*改”自己身体的能力。 肉体不变的稳定性被打破了。而同时,网络的兴起带来的虚拟化的人 格,使得人格的稳定性也变得面目全非。尽管不是常常可以看到,但 如今想要让自己脱胎换骨成为另一个人,不再是无法做到的想象。 和精神失常不同的是,虚拟形象的出现并非一种人格或外在形象的改变,它*像是自成体系的人格或外在形象的新生。每一个通过社 交软件进行交际的人们,都在注册账户的那一刻重新解构了自己的形 象和人格。在心理学的理论中,每个人都有多人格的倾向,人们借助 网络将这样的潜在心理发挥到了**。尽管这并不能称之为病态,但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多重的人格身份势必会互相影响。这种影响 可能只是对思想和语言上的切换造成轻微混乱,也可能只是使人们 *加封闭自我,逃避社交,但*终每一个个体的轻微变化,就左右 了整个人类社会形态的人们在网络上扮演**不同的自己毫无心理障碍,因为这一切前 提是虚拟的。人们的潜意识中,虚拟等同于虚构,每个人都有重新创 作自己的心理冲动。这一方面其实是借由虚拟世界完成自己对现实生 活的修正,而另一方面也是逃避现实角色的**手段。所以,尽管虚 拟形象的产生在网络兴起的*初曾经短暂地引起过人们的担忧,但它 带来的心理快感很快就让人们忽略了这微不足道的担忧,从而很快便 适应了这种新生事物。 然而尽管每个人都看出了网络兴起的前途无量,但网络的发展仍 超乎人们的想象。二十年的时间里,网络几乎建立了一个完整的虚拟 世界。这也不再是一种精英文化或者少数年轻人的时尚,它已经逐渐 成为全民参与的又一项生活必需。人们利用网络的时候,早已不只是 取一个充满了后现代风格的网名来掩盖真实自己这么简单了。形象、 性别、行为、喜好,几乎一切东西都可以通过网络来呈现,同时也通 过网络来重新塑造。老一辈的人对网络社交的普遍印象是不可信,而年轻一代人对网络社交则**不存在信任上的疑惑。这是因为对于大 部分人生阶段仍旧停留在传统人格认定方式的上一辈人来说,形象和 人格通常都是高度稳定的,不稳定的人格背后通常有着不可告人的隐 患。而对于成长于网络兴起的一代人来说,虚拟的形象和真实形象之 间的距离差与其说不值得困惑,毋宁说是一个理所应当的现象。 几乎不需要分析就可以知道,等到上一代人全部死去,这个世界 甚至不会再有对虚拟形象的不对等人格产生疑问的声音。虚拟世界将 以一种正当而合理的姿态与真实的世界并行不悖。这相当于每一个人都有至少两个以上的不同人格,尽管并不是存在于同一个空间,但却可以轻易地产生一个身体拥有两个**不同形象和人格角色的状态。 一个存在了几千年的人类自我认定机制土崩瓦解了。肉体和人格都不再是一成不变,尽管大多数时候我们仍然不会注意到这个问题,但实际上每个人都成了一艘航行的“特修斯之船”,在形而上的哲学层面,每个人都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认定自己仍旧是昨天的自己。哲学家大卫·刘易斯(D**id Lewis)的诠释理论,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现代人类遭遇的肉体“特修斯之船”的尴尬境地,但却对 虚拟形象造成的多重人格毫无作用。因为我们看不到虚拟人格和现 实人格之间的联系。它们之间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也几乎可以做 到**不发生交集。人们在两种人格和形象之间来回切换,并不会 去思考“当两种人格和形象的比重接近等同的时候,究竟哪个才能 代表自己”这样的哲学问题。如果用思想实验的语境来描述这种情 形的话,那可能是:“一艘不断航行的特修斯之船遇到了另一艘完 全不同的也被命名为特修斯之船的轮船,两艘船均有证据证明自己 才是特修斯之船,却并没有办法来判断谁才是真的那艘。” 尽管在哲学意义上,这听起来令人十分担忧,但在现实意义 上,“双重人格”并没有给这个时代的人们带来太多困扰。人们有足够的判断能力可以区分现实与虚拟之间的差别,当事人切换自己的角色也毫不费力。但,这并非说在现实中不会存在任何问题,当一个人从虚拟角色认识另一个人的时候,虚拟的形象和人格就会成为认知这个人的**标准。古老的认知规则依然是人们交际时认知另一个人的**手段。倘若*终交际延续到了现实层面,“双重人 格”的落差,*终只能迫使我们回头来质问“特修斯之船”里的那 个问题——“哪个才是真正的你?” 另一方面,网络毕竟还太过年轻。在不到二十年的时间里,尽管它的发展迅猛,但是至今依旧没有**脱离娱乐和工具的角色。 人们对待娱乐总是漫不经心的,这使得“网络究竟以怎样的姿态悄 然改变着我们”这一重要课题迟迟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每个人都 还天真地认为网络无非是一种接近于消遣的活动,仿佛每个人只要 愿意就可以随时抽身远离。但事实上,**的人们已离不开网络了。 网络已经悄然进驻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并且当网络继续存在并 扩张下去,将会*大程度上统领我们的生活,而毫无疑问也将继续 伴随我们的余生,这个虚构的世界真的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了。尽管 网络文化的发展使得网络给人的感*和*初生硬的虚拟角色所不 同,但它仍然改变不了让我们多人格化的本质。 这样的现实导致,一方面我们越来越依赖网络,我们在网络上的形象和现实中的形象尽管不同,却彼此都能繁茂地生长,这使得两种形象都变得不可或缺;但另一方面网络却依然保持着高速流动和不确定性,我们在网络上的形象可以轻易地遭到摧毁,这些由数据和程序构成的虚拟世界中的“我们”,可以在脆弱的密码盗窃中轻松地转换成他人的“角色”。又或者我们可以亲手将自己建立起的一切虚拟形象瞬间毁灭,推倒重来。这种不稳定性颠覆了人类社会长久以来对于人格认定的思维定式。在荒诞和无序的氛围下,让网络中的你我既难形成长效稳定的情感交流也缺少维护个人形象的行为约束力。毕竟,我们还有一个现实世界可以逃回。 网络带来的多重人格*终会给人类社会带来怎样的意义,现在还有些扑朔迷离,但如果论及其本身所存在的哲学意义的话,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内心深处那个渴望释放出来的真正自我。 它会颠覆你过往的认知,重塑你对物理学以及世界的看法。通俗而深刻的论述了时下热点人工智能以及相对论所引申出的各种问题。 语言新奇有趣,一改过往物理学给人们留下的深奥死板的印象,让读者在愉悦的阅读体验中感*到物理学的神秘与奇妙。 通过本书可以了解到时下*经典的思想实验,让读者*有参与感,对时下的哲学以及物理实验有*清晰的认知。 或许物理学对于普通人的而生活,并无太多的必要性,但是我们随着人类的发展走到**,我们是否应该站在*高处看一眼我们这个熟悉而陌生的世界呢?一如作者阿溟所言,“作为一个普通人,了解这些涉及宏大主题的思想实验可能并不会对我们的生活带来太多改变,但是,每个人的生命里都应该有那么一个时刻,超脱于自己,站在人类全体的高度上,去思考一下关于这个 世界的**答案。我想,不管会不会有结果,那一刻,就是我们生命中*富有神性诗意的瞬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