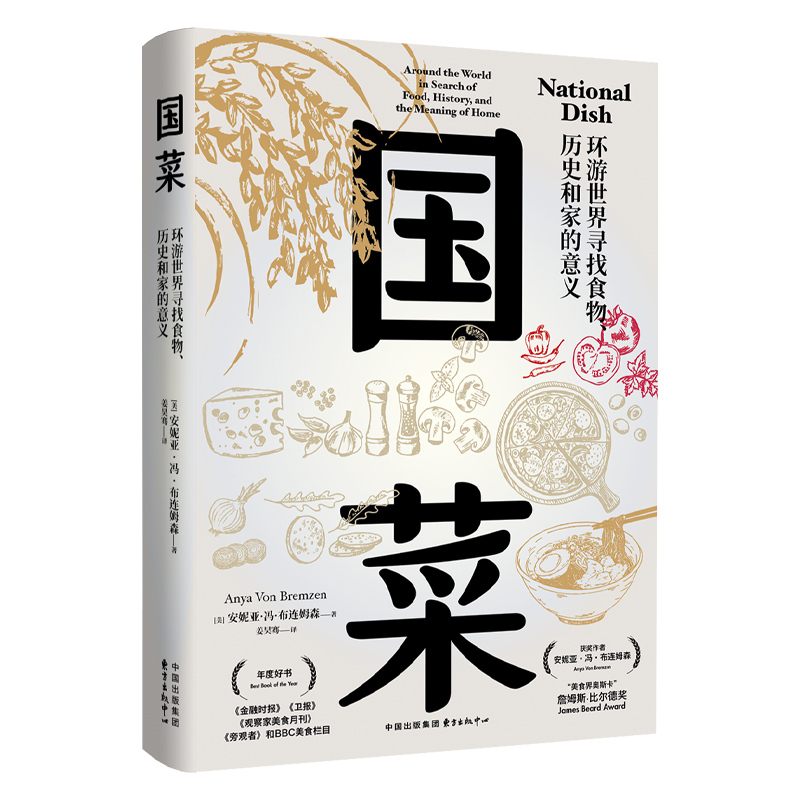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53.10
折扣购买: 国菜:环游世界寻找食物、历史和家的意义
ISBN: 97875473256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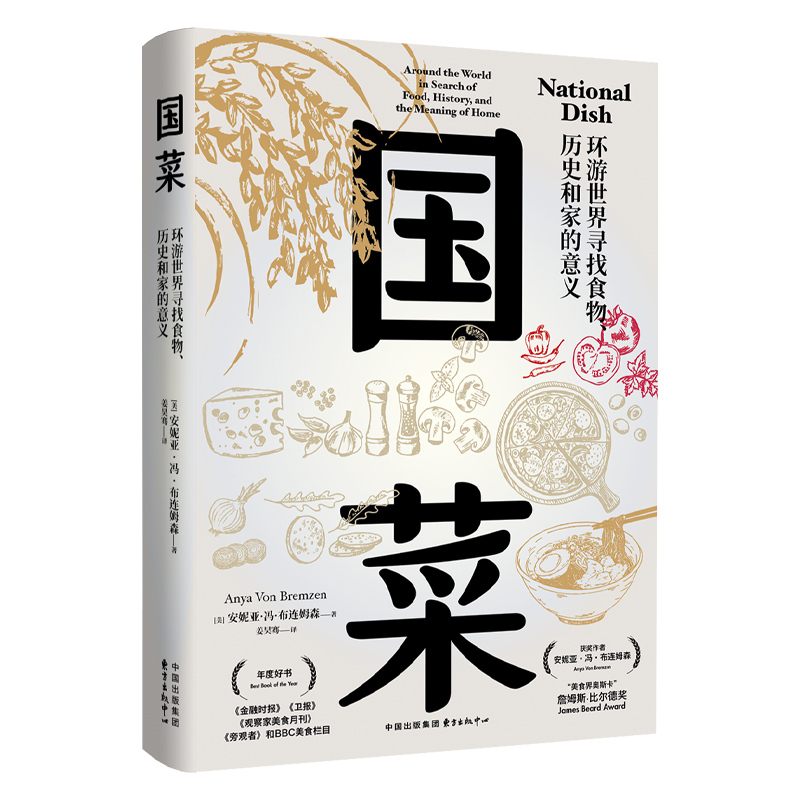
安妮亚·冯·布连姆森(Anya Von Bremzen),美食作家,三度荣获“詹姆斯?比尔德奖”(James Beard Award)。在莫斯科长大,自茱莉亚音乐学院取得硕士学位。《漫旅》杂志特约编辑。著有五部备受好评的食谱,包括《新西班牙餐桌》《最佳料理:环游世界八十道食谱》《请上桌:俄罗斯烹饪书》等。她是《食物与酒》和《美味》杂志的专栏作家,也为《纽约客》《出发》《洛杉矶时报》撰写文章。她在杂志上发表的作品曾多次获选收入“年度饮食文集”。
火锅是我心目中的标志性法餐,我来巴黎就是要钻研它。记载这道菜的菜谱作者是一名影响深远的19世纪大厨,他的非凡经历足可以写成一部传奇小说。罗伯斯庇尔恐怖统治期间,玛丽—安托万 · 卡雷姆(Marie-Antoine Carême)被贫穷的父亲丢弃在巴黎街头。要不是他已经真实存在了,法国文豪也肯定会把他编出来—是巴尔扎克呢,还是大仲马?两人都是美食家。自学成才,魅力非凡的卡雷姆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头戴厨师帽的国际名厨(事实上,白色厨师帽就是他发明的)。他不仅是法国大菜中糖丝造型的宗师,还确立了四大母酱,从中演变出了对法国人的自我定义无比重要的无数“子酱”。他是皇室大筵与那个时代的G7宴会的主理人,将法餐至高无上的地位传遍了世界。或者用现代一点的话讲,卡雷姆代表法国品牌主持美食外交(gastrodiplomacy,表示食物蕴含的政治软实力的新潮词)。 卡雷姆的沙文主义著作影响力甚至还要更大。他在1833年的巨著《19世纪法国烹饪艺术》(L’Art de la Cuisine Fran.aise au Dix-Neuvième Siècle)中高唱:“法国啊,我美丽的祖国,唯有你的胸膛中融汇了美食的喜悦。” 那么,今天要如何创造国菜和餐饮文化呢?我将会发现,尽管答案很少一目了然,但经典菜谱永远是好的起点。法国史名家普丽西拉 · 弗格森(Priscilla Ferguson)认为,卡雷姆的著作通过美食和食物用语将“法国”统合了起来。当时,法国出版物已经开始向心情急切、范围更广的资产阶级公众介绍旧制度下的贵族美食了。弗格森写道:“在合众为一的国族建构大业中,卡雷姆的法餐成了一种关键建材。” 卡雷姆对公众表示:“我的书不是写给豪门巨室的。我的希望是……在我们美丽的法国,每一个公民都能享用精美的餐点。” 卡雷姆巨著的开篇美馔就是pot-au-feu,意思是“火上的锅”,或者就叫“火锅”。肉汁、牛肉、蔬菜融于一锅,汤与主菜合一,一碗火锅便是卡雷姆亲封的“纯正国菜”,是平等与博爱的象征。 火锅承载着厚重的法国文化。伏尔泰将它与礼仪联系在一起;巴尔扎克亲切地谈起它带给市民的抚慰,甚至出言不逊的煽动家米歇尔 · 维勒贝克(Michel Houellebecq)也有同感;学者们则将它评为“家庭聚会的神奇核心”。我本人对它的液体成分特别着迷,也就是高汤(bouillon/broth)—那是所有法餐酱汁与汤品的芳香基底。 卡雷姆的继承人,美好时代上流风华的独裁者,奥古斯特 · 埃斯科菲耶(Auguste Escoffier)断言:“做菜,至少是做法国菜,高汤就是一切。” 高汤既家常,但同时又有着笛卡儿式的存在意味:我熬高汤,故我在做法餐。 “卡雷姆……火锅……这个话题太重要了。”法国美食史学家贝内迪克特 · 博热(Bénédict Beaugé)很支持我的项目。“可惜啊,现在太多人不在意了。” 贝内迪克特年逾古稀,白发渐稀,苍白的面庞庄重而慈祥,散发出深厚谦卑的人性光芒—与聒噪的法国知识分子恰恰相反。他住在巴黎西边,离埃菲尔铁塔很近,家里摆满了书。他家所在的卢尔梅街(Rue de Lourmel)平淡如水,我在街边发现了一家中东自助餐、一家日餐店,还有一家名叫“B计划”的嬉皮文化爱好者酒吧。 我的开场白是:“真是新的全球巴黎啊。” 贝内迪克特说:“还有乱,从餐饮角度来说。餐饮乱象现在已经持续了将近20年了,反映了法国身份认同的宏观乱象……不过,也许是乱中有治?” 但与我一样,他也在思考“关于法餐文化、关于一个伟大餐桌文明的顶层理念”。他说,巴黎如今似乎只有日本大厨执迷于法餐文化,而突尼斯面包师傅已经在法棍大赛上得奖了。 “没错,外来饮食正在永久地改变巴黎,”他承认,“但问题是什么呢?我们法国人不像你们美国人那样有明确的熔炉国家意识。” 这话没错。我要是向记者朋友询问巴黎的族群构成情况,他们会严肃提醒我,法国法律禁止发布关于族裔、种族或宗教的官方数据—如此一来,类似13区内的这种移民社区变得无声无形。一切都是以对肤色视而不见的普世共和理想的名义。 “不过还有火锅呢!”贝内迪克特点头称是,“那个美妙的、有趣的玩意,一道十足的家常菜—就是高汤炖肉—但又是十足的国菜!” 卡雷姆呢?他温柔地笑着,仿佛在谈论一个心爱的老伯。“一个艺术家,我国厨界的第一个学问家,一个笛卡儿式的灵魂,他为法餐赋予了逻辑基础和语法。然而……”贝内迪克特抬起一根手指,“法餐的理性化与随之而来的民族化—其实并非始于卡雷姆!” “你是说拉瓦雷纳(La Varenne)吧。”我答道。 弗朗索瓦 · 皮埃尔 · 德拉瓦雷纳(Fran.ois Pierre de La Varenne)是出身勃艮第的德鲁塞尔侯爵(Marquis d’Uxelles)的“厨房侍从”。1651年,他发表了《法国烹饪》(Le Cuisinier Fran.ois)一书。之前的将近一个世纪中,意大利文艺复兴菜谱的改编版横行法国。《法国烹饪》是第一本法国原创菜谱,也是全世界第一本以国家命名的菜谱。 现在很难想象,但直到17世纪50年代为止,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专门编纂的“国菜”菜谱一类的东西。穷人靠稀粥野菜为生(当年没人愿意吃,如今却被奉为“传统”),各国宫廷的饮食则是五湖四海,用来自远方的美食炫耀权势与富贵。全欧洲菜谱抄袭成风,不以为耻,以至于欧洲(乃至伊斯兰世界)精英在宴席上吃的东西都差不多,有烤孔雀和烤白鹭,有巨型馅饼(有时里面装着活兔子),还有无处不在的白布丁,这是一种受到穆斯林影响而形成的糊冻菜肴,原料包括米饭、鸡肉和杏仁露。文艺复兴时期的菜谱甜倒牙,动辄一斤肉放两斤糖,滥用进口的肉桂、丁香、胡椒和藏红花,以至于一名历史学家打趣道,什么菜都是一股劣质印度菜的味道。 《法国烹饪》是欧洲烹饪巨变的最早记录。拉瓦雷纳的名著中基本摒弃了厚重的东印度香料,而改用红葱头和香草等“法国香料”;肉菜一概不加糖;以乳化黄油为基底的顺滑酱料开始取代中世纪的浓烈酸甜酱汁。《法国烹饪》里点缀着精巧的蔬菜炖肉和清爽的沙拉,还有法式炖牛肉(boeuf à la mode)这样高辨识度的标准法菜。一名与拉瓦雷纳同时代的人对这种新式“本味”菜肴做了最精当的概括:“包菜汤就应该纯是包菜味,韭葱汤就应该纯是韭葱味。”这句现代箴言最初出现在17世纪中期的法国。 “在拉瓦雷纳之后的一个世纪里,”身边堆满了书的纤弱名宿贝内迪克特说,“启蒙精神独领风骚,印刷文化迎来爆炸式发展。”伴随着卢梭的自然崇拜—看似粗鄙,实则非常精巧昂贵—狂热的新式科学方法应运而生。两者联姻带来的后果之一,便是高度浓缩、半食半药的高汤受到追捧。 那这些启蒙灵丹妙药的名字叫什么? 餐厅(restaurant)。 正如历史学家丽贝卡 · 斯庞(Rebebba Spang)在《餐厅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the Restaurant)一书中所说:“早在餐厅成为就餐场所的几百年前……餐厅本身就是食物,一种滋补高汤。”作为场所的餐厅—直到19世纪中期都是巴黎独有的胜地—最早出现于1789年革命前的20年间,当时是金碧辉煌的“汤疗”中心。在西方历史上,食客第一次可以随时到店,按价点单,分桌用餐。到了19世纪20年代,巴黎约有3 000家餐厅,样貌和今天的餐厅已经很像了。餐厅是暴食美学的圣殿,没错—祭品就是松露马伦哥炖鸡与奢华的水晶灯。但同样重要的是,餐厅是社会文化地标,为一种法国特有的新式美食文学哲思提供了灵感—吸引着英美朝圣者的到来,按照斯庞的说法,这些人以为法国的“民族性体现在餐厅里”。他们的想法是对的。 当我准备告辞,留下贝内迪克特与他的文字和历史独处之际,他告诫我:“当然,国菜不是一夜之间出现的。”那是一个反映了文化治变迁的漫长过程。但他强调,法餐自从17世纪中叶就创新求变,别出心裁,而随着餐厅的发展和美食评论家的诞生,这个法国独有的特征愈发突出。另外,从拉瓦雷纳开始的法国餐饮人代代凯歌高奏,反复向本味,向更创新、更科学—也更昂贵—的精纯厨艺效忠。卡雷姆呢?他的“绝大部分”菜肴都奉行“朴素、优雅……华贵”的原则。埃斯科菲耶号称在卡雷姆基础上删繁就简—在接下来的20世纪初,倡导地方菜的美食资产阶级运动嘲笑埃斯科菲耶穷奢烦冗。到了20世纪70年代,反叛传统的“新烹饪”(nouvelle cuisine)大厨博古斯(Bocuse)、特鲁瓦格罗(Troisgros)之类全盘否定卡雷姆—埃斯科菲耶传统,斥之为“糟糕的褐酱和白酱”,同时树立起属于他们自己(而且贵得让人惊诧)的崇尚清爽天然的胜利旗帜。 但为什么—为什么在新烹饪革命之后,推陈出新、崇尚理性的独特法餐文化陷入了惊人的徘徊与困顿呢? “费兰。” 尼古拉 · 沙特尼耶(Nicolas Chatenier)用夸张的忧郁语气报出了罪魁祸首的名字。尼古拉衣冠楚楚、形貌俊朗,是一个40岁上下的商人兼花花公子,现任圣培露50最佳餐厅法国评委会主席。圣培露餐厅排行影响力巨大,是米其林餐厅排名的主要对手。 他说的是费兰 · 阿德里亚(Ferran Adrià),加泰罗尼亚先锋派大厨,曾经是西班牙布拉瓦海岸(Costa Brava)斗牛犬餐厅的天才厨师。20世纪末,阿德里亚横空出世,仿佛集魔法师与科学家于一身,举重若轻之间,巧妙机智地挑战、解构和重新定义了法餐的语法和逻辑—正如毕加索和达利颠覆和激发了艺术界一样。 尼古拉和我在思考法餐大厦倾覆的灾难,地点在一家名叫“鸡锅”的新锐高档餐厅,一份鸡肉版火锅要卖60美元。 尼古拉出身巴黎市民家庭,在他的记忆中,家人过节去法国各大美食圣殿的经历富有魔力。一名留胡子的年轻嬉皮士男服务员端来了高汤炖煮的正宗布雷斯黄鸡,神情里带着千禧一代的冷漠嘲讽。同时,尼古拉如梦似幻地回忆道:“罗比雄Jamin餐厅啊,跟糖果盒似的……特鲁瓦格罗家那童话里一般的甜点啊……”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世纪初的时候,还是一名雄心勃勃的美食记者的尼古拉对当时甚嚣尘上的法餐危机深感困扰。于是,他写了一篇纪实长文。没有人想听他讲的话。他咯咯笑道:“大家骂我是英国特务,我可不是胡编!” 他的眼神变得忧愁。“法国,几百年来的美食大帝国。最优秀的培训,最优秀的出品,最优秀的厨师。然后……”他惨淡地举起手,“《纽约时报》把费兰放在封面上,文章里讲法国衰落,西班牙崛起,这是国耻。” 我责备他道:“尼古拉,你少来,那篇文章都快20年了!” “这边的人还在谈论它。”他向我郑重保证。 西班牙人表现出了“惊人”的团结,围绕在费兰身边,而在乔尔 · 罗比雄(Jo.l Robuchon)和阿兰 · 迪卡斯(Alain Ducasse)的领导下,当代法国人却在相互争斗。尼古拉思之神伤。 “这和70年代新烹饪那帮人不一样,”他坚称,“特鲁瓦格罗、博古斯、米歇尔 · 盖拉尔(Michel Guérard),他们聪明,真诚—团结。” 确实,他们使用了1968年的激进修辞;革命弥漫在空气中。但他们抓住了时机—那属于一股普遍的、更庞大的文化能量的一部分。“当年的法国万象更新。电影有新浪潮,文学有新小说,文化批评也有新角度。我们是文化与时尚之都—戈达尔、特吕弗、伊夫 · 圣罗兰!” 他停下话头,打了一个鸡肉高汤味的悲伤饱嗝。“之后是希拉克治下停滞不前的12年。缓慢的,乏味的[叹息]……衰落。” 所以,法餐危机的原因其实不是费兰? 尼古拉耸了耸肩,这是法国人表达赞同的动作。“是一连串危机。” 比如,米其林那过时的、难以为继的高档餐厅标准逼得一些大厨破产,甚至还有大厨被迫自杀;2000年实行35小时工作制,外加19.5%的苛刻增值税(后来调低了),让本就困难的餐厅雪上加霜;中低档餐厅爆出使用预制菜和冷冻食材的丑闻;在乡下,连锁超市和工厂化农场威胁到了地方传统。还有,全球化快餐入侵来了。 “法国,灿烂餐饮文明的输出国,迷上了麦当屎! ”尼古拉悲道,“就连我们的法棍都变差了。预烤的,冷冻的,工业的。” 但是,现在看起来一切都挺好。法棍又变好了,千禧一代追捧农场直供的有机鲜蔬,仿佛连上了卢梭的自然崇拜。这股新潮流在巴黎东部尤其兴盛,带来了布鲁克林风的咖啡馆、创意鸡尾酒和受到亚洲文化影响的餐厅。“如今,巴黎的所有界限全都模糊了,”尼古拉宣称,“太有意思了!好吧,外界抨击一度让我们落伍—但我们现在思想开放了!我们或许失去了国菜的理念,但我们已经向外界开放了。去金马车看看吧,”他劝我道,“日本人开的一家新派粤菜馆,超酷的……” “等等—你是说,巴黎餐饮界之所以有趣起来,是因为大厨们抛弃了法国性的观念?” 尼古拉哽咽了一下。他看上去忧心忡忡。作为圣培露50法国区的首席评委,他必须维护民族价值。“好吧,算是有一点吧,”他让了一步,“但现在大家又有小馆(bistro)情怀了!芹菜根沙拉、鸡肉火锅,就咱们刚刚吃的这些。看看周围吧:座无虚席,晚晚爆满。还是这个价。” 风土啊,他一边遐想着,一边把叉子插进了布雷斯鸡的身子里,生猛吓人的鸡爪还支棱着。这也许就是法国永远的回答,真正的民族叙事。法国不可思议的物产……还有法国人谈论国产品的卓越话术,打开了全球的食欲,满足了世界的胃口。 吃完饭,我在月光下的塞纳河畔漫步,思忖我与尼古拉的谈话,无视了法国爱好者们不避劳苦、趋之若鹜的浪漫水滨。普丽西拉 · 弗格森论证道,法餐至高无上的地位是因为食物本身—布丁就是证据。但正如尼古拉主张的那样,另一个原因是法国人太擅长话语了:他们的谈话,他们的写作与哲思升华了美食,吃不仅仅是维生,甚至不仅仅是展现上流阶级的权势,而成了一种与文学、建筑、音乐比肩的文化形式。 但我又想到,法国人的谈话终究伤害了法餐。 因为它变成了故步自封的本质主义。随着别处迸发出进步思潮—西班牙有天马行空的新烹饪科学,加利福尼亚和斯堪的纳维亚关注可持续理念—法国则形成了执念,为失去话语加持下的统治地位而焦躁。他们的故事变成了怀旧和辩护,刻板傲慢,墨守成规。我回想起10年前圣保罗的一场星级厨师大会。加泰罗尼亚青年糕点魔法师霍尔迪 · 罗加(Jordi Roca)献上了一道神奇的浮空甜品。巴西大厨阿莱士 · 阿塔拉(Alex Atala)激情畅谈亚马逊的生物多样性。法国厨师呢?食神阿兰 · 迪卡斯手下的厨房团队登台大讲……高汤的重要性。我还记得自己和听众都在翻白眼。那就好比在人工智能峰会上谈钢笔。 可我自己就在巴黎,站在齐膝高的高汤里,研究火锅还有高汤的历史与科学原理—探寻美食与土地之间的广阔关联。比方说,我惊讶地发现,一杯小小的18世纪养生高汤竟然直击法国启蒙运动多个话题的交叉点,包括烹饪、医药、化学、方兴未艾的消费主义,还有古今口味之争。但一个世纪后,高汤又成了餐饮民主化的代表,因为19世纪末的巴黎涌现出了名为“汤馆”(bouillon)的廉价食堂。汤馆是全球快餐连锁店的雏形,在赏心悦目、干净卫生的环境里向贫民阶层出售高汤炖牛肉外加几种简单配菜。 如今,在摆满了巴尔扎克时代小玩意的13区公寓里,我再次研究起卡雷姆《法国烹饪艺术》的开篇菜谱“家常火锅”。 陶锅里放入四磅牛肉、一大块小牛肉、一只插在钎子上烤至半熟的鸡、三升水。后续加入两根胡萝卜、一个芜菁、韭葱和一块插入洋葱里的丁香…… 菜谱简明易懂,只是有点古怪。为什么鸡要烤到半熟呢? 贝内迪克特告诉我,这道菜谱之所以经典,是因为卡雷姆的序言资阶级火锅剖析》。这本书是御厨卡雷姆写给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的,他在序言中讲解了高汤的科学原理及其对资产阶级女性做菜的好处—高汤弥合了性别与阶级的鸿沟。他称赞读者道:“照看养生锅的女性哪怕对化学一无所知……已经从母亲那里学会了如何烹制火锅。”学者们认为,这篇序言让火锅真正成了国菜,指引着一代代作家和厨师从这道“什锦一锅出”动笔,撰写自己的著作。 但我问我自己,一道菜还能通过什么方式,有什么原因会被奉为“国菜”呢? 有在海外取得的意外经济成功(意大利比萨),有对游客的吸引力(希腊木莎卡),有在艰苦岁月滋养了大众(战后日本拉面)。有时甚至直接就是法律规定:请看泰式炒粉这个奇特的案例。这道菜源于中国(日式拉面也是如此),经过“泰式改良”后加入酸角和棕榈糖。20世纪30年代的銮披汶 · 颂堪立法将其定为国民街头小吃。此举是他计划的一部分,其他做法包括将国名“暹罗”改为“泰国”,禁止少数民族语言,还有不许华人上街摆摊。 当然,在所有竞争者里面,什锦炖菜是最有说服力的民族象征,因为它有一种神奇的象征力量。它不拘贫富,跨越地域界线,将不同的历史过往连为一体。在巴西,黑豆炖菜(feijoada)被认为将原住民、殖民者和非洲黑奴文化融合在这一锅黑豆和猪下水的炖菜里。古巴有一种多种肉配薯类的炖菜(ajiaco)跟它如出一辙,也是同样的说法。再来看(如果非要看不可的话)纳粹对德式一锅出(eintopf)的诡异推崇,企图从中发现神秘的人民共同体。直到20世纪30年代为止,“eintopf”这个词都从未见诸书刊,请莫见怪。(我后来发现,类似情况并不少见。) 现在要讲我的火锅,还有它真实的历史源头了。尽管火锅不算是农家菜(农民一年才吃得上一次肉),但它依然被轻易神化为法国共和信条的完美载体,“全法国”的博爱之锅。就连眼高于顶的埃斯科菲耶都对它赞誉有加:“这道菜虽然简单……却构成了军人和劳工……富人和工匠的完整晚餐。”早在埃斯科菲耶称霸的美好时代之前,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雄心—通过全民法语教育、服兵役、区域整合和乡村现代化开展激烈的国民齐一化运动—已经基本实现了。尽管女性依然是二等公民,直到1944年才有选举权,但用一名学者的话说,“教玛丽安做饭已经成了一项无比重要的民族议题”。几乎每一本女性家政学教材的开篇都是火锅,19世纪末有一本面向资产阶级女性的热门家政杂志就叫《火锅》。更有甚者,火锅还完美体现了那个时代地方主义者的“多元合一”理念,因为法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火锅版本[朗格多克有柴捆汤(garbure),布列塔尼有料肉锅(kig ha farz)],如今它们都被颂扬为全民族宏大美食文化的一部分。 我越是琢磨,就越觉得火锅简直是“国菜”大厦里的一堂显而易见的大师课。 只不过…… 我问过的人谈起它用的都是过去时,慵懒怀旧的语气—“外婆菜嘛”,乡下礼拜天中午吃的火锅呀—然后就上气不接下气地推荐起热门刈包店,或者精品布鲁克林风梅兹卡酒吧。有人跟我宣称两个火锅专精的重量级大厨,结果两人都在亚洲享受长假,而且从喜气洋洋的照片墙(Instagram)状态来看,他们一时半会是不打算回国了。 就连法餐名家阿兰 · 迪卡斯似乎都将这道经典“国菜”扫到了公交车底下。 我到他的头牌重镇—雅典娜广场酒店餐厅拜访了他。听到我的提问后,他思量着答道:“卡雷姆……火锅……嗯……” 迪卡斯现年六十有余,身着一尘不染的棕色西装和他的招牌鞋—阿尔登牌厚底鞋。他屡摘米其林星,旗下餐饮帝国横跨好几个大洲,在我脑海里的形象相当于现代企业家版的卡雷姆。他是一名大牌文化企业家和美食外交家,曾代表法国品牌在凡尔赛宫多次招待国家元首。 “火锅……”迪卡斯摇了摇满头银丝的脑袋。他已经皈依了卢梭式的自然烹饪—法国人总在重申的“自然”—如今的他关注地球健康。红肉?他皱起了眉头。对环境不好。 “高汤,底汤,经典法式酱料……卡雷姆,埃斯科菲耶……”迪卡斯心不在焉地总结着我的提问。“当然了,这是我们法国人的DNA……依然在激励着我们。”尽管他听起来兴致不高。“在我们的业务里占,”他停下来算了算,“大概10%吧。可能还不到。” 10%? 我想到了圣保罗的那场舞台秀,妄想法国高汤永远天下第一的陈腐之气。 几天前,我的朋友,《伊都锦》(Elle)杂志法国版美食版主编亚历山德拉 · 米绍(Alexandra Michot)就要不讲情面多了。她连珠炮一样地说:“我们用了整整一百年才摆脱卡雷姆—埃斯科菲耶传统,忘掉霸道的法餐语法。现在,我们终于自由了!未来是美妙的。” 基本就是迪卡斯那句话的核心意思。 迪卡斯隐晦地承认,十年前的法国餐饮界有点压抑。但今天呢?“今天人才济济,多元丰富—亚洲菜、北非菜、小馆的新诠释。新故事有很多,全都是独特的、个性化的、个体化的。” 这是我从尼古拉和其他人那里听到的原话,也是我的经验之谈—但从“建制本制”阿兰 · 迪卡斯嘴里说出来,我觉得那就是法国的新官方口径了吧:普世已死,地方万岁。法国大菜本身呢?基本上也死了—因为就在我拜访他几个月后,迪卡斯就被赶出了声誉卓著但无利可图的雅典娜广场店,要和阿尔韦特 · 阿德里亚(Albert Adrià)合作开一家快闪店。阿尔韦特正是迪卡斯老对头费兰的亲弟弟。我上一次听说他,是他筹划在某地开一家素食汉堡店。 那么,在这个似乎已经失去兴趣的法餐发源地,我的卡雷姆/火锅计划—这是探究法国美食与身份认同的逻辑起点,我是这么认为的—又将置于何地呢? 就连我那热爱法国的年迈母亲也看到了老生常谈里不好的一面。她刚刚从莫斯科回来,在巴黎转机回纽约。 她早晨吃了块突尼斯版“东欧馅饼”(pirozhki)和柬埔寨版“俄式布林饼”(blini),之后去本地肉铺的路上问我,还叫我俄语小名。“可是,安钮特呀……干吗要做火锅呢?要说法国国菜的话,难道不应该做库斯库斯(couscous)什么的吗?” 我想到了刚刚读到的一段形容,作者是一名阿尔及利亚裔政治活动家:法国是一个“麦当劳—库斯库斯—牛排—薯条社会”。全球化的风很大。我是不是荒谬地落入了某个骗游客的“正宗”骗局,对一道封存在琥珀里的菜肴心存期待?我是不是太天真了,在追逐某道老掉牙的书本里的菜,在一个官方奉行无视肤色的大政方针,多元化漂都漂不白的国家的跨文化首都里寻找火锅那所谓的“民族”叙事? 说实话,“法国人最喜爱的菜肴”调查中哪里还有火锅的位置? 大约十年前,库斯库斯真的登顶排行了,引发了司空见惯的沙文主义呼号,英国报纸免不了嘲笑,头条里大谈“法国被自己的洋葱汤呛死了”。(la France profonde choking on its soupe a l’oignon.)(请注意,狡猾的英国人把自己的美食符号从烤牛肉换成了鸡肉玛莎拉,以此彰显文化多元。)法国近期的调查结果看上去会让民族主义者安心一点,库斯库斯排名第八,香煎鸭胸排名第一(不过,鸭胸肉也算一道菜了? )但话虽如此,这些日子里法国人最爱的垃圾食品是一款墨西哥卷饼和土耳其烤肉的私生子,黏糊糊,肉量满满,名字叫“法式塔可”。 除了危乎高哉的贝内迪克特 · 博热以外,全巴黎唯一真心对火锅有热情的人似乎是摩洛哥肉贩拉比先生。 我母亲非要买点肉,我陪她进店的时候,他兴奋地都在搓手了。“哎呀,你说火锅啊,安妮亚女士?” “火锅,哦啦啦,好极了!”法蒂玛女士表示赞同。她是柏柏尔人,店里的常客,买了两公斤颤悠悠的羊脑子。 拉比先生的店是意大利大道上最欢乐的一家清真肉铺。这是一座生机勃勃、弥漫着孜然香气的社区中心,店里挤满了穿廉价皮夹的男、牛仔裤磨破了的女孩子、包头巾的主妇,大家用法语、柏柏尔语和阿拉伯语八卦着难测的巴黎生活。白头发的拉比先生身宽体胖,散发出一种粗犷活泼的气质。他当年在摩洛哥的索维拉市(Essaouira)做工程师,但现在到了巴黎,谁会给他体面的工作干?“巴黎啊,”他感慨道,“哪里有人性?天气冷,古典范,东西贵。”清真肉贩当然再好不过。因为?“因为法国人懒得天刚亮就起床,完全不跟动物打交道。” 他还暗示道,清真议题引出了法国人排外思想中最恶劣的一面。 “安妮亚女士,很快他们就会逼我们吃火腿了!”拉比先生轻声道。 但他现在全心热爱火锅。“Gite,paleron,plat de c.tes4”。把这些经典(且无法翻译)的牛肉部位重重放到秤上,接着夸张地拿出两根大棒骨,开始对半锯开。 “不好意思,拉比先生,”我小声说,“我不要gite和plat de c.tes……”我专门点了卡雷姆指名的5磅牛臀肉、一块鹿排—还有一只烤到半熟的鸡。 拉比先生吃了一惊,甚至有一点被冒犯。他的专业技能,还有他在法国文明使命中的工作正遭受质疑。是谁在质疑?是一个连“再见”(au revoir)都搞错的人。“但是,安妮亚女士,”他郑重地摇头,“正宗火锅不是这么做的。法国菜是有规矩的(il y a des regles)。” “火锅里放鸡肉?从来没有(Jamais)!”法蒂玛夫人宣告道。 我在手机上给拉比先生看了卡雷姆的经典菜谱。他还是不相信的样子。我把手机传给店里的人看。有人发表了意见。戴头巾的妇女翻着白眼咯咯笑。 突然间,我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感受。在这家满是移民的店里,我才是“他者”,是不懂法国的规矩、未经教化和同化的闯入者。没错,归属和认同也可以是流动的,是因地制宜,是相互作用。这里的人仅仅五分钟前还在抨击法国,现在就在把“法餐传统” 当作自己的东西来辩护了,至少暂时如此。 “好奇怪的场景,”我们带着肉回家的路上,妈妈对我说,“我不敢想象咱家杰克逊高地的哥伦比亚肉贩纳乔先生会教我们做美国菜。” 不知道你有没有体验过五平方米的法餐重镇?在秋日热浪突然袭来,巴黎人纷纷出门到户外咖啡厅享用龙舌兰鸡尾酒和清爽的亚洲沙拉时,却偏偏到一个连台面都没有的厨房里做法餐? 呃,我可不仅仅是打算办一场小小的朴素家庭火锅聚餐。不,女士们,先生们:为了我的项目,为了纪念我的母亲,我决定要依托一整个宏大的事业。官方认证的“法国盛餐”。 这是什么? 2010年,国菜品牌已经是一门赚钱的生意了。秘鲁、泰国、韩国、日本和墨西哥都忙着开发本国餐饮软实力,助力旅游业与出口业发展。当时,经过法国美食文化遗产委员会的多年大力游说,“法国盛餐”(le repas gastronomique des Fran.ais)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是非遗名录—它的初衷是“文化遗产去殖民化”,但很快被各国霸占,用来推进本国的形象建设工程—首次承认厨艺和其他民俗,比如秘鲁剪刀舞。(当年“传统墨西哥餐”也入选了。) 教科文组织对法国盛餐的描述开头是“团聚,美食的愉悦……精美用餐环境……”这些空话。接着就是颂扬历史悠久的法餐语法:“定式,首先上开胃菜……最后是酒品,中间至少有依次奉上的四道菜,即头盘、肉或鱼配蔬菜、奶酪和甜品。” 看啊,这就是我的规定计划。 教科文组织的荣誉是文化界的大事,迎来了彰显民族情绪的报纸头条,比如“法国向人类献上国菜”和“世界羡慕我国美食”。然而,另一份讥讽的英国头条(当然是英国了)概括了全球反响,大意是尽管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了法餐的地位,但是法餐“堵塞动脉的肥腻和拘谨的呈现方式,已经和老式红白方格桌布一样不时兴了”。 但我,一个坚定的反爱法人士终于在局促的公寓餐桌旁坐下,擦去汗水,为我们的“定式”菜……体验清理好桌面。这或许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对法国,对巴黎生出爱意。这是一顿如博物馆展品般美妙的菜肴。开胃菜是利莱白葡萄酒配蛋黄酱鸡蛋和卢梭水准的红宝石小萝卜配阳光般灿烂的黄油。真正的开胃菜是法国千禧网红酥皮肉派—外面是老佛爷百货时髦的食品大厅买来的建筑师级正宗卡雷姆派皮,内里是猪肉冻、松露和肥肝拼成的马赛克。我和妈妈把堵塞动脉的牛骨髓倒在本地突尼斯面包师出品的获奖法棍上,妈妈赞许地说了声“嗯”。接下来是卡雷姆那琥珀色的高汤火锅,汤盛在华丽的瓷杯里。然后是拉比先生的精品清真牛肉、鸡肉和小牛肉,火候全都大了,不过算不上惨烈—结尾是冒着泡泡的卡芒贝尔奶酪(一名人类学家称之为法国的“民族神话”)和金箔点缀,富有光泽的深巧克力色怡口莲。 1. “美食界奥斯卡”詹姆斯·比尔德奖三届得主安妮亚·冯·布连姆森最新作品。 2. 《金融时报》《卫报》《观察家美食月刊》《旁观者》和BBC美食栏目年度好书。 3. 了解一个国家的灵魂,从它的国菜开始。《国菜》带你踏上一场独特的环球美食之旅,通过各国国菜的历史演变,揭示它们背后的文化意义与社会变迁。本书将历史与美食巧妙结合,在品味美食的同时,也能感受到历史的厚重与文化的韵味。 昊骞,青年译者,先后就读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和阿姆斯特丹大学ILLC逻辑学专业。已出版译作包括《毛姆传》《疼痛部》《战争艺术史》《21世纪的21位思想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