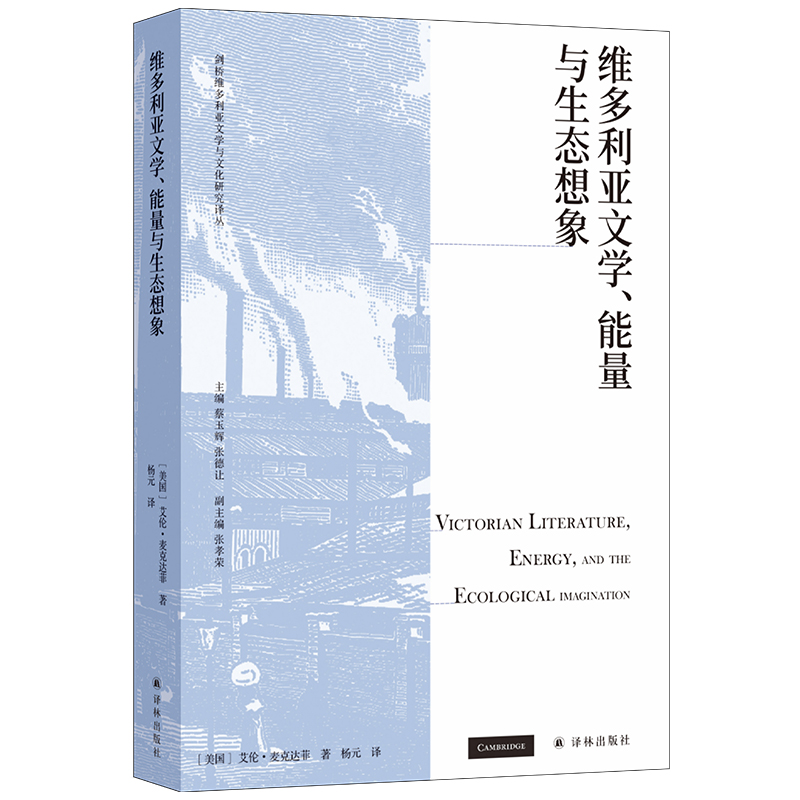
出版社: 译林
原售价: 75.00
折扣价: 47.30
折扣购买: 维多利亚文学、能量与生态想象
ISBN: 97875447886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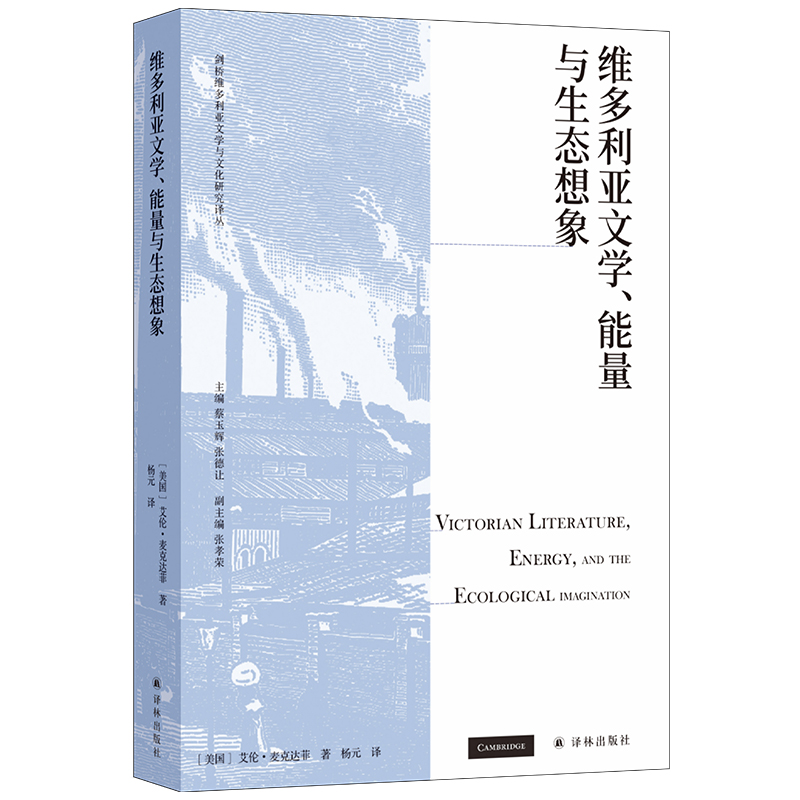
艾伦·麦克达菲(Allen MacDuffie),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英语系助理教授,毕业于哈佛大学。主要兴趣为维多利亚文学、文学与科学研究、生态文学及批评。
第一章 城市与太阳 热力学 19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热力学的发展在发起挑战的同时,又强化了生产主义所描绘的图景。一方面,人们用更为严格的数学术语来阐释能量守恒。通过建立热能的机械能当量,并用统一的度量衡即做功能力来比较各种不同的能量形式,焦耳、罗伯特·迈耶和其他一些科学家就能够将一个形而上学的公理通过实验而加以量化。曾经,人们所持有的普遍的、完全的守恒观只是一个很松散的想法,现在却有了坚实的基础,人们可以对不同能量形式之间的相互转化进行测量,而不是只凭断言了。另一方面,工业技术操作中观察到的能量耗散问题,在热力学第二定律中正式被提出,这也使得人们很难忽视不可逆和废弃物的问题;事实上,它把这些问题置于看似激进的新的宇宙论的中心。 我们将在下一章中详细研究第二定律。现在,我想提醒大家注意热力学第一定律,因为它是在19世纪中叶提出的,而化石燃料的概念有一些模棱两可。一方面,它的确对巴贝奇等作家总结出的严格的能源经济加以强调并使其规范化。热力学第一定律针对能量的可为和不可为建立了一系列的规定,并且用严格的数学方法说明了人类不可能从无中生出有来。这在对第一定律科学的和通俗的讨论中都很常见;鲍尔弗·斯图尔特写道,“机械的世界不是一个制造能量的工厂,而是一个集市,我们带来一种能量,将其改变或交换为另一种等效的能量,使其能更加适合我们,但如果我们手上什么也没有,那么我们必定什么也拿不回来”。因此,第一定律确立了做功所受的限制,也控制了人们对物质世界的无限延展性和可开发性的幻想。 从另一方面来说,以前的生产主义论著就如何对待化石燃料使用了许多形而上学的推断和修辞手段,能量守恒也依赖于此。我们在焦耳的著作中可以听到自然神学的回声,许多人认为他是把能量守恒送上科学大道的第一人:“实际上,不管是机械的、化学的还是生命体的自然现象,几乎都是借助空间、天然力量和热,存在于连续不断的能量转换过程中的。由此,宇宙中得以维持这一秩序,即无一生乱,无一消散,但是整台机械复杂如此,却能够平稳和谐地运转。”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们,尤其是那些为普通大众撰写作品的人,在创作有关能量的热力学作品时,并不只是否认或隐瞒第一定律的形而上学的基础;他们还对此着重强调,常常将能量守恒的根源追溯到自然神学、德国浪漫主义以及古典哲学和神话学的理论上。譬如,弗莱明·詹金认为,卢克莱修“预言了能量守恒学说”。 赫尔曼·冯·亥姆霍兹是“发现”第一定律的关键人物之一,他尊崇歌德,认为其预测了热力学理论;英国的科学自然主义家约翰·廷德尔声称,是卡莱尔“充满诗意地,却也准确地预见到了能量守恒理论”,他还引用了《衣裳哲学》中的一段文字,稍后我们会详加讨论。这里为能量概念建立了一个发展的系谱,让读者相信,他们的发现证实了宇宙的图景和物理世界的经验是稳定的、为人们所熟悉的,也许还是令人欣慰的。 事实上,一个人可以热心于使用工业能源的奇妙世界和新技术打开的令人目眩的新前景,同时又认为,这样的世界仅仅是人们早已知晓的,或者是先辈们早已预见到的力量和定律的新的表达方式。特别是廷德尔,他说自己早已知道这些令人惊诧的事情,他既想让读者大吃一惊,又想安抚他们,于是他常常要在其中寻找一条有趣的修辞路线。以下文摘选自他的《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热》,这也是维多利亚时代最为出名的一部热力学著作: 我们转到其他星系和恒星上,它们都能像我们的太阳一样释放出能量,但它们也没有违反这一定律,它们身处变化中依然保持其永恒性,持续地发生着能量的转移和转化,但最终能量既不会增加也不会损失。这条定律体现了所罗门的格言,太阳底下无新事,教我们在它无穷变化的外表之下,到处去寻找那相同的原始力量。对自然而言,什么也不能加入进去;从大自然中什么也不能带走。 实际上,廷德尔提出了两个相互关联的观点。借助能量不增不灭的说法,能量守恒在流动的现实之下建立了一个不变的秩序:即便是根本性的物理性转化,也只是永恒定律的一种不同表达而已。但是他又指出,能量守恒概念也认可现实中某种历史悠久的经验—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圣经》的格言式的智慧了。这样,人类思想自身的发展行为与能量相像:其外部形式多种多样,却都是深层秩序和同一性的各种不同的表述而已。正如他在其著名的《贝尔法斯特演讲》中所说的: 这个世界不仅信奉着一个牛顿,还尊崇一个莎士比亚;不只有一个波义耳,还有一个拉斐尔;不仅有一个康德,还有一个贝多芬;不仅有一个达尔文,还有一个卡莱尔。从整体上来看,人的特性不在他们中哪一单独个体的身上,而在所有人的身上。他们相互之间并不对抗,而是相互补充,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融合……人类的思想,带着朝圣者对远方家园的渴望,将要转向孕育其成长的神话,并试图改造它,以便让思想和信仰统一起来。 在《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热》这本书的末尾,廷德尔显然对宇宙中能量的规模感到惊奇异常,他坚持认为,在他的科学物质主义和神话化的宇宙之间,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在精神和物质之间存在着一个本体论的灰色地带,能量巧妙地处理了二者之间的分歧: 波浪会削减为涟漪,涟漪也会增强为波浪;盈千累万会缩减为渺小的数字,渺小的数字也会扩大为盈千累万;小小的星体会膨胀为巨大的恒星,恒星也能分解成小小的动植物,这些动植物又将融化在空气中,但能量流却是亘古不变的,经年累月,它带着旋律滚滚向前,地球上所有的能量—生命多样的形式和现象多变的呈现,都只是它节奏的调整而已。 从生态学意义上说,廷德尔声称“太阳底下无新事”的问题在于,至少就人类文明而言,化石燃料的“原始力量”实际上是新的力量。化石燃料的使用除了表明它在自然环境中发生着不可逆的变化,在“持续地发生着……转移和转化”,还有其他的意义。廷德尔的著作往往会从对具体技术和自然环境中能量做功方式的细致描述,突然跳跃到广阔的宇宙秩序的图景。他一直强调宇宙能量供给的有限性,并暗示人类活动对这种有限性不会造成有效的影响: 看看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能量总量:煤田里储存的能源;天上的风与地上的河;还有我们的舰队、军队和枪炮。它们都是什么?它们都来自一小部分的太阳能,不到总量的二十三亿分之一……用我们地球上最大的度量来测量的话,这样的能量库也是不可限量的;但倍感荣幸的是,我们拥有超越这些度量的特权,只将太阳自身看成是广袤空间当中的一点,仅仅是沧海一粟。 虽然廷德尔强调,在宇宙能量的海洋里人类显得微不足道,但是这并不会伴有因生命渺小而产生的生存焦虑。的确,正如本书在其他地方说明的那样,工业技术的发展让人类能够获得无穷尽的力量。如果说廷德尔看上去是在贬抑人类世界的话,那么他的意图也只是对等待我们去利用的巨大的能量库表示惊讶而已。正如我们在赫胥黎的著作中读到的,起初作者像是在赞美大自然,但实际上这只是夸赞人类的另一种方式。我们也许很渺小,但是我们的智力赋予我们“超越……的特权”。 因此,工业技术既帮助我们获得了能量,又让我们知晓了自然永恒的稳定性。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很难发现人类使用能源的方式有什么毛病。这个问题,在部分意义上,可以归结为廷德尔对“自然”一词的使用方式,它往往意味着将宇宙抽象化(正如上文“对自然而言,什么也不能加入进去;从大自然中什么也不能带走”),而不是将其看成一个有限的地球环境,或者物质生态系统。这不同于人们在达尔文观点中看到的自然的概念,比如,他使用的著名比喻“纠缠体”(tangled bank),以及《物种起源》中对许多生命有机物存在的复杂动态网络的描述,这些都不只是强调自然的变化无常,还强调了单个变化对整个系统产生的级联效应(cascading effects)。虽然在进化论和早期热力学著作中,转化是较为常见的比喻,但是后者更倾向于把转化的观点建立在稳定不变的基础之上。自然是不断转化背后维持稳定的保证,而在达尔文的作品中,自然就是转化。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如此强调自然永恒的不变性,抹杀了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而把自然界看成是正常运转的生态系统。 更重要的是,廷德尔让“所有能量形式都具有统一性和同一性”这种生产主义说辞上升到一个新的水平,直到工业活动和资源开发不仅变得完全自然,而且成为太阳能的必然的表现方式: 他先建造森林,后又砍伐树木,而令树木生长和挥舞斧头的两种力量,却是同根同源。三叶草发芽开花,割草机摆动镰刀,它们都是由相同的力量驱使着。太阳从我们的矿井里挖出矿石,他卷起钢铁;他把盘子钉起来,把水烧开;他拉动火车。他不仅让棉花生长出来,他还抽丝纺纱,编织网络。举起锤子,转动轮子,或者抛出织梭,这无一不是太阳的功劳。他将能量挥洒入太空,但如果这能量受到了限制,我们的世界也将举步维艰。就像海神普洛透斯在施展他的法术一般。 作者用抒情的笔调描写太阳把有机与机械、自然形成与工业生产自由融合的情况,直到在能量自由循环的迷宫中生长与消耗之间任何有意义的区分都消逝不见。在这里,森林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消失都是能量的不同表达方式。在建造和砍伐的工作之间绘制了一条平行线,让工业生产的过程变得自然化—确实,“建造”森林这样的语言意味着它已经是生产制造领域的一个部分——但是这似乎也让资源和环境的大规模开发成为一件自然的事件。对宇宙中这种原初性和统一性的强调,抹杀了时间性的差别作用;一句“他先建造森林,后又砍伐树木”很轻易就达到了句法上的平衡,遮掩了建造和砍伐二者背后深层次的时间上的不匹配性。前者,即一片森林的成长,可能需要数千年的时间,而后者则只需数周或数月即可完成,但这种“转化轻易就能发生”的感觉却勾销了这些重要的生态差异。这是我们在赫胥黎和巴贝奇观点中看到的有关不匹配性的精巧实例,原本属于不同时间范式的活动和过程却让人们产生了一种和谐的周期性的错觉,这种错觉是在生长与砍伐、发芽与修剪的如《圣经》所述一般的节奏中产生的。在这个纯粹是动作性的世界中,是由人的劳动完成,还是由煤炭、水力或者其他方式完成,它们之间的区别消失殆尽。人们使用的不再是一座有限的资源库,而只是早已在这个世界上循环往复的普遍原理的另一种形式。 廷德尔在《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热》的末尾对宇宙的抒情,说明他脱离了热力学第一定律发展过程中严格的实验性特点,的确,他也脱离了该书前几章中他自己对能量的描述。但强调这些观点的宇宙论特点也是此间人们讨论和传播能量守恒的典型方式。伴随着人们对新能量定律的规律性和合理性的兴趣,人们认识到能量守恒定律被认为只是自然界机械发生着的事情,因此,并不需要人类的监管。正如赫伯特·斯宾塞所指出的,这种混淆就深藏在所使用的那些术语上。他在《第一原理》中坚称,他所谓的“可持续的力量”要优于人们常用的“能量守恒”,因为后者会令人误解,含有“保护者和保护行为”(a conserver and an act of conserving)的暗示。从很多方面来说,斯宾塞和那些误传能量运转方式的人都犯了同样的错,他追随迈克尔·法拉第和W. R. 格尔夫,偏爱于使用“力量”一词而非“能量”,进而使得问题更加令人困惑。但是他认为“守恒”这一术语携带的隐含主体性让人困扰,这点是正确的。虽然斯宾塞的说法不是出于对资源利用和可持续发展的关注,但我们还是能看到一个隐含的“保护者”的概念,它建立了所有的能量关系并对其失衡现象进行纠正,这可能会掩盖人类对自然界资源的影响。 在某种意义上,对机械性守恒的这种暗示,以及对宇宙论图景的强调,是很奇怪的。如果讨论能量守恒常会导致人们不再关注各种能量形式之间关键性的差别,或忽视表明实际能源使用情况的效率和经济问题,那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热力学如果不热衷于此类差别和问题的话,甚至就不可能作为一门科学而存在。热力学最先从工程学传统发展而来,那时,节约能量和避免浪费都至关重要。作为生产动力的能量价值,鼓励着研究人员以精确、量化的方法了解其性质和限制。廷德尔对热的研究以相当引人注目的方式触及了关键性的生态问题。1859年,他开始研究地球大气层捕获太阳能量并阻止地球失去热量速度过快的过程。廷德尔意识到,如果没有“大气层的包裹”,地球很快就将“无法居住”。经过一系列的实验,他发现复杂的分子会捕获热量,而简单的分子则帮助热量毫无阻碍地扩散到外部空间去。斯蒂芬妮·佩因在《新科学家》杂志上发表观点,指出廷德尔发现了“煤气——一氧化碳、甲烷和其他碳氢化合物的混合气体——像木块一样会成为辐射热的阻碍”,佩因认为,这一真知灼见将他带到了描述人为影响全球变暖的门口。我们将在第五章中看到,约翰·罗斯金从富有想象力而不是完全科学的意义上迈出了这一大步。因此,廷德尔的著作表明,对热的行为进行热力学研究,会引发人们对人类能源使用和全球环境之间的关系呈现出的生态问题做深刻的思考。纵然同时它还依赖于比喻、修辞结构和形而上学的假设,并由此使得这样的问题更难以表达。 能量资源与城市 如果像威廉·斯坦利·杰文斯所说的那样,“煤炭,实际上,与其他商品的关系并非比肩站立,而是完全处于居高临下的地位上”,那么,生产主义便更强化了马克思所谓的商品拜物教中一种独特但又普遍的形式,即这样一种趋势,它往往意味着掩盖了真正的自然能源,以及对其进行提炼时自然和人类所付出的代价,而聚焦于它超凡的效用。当廷德尔提到“海神普洛透斯在施展他的法术”时,他既呼应又加强了一种共同的倾向,即以神话或神秘的术语来架构能源。斯迈尔斯这样描写工业运输网络的发展: 当我回顾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的这些伟大的事业时,感觉就像我们在自己这一代人中发挥了魔术师手中魔杖的力量。我们削平了山坡,填满了山谷;如若这一时权宜还显得不够壮阔,就建起高大雄伟的高架桥,若有高山阻碍道路,就建起宽敞宏伟的隧道穿行其中,这样才能意得志满,见证我们这个国家百折不挠的能量,以及我们的工匠无与伦比的技艺。 就像自然神学对煤炭用途的叙事一样,上述描写表明,对能源的驾驭能力是对铺展开来的历史叙事的实现。但这也说明了讨论能源时面对的另一个关键问题,即“能量”本身的模糊性。在斯迈尔斯的著作中,“这个国家的能量”可能是提醒人们总体上英国拥有的资源,以及实际上被用来实现这些奇妙的转化所使用的驱动力,包括煤炭和人力。但是,把这种能量称为“百折不挠的”且将它与“工匠无与伦比的技艺”联系并用,表明斯迈尔斯在这里也是把能量作为一种民族特性来谈论的。也就是说,实际上的能源被神秘化,不仅通过魔法和预言的想象,而且通过能量的产生方式,或将其视为英国人的特性。在巴克兰和其他人的思想中,我们也看到与这段话类似的文字,煤炭被想象成为上天对这个国家福佑的标志;似乎能源使用的景象更是有助于提升英国人的道德信力。“能量”一词让斯迈尔斯得以巧妙地应付出现的问题:他能一边谈论工业所用能量的实际物质基础,一边让它继续植根于能够证明它或使之成为可能的道德或精神品质中。工业产生的奇迹似乎并不建立于物质资源的基础上,而是出于国民特性。廷德尔在《作为一种运动形式的热》中对能量守恒的赞歌也提示人们,这个使用能量的新奇世界只是对一系列人们熟知的真理所做的另一种表达罢了。 但是人口的高速增长和城市中心能源的迅速消耗,正是生产主义对自然和创办的实业间可以轻易进行能量交换的兴趣所在。我们也许可以拿卡莱尔在《宪章运动》中对曼彻斯特的描述来举个例子,这座工业城市被描绘成自然能源的伟大表现: 你有没有听清周一早晨五点过半曼彻斯特觉醒的声音?那成千的工厂喧嚣繁忙,像大西洋潮澎湃奔涌,那上万的纱锭和线轴开始旋转轰隆—你若清楚,便应知晓,那正如尼亚加拉大瀑布,又或更甚于它。棉纺的结果是裸身者有所衣,而手段则是人对物质的胜利。 这便是用生产主义的语言描述出的城市。比尼亚加拉大瀑布更甚,如大西洋潮澎湃奔涌,曼彻斯特暗暗地替代了太阳的角色,它觉醒后的活动标志着一天的开始。卡莱尔还在其他地方清楚地表明,这样的场景从春天开始,纱厂的运转与太阳四季的周期运行步履一致。卡莱尔借助这样的图景,展示着一个崭新的曼彻斯特,并在其他能量形式和自然节奏里展现它的延续性。它们的差别在于,这些工厂还能因人类持续的努力而控制和组织能源,就像他在《时间的标志》中所说的,“与野蛮的自然做斗争”。生产主义的观点并不只是让工业和自然并行一致,它还要将自然转化成一种动力的来源。就像廷德尔在描述太阳驱动火车、开采矿石时所说的,同时出现的自然的工业化和工业的自然化摘除了所有的指涉,包括工厂工人、机器、容纳这一切的环境、消耗的自然资源,以及使得生产成为可能的其他具体因素。 那么,将欣欣向荣的城市纳入生产主义框架中就出现了一个问题,虽然我们可以把城市比作太阳,但是城市并不是能源,它也不受太阳能的驱动,而它耗费的巨大能源也不是不会产生严重的环境代价。虽然卡莱尔希望在他的比喻体系中将城市和刚刚释放出巨大力量的工业都包含进来,但是这些现象引发了一些困难,这是他的生产主义观点不能轻易改变的。特别是废弃物的问题,这在尝试着以自然周期的方式展现工业生产的过程中是个无法解决的难题。比如,读者可以注意一下《论英雄、英雄崇拜和历史上的英雄业绩》中的一段文字提到的能量(卡莱尔称之为“力量”)与废弃物的关系: 力量,力量,处处皆是力量。人们本身也是中心的一种神秘力量。“落在大路上的每片枯萎树叶中都有这种力量,否则,它怎能下落呢?”而且,还可以断言,对于信奉无神论的思想家来说,如果这种力量可能存在的话,这也必定是一个奇迹。这个巨大无限力量形成的旋风包围着世上人们,它永不停息,无边无际,永恒持久。 这里,掉落在大路上的一片枯叶,成为一种废弃物,它也被认为积极地参与到各种力量的关系网中。即便枯萎也是一种充满活力的行为,是完全协调的、富有生机的宇宙运行的一部分,正如他在《衣裳哲学》里所说的,宇宙中,没有什么是“孑然孤立、脱离开来的”,每一物都“与整体紧密相连”。这里,卡莱尔试图将自己的立场和他所认为的狭隘的笛卡尔派唯物主义者区分开来,因为他们将死亡的物质和活着的力量加以区别,并把运动视作离散粒子在空隙中的穿越行为。而卡莱尔采取这样的立场,就让自己和廷德尔这样年轻一代的科学唯物主义者的观点更为融洽。 但是有关废弃物的问题不会轻易地得到解决。如果和在这里一样,这废弃物像树叶一般,以有限的、单一的有机形态出现的话,他就能轻易地将其纳入自己有关力量关系的形而上学的体系中去:“不要轻视破旧布片,人类用它来造纸,也不要看轻枯枝地被,大地借它生长出谷物。如果我们正确地看待一切,那便没有什么卑微物体是毫无用处的;所有的物体都像一扇窗户,透过它,哲人的眼睛会看到无限。”一片枯叶,一块旧布,还有参与到农业生产自然周期中的那些“枯枝地被”:它们都是废弃物的不同版本,能在有机体的生长消亡这幅稳定的生态图上轻松地找到自己的位置,其结果也打开了一扇扇“窗户”——就像曼彻斯特一样——去观看把整个宇宙合为一个生产整体的奇特的力量原理。他写道:“这枯萎的落叶没有死亡也没有消失,它的内在和周围都有力量,尽管这种力量作用的次序有所颠倒。”这意味着某种轻易的、完全颠倒的能量经济的存在。 但其他大规模的、改变环境的废弃物形式就不能如此巧妙地融入这幅图景中来了。针对它们,卡莱尔运用形而上学这样的应急防护措施,将其抽象为寓言,或是从“真正的”自然过程中分离出来后本质上而言的某种附带现象。在《宪章运动》中,他问道:“什么是不义?”他的回答是:“那就是无序、虚假、不真实的另一个代名词,是构成自然的那些真实的东西所要拒绝和否认的,因为其自身并不是混乱,也不是废弃物造成的旋风般的毫无根据的幻象。”他说,自然并不是“废弃物造成的旋风般的”样子,因此,废弃物、混乱、无序只在道德范畴中是具有深意的;它们仅仅是人们感知的问题,因而从根本意义上来说,并不是真实的。他在《过去和现在》中也持有同样的观点:“我们把短暂的肤浅的表象误作永恒的核心的实质;我们已经脱离了这个宇宙的法则,现在却发现这无法则的混乱和愚蠢的喀迈拉就要将我们吞噬。”卡莱尔在这里并没有具体点明是哪一座城市,但是显然这令人晕眩的混乱和毫无法则的现象让我们想起那座城市。事实上,这段话与一系列的城市表述相吻合,这样的城市被设想成一种荒谬的集体幻觉。 卡莱尔将废弃物归结为“幻觉”,他在讨论曼彻斯特时,把这个问题推到了前台: 曼彻斯特,到处都是飞舞的棉絮,烟雾尘埃、喧嚣污秽,是否让你惊骇不已?其实不然:在这样恶浊的外包装之下,藏着一种珍贵的物质,美丽得如梦幻一般,但不是梦想而是现实;事实上,这外包装正在竭力挣扎……抛弃自我,让美丽得以自由且为人所见!……烟尘和绝望并不是它的本质[城市];它们都可以从中分离出来,在这个时刻,它们难道不是强烈地想要挣脱开来? 很显然,废弃物在这里仅仅作为一种知觉而存在,一种可以从现实中分离出来的外部表象。卡莱尔在能量中寻找叹为观止的生产力的可能性,但是为了让曼彻斯特与这种设计相吻合,生产性的产出,即“物质”,必须从它的副产品,即“外部表象”中分离出来,并把废弃物说成只是“外包装”而已。他提出,曼彻斯特出现的浪费问题反映了人们还不能认清“现实”,因此令人尴尬的是,看起来是反对浪费的立场,其实只是否认它的存在而已。卡莱尔和巴克兰一样,把废弃物看成是“某些人看到”的东西,而不是事物深层次的真实部分。这种把废弃物非物质化的观点将会再三出现在后面的章节中。 从这一点来看,卡莱尔所表现的城市也很有趣。尽管他在城市中找到了自然具有能量的新的可能方式,但那还只是一个理想,并且越来越难以维持。要建立一个形而上学的体系,以生产力和力量的不可毁灭性为前提,这意味着,生产力在城市中心实际上发挥作用需要能让其大展拳脚的场所。然而,这就不可避免地得出以下结论:这种力量必定产生废弃物和污染。卡莱尔试图“抛弃”“分离”,且更明显地是要“否认”这些废弃物,他显然是在信口胡说而已。这座城市的早晨,或许在某些方面与初升的太阳很相似,但实际上,城市并不能制造能量;相反地,它们依赖于地球能量储备的大量开采。它们排放出的废弃物也不能简单地说成是“以相反的方式作用的力”,因为这种轻易就能得到的顺序颠倒或者周期循环,正是城市消耗模式所要瓦解的。我们可以看出卡莱尔在这点上模棱两可,因为他在自己的著作中用很相似的方式来表达这种力量和废弃物含有的力量:自然被描述成“巨大无限力量形成的旋风包围着世上人们”,并且是“永不停息”的。但是他使用同样的意象,“废弃物造成的旋风般的”混乱 “就要将我们吞噬”,以此来表明在英国人口中心正在发生着生态破坏(除了别的现象之外)。卡莱尔想在能量运动的两种方式之间强加入一条道德分界线,尽管使用能量的方式很显然涉及道德的问题,但是人们越来越清楚,废弃物已经成为工业生产和城市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 正因如此,卡莱尔对曼彻斯特的颂扬最终是站不住脚的,因此在他的著作中也显得反常。他将自然和人类的能量形式合二为一的观点,也就常常需要他撤出城市中心: 让我们就在这里停下脚步,在田野上播下种子;在这里,让我们学会停歇。在这里,实际上,我们种植的果园就将结出累累的果实;橡子将长成高大的树木,提供一片宜人的阴凉,只要我们静心等待。只要我们静心等待,四处会有多少生机!我们将穿越湿地建造堤道,用力量去净化水渠;我们将跨越举步维艰的石岩;还有踏平的小径,仅仅用人脚即可夷为平地,它们也终将形成。没有哪一个困难不能将自身打磨成一次胜利。 建造堤道,而不是通衢大路;筑成小径,而不是火车铁轨;净化水渠,而不是下水道;重重困难奇迹般打磨着自我。这段文字是在隐去了日常的意象和环境之后,生产主义为工业和自然的合二为一献上的赞歌。这些发挥作用的力量都消失在行动者缺失的语言的迷雾中,就像廷德尔使用的太阳能动作用的修辞一样。这段文字没有受到资源有限性之类问题的困扰。当卡莱尔转向“煤炭的力量”时,就像下面这段摘选自《衣裳哲学》的文字所说的,他将其从可能引发问题的城市的地理环境中抹掉了: 我骑着马穿过黑森林,不免自说自话:这小小的如星子般的火焰在黑暗愈加浓郁(夜已将近的时分)的沼泽上闪烁,面庞乌黑的铁匠弯腰朝向他的铁砧,你呢,只是来换一对你丢失的马蹄—这是不是从整个宇宙上剥离下来的独立的、分开来的一小点?还是整个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你这愚蠢的家伙,这铁匠的火焰(根本上)就是来自太阳,自诺亚洪水发生之前、自天狼星在宇宙中运行以来就循环流动的空气护养着这簇火焰,其中产生了铁的力量、煤炭的力量以及奇特的人类的力量之间巧妙的契合关系、相互的斗争以及最后某种力量的胜利;它就像一个浩瀚的生物有机体身上的一个小小神经节或者神经中枢。 正如安德伍德所认为的,“将这幅图景投射在德国,而且是某个偏远的乡村,是让这个铁匠不仅在空间上而且在时间上远离伯明翰的工厂”。应该指出,廷德尔是如此推崇这段话,并用它来证明卡莱尔“充满诗意却也准确地预见到了能量守恒理论”。廷德尔研究出的系谱也在人们广泛争论的话题范围内,即谁能获得发现热力学第一定律的殊荣。但是它说明了人们对能量守恒和能量守恒定律的轻视;也就是,能量总是自动进行保存这样的形而上学的概念,和将能量视为一种数量上可测量的做功能力、一种资源的热力学概念。乔治·莱文认为,对于卡莱尔来说,“自然秩序将会再次坚定自己的立场,反对所有人为的机械的发明,这些发明以虽然是非理性的但又如神灵一般正义的能量来掩饰所有经验和生命来源及意义的连续性。在这样的道德和宗教力量的语境下,城市几乎无迹可寻”。虽然莱文在这篇论述中并未明确地给“能量”和“力量”刻上历史科学的记号,但他使用这些术语也正是想表明这样的语境。对于卡莱尔来说,能量依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不是一种资源,这也正是他将城市降格为一种“几乎无迹可寻”的现象的原因。 如果说起初能量把工业和自然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一个完美的、神意支持的生态整体,那么城市化进程,以及对巨额能量的日渐依赖和日夜不停的使用就会在19世纪中期引发了另一量耗竭相关的话语。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到了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紧迫性增加,城市里巨大的能源消耗使得人们广泛地关注到工业发展和资源使用不可持续的动态。实际上,在一些评论家眼中,消耗的能量数额让人们预见到,从煤炭供应、农场耕地到太阳本身,所有事物最终都将衰退。克里斯托弗·哈姆林认为,虽然在随之发生的大规模的工业行为和人口增长之前,城市可能会与环境保持一种“大体上的有机平衡”,但是“到19世纪40年代早期,当城市健康委员会本能地走进英国城市的后院时,这种平衡就到头了。在那里,譬如,污浊的下水道和化粪池中,高耸的垃圾和排泄物上,还有教堂墓地里甚至肢体裸露在外的、成堆的死尸里,他们发现大量的腐烂物质堆积着”。在维多利亚人的想象中,这些有机垃圾与能量紧密联系,我们将在下一部分详细讨论这个问题。要让人们注意到,工业和自然界之间默契的能量交换,曾经点燃了生产主义的想象,现在,它由于现代城市的出现而被逼入危境。虽然维多利亚人擅长于借助各种各样的形而上学和道德的外衣,遮蔽废弃物的物质特性,但他们还是没能了解如何在物质意义上将其从自己的生活经验中消除。 热力学定律,如同达尔文的进化论一样,给19世纪英国乃至此后的整个世界带来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现代世界的能源衰竭、环境污染、土壤退化、城市生态危机等问题,以及可持续发展的观念,可以说均与维多利亚时代息息相关。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文学家也将热力学叙事大量地写入他们那个时代的文本之中。 本书作者艾伦·麦克达菲综合了科学和文学的研究视野,重新回到马尔萨斯、T.H.赫胥黎、查尔斯·狄更斯、约翰·罗斯金、约瑟夫·康拉德等人的作品中,在维多利亚时代与当今21世纪的“后工业”社会之间建立起连续性,引导读者重新思考能量、资源、环境对于人类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