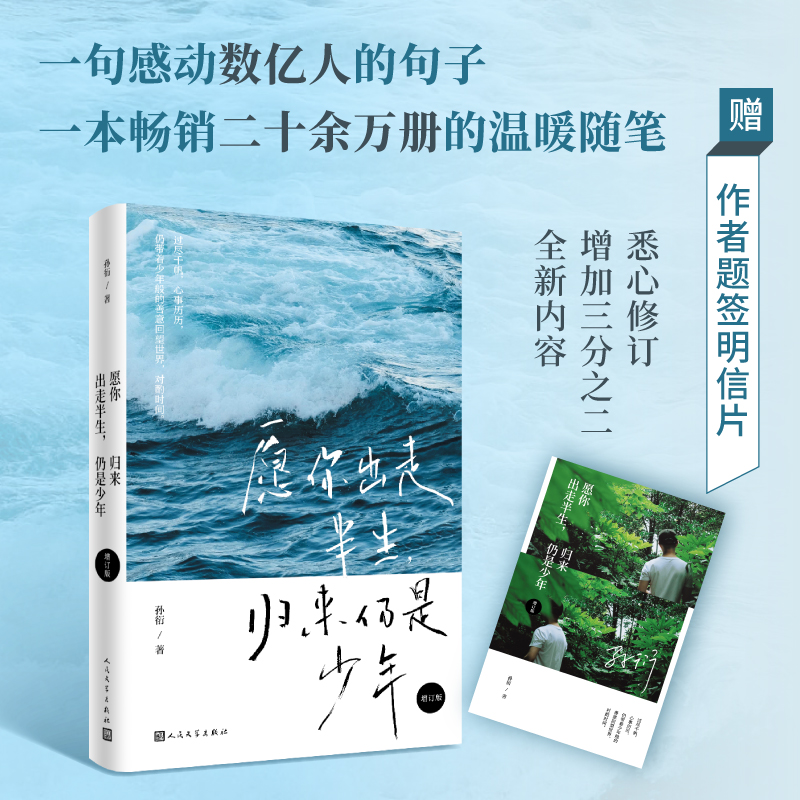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9.70
折扣购买: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增订版)
ISBN: 97870201816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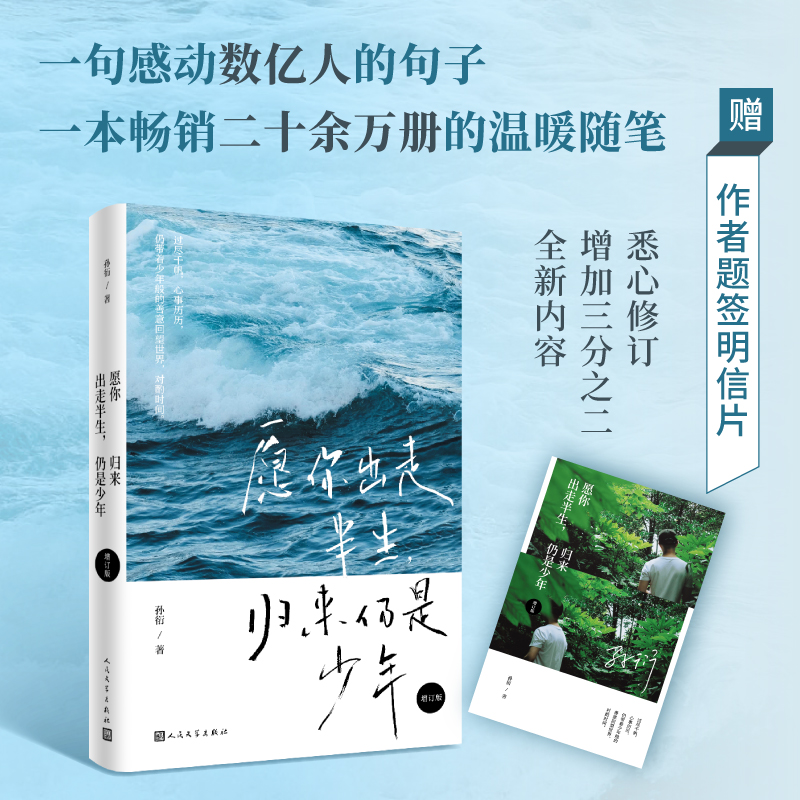
孙衍 豆瓣认证作者,书评影评人,情感励志专栏作家,书籍装帧设计师,江苏省作家协会会员。 作品散见于《解放军文艺》《散文诗》《美文》《读者》等报刊。著有《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生活一半是回忆,一半是继续》《愿你不遗余力,终有未来可期》等散文集。 《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曾屡次登上各大图书购物网站畅销排行榜,书名成为在大众中广泛传播的流行语,每年毕业季更是被频频写入众多高校的校长致辞。
少年飞走了 要不是我那次回家探亲时的骑行,或许我永远也不会再见到青了。青是我初中的同学,我们相处的时间不过半年他就退学了,后来便音信全无。 那年夏天,我骑着单车沿着郊区一条林荫大道行进的时候,青突然从路边出现了,他告诉我他家就在这里,他带我参观房前屋后种的那些绿色的植物,还有叫不出名的花,他还是那么喜欢花鸟虫鱼,像上学的时候一样。他告诉我,要不是在城里上班,家里也会养一些小动物的,实在无暇照顾,便只好作罢。 我们开始聊上学时候的趣事,就像发生在昨天一样。但显然,青的额头已经没有那时候的光洁,笑容也不再阳光,多了些生活强行赋予的艰涩。是啊,谁敢与岁月为敌呢?在时间面前,我们都是失败者。 那年暑假过后,青因为上学期生了一场奇怪的病,不得不休学,然后转学插班到了这个学校。我清晰地记得学校的围墙很高,高到像深宫大院,高到连夏天的风都难以吹进来。好歹学校的院子里有密密匝匝两个人也围抱不过来的梧桐树,宽大的叶子可以给予我们一丝阴凉。 刚入学的时候,我极不适应,经常自觉不自觉地盯着窗外的树叶发呆,仿佛那里装着另一个世界,神秘而又空洞。即将进入青春期的人是多思多虑的,但没有人会理会你。青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在我的面前的,他面庞清俊,明眸皓齿,干净得就像佳洁士广告里的小男生。 午休的时候,他笑着说我带你去一个地方吧,你一定喜欢。我跟着他跑了出去,穿过学校硕大的铁门,朝远处跑去。很快,我们到了一片杉树林,杉树林异常整齐,像整过队的士兵。里面也夹杂着一些其他的树种,比如松树、柏树,还有一些白杨和泡桐。走得深了,阳光似乎也不见了,里面黑压压的。青一直往里面跑,直到我们都气喘吁吁,他才停了下来,然后指着地上的一个草窝说:你看。 我下意识低下头,发现草丛里是一窝红彤彤的东西,那是一群初生的鲜活肉体,准确地说是一窝小老鼠,那些还透着红润光泽的小生命在草窝里耸动着。我胃中一阵翻涌,本能地后退了几步,直到撞到一棵树上。我双手扶到树上,感觉手中有些黏黏的。我一下子觉得糟透了,感觉受到了羞辱。但青却半蹲在地上笑了起来,他笑得上气不接下气,露出他洁白的牙齿。 我有些生气地说:“你够了,我不想再看到这种恶心的东西。” 青意识到我是真的生气了,便停止了狂笑,说:“你手里是不是摸到了什么?” 我点点头。 他说:“这是松香,这种东西还可以当蜡烛用呢,既能照明又能取暖,到了冬天你就知道这东西的好处了。” 我从树上将那团黏黏的白色结晶状物剥了下来,放到鼻尖闻了闻,果然有一些淡淡的清香。 青说:“你可以多剥一些下来,冬天的时候点燃它们,一定会又漂亮又暖和。”他边说着边在树上剥起了松香。 就是从那天开始,我们成了朋友,也是从那天开始,我才知道,一直以来那些小老鼠才是他真正的朋友,他并没有觉得那些小生命是人类的敌人,而是隔三岔五地去看它们,甚至他也会带一些食物过去给它们吃。在我看来这种事简直太不可思议了,但他却一直这样坚持着。 慢慢地,我适应了学校的生活,成绩也开始好了起来,老师也开始对我刮目相看,经常让我代表班级参加学校的一些知识竞赛、作文比赛、书画比赛等等。青似乎对这些并不感兴趣,他仍然每天往杉树林跑,他像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学习已然不那么重要。 青是那么喜欢大自然,他不但会带我去杉树林剥松香,还会带我去河边的一片银杏林,入秋后的银杏林一片金黄,青摘下一片放到我的手中说,你喜欢看书,可以拿回去当书签。然后他又奔跑了出去,回头大喊:“你快来看,猫头鹰,这里有猫头鹰。” 我顺着他的方向望去,一棵银杏的枝头真的栖着一只猫头鹰,那只猫头鹰个头不大,似乎并没有受到惊吓,正呆呆地望着我们。 青说:“猫头鹰是有灵性的,一般只有夜里才会出现,我们不要惊动它,不然它会去杉树林吃了那些小家伙。”青说这话的时候,神神秘秘的,好像有某种预兆似的。 相处久了,我才发现青其实并没有什么朋友,他的朋友是那些树、那些叶子、那些鸟类和小动物。他经常奔跑在大地上、树林里,还有秋天的风中。他把松香、银杏都给了我,好像这些与他无关,又好像他自己就是它们的一部分。 青的成绩一直不好,但植物学和动物学的课程却听得非常认真。也许,他就是为大自然而生的。 冬天到了,同学们都相约着上街买帽子手套,青有些迟疑,说:“我们可以用松香取暖啊。”我拉了他就走:“教室里可不能点燃松香的,老师发现了可怎么办?” 街上人并不多,我们穿过一条条巷子,像穿过一条条阴暗荒凉的河流。直到在一个商场的拐角处,青突然停止了脚步,他的眼神停留在前面一个摆地摊的人身上,那是个个头很矮小的中年人,穿着一身破旧的蓝色卡其布衣服,衣服很旧了,甚至有些地方有了破洞。他佝偻着腰蹲在地上,面前是一个同样破旧的编织袋,上面放着一些类似方便面调料包的小物件。青眼睛直直地看着那个人,然后忽然掉转身,朝后跑去。我大声想喊住他,但他一眨眼工夫就不见了。 前面的同学回头看着青远去的身影,有的沉默不语,有的嘴角发出轻蔑的笑。但最终还是有同学说出了真相,那个中年人是他的父亲,摊位上摆放的其实是老鼠药,而他的母亲因为精神失常早早失去了劳动能力,全家就靠他父亲卖老鼠药为生。 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青是那样地不合群,那么爱那些不具攻击性的植物,那么想要去保护那些落荒的小老鼠。他从不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也不和同学有任何学习上的交流,他总是像我当初那样,望着窗外的树叶发呆,偶尔一只鸟儿飞过,也能让他半晌回不过神来。或许就是因为我也有过这样的目光,才让他觉得我可以成为他的朋友。 那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还未到放寒假的日子,河面上已经结了厚厚的冰,这在江南是十分罕见的。青经常在课间休息时跑到河边敲一些冰块回来,放在路边,再点上松香,看着冰块一点点在松香的暖意里融化,然后笑得前仰后合。 他说:“你看,你快看,冰融化了,松香是不是可以取暖?” 临近期末考试,班主任开始找同学们轮流谈话。我们看着同学们一个个从教室离开,每个人回来时的表情都不一样,仿佛刚刚经历过一场拷问,有的释然,有的困惑,有的振奋,有的颓唐。但我们还那么年轻啊,又有多少人会懂得少年的愁从何而来,恰恰可能就是因为不经意的一次谈话,一个眼神,我们便茶饭不思,夜不能寐。 自从那次谈话后,青便消失了,第二天他的座位便空空如也。他像冬天的候鸟一样飞走了。 青边给花草浇水边招待我坐下,说要留我吃饭,我执意要离开,骑行刚刚开始,路还很遥远,我不能就此停下来。临上路的时候,我一只脚踩着脚踏板,发出哗啦啦的声响,像停不下来的光阴。 我问他:“青,你当时为什么要退学?” 青先是摇了摇头,说:“你也知道我家的情况,而且班主任找我谈过话,让我不要和你在一起玩,怕影响到你学习。我觉得这样上下去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感到震惊又生气,因为班主任的一段话,我就失去了青这个好朋友。 我不知道是怎样离开青的家的,逝去的友情却再也找不回来。 文艺,一种温柔抵抗世界的方式 从前,提到“文艺青年”,大约是说这个人爱看书,喜欢舞文弄墨;喜欢音乐,差不多达到发烧友的水准;爱好电影,对于电影人和文艺片如数家珍…… 不知何时开始,“文艺青年”这个词已经变得陌生,大家都唯恐被贴上“文艺青年”的标签,仿佛“文艺青年”是避之不及的一类特殊人群。 有个周末,我赶着去书店做讲座,半路上却发现相机落在了办公室,当我返回写字楼下时,才知道电梯出了故障。我只好将手上的两本诗集放到了前台的大叔那里,让他暂时帮忙保管。当我气喘吁吁地飞身下来时,那位大叔正津津有味地读着其中一本诗集,他都没有意识到有个人站在他的面前。 我抱歉地表示我要赶时间。他才将诗集递过来,并对我说:“能送我一本吗?”我说这是做讲座用的,总共才这两本,给了你我讲座就做不起来了。如果你喜欢,回头我再送你。 前两年,我都会跟着我们的发行同事去仓库清理书目,将已过版权期的图书销毁,再将新书放到显眼的位置,并贴上标签。理货员师傅一直在喋喋不休地说着他们理货的不易,不停地进货出货退货理货,打包裹,上架子,填单子,他们好多人年纪并不大,但看上去都很憔悴。成天在暗无天日的仓库里劳作,看上去像一个个饱经沧桑的老人。 活做到一半,我发现有个理货员师傅坐在一辆铲车上,正默默地读着一本书,书封正是我编辑的一本书,他认真地读着,旁若无人,在昏暗的灯光下,他犹如一个忘我的思想者,置自己于世界之外。我有些愤懑地对发行同事说,谁说这书不好卖的,你们看,连一个理货员都在读! 有一阵子,总有陌生的作者到编辑部投稿。投稿的作者里往往年纪大得多,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占多数。他们来的时候,往往随身带着一个背包,背包鼓鼓囊囊的。进了我们办公室,他们会很客气,声音洪亮的会说,这是编辑部吗?请问向你们投稿找谁?这种大概率退休前是一个领导,习惯了大声说话。也有人小心翼翼地,敲了门也不进来,站在门口,嘴唇哆嗦,话语也不清不楚,原来是从外地来的,口音又重,这种可能是在某个小城市谋过职位,现在赋闲在家就重拾写作爱好。 这些老人都有个共同的特征,喜欢写长篇小说,洋洋洒洒几十万字,小说里的故事都是亲身经历的,他们希望通过小说来记录自己的人生。我记得有一个将近八十岁的老人,看上去精气神非常好,他过来的时候,身后跟着个中年人,说是他的女婿。老人的小说记录了他从年轻时当兵,退伍,进入国企,又下海经商,经历商战。可以说故事非常精彩,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史,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侧面。女婿说,老丈人退休后就一直在家里写作,已经写了十几年了,他年轻的时候就喜欢写作,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加上工作后很快走上了领导岗位,就把写作这事搁置了。退休后,就想好好地写,把自己一生的故事写下来。 也有对爱好至死不渝的,比如有的老人喜欢写对联,创作的对联有几百副,甚至上千副,自己找印刷厂做了假书,递过来的时候已经翻得很不像样。看样子,他对自己的作品很是珍视,爱不释手地翻阅了无数遍。写诗的,作画的,大致也是如此,他们会像集邮的、钓鱼的那些老人一样,对于自己的作品爱护有加,总是要想办法把它们变成出版物。 参加一个学习班,认识了几个年轻的诗人。其中有一个在街道上班,这让我们很讶异。他说自己也是通过艰难的考试才获得这份工作的,为了生存嘛。但他更爱的是写诗,他喜欢在不被人关注的角落写诗。我常常看到他,在闲暇时,独自在一旁,烟一根接着一根地抽,看到我们过来,会说抱歉。他是怎样一个年轻的诗人呢?后来,我看到他的诗,惊为天人。字数不多,行数不多,但就在那仅有的数十个文字里,却有一种力量。大约是他在基层工作,见多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尤其懂得人之艰辛,知道生的力量。他曾经跟我说,写诗太苦了,相较于写小说和散文,写诗似乎永无出头之日。但他又说,是真的喜欢,没有诗,大概就找不到任何存在的理由。诗歌和其他文学载体一样,真的会成为一种信仰吧,可以支撑一个年轻人,不舍昼夜,面对长长短短的句子,深耕不辍,不问前程。 这个世界从来都不缺乏喜爱文艺的人,我小时候认识的一个姐姐,她曾经疯狂地迷恋唱歌,写小说,她敢爱敢恨,逃避父母安排的相亲离家出走,与相爱的男友私奔,做尽了一个文艺青年所能做“离经叛道”的事。后来,她像一条被打捞的鱼终被收入网中,每天带着孩子过起所谓“正常人”的生活。 不知道从何时起,我们忘记了那个爱好文艺的自己,就像我们永远不知道,这个世界的真正走向。但至少,我们懂得读书的意义,还有思考的重量。没有这些,这个社会只会更加糟糕,污浊之气会填满每个角落,暴戾会更加横行,文艺,是我们温柔抵抗世界的一种方式。 一个看门大叔,一个仓库的理货员,一个执迷于文字的退休老人,一个基层的诗人,在工作之外,他们还有自己的一方小天地可以凝神自处。即使现实的枪一直指着自己,依然可以从容不迫。 1. 由畅销书作家孙衍创作,用近五十篇在豆瓣上创造10万+阅读量的走心文字,记录成长中的人和事,讲述那些隐藏在成长过程中念念不忘的深切感受,给每一个曾经的你,和回不去的自己。 2. 一句感动数亿人的句子,一本畅销二十余万册的温暖随笔。一篇篇故事平静中有曲婉,一行行文字尽显真诚雅丽。故乡风物 、军旅生活 、民间高手、世情人心,作者悉心修订,增加三分之二全新内容。 3. 苏童(作家、茅盾文学奖获得者)| 葛亮(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韩松落(作家)| 石钟山(作家、编剧)| 徐海(凤凰传媒总编辑)| 黄梦莹(青年演员)| 赵丹(荐书人)| 阿束(电台主持人)| 好妹妹(独立音乐人)| 阿SAM(生活家、畅销书作家)| 宋小君(畅销书作家、热门IP制造者)| 黄进(中国政法大学校长)| 鹿菏(作家、人气画师)| 聂昌硕(版画家、书画收藏家) 温柔推荐。 4. 这本书是一个人的生活史,亦是一个人的心灵史,《愿你出走半生,归来仍是少年》(增订版)传递的是这样的生命体验——希望的种子始终不曾干枯,热情的动力始终不肯懈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