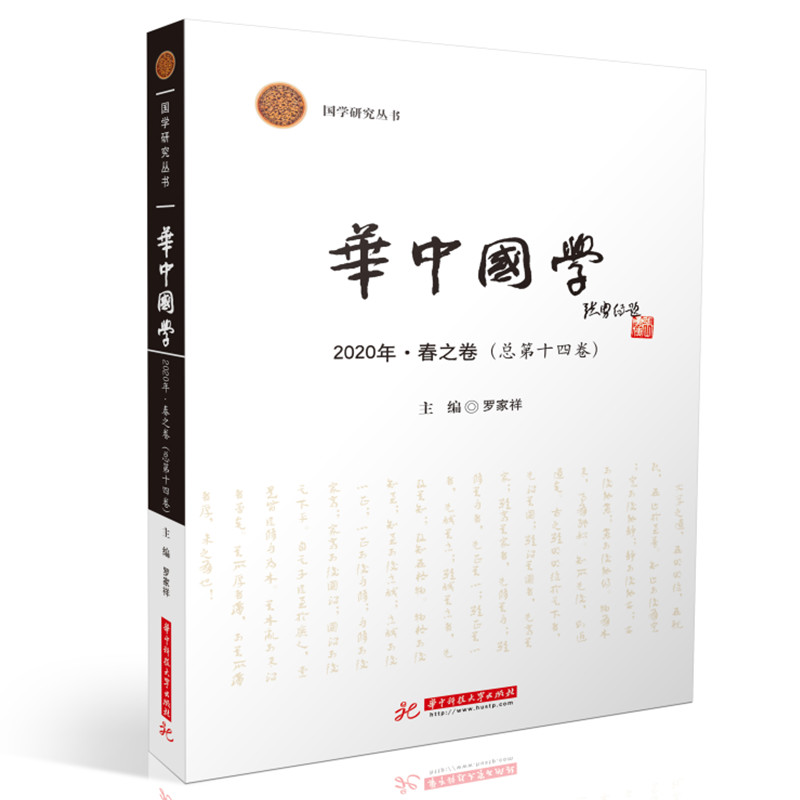
出版社: 华中科技大学
原售价: 88.00
折扣价: 56.40
折扣购买: 华中国学 2020·春之卷(总第十四卷)
ISBN: 97875680782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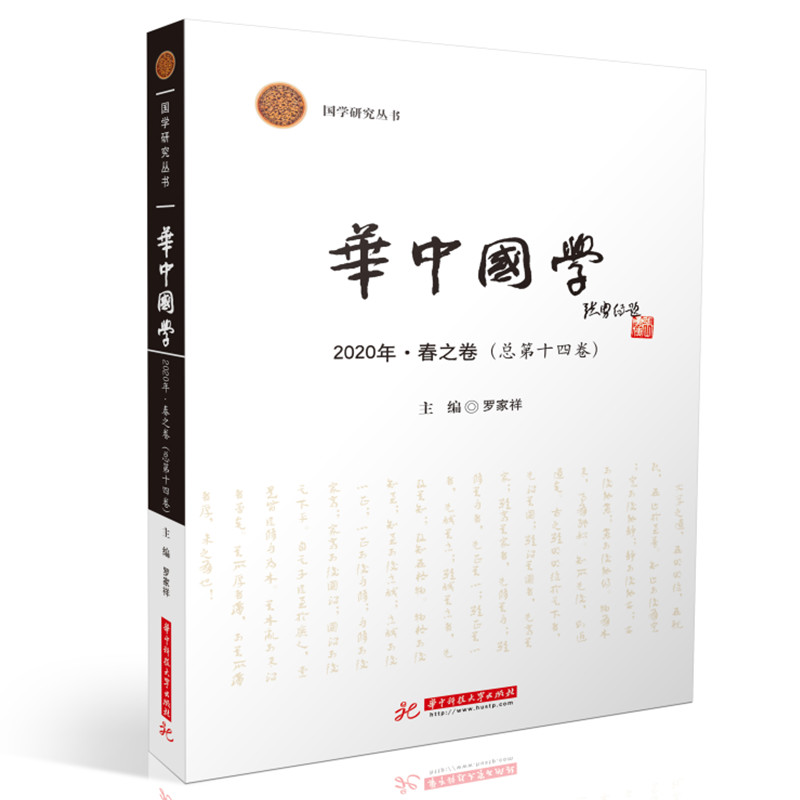
1957 年生,湖北天门人,现任华中科技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华中科技大学人文学院和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导师、国学研究院院长、人文学院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兼任教育部历史学科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宋史研究会理事、湖北省历史学会副秘书长。两宋政治史、两宋学术文化史方向学术带头人。 分别于1982、1985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学位;198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获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已故著名历史学家邓广铭教授。1993 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 1993 年 9 月- 1995 年 9 月应邀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 1996 年被破格晋升为教授。湖北省跨世纪学术带头人。先后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历史文化学院副院长。 2001 年 3 月调入华中科技大学组建历史学科。入选2005-06年度中美富布莱特学者,并应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邀请赴该系进行为期一年的学术活动,其间应邀赴得克萨斯大学历史系(El Paso)进行学术讲座。获选华中科技大学2009年“我*喜爱的导师”,华中科技大学2011年十佳“师德先进个人”。曾先后承担国家社科基金办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与宋代社会》、教育部下达的科研项目《王氏新学研究》、教育部优秀青年教师基金资助的《从新学到理学 ――11 世纪后半至 13 世纪初年宋学主流的嬗递》等课题。目前承担有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规划类项目《两宋学术嬗递与政治变迁》。独著、合著学术著作 5 部,合译学术著作 1 部,在《中国史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 50 余篇。代表作有《北宋党争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宋代政治与学术论稿》(香港华夏文化艺术出版社)等。
精彩文摘1: 第一句话:明确问题意识。 问题意识是指要解决的一个什么问题。“问题意识”大家都在使用,一讲到写作都要说“问题意识”,至于什么是问题意识,很少有人解释,总觉得是一个我们可以意会、可以理解的东西。其实按照我的说法,关于选题价值的理性自觉,这就是问题意识。选择一个问题的时候一定首先要明白这个问题,而不是说看到一个问题,关于它目前的研究是空白的就去盲目选择。没有研究过的问题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去研究。过去也就是我们年轻的时候,前辈老师(包括一些编辑部的主编)讲写作,强调“三新”,想要发表文章,“三新”至少具备“一新”。第一个是新观点,第二个是新材料,第三个是新方法。文章的写作,“三新”必具其一,*好是三者都有,才有发表的价值。其实在我看来,“三新”还是不够的。新的东西,哪怕是一个新的观点,真的就一定有价值吗?我做了《史学月刊》主编十六年,从主编位置退下来以后又做了六年的编辑,经常在出去开会的时候碰到一些年轻人说自己的文章下了很大的功夫、包含某个新问题或者新观点,结果却被退稿。我想说的是,文章研究的是一个没有人涉足的新问题,应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别人确实没有发现这个问题,你发现了,这确实是一个独到之处;另一种情况是别人曾经也发现过,却认为没有什么研究的价值。如果是第二种情况,那就不能仅仅因为别人没有研究过而认为有价值。所以选题这个问题,一定要考虑到选题价值。 什么是问题意识?就是关于选题价值的理性自觉。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价值何在?我在跟同学们讲论文写作的时候,讲到三句话。这三句话是从一开始选题到写作,再到文章写完,一直都需要思考的。第一句话:我提出的是一个什么问题。也就是说,首先要明白自己说的是个什么问题。现在存在一种现象,就是年轻人找不到选题,抓到一个问题就写,看到一个问题就兴奋,不考虑这个问题是什么,认为只要别人没写过,那就是一个新问题。要明白自己提出的问题是什么、它属于什么学科范畴、它是在怎样的学术背景下提出来的,等等,要心里有数。第二句话:我为什么要研究这个问题。现在学界有很多论文没有明确的问题意识,原因就在于这些文章不是真正为了学术,而是为了功利。作为教师需要评职称,作为学生需要毕业、拿奖学金等,所以很多人抓到问题就去做,而不考虑问题的价值何在。第三句话:这个问题的解决将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一个问题被认为有价值,那么这个问题解决之后,在学术界会产生什么影响,它会影响到哪些人,哪些人看了就痛快,哪些人看了会不高兴……文章一定要有影响力,人们只有真正了解文章的价值、文章将会产生什么影响,才会真正地被它激励起来。我觉得,写作对学术有所建树,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不能不考虑它的价值。历史研究是为了活人而不是为了死人,我们要研究它,就是因为它依然影响到今天,研究它会对今人产生什么影响,使今人有所借鉴,这是历史研究的目的所在。我不赞成过去有些学者“为历史而历史”的说法,那是自欺欺人。历史上留下来的任何伟大的作品,都有着对现实人类命运的深切关怀,这些作品中一定跳动着现实的脉搏。这样的作品才能激荡现实人的心灵,才会有生命力。 选题有两个标准,一个是社会价值,一个是学术价值,一般都是这样讲的。所谓社会价值,就是这个研究为现实人类提供了借鉴,能够给人以启发。前些年我做过居延汉简相关研究,发表了十几篇文章,出版了两本著作,但这些在我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因为这些研究距离现实很远。除此之外的研究,我个人觉得都是出于对现实的思考和关怀。我在2016年发表的关于“秦至清皇权专制社会说”的一组文章,回答秦到清这两千多年中国社会究竟是个什么状况,我简单地把这一时期叫做“皇权专制社会”。人们对其常识性的认识也是专制社会,我就要论证为什么把它称为“专制”,专制体现在哪些方面,于是从理论上、思想上等方面写了五六篇文章来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也确确实实有一定的影响。如果大家想要再看我的文章,可以看2013年我在《中国史研究》上发表的《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如果我这一生要选出来一个代表作,这篇文章我觉得是可以作为代表作的,它反映了我对治学的一种理念。其实历史学家,或者说只要是从事历史学研究的学者的问题都来源于现实。真正的历史研究都来源于现实,从现实中获得启发,再由这种启发去回溯历史,从历史的相关事实研究中寻找现实的答案。其实,正如英国学者卡尔说的,历史研究就是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对话,是现在跟过去之间的永无止境的问答交谈。我们代表现实,现实与历史对话,这就是历史研究。离开现实,我们就没有选题;远离现实的选题,在我看来很多都是无病呻吟。大家现在刚读研究生,对学术界的状况可能还没有多少了解。实际上,我对中国的学术现状并不乐观。我在2006年上海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发言,讲到现在的学术研究,评价它是“三无”史学,即无理论、无个性、无灵魂,这一说法引起哗然。有些文章对于社会、对于学术,可有可无。我不是在故意贬低我们当代史学,而是我自己的真心感受。 文章不是随便写的,解决一个具体问题一定要有它的社会价值,除了社会价值这样一种判断以外,还有一种文章不可能直接关系到社会现实,因为史学大厦的建构是需要一块一块砖积累起来的,是需要有深厚的基础支撑的。整个历史学的功能是关乎现实的,但不能要求每一项具体的历史学研究都直接与现实挂钩,所以第二个标准是学术标准。除了社会价值、社会标准以外,还有学术价值、学术标准。这个学术标准不是很随意的,比如前边说到的“别人没写过的就是有学术价值的”。这个学术标准是指研究的问题一定是一个学术链条中的节点。比如某一个问题在学界已经有了多年的研究,但是还有许多缺环,你的研究补充了其中一个缺环,这样就可以称之为学术价值。如果研究的问题与学术史没有关系,不属于任何学术领域、任何学术链条中的一环,完全是孤零零的一个具体的历史现象,那么它的研究对现实、对学术没有任何意义,这样的选题就没有什么意思。过去讲写作选题,人们经常举这样的例子:有人研究洪秀全到底有没有胡子,这个问题对于历史博物馆悬挂洪秀全画像到底怎么画胡子可能有意义,但是画不画胡子都是洪秀全,其实没有多大意义;有人研究杨贵妃入宫前到底是不是处女,这样的研究有什么意义呢?一个人老是做这样的文章,你即使发表了上百篇乃至几百篇文章,大概也无法成为专家,充其量是个杂家。所以研究的问题要么具有社会价值,要么具有学术价值。如果有社会价值,就一定有学术价值;如果不能保证有社会价值,那么一定要有学术价值。这两者是判断选题是否有意义的重要标准。 同学们现在都想写论文,选题从哪里来?大家可能很希望从别人那里得到一个题目。题目从哪里来,我觉得没有多少好的途径或办法。大体上说,一个是我刚说到的选题要具有现实意义,我们可以从现实中寻找灵感,这就提倡我们都要关注社会现实,要有很强的政治使命感,为现实人类服务。这个政治使命感,是为了现实人类的命运,比如中国要走向文明、民主、法治,要走向人的解放,要实现人类的命运,就要尊重人的个性,培养建设真正的独立人格等。这才是关注现实,而不是说关注现实政策。如果我们从现实中获得启迪,那么我想写出来的文章是有价值的。之前提到的我的代表作、反映我学术理念的文章——《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这篇文章的灵感就来源于现实。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在中国化的进程中,曾达到教条主义、公式化那样登峰造极的地步,给中国民族带来如此之大的灾难,为什么?马克思主义是科学,而且我非常尊崇、敬仰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个人。我专门为这两个人写过一本书——《伟大的人格》,主要写马克思、恩格斯的人格精神,这本书于1992年出版。我非常佩服这两个人,但我是把他们作为学者、科学家、探索者来佩服的,至于他们的思想理论如何,则另当别论。探索是一个过程,有可能得到的东西非常符合历史化的进程,但是也有可能并不符合,这些是次要的,关键是真正的探索。马克思、恩格斯的理论成果在中国的命运为什么走向了教条主义?我就在思考这些问题。我总觉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走向这样的地步是有一定原因的,一定是有违背学术发展规律的因素干扰了它。在秦汉史研究中,我看到汉代儒学变成经学,恰恰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是一个很悲惨的命运。孔子创立儒学,任何人都可以对它进行解释,孟子、荀子都对它有进一步的发展,因而在战国时期的儒学,作为一种可以被发展的学术就有着鲜活的生命力。但当汉代“独尊儒术”,儒学变成国家意识形态以后,它就成为一种非批判性的学术。真正的学术本质是批判的,而经学的本质是非批判的。两千年至今的经学是怎么做的?它的随听疏》时,考定法成其人为吐蕃沙门,生当唐文宗太和之世,译经于沙州、甘州。其与玄奘相比,两人都是“沟通东西学术,一代文化所托命之人。”陈寅恪先生是学术界第一位论述藏族杰出翻译家法成事迹的学者。陈寅恪:《大乘稻芊经随听疏跋》,《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254255页。敦煌佛经中有些经卷写于南朝或南方,考其题记年月地名可知。陈寅恪先生认为这些经卷是隋太祖武元皇帝杨忠(隋文帝杨坚之父)携往西北,遂散在人间,留传至于今日。因为杨忠曾是西魏遣攻梁诸将中的一员,其人*为信佛,江陵既下,城内所藏佛经尽为其所有,后为泾豳灵云盐显六州总管,居西北之地凡五岁之久。这当然是陈寅恪先生的一个大胆假设,但也并非没有道理。陈寅恪:《敦煌石室写经题记汇编序》,《金明馆从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第200206页。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高僧的著述也多有研究。《大乘起信论》相传为古印度马鸣所作,有南朝梁陈间真谛的译本,但近人多认为是南朝时人所伪撰。《大乘起信论》前有真谛弟子智恺序,有人亦认为是伪序。陈先生在《梁译大乘起信论伪智恺序中之真史料》一文中认为智恺序中“值京邑英贤慧显智恺昙振慧旻与假黄钺大将军萧公勃以大梁承圣三年岁次癸酉九月十日于衡州始光郡建兴寺敬请法师敷演大乘,阐扬秘典,示导迷途,遂翻译斯论一卷”一节为实录。陈先生从两个方面加以证明:一为年月地理之关系,二为官制掌故之关系。陈先生进一步提出:“至以前考证大乘起信论之伪者,多据《历代三宝记》立据,其实费书所记真谛翻译经论之年月地址亦有问题,殊有再加检讨之必要。”陈寅恪先生在《南岳大师立誓愿文跋》一文中对佛教天台宗创始人智顗发愿文的真伪进行了研究。陈先生从誓愿文中年历、地理二事及当时社会文化状况背景,还有天台宗学说的根据来源论证了誓愿文决非伪作,从而恢复了“其书不独研求中古思想史者,应视为重要资料,实亦古人自著年谱*早者之一”的历史地位。《大乘义章》、《大乘法苑义林章》、《宗镜录》是我国集录佛教各宗教义的三部专书。陈寅恪先生《大乘义章书后》:“当六朝之季,综贯包罗数百年间南北两朝诸家宗派学说异同之人,实为慧远。远公事迹见道宣《继高僧传》捌。其所著《大乘义章》一书,乃六朝佛教之总汇。道宣所谓‘佛法纲要尽于此焉’者也。”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61页。 *后我们来谈一谈陈寅恪先生在道教史上的研究成果。 道教创始于东汉后期,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陈寅恪先生在30年代曾撰写了《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这是研究早期道教*有功力的文章之一。陈先生详细考证了天师道的起源及与滨海地域的关系,还论证了早期道教与两晋南北朝政局的关系。由于“魏晋南北朝之学术、宗教皆与家族、地域两点不可分离”,陈先生在该文中还详细论述了两晋南北朝的天师道世家及天师道在全国的传播情况。但是,陈先生对早期道教“悉用滨海地域一贯之观念以为解释”似嫌牵强;将张角混同于天师道,又属失考。这当然是白璧微瑕。继《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之后,陈寅恪先生于1950年又发表了《崔浩与寇谦之》一文,阐述了北魏时期儒道相互利用,少数民族统治者与汉人大族互相利用的政治特点。该文考证,寇氏为秦雍大族,世奉天师道,在曹魏时与张鲁一起迁入中原。崔浩为清河望族,也是天师道世家。该文又指出,道教每一次改革,必受一种外来学说的刺激,寇谦之即袭佛教律学改造旧天师道。该文可以看作《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的续篇。陈寅恪先生这两篇关于道教史的文章淋漓尽致地发挥了他关于宗教与政治终不能无所关涉的见解,给了我们以许多有益的启迪。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47、89140页。 我们从上述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成果不难看出,陈先生的研究着眼点很高,结论很精僻。陈寅恪先生一生研治的重点是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历史。大家知道,中古时期的历史具有极其丰富的内容,中古时期是中国思想文化*活跃的时期,也是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交汇冲突*激烈的时期,*突出的表现就是佛教的传入及道教的兴起。陈寅恪先生把它们当做中古历史的组成部分来研究,将它们放到当时的社会状况中去考察,因而也就取得了许多超越时人的成就。 精彩文摘4: 本书含有两条明暗相交的发展脉络:一是唐蕃古道开通后唐蕃关系几度变迁的客观历史事实;二是考察团队沿着唐蕃古道的走向依次推进考察,感悟并阐述这一段历史事实的前因后果。作者将历史书写与现实活动紧密结合,用实际考察行踪推动行文发展,叙述方式别有特色,主要体现在以下三点。 第一,在古代文献记载的基础上,根据考古实物和实地调查的方法,通过调研行纪的方式描述历史遗存的分布与现状。一般人认为田野考察对近现代的历史研究有很大帮忙,对古代史研究的价值就很有限了。近代以来,我国西部地区虽然也有很大变化,但因为有山川的限制,相对于东部平原地区来说,交通变化非常小,民众的生活方式也保留着很多历史遗存。所以,要研究中国古代历史的发展,对西部地区进行田野考察也是必不可少的方式,会获得意想不到的收获。民国以来,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唐蕃古道的考察。民国时期吴景敖著《西陲史地研究》,对“吐谷浑通南朝罽宾之路”“河湟洮岷吐蕃之通路”“党项故道与尼波罗故道”等道路以及涉及的岷州、洮州等地进行了实地考证,绘制了“唐蕃茶马市易干线图”“唐蕃交通要道清水界路图”等,为唐蕃史地研究奠定了基础。马鹤天《甘青藏边区考察记》叙述了作者自西宁南行经玉树入藏的经历,对沿途的社会风貌、自然环境做了详细的记录。青海省博物馆与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在19831985年间,进行了六个月的“唐蕃古道”实地考察,出版了《唐蕃古道考察记》唐蕃古道考察队编:《唐蕃古道考察记》,陕西旅游出版社,1989年版。。此书副主编之一的考察队成员陈小平还著有《唐蕃古道》一书,先从长安到逻些(拉萨)涉及的地名、路程及其历史记载,而后用近一半篇幅讲述了自己参与“唐蕃古道考察队”的见闻陈小平:《唐蕃古道》,三秦出版社,1989年版。。胡戟、齐茂椿根据2006年10月从拉萨出发沿唐蕃古道至西安的考察,著有《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胡戟、齐茂椿:《重走唐蕃古道:接文成公主回娘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从长安到拉萨:2014唐蕃古道考察纪行》则记录了陕、甘、青、川、藏五省区考古院所联合在2014年对唐蕃古道进行的考察资料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等编:《从长安到拉萨:2014唐蕃古道考察纪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这些学者考察的视角不一,行文撰写方式也不同,多偏重于纪行,历史感不是很强,但这种亲身前往实地考察的精神一直鼓舞着后世学者,为今人的研究打下基础。张教授《唐蕃古道》一书,正是对前人躬亲探索精神之继承,他自驾一辆桑塔纳小轿车,克服各种困难,以文成公主和亲吐蕃为线索,对于涉及到的遗址遗存都尽量亲自前往踏查并搜集一手资料。 第二,以唐蕃古道为线索,体现出青藏高原相关遗址考察与沿途广大区域的点与面的有机结合,为历史考察活动提供了新视角和思路。古往今来汉藏两地之间大规模的地理变动极少,从遗址遗存的实地调研与考察来分析历史事件具有相当的可行性。《唐蕃古道》在实地走访调查的基础上,梳理了从长安至逻些相关的历史文化遗存。尤其在青海、甘南一带,那里是唐蕃拉锯的重点地区之一,分散着大量遗址点,是历史事件的重要载体,如石堡城遗址、日月山遗址、大非川遗址等,都是唐蕃之间曾经爆发的重要战役的见证。本书以唐蕃古道为线,通过实地走访和观测将沿途的遗址点串联起来,在相应的历史背景下对比其地理形态,对唐蕃之间战略、战术的分析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与前人的考察纪行相比,更具有学术性。本书涉及的考察范围广阔,以唐蕃关系为主要背景,但并不囿于唐代,上溯昌都澜沧江畔的卡若遗址、柴达木盆地都兰县诺木洪等史前时期遗址,探索当地的历史渊源;下至清代治理西藏的策略、相关历史遗迹以及当今西藏交通网络建设、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历史借鉴。行文中又以文献记载与调查实况相互印证,如将河西走廊上的弘化公主墓、凉州会谈的白塔寺等遗址作为相关文献记载的史料补充,并广泛吸取前人的见闻记录,与当下的实景进行对比,尽量保证历史事件和遗址调查信息的完整性,展现不同区域、不同时代的文化联系。 对于有着丰富人文内涵的自然遗迹,书中也着墨较多,青藏高原雪山林立,湖泊众多,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本书对吐蕃进入西域的天然通道之一昆仑山、松赞干布迎亲的鄂陵湖畔等皆有论述。在史学论述中也能够守正出新,将历史知识融入考察行纪中,突破了长久以来青藏高原历史研究过于注重文献的局限,增加了实考察的印证,有助于我们进一步了解唐蕃之间关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的交流情况。 第三,阐发了唐蕃古道新的时代特征。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唐蕃古道作为丝绸之路南线的重要交通网络,将青藏高原纳入了东西文明交流的体系中,同时又从拉萨延伸至琼结、日喀则,越过喜马拉雅山脉至尼泊尔、印度等国家,连通东亚大陆与南亚次大陆,使得西藏打破了封闭的自然地理的局限,成为经济文化互动的交通枢纽。唐蕃古道成为青藏高原文明*终融入到中华文明体系强有力的纽带,并与“高原丝绸之路”共同体现了道路交通对于青藏高原经济文化发展的重要价值,这正是对“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的全新阐释。 当然,对于大众读物来讲,资料的丰富程度更能提升图书的吸引力,该书在资料使用方面还可进一步完善,一方面尽可能多利用自己拍摄的图片,注明拍摄时间,另一方面如若不得不使用他人的图片时要详细注明出处。由于藏区同汉地之间存在的地理阻隔与语言文字的障碍,使得藏地一直处于神秘、封闭的态势,大众对其历史渊源的了解有限。唐代虽有诸多关于吐蕃的记载,但局限性较大,如吐蕃势力曾在西域活动了170余年,在新、旧唐书的《吐蕃传》以及《册府元龟》《资治通鉴》《全唐文》等史料对此都有所记载,但侧重于军事争夺,对吐蕃在当地的行政组织、社会生产等情况语焉不详,这就突出了藏地史籍材料的重要性。公元7世纪吐蕃本土文字产生之前,民间流传着大量传说,可作为史实的重要辅助材料,后世又不断产生了大量藏地史书,诸如《红史》《青史》《郎氏宗谱》《汉藏史集》《萨迦世系史》《新红史》《西藏王臣史》《卫藏圣迹志》《西藏王统纪年》《巴协》等著述,虽然其中一些史籍不可避免地蒙上教法的色彩,但不失为通俗读物中丰富的原材料。藏族历史名著《贤者喜宴》中记载了这样一则故事:达日年塞赞时幼为盲童,请“小邦吐谷浑王”前来医治,吐谷浑王前去医治王子时,并未见到吐蕃王,而是从悬挂着饰以松耳石的王子小靴之门穿门而入。而当吐谷浑王的母亲得知此事,便作出了“将被置以吐蕃统治之下”的预言,后来吐谷浑果然被吐蕃所灭,属民尽归吐蕃巴卧·祖拉陈瓦著,黄颢、周润年译注:《贤者喜宴——吐蕃史译注》,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唐蕃古道》一书有选择性地吸纳诸如此类的史料,使得历史事件的描述更为生动,史实阐述更为通俗,强烈的代入感使得读者对于唐蕃关系的变迁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 总的来讲,该书作为一本大众读物,打破了学科藩篱,内容丰富翔实,视野开阔,体现了对考古、历史和地理等多学科的并举,也涵盖了水文、物候、疾疫等内容。依托于历史,又高于史实的单一叙述,历史现场感强,文笔流畅,古今结合,附有两百余幅彩图,既可以摅怀旧之蓄念,又可以发思古之幽情,是值得推荐的优秀历史读物。一般来说,历史专业学者写普通读物较为困难,《唐蕃古道》一书则可为历史专业书写和大众的学术普及提供一条尝试途径,正如马大正先生在序言中说:“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让文化充满雅趣,让大众在雅趣熏陶下揭谜心醉。”让我们期待读者更多的评判!方法论就是名物训诂、制度考据,而不是一种批判性的学问。后人对经学典籍只能校勘、注释、解释,而不能怀疑和批判,不能有任何带有否定性的发展。《汉代儒学的经学化进程》一文大概有四万字,发表以后有一定的影响,大家一看就知道我的立意何在。 文章发表以后,我还没有收到杂志,读者就已经看到了。当时第一个给我打电话的是安作璋先生,他是秦汉史大家,安先生讲到:“振宏啊,你这文章写得啊,建国以后政治与学术的关系如何如何,你这篇文章说得很透彻啊!”我相信我写的文章在座的你们都能读得懂,我的文字绝对不是艰涩的,肯定能读懂。我觉得我20世纪90年代以后搞的秦汉史研究没什么无病呻吟的东西,灵感都来源于现实。包括上大学时我写的东西,都是关怀现实的。 说实在话,上大学时写文章非常激动,觉得自己在同一个世界作战。我在大学二年级发表第一篇文章《封建时代的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吗?》,是与河北大学著名教授、宋史学界的权威学者漆侠先生商榷过了的。他认为农民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但我认为农民不是革命民主主义者,我在写作中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不是在针对漆侠先生,而是在与整个学术界作战、与整个左倾思想作战。农民怎么是革命民主主义者?这都源于我内心一种很强烈的现实情感,做这个选题就是在参与现实政治生活中对左倾路线的清算。我上大学时提出一个课题叫做“西汉官吏立法研究”,当时确实没有人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很大,所以我就在毕业的时候做了一个“西汉贵族官吏坐罪问题考证”研究,是这个大题目中的一个小问题。毕业以后我开始做史学理论,秦汉史的研究暂时搁置。20世纪90年代末,安作璋先生出了一本书《秦汉官吏法研究》。其实这些问题都来源于现实,现在的学生基本不关心政治、不关心现实,这样是不行的,必须有一种政治的敏感性,没有政治的敏感性和感悟力,是没有办法做学术的,是不会提出有价值的选题的。 关于获得选题的第二个途径,我想大家可以直插学术前沿。即使大家只是本科生,也可以直插学术前沿,关注学界目前正在讨论的问题。我们与理科比较的优越性在于哪里?举个例子来说,理科的话,不懂初等数学就不太容易懂高等数学,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性很强。但是文科不同,只要认字就可以了。所以再大的学者写的文章,读者也能够看得懂,看了就能理解,理解了就有问题可以讨论。只要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问题就是争鸣,只要有争鸣,就有漏洞可以钻。为什么会出现争鸣呢?那就是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看法有不同的逻辑,哪怕使用的是同样的材料,有同样的理论指导。就像过去学界讨论的“五朵金花”,都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都是使用基本相同的材料,却引起了一段时间的争论。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就看他们讨论问题时有没有漏洞,只要有漏洞,都可以成为选题的来源。其实我有一些文章就是直接介入前人的讨论,比如我刚才说到的同漆侠先生商榷的那篇文章,其影响是较大的。那篇文章在《文史哲》1980年第1期发表出来以后,《光明日报》、《解放军报》、《新华月报》(文摘版)等报刊都进行了报道,但是大家都不知道我是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 我在《历史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1986年第3期的《“终极原因”与“相互作用”》。那篇文章就是一个前沿问题。我可以吹嘘一下,那篇文章可以说在《历史研究》的历史上,是除了约稿文章以外,自然来稿文章中发表速度*快的一篇。3月初投给他们,6月的第3期就登出来了。《历史研究》如此迫切地想要发表这篇文章的原因在于,1980年金观涛、刘青峰在当时的《贵阳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的结构:一个超稳定系统》,讨论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的原因。他们用控制论、系统论的思想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长期延续的问题。文章发表后,他们又于1984年在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该书又被压缩成八九万字的一个小册子,题目叫《在历史的表象背后》,在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金观涛夫妇用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历史,有一种新鲜感,作品一发表,一下子就影响了史学界,青年人一看就跟着走了,但是年龄稍大的人不易接受。金观涛那个时候也就30多岁,血气方刚,不知道把话说得圆润、平和一些。他文章开头提出“要让现代科学之光照进晦暗迷人的历史研究领域”,他的意思是只有现代科学才能照亮历史研究。当时一下子引起了讨论的热潮,年轻一代的人支持新的研究方法,另外一些人则公开写文章批判金观涛对唯物史观的否定。 当时我做史学理论研究,也很关注这个问题。我研究发现:唯物史观本身就包含了相互作用,唯物史观寻找终极原因是不错,但是唯物史观寻找的终极原因是生产力,生产力是整个历史的基础。然而生产力本身是由生产工具、生产资料、劳动者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的,并不是单一因素作用的结果,正是三要素的相互作用形成了终极原因。再向前看,其实“相互作用”是个古老的思想,哲学讲相互作用,到了近代以后,黑格尔把“相互作用”提得很高,他有一句话叫“事物在相互作用之外什么都不是”,就是说,所有的事物都是相互作用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就吸收了古希腊哲学以至黑格尔哲学的相互作用思想,并将其纳入自己的方法论体系。所以不能用“相互作用”理念排斥唯物史观,唯物史观本来就包含相互作用。问题在于,马克思讲的“相互作用”是把黑格尔的“相互作用”提升到更加辩证的水平,这是马克思的推进,但是他的“相互作用”仍然停留在比较初级的阶段,因为马克思所处的时代自然科学发展得不够充分,他依靠的自然科学成果无非是当时的三大发现——进化论、细胞学说、能量转化。这种自然科学的水平与今天相比相差得太远,所以当时的“相对作用”只发展到辩证的水平,再加上马克思的注意力并不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研究也就没有完全展开。现代科学出现后,重新强调“相互作用”,把“相互作用”的形式完全展开化、丰富化、具体化、可操作化,应用的可能性变得更大。所以拿现代科学方法来丰富和发展唯物史观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我们唯物史观为什么要排斥它呢?唯物史观应该吸收“相互作用”思想来丰富自己,在吸收它的时候再去注意这种新的现代科学方法的局限性,优秀的部分要吸收过来,变成自己内在的方法论。 我的文章把原本斗争激烈的双方融合起来,为学术界的讨论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所以《历史研究》非常迫切地想要发表这篇文章。当时我只是一名普通的青年教师,但是我发现了这个问题,抓住一个前沿性的问题,就有可能做出别人想不到的成果,这是完全可以的。所以选题要直插学术前沿,要关注社会动态。不要觉得自己现在没有能力与学术界对话,不存在这个问题。有些事情不一定要等到自己非常丰满、非常成熟的时候再去做,有多少水平说多少话就可以了。以前没有网络的时候,我给本科生上课,要求大家每个月一定要进图书馆一次,把图书馆*新期刊翻阅一遍,翻阅一遍就能了解自己关心的问题和目前学术界的研究现状。现在网络非常方便,中国知网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所以大家要主动关心这些事情,从学界的讨论中寻找问题。 第三个获得选题的途径是自己平时的积累,主要是读书、思的积累。读书要讲究方法,我一直说读书要带着批判的眼光读,读书就是找毛病的,不要把读书当做一种被动的学习,当你找毛病的时候获得的东西要比被动读书获得的东西多得多。只有带着批判的眼光读书,才能真正读出东西来,才能发现问题、积累问题。 我读大学的时候,在《中国史研究》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两汉地价初探》。那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暑假,我没有回家,读了一套《汉书》后在《汉书·李广传》中发现一个问题:汉武帝在位时的丞相李蔡,武帝赐给他二十亩地,结果他盗取三顷,*后治罪,坐赃四十万钱。我一想三顷土地四十万钱,那么一亩地就是一千三百钱,但是我学秦汉史的时候说到地价都是讲“亩价一金”。一金在汉代是一万钱,但是我看到的这个例子中一亩地值一千三百钱,两者差距太大了,而且这个赐的土地又是好土地,所以我就对地价产生了怀疑。然后我再去翻阅《汉书》,寻找是否还有与地价相关的材料,就发现一则材料讲到汉元帝的时候有一个叫贡禹的人,在地方上很有名,皇帝召他进京。贡禹家里很穷,有一百多亩地,但是土地非常贫瘠,在山东琅琊一带。他为了进京见皇帝,需要准备一套马车,所以《汉书·贡禹传》说他“卖田百亩以供车马”,这一百亩值多少钱呢?我就根据他置办的马车来推算,那种马车在汉代叫轺车,有驾一匹马的,有两匹马的,也有四匹马的,我就估算贡禹应召进京晋见皇帝乘的轺车应该是几匹马,再根据汉代一般情况下马的价格、轺车的价格,估算出一亩地大概是几百钱。我再用汉代牛车与马车的大致比例推算,得出的结果也是一亩地几百钱。这样我就有了直接材料、间接材料,否定了“亩价一金”的说法。现在只有一条半材料,我就去请教我的老师该怎么去写文章。朱绍侯先生说近代以来出土过一些买地券,可以尝试从这些出土材料中找找,看有没有新材料。我就通过一些“特殊手段”进入资料室,在半个月的时间里把所有近代以来的考古资料都翻阅一遍,找到了大概20多条材料,这就是汉代的地价资料。我*后考证的结果是汉代地价(好的土地,水浇地)在一千多钱到两千钱之间。虽然这个问题不是具有直接现实关怀的问题,但这个问题是学术史链条上的一个节点。当时学界讲到汉代土地兼并很迅速,既然要讲土地兼并的问题,如果连地价、土地如何交换这些内容都不知道,那就没有办法继续研究,所以地价的考证是有意义的。我在1981年初写出这篇文章,投到《中国史研究》,6月就发表了,8月我拿到了刊物。当年9月西安成立全国秦汉史研究会,朱绍侯先生去开会,本来想把我的文章带去,但是想到已经发表就不再带去了。在那次会议上,《中国史研究》编辑李祖德先生(李先生后来做了《中国史研究》的主编)问朱先生:你们学校的李振宏先生怎么没有来?朱先生说我是学生,没有资格参会。李祖德就很好奇,一个学生怎样能够写出样的文章,他就拜托朱先生,让我与他进行联系,从此我就与李祖德先生建立了联系。半年以后我毕业了,留校教史学概论,没有再做秦汉史研究,我就把这些情况向李先生汇报。时隔一年,史学理论研究会开始筹备建立,全国第一届史学理论研究会在武汉东湖召开,李祖德因为跟我有联系,知道我是做史学理论研究的,刚好他在筹备这个会议,于是就给我发了邀请,所以我就走进了史学理论研究领域。一篇文章,因缘际会,在会议上结识了很多的朋友,学术圈子就逐渐建立起来了。 问题的积累是靠读书,读书时思考问题、寻找问题,暂时解决不了但是有意义的问题,就可以把它记下来。青年人往往是一开始不自信,自己想到了问题,却把自己的思想火花掐灭,非常可惜。大家有了想法就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即使这个问题暂时无法成为选题、无法被解决,随着知识的积累、学识的增长,回头看的时候这个问题就很有可能成为选题,选题就是这样积累出来的。想法是无形的,假如不及时记下来,一旦消失就再也没有了。 选题的来源我想大概无外乎以上几种情况,当然不排除一些研究生导师会为大家的选题提供思路,这都是有可能的。此外,我想跟大家交流一下做什么样的题目适合我们硕士生,这里有一个说法叫“大题目”和“小题目”。该怎么处理大题目和小题目的关系?像你们这些年轻人,按照你们的学识、积累和基础,是适合做小题目的。就材料的范围、问题的架构来说,小题目易于驾驭。但是问题在于,你们胜任小选题,却只能看见大选题,因为你还没有走进去,没有进入研究领域。就像我们在外边看一座大楼,只能看到这座楼的外观,有几层、有多高,至于里边的结构怎么样,就必须要走进去才看得到。 比如我上本科的时候,面临毕业论文的选题,有的同学说那就写中国古代史吧,你说要具体一点,他就说那就写农民战争吧。这样的题目如此之大,如何写?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就是没有走进去,当然找不到小题目。现在的问题就是大家还没有进去却需要开始写文章,适合小题目但是发现不了小题目。这种情况下怎么办?我的主张是写大选题下的小选题。大家既然看到了大选题,那么可以把大选题做一个逻辑分解,化整为零,一直化到可以做为止。我读书的时候发现官吏立法研究前人确实没有做过,我认为当世一些官员的做法太不合适,却也没有关于官员的立法,而我看到汉代的官员管理非常严格:一个官吏今天来值班,叫做“视事”,中午没有回家吃饭,那你在官署里吃了什么饭,吃了哪几个菜,每个菜几个钱,都要记录得清清楚楚的。我们到了一九八几年才有了一个党员生活准则,立法上更不完善。所以我研究这个问题确实是想为现实提供借鉴。但是这么大一个问题怎么做?我把汉代官吏立法分为刑事立法和行政立法,先划分这两大块,然后考虑汉代官吏做什么事情是犯罪、罪名是什么,先把法律本身考订出来,这就是一个需要做的大工作。之后讨论这个立法贯彻了什么精神,官吏立法有没有立法原则、立法精神。古代官吏被罢官、免职之后复出是很正常的现象,不像现在官员复出很难,老百姓也不接受。实际上,培养一个干部成本很高,干部犯了错误,停职几年有所反省再干是正常的。汉代的官吏经常复出,有的人甚至可以复出三四次,但是牵扯到赃罪,也就是经济犯罪,他就不能复出了。所以立法的原则是值得研究的。另外,官吏犯法和老百姓犯法,量刑一样吗?官吏有没有特权?这个也可以研究。这些都是刑事立法方面可以考虑的问题。行政立法涉及到的问题就更多了,依旧可以由大化小,再去处理。把大选题中分解出来的小选题一个一个解决,*后再建构起来,那就是一本书,你就成专家了。如果一个人一辈子做了很多零零碎碎的小问题,问题之间都没有联系,那你就不足以称之为专家。 做大选题里的小选题是可以构成知识体系的,所以硕士阶段*后的论文不一定做得很小,可以宏观一点,尝试一下大的选题。有些人认为大的选题年轻人无法驾驭,我不这样认为,大家可以大题小做、大题简做。几万字可以把一个大问题做一个框架性的解决,可能细节问题不能够得到一一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大的脉络、主干是可以解释清楚、构成框架的。论文完成就相当于把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都进行了思考,这就为下一步的研究奠定了一个很好的基础。用现代话说,我们的选题是要具备“可持续发展”特性的,如果一篇硕士论文、博士论文写完后再也没有研究的空间,那这样的选题有什么意义呢?我们看到有些人本科学位论文到硕士论文,再到博士论文是构成体系的。所以我觉得选题还是要选择相对宏观的题目,然后做大选题中的小选题。 第二点是“生题”和“熟题”也可以做一个比较性的思考。所谓“熟题”,就是大家都在做的、经常辩论的题目。这样的题目由于大家都在做,所以做起来的难度就像我们打攻坚战一样不容易;好处在于大家争论了很长时间,基本的资料都已经被掌握,不用自己再去创建一个资料体系,借用他人的资料就可以了。另一点是大家使用的概念已经比较成熟,也就不用再创立概念。熟题的好处还在于大家的观点已经比较成熟,你只要有一点点新的看法,围绕这个看法写文章,那就是对这个问题的贡献。但是难度就在于大家讨论得很充分,想要有一点新的看法谈何容易!不过我们青年人思想敏锐,指不定就在哪个地方发现了新问题。“生题”就是从来没人做过的题目。既然是从来没人做过的题目,那就像是开荒、拓荒。本来是一片不毛之地,随便拿锄头刨几下,种子一撒,第二年就会长出苗来。生题的话,既然没有做过,那么就算做得不够好,只要问题本身有价值,那也是该问题研究的*高水平。这种情况下,提出问题本身就是贡献,启发学界关注、研究这个问题,就有发表的价值。但是生题做起来的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解决这样的问题,资料要靠自己搜集、要创造一个资料体系;其次,解决这个生题没有其他文章可供参考,解决的路径、方法都要自己来设计,更麻烦的是有些时候可能要提出新的概念,创造概念是相当不容易的事情。 就我的体会来说,生题就是拓荒,熟题就是攻坚,我的想法是与其“攻坚”不如“拓荒”。我做的《两汉地价初探》就是一个生题。那个生题的资料全部是我摸索出来的,那篇文章中我还创造了概念,因为当时我把这个地价考证出来以后,按说这个问题是完成了,但是我不甘心。因为下了这么多功夫,万一我的文章刚发表,有一个人在家挖红薯窖,挖出来一个买地券,发现地价是两万,就把我的研究推翻了。我不能被轻易否定,所以我要对汉代地价进行一个理论研究——根据汉代的生产力水平、物价水平、汉代的政治特点,大概地价也是如我所考证的那样。我要在理论上解决这个地价问题,我考证的这个地价是个一般性问题,如果出现别的差距较大的证据,那只能说明是个别,个别否定不了一般。于是,我提出一个“封建地价”的新概念。“封建地价”这个概念从哪里来,没有人说过这个话。马克思《资本论》讲到资本主义地价是个公式,地租除以利息率。封建地价没人讲过,后来经过了艰辛的过程我还是把这个问题解决了。解决了这个问题,这篇文章就有了特色,就不是停留在考证阶段。所以想告诉大家我的体会:在写作中都会遇到困难,在你认为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那就该高兴才是,因为文章要出彩了,创新的东西可能就要出现了。如果一篇文章轻而易举就完成了,那别人一定也会想到的。所以写文章必须遇到困难,实在解决不了的时候也不要退缩。就我几十年写文章的经历来看,没有到*后都解决不了的问题。只要想解决,就一定能解决,这是我想给大家的信心。 解决问题有时候是需要灵感的,灵感从本质上来讲是不期而至的东西,灵感不仅仅属于文学创作,实际上好多研究都需要灵感。虽然灵感是不期而至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创造迎接灵感的环境。这个环境就是对问题执着的思考,持之以恒的、坚持不懈的、长时间的定向思维。假如可以很长时间一直思考这一个问题,头脑一直处于高度受激的状态,那么就有可能被一件什么事情莫名其妙地激活了灵感,甚至一片树叶的掉落也能使你获得灵感。现在我们文章写不好,问题在哪?就在于没有深度思考,没有把问题想清楚,没有想透彻,在那里憋出来的几句话是不顺畅的。你们现在不知道过去我们写文章的过程,一万字的文章要写三千字的提纲,再修改提纲,以促使思考进一步成熟,修改完三千字的提纲还不动笔,我要再写三千字的提要,把*想表达的文章的主体部分集中地表达出来,通过这个表达检验思维是否成熟。提纲是个线索式的逻辑结构,提要是主体部分的简要阐述,到这个时候,才觉得整个文章完全了然于心,思考得非常成熟才开始动笔。在过去不花半年以上的时间,就难以写出一篇真正的文章。现在有的同学一两个星期就想写出一篇文章,真是太天真了!当你真正思考成熟的时候,又知道你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问题的解决将带来多大的影响,这个时候将会有巨大的力量激励着你,自己就会忍不住想要去表达了。一旦提笔,思如泉涌,文章写起来一气呵成,非常有气势。文章不是写出来的,是从心底里流出来的,它是思维的成果。只要思考得成熟,当然就能写出好文章,这个时候才能出文采。 以上是我讲的选题的问题,其实做文章就是做选题,我做《史学月刊》编辑这么多年了,不怕打击大家的积极性,其实编辑很多文章都没看就退稿了,很多时候就只看一个题目,只有选题有意义才会继续看文章,所以大家要在选题上下功夫。 我现在讲第二句话:确认相关研究的差异性,就是确认你自己的研究和前人研究的差异性。 当你有了问题意识,认为这个问题有价值,确定这个选题的时候,你需要做的第一步工作就是查阅相关的学术史,梳理在你选定的这个问题上,前人做了哪些工作。大家应该对前人所做工作有完全的了解:他们在理论上、思想观念上达到了什么程度、提出了哪些观点;在资料运用上使用了哪些史料;在方法论上使用了什么样的研究方法……把这些统统做分析,然后开始考虑自己想要研究的东西;想达到的*后成果;和前人相比,区别度在哪里、不同于前人的地方在哪里。区别度越大,你的研究越有价值;没有区别度或者区别度根本不显著,那就不要再继续研究了,这是没有价值的。所以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研究与相关研究的差异性。这是要做的第二步的工作,也是一篇文章能够成立的一个*重要的基础。文章再有价值,前人研究过了,那么你的选题就不成立了。做学问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往前推进的,所以你必须要有区别于前人的地方。这是第二点要求。 我要讲的第三句话: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与途径。 考察前人的成果后,觉得自己的选题区别于前人、有价值,选题就可以成立了。接下来就该考虑选择什么样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要有自觉的方法意识。我觉得中国学者的方法论观念较为淡薄,不少学者以唯物史观为*高的方法论,认为有了它就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其实,它只是一个*高的原则的方法论,结合到具体研究,每个问题的解决都应该有针对这个具体问题的特殊的研究方法,有自己特殊的方法论问题要考虑。方法是由内容决定的,内容是方法的灵魂。任何一个选题都有特定的历史内容,对于特定的历史问题的解决,针对特定内容应该有相应的方法,所以做学问解决问题都要考虑方法论。然后是解决问题的途径,从哪些角度或者从哪几个层次去论证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文章的结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对于如何组织自己的文章结构,要研究解决这个问题需要从哪几个方面着手,是横向的、逻辑性的文章结构,还是纵向的、层层递进的逻辑结构,采用哪种结构解决这个问题才是*为合理的。所以要在结构问题上多下功夫。天下所有的文章都是讲究结构的,诗歌、散文都是有结构的,所以我认为要养成自觉的结构意识,如何去结构文章就是如何去表达,把这个问题立起来。研究同一个问题可以有不同的结构方式,但是一定有一种结构方式是*适合的,一定要找到*适合表达这一主题的结构方式。其实文章的结构问题也就是文章意识,有没有文章意识就是有没有结构意识、会不会组织文章结构。希望大家通过练,可以做到只要给一个题目,马上就知道这个问题该怎么解决,必须从哪几个方面入手。尽管对问题涉及的材料还不甚明了,但是离开这几个方面的论证,文章就立不起来。到了这一步,就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了。这些事情都应该落实到平时的阅读中去,平时看书不要总看别人写了什么,要多关注作者是怎么表达的,看他的研究方法、逻辑结构,这都是应该在平时的学习中培养出来的一种自觉意识。 第四句话:与学术界对话。 不和学术界对话的文章不是真正的学术文章,是不合格的学术成果。大家可以看西方的学术论著,大都在和别人讨论问题,自己的思想是在和别人讨论问题的过程中确立起来的,这就是和学术界对话。现在很多中国学者是不习惯这种模式的,通篇文章都是自说自话,好像一篇文章几万字或者一本书几十万字都是作者自己的,完全没有参考别人的成果。西方学术界瞧不起中国文科的东西,有一部分原因在于,别人看你的文章或者书,不知道哪些是你自己的,哪些是别人的,人家不可能相信这些都是你自己的成果,没有人是这样写文章的。几十万字的书都是作者别出心裁,文章的思想观念没有借鉴他人,都是作者构造出来的,这是不可相信的事情。加之不做注释,不和他人对话讨论,所以别人不相信我们成果的真实性和可靠性。到目前为止,这个情况还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这些年我也经常到一些学校主持硕士、博士论文答辩,我看到很普遍的情况是,一篇硕士论文后的参考文献列举了一百多种,博士论文列举了二三百种,多得吓人,但一看文章,他却并没有引用到这些参考文献,只是在文章前边的综述中提到哪些人写过什么。这些人写过的东西你都是赞成的吗?难道不应该是不赞成然后才来研究这个问题的吗?正是因为前人研究得不够,才留下了继续探讨的空间。既然前人的研究不充分,那你怎么不与前人对话呢?为什么不把他们的研究内容引用到自己的文章中进行讨论呢?所以现在的文章不能够保证质量,这是很大的一个原因。其实学术的深入就是在不断对话中获得的,当你发现别人的研究不够好,这个观点靠不住,或是因为引用的材料不是*关键、*根本的材料,或是因为对材料的解读出现了偏差,或是因为文章布局结构出了问题,或是因为对方的理论思想不够。当你在批评他、和他讨论的过程中,就把自己引向深入了。有一个学者说过,一篇博士论文二三十万字,假如在论文中没有看到引用近二十年来出版的著作的话,仅此一条就可以判断文章是不合格的。博士学位论文是一个比较宏观的选题,不可能学界近二十年都没有相关研究,即使不是直接关注的这个问题,相关的问题也一定关注过,肯定有讨论的空间,结果你没有讨论,那么就是无视学术界的成果,你就不知道怎么做学术。仅此一条就判断你不合格,我觉得这样的话并不过分。其实文章后边的参考文献,大部分是要文章中去的,在文章中讨论,这样文章本身很鲜活,文风也很好,也能够把自己的研究推向深入,锻炼自己逻辑思维的能力。前人没有把这个纳入学术规范,我把这一条纳入研究规范,不这样做就不是规范的研究,研究都应该是和别人讨论问题。 以上就是我所讲的研究规范的四句话:明确问题意识、确认与相关研究的差异性、选择研究方法与途径、与学术界对话。如果四个要素都具备了,那就可以产出具有真正学术意义的研究成果。 精彩文摘2: 《救荒全书》对传统荒政思想的继承与创新,总结归纳其思想特色。 一师古:对历代救荒基本思想的梳理与继承 “灾荒”乃是由于自然界的破坏力对人类生活的打击超过了人类的抵抗力而引起的损害。邓拓:《中国救荒史》,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页。自进入历史时期,灾荒便与人类社会相伴随,人们也开始不断总结经验,寻求救荒之策。先秦时期的《周礼》便曾提出荒政十二策,并成为历代救荒的基本原则。在中国历史的演进过程中,救荒制度与救荒思想日趋完备。《救荒全书》辑录此前时代经、史、子、集中大量的救荒内容,对历代救荒思想进行了梳理、总结和继承。 1.天人感应禳弭观。 先秦时期,人们对自然的认识有限,往往将灾荒归咎于上天所降,如甲骨卜辞载有“帝令雨弗足其年”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三六三片,《郭沫若全集·考古篇(第二卷)》,科学出版社,2002年,第364页。、“帝其降堇”郭沫若:《卜辞通纂》第三七一片,第366页。等语,从而也就有了祷神消灾之法。《周礼》言“索鬼神”,注引郑众云:“索鬼神,求废祀而修之,《云汉》之诗所谓‘靡神不举,靡爱斯牲’者也。”《周礼》卷一九《地官·大司徒》,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本,中华书局,1987年,第741页。即灾荒发生时,要广泛祭祀鬼神。至汉代,“天人感应”之说流行,灾异也与政治紧密联系起来。“天所以有灾变何?所以谴告人君,觉悟其行,欲令悔过修德,深思虑也。”班固撰:《白虎通义》卷六《灾变》,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本,中华书局,1994年,第267页。灾荒发生被认为是王政不德的结果,要求统治者反省思过。《救荒全书》继承了传统禳弭观,将“修省”、“祈祷”作为救荒的根本之策,列在“治本”章之首。 “雨旸不时,固有祈祷之法矣,然祈祷岂空文也乎?从来天人一气,征应不爽,必且侧身励行,悔过省愆,自足以御灾召祥。”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治本章之修省,第545页。祁彪佳将自然变化与人事相关联,体现出他对灾害发生缘由的一种朴素认知;而且他相信只要诚心祈祷,便可以抵御灾害。虽然这不免带有迷信色彩,不过,他强调砥砺德行、反省过失,也是在告诫君臣不可漠视民生。祁彪佳列举了历代因灾降而修省祈祷之事,如记录明世宗朱厚熜之言:“他天时亢旱,虽繇朕不德,亦因天下有司暴贪,为民害,干天和”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治本章之祈祷,第548页。,实际上是借弭灾揭露人事不修的现状,表达了革除弊政的迫切希望。 2.重农保民为要务。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保民自然是救荒要务。“岁虽凶败水旱,使百姓无冻喂馁之患,则是圣君贤相之事也。”《荀子》卷六《富国》,王先谦撰《荀子集释》本,中华书局,1988年,第184页。农业是传统社会的经济基础,更是广大民众的生活支撑,如汉景帝所言“农事伤则饥之本也”班固撰:《汉书》卷五《景帝纪》,中华书局,1962年,第151页。,故而历代救荒均将重农视为治本之策。《救荒全书》继承了传统民本、重农的政治思想,指出“帝王戡乱致治,必在乎拊恤亿兆”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举纲章之圣谟,第507页。,“播时百谷,蒸民乃粒,为千古救荒之祖”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举纲章之古画,第518页。。 祁彪佳深刻认识到救荒不力会导致社会动乱。“农政修举,则虽天灾流行,亦可人事挽其半。”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举纲章之古画,第518页。要以发展生产、重视仓储来预防灾害,劝课农桑,兴修水利,开垦屯田。当灾荒来临,则要及时赈济百姓,帮助其恢复生产。“言拊流者,宽徭减赋,赈恤于方饥之时,此盖治其本也。待其流而后招徕安集,第为治其标耳。然灾荒重大,或不得不轻去其乡,故须标本兼治,乃使民命有皈。”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宏济章之拊流,第831页。灾后要采取赎鬻、养孤、安老、保婴、掩骼等系列措施,尽力安置灾民生活。 3.重视预弭与存备。 救荒于已然,不若备荒于未然。早在先秦时期,储粮备荒的思想就已出现,《周礼》记载“遗人”职责为“掌邦之委积,以待施惠”,并强调“县都之委积,以待凶荒”。《周礼》卷二五《地官·遗人》,孙诒让撰,王文锦、陈玉霞点校《周礼正义》本,第986页。管子更是利用轻重散敛之术来备荒富民:“请以令与大夫城藏,使卿、诸侯藏千钟,令大夫藏五百钟,列大夫藏百钟,富商蓄贾藏五十钟,内可以为国委,外可以益农夫之事。”《管子》卷二四《轻重乙》,黎翔凤撰、梁运华整理《管子校注》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1465页。 《救荒全书》继承了重视灾前预防的战略思想,“饥馑骤至,苟非先事讲求,早有成画,而待临期仓碎,后为调剂,则虽良法在前,亦成弊数耳”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治本章之豫计,第561页。,强调居安思危,做好备荒,其主要措施有发展农业、兴修水利、重视储备等。书中“厚储”一章更是详细论述了义仓、社仓、预备仓、广惠仓、丰储仓、济农仓等历代备荒仓储制度,强调仓储“要在主守得人,散敛有法”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厚储章之社仓,第608页。,重视劝惩稽考,因时、因地制宜。另外,祁彪佳还探讨了置义、社田的好处,介绍了官府内外储谷的备荒办法,并提倡民间自储自粜。此外,“治本”一章中还提及到设置耑官,专以备荒为务。 二通今:对明代荒政思想时代特色的总结 明代前期,救荒制度尚较为完备,且推行有力。到明代中后叶,始渐废弛,于是有识之士纷纷著书立说,探求救荒之策,这使得传统的救荒思想逐渐成熟化、系统化。《救荒全书》详细记录了历朝皇帝圣谕和朝廷明例,又汇集林希元、屠隆、周孔教、刘世教等“近来诸公所刻赈史、荒政凡二十余种”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凡例,第499页。,其中体现出来的荒政思想更是具有了鲜明的时代特色。 1.鼓励民间力量参与。 有明一代,至后期呈现出地方官府职能弱化、财政困难、救荒能力不足的社会局面。与此同时,乡绅富户则拥有大量财富,在地方事务中也有一定话语权,在地方治理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作用。 因此,明末普遍注重利用民间力量参与救荒,特别是劝富济贫。比如屠隆辞官回乡后,撰《荒政考》,强调官府应奖劝富户自愿出捐:“夫上躬先仁义,而其下有不望风响应者,否也。又需悬赏格以劝民,颁科条以鼓众,或量其所捐而优以礼貌,风以折节,奖以旌扁,荣以冠带。”屠隆撰,夏明方点校:《荒政考》,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08页。实际上当时许多赈灾官吏的策略与屠隆如出一辙,“视所捐多寡,优以匾额、冠带,仍免其徭役”钟化民撰,夏明方点校:《赈豫纪略》,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156页。,而曾任职县令的刘世教更是直言:“赈之所自出有三,曰朝廷、曰有司、曰富家巨室”刘世教撰,夏明方点校:《荒箸略》,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286页。,将富户视为赈灾主力。 《救荒全书》充分吸纳了这些观点,并强调“富民者,国之元气也”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当机章之劝富,第698页。,又提出了求“安富”的主张。“督责之法固不可行,惟有遍行申谕,动之以祸福,怵之以利害耳。”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当机章之警谕,第709页。这样因势利导,令富户自愿赈灾。祁彪佳还摘录了姚江文学邹光绅的建议,指出官府该如何引导乡绅富户发挥作用:“劝法有三:一者速令粜谷,不许留匿,不许顿粜奸牙,以出境外;二者暂贷通商,数月后即还其本;三者直令捐助,或给匾,或考试加之意。”祁彪佳撰,夏明方、朱浒校订:《救荒全书》当机章之警谕,第701页。除了劝勉他们粜谷、捐助、放贷,官府还可以委之赈事,令其参与审户、核饥、除恶等事务。 2.积极利用市场规律。 在明代,南方商品经济繁荣,不少荒政文献的作者正是来自南方,他们普遍懂得利用市场规律来救荒。在当时,禁抑价以促进商品流通从而平衡粮食价格,已成救荒共识。林希元曾在奏议中直指抑价之弊:“尝见为政者每严为禁革,使富民米谷皆平价出粜,不知富民悭吝,见其无价,必闭谷深藏,他方商贾,见其无利,亦必惮入吾境。是欲利小民而适病小民也。”林希元撰,俞森辑,夏明方、黄玉琴点校:《荒政丛言》,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99页。无独有偶,生员张陛在家乡赈灾时,曾“誓众曰,但毋遏籴,石米愿羡市价五分。于是牙家辐辏,集米计千有余石,赈事遂办”张陛撰,夏明方点校:《救荒事宜》,李文海、夏明方、朱浒主编:《中国荒政书集成(第一册)》,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03页。,希望通过提高粮价来吸引商贩。 《救荒全书》同样注重运用市场规律,要求官府以“和籴”之法备荒救灾,以济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