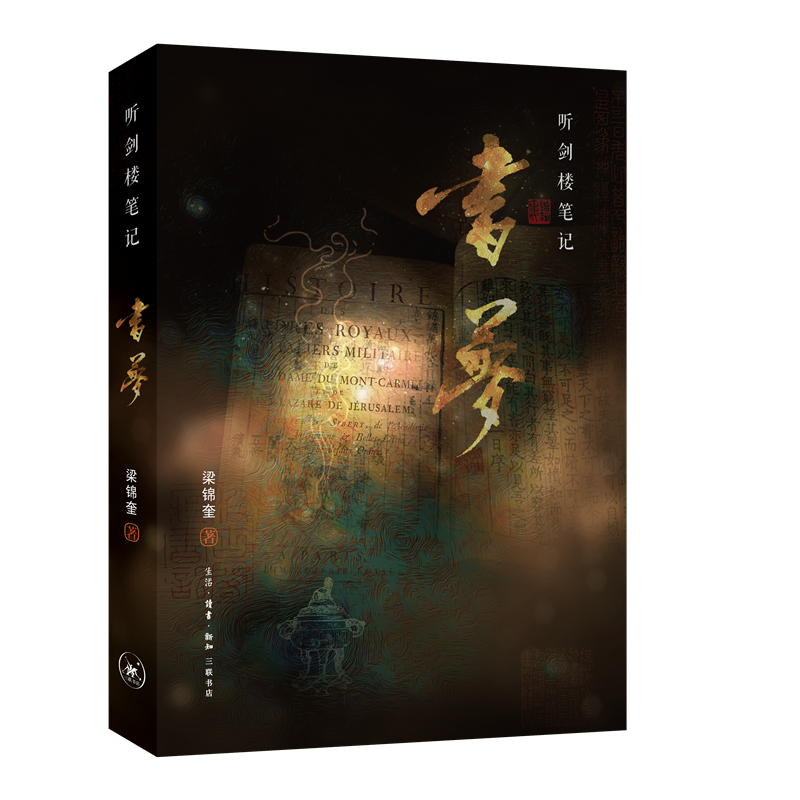
出版社: 三联书店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5.60
折扣购买: 听剑楼笔记 书梦
ISBN: 97871080736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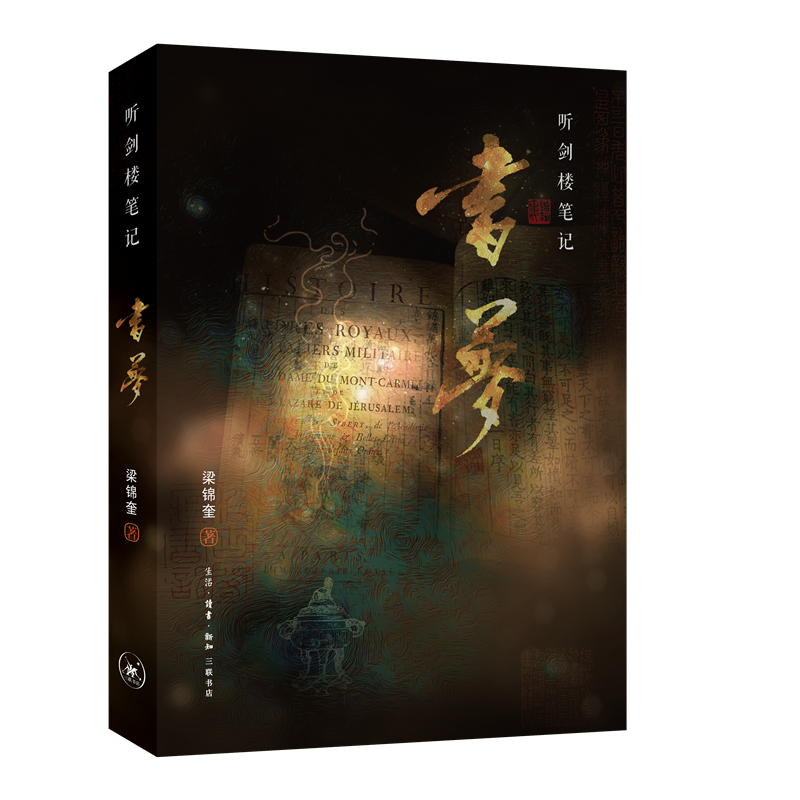
梁锦奎,1949年出生,祖居陕西省西安市。爱文学、艺术,好读书、藏书。长期从事文字工作,涉猎历史文化、经济研究、城市规划等领域。近年出版了文化随笔集《听剑楼笔记 花影》(三联书店,2014年)、《听剑楼笔记 云烟》(三联书店,2016年)。
路近城南已怕行,伤情 ——忆西安盐店街西头的“三才书店” 1966 年,书店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勒令停业并当街烧毁全部藏书,店主也被赶回原籍务农。1976 年后,店主回西安,家兄顾旧情安排他在街道办上班,工作稳定,得以善终。 陆游《十二月二日夜梦游沈氏园亭》:“路近城南已怕行,沈家园里更伤情。香穿客袖梅花在,绿蘸寺桥春水生。 ”西安的城南也有值得魂牵梦萦的回忆,只是早已人事俱非。 从清初以来,西安城里的老户人家主要集中在城南,碑林、文庙、书院、省市报馆、图书馆、古旧书店等文化场所也在城南。全市最有影响的租赁书店 —“三才书店 ”就位于城南盐店街的西头。 家兄梁春奎从区政协岗位退休后,参与《碑林区志》撰写,有多篇关于区街文化典故的博客,其中一篇是《三才书店和古旧书店》,记叙了那年书店被“勒令当街焚书”的情形:“长发三才惊恐万分,慌张中连户口本同书一并投入火中,幸得人捡出。其后,随居民上山下乡,三才书店从此倒闭。1976年后,得以赦免返城,衣食无着。其时,街办正缺一全日门房,时为街办小令,遂嘱其担任之。 ”家兄的文章唤起我许多幼时记忆。略有遗憾的是有些地方述之未详,借机在此补足。 我家就在盐店街 盐店街东西走向,长约半里,实测 277.5米。街道中部北侧有寺庙曰文昌宫,庙巷北通西大街,正对都城隍庙。通过唐长安城地图覆盖考证,这里是唐皇城里的宗正府衙门和右领军卫衙门之间的街道。盐店街东头是丁字路口,连接唐长安中轴线上的朱雀大街。明清后城内这段朱雀大街曾名广济街,有寺院景龙观(后名迎祥观)。街西头是十字路口:西边梁家牌楼街,牌楼为清初建立,彰表的是清初名将、官至江南提督的梁化凤,现牌楼无存,唯留街名;北边是琉璃庙街,因屋顶使用琉璃瓦而得名;南边北四府街,是明代秦藩王四个王子的府邸所在。 同治四年( 1865)在这里设官营盐店。盐铁从汉代起就属官家专卖,是国税的重要来源。盐店开张后,每日有大量现金交易,外国银行和民间银号、钱庄纷纷前来设点收储和放贷,多达二十家,分布在盐店街和梁家牌楼北侧,成为西北地区的金融中心、西安的“华尔街 ”。各路镖局、会馆也来此安营扎寨,比较有名的如东北“五省会馆”(原名八旗奉直会馆)就在盐店街中段,其他各省会馆分布周围街道,云集四海客商。这些商人日常消费、消闲场所,大都在附近的南院门、五味什字街和大小保吉巷,这里有民国时全市最大的西药店、老字号“藻露堂 ”中药店、西式电料行、高档洗浴中心“红星池 ”,有鲁迅等名人造访过的西安古旧书店、“四大名旦 ”之一的尚小云领衔的京剧院、冯玉祥倡建的卖日常小百货的第一劝业市场,还有大大小小的烟馆、妓院。如要烧香敬神,则到西大街对面都城隍庙去,庙门外有大牌楼,热闹类似北京的天桥广场,江湖把式你来我往,各色人等混迹其中。 1949年后,原来居住在这里的官宦、富贾大多逃散或放弃产权交公,加之诸多会馆弃用,留下许多空宅院,多为明清和民国式样的四合院,新政府的工作机关于是陆续进驻。最早成立的市民政局就设在街东头南侧的深宅大院。 1950年,母亲在西木头市小学教书,全家住学校隔壁。1952年母亲调到市民政局,便搬家到盐店街 73号院,与民政局对门。民政局是一个四进院,所谓四进,指四个院子套在一起,以穿堂相通。进了大门,东西有相对的厢房,过一间“一明两暗”的穿堂,便到第二个院子,又是东西厢房,再过一个穿堂到下一个院子,如此四进。这种进深的院子有后门,供买卖杂物和清运厕所秽物的人进出。我三四岁的时候经常到局里玩,记得曾从盐店街机关大门进,从五味什字街后门出来。由于多是在下午机关下班时去,院子空荡荡的,我独自走过一个又一个小院还见不到人,会有点害怕。这个情景幼时经常在梦中出现:我怎么也走不到大门外,天快黑了,周围还传来门窗自动关闭声,令人心悸,想喊又喊不出声音。长大后,偶尔还做过这样的梦。 和三才书店成为隔壁 1956年,位于街西头 39号(后改为 24号)院的民政局家属院建好,我们再次搬家,与三才书店成了紧隔壁。 说是紧隔壁,其实没有墙壁连接。因为书店不是正规建的,它的西边是一家私人经营的带阁楼的小杂货铺,铺子与东边我家院子门口的檐柱都伸出一截,与滴水檐齐,之间是属于北四府街一家院子的后墙,约有两间房的宽度,店家就在这两面外伸的檐柱之间搭建了一个一米多纵深的铺板门面,并充分利用檐柱的高度加装一层木板形成同等面积的小阁楼。这便是“三才书店”的经营场所。放在今天绝对属于违章建筑。 “三才 ”的名称当然来源于天、地、人三才的说法。这个书店在西安很有名,足以与钟楼新华书店、南院门古旧书店并称,只不过规模小得多,是一家专门出租和可供读者阅览连环画书籍的特色小店。从房屋的建造和店里的藏书看,起码在 20世纪 40年代中期就存在了。西安人把连环画叫“娃娃儿书 ”,文一点儿的叫“小人儿书 ”,当年是无数儿童梦寐以求又求之难得的读物,它的吸引力就在于此。那时城南的许多街道上也有“娃娃儿书摊 ”,多是在门口地上铺块布,或立个书架,摆上三四十本小书,供路过的大人小孩阅览,不能出租,其数量、品种和更新速度根本不能与三才书店比,而且一下雨就收摊儿,不能如三才书店春夏秋冬风雨无阻地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讲,三才书店是西安规模最大、品种最全、历史最悠久的小人儿书店。我从六七岁起便与它为邻十年,得以饱览群“小人儿书”,该是多么大的幸事! 39号院是民国式样的四合院。大门类似北京传统民居常用的“如意门 ”和“蛮子门 ”的混搭,是街上最讲究的。前檐出廊较多,砖砌檐柱宽大,门楣门框浑厚,门扇结实沉重,两个石礅贴在门框上,一尺高的门槛嵌在石礅里,门上有一对生铁铺首,半夜敲门用。大门内有门廊,左侧有门房,前院东西为两间的厢房,北边是三间临街房俗称下房,南边是四间的上房,所谓民国式四合院,主要指上房为两层新式楼房。西厢房与上房之间空地是井台,有绞水辘轳。上房左侧有一带门的通道到后院,后院西侧盖有厕所,分男女,有门窗,有水泥砌衬的大小便池,当年算是很卫生了,还有电灯照明。39号院属于比较高档、设施比较齐备的宅院。 说是民政局家属院,其实只有我家算是家属房,其余是单身职工的午休房,后来又陆续搬走,在很多年里院子里只有我们一家。空置的屋子都没锁门,想在哪个房间玩儿就在哪个房间玩儿,这段时光令人难忘。后来院子移交市兵役局,开始住进带家属的现役军官,最后又交回市房产局管理,院子住满,再无昔日清静悠闲景象。 搬家的当年我刚好上小学,学校用的是位于街中间小巷里的文昌宫旧址,文昌宫后改名城隍庙,西大街上的那个庙叫都城隍庙,总管西北,这个庙只管西安。 家里把厨房安顿在门道的门廊一侧,盘灶头,安风箱,放一张大梨木案,大水瓮,用桐木瓮盖遮苫。每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回家,我都坐在门道烧锅拉风箱,帮外婆做饭,不论春夏秋冬,一坐就是一两个小时。过年做年饭、蒸馒头,经常要一坐半天,连续拉几天火。好在一边坐小板凳拉风箱,一边可在膝盖上放本书看。小学六年读课外书的时间有一半是这样度过的,安详、井然之情境常可回味。 与书店主人的第一次接触 搬进 39号院不久,有天中午我照常坐在门道拉风箱看书,背朝着大门。忽然听到有人在门外和我打招呼:“看书呢? ”我转过身,见是个留着分头的陌生人,就问:“你找谁? ”没想到他一个大人,见了我这六七岁的小孩说话脸都红了,显得很腼腆:“我是隔壁书店的,能不能去你家院子上一下茅房? ”那时一般西安人把厕所还叫茅房,文明点的才叫厕所。那时民风淳朴,生人上门问个路、讨口水喝甚至在大门里避个雨、歇个脚都司空见惯。我很自然地起身领他穿过院子,到后面指点了厕所方位,然后继续回来拉风箱。出来时他冲我点头笑笑,脸似乎更红了,我也冲他点头笑笑。 来一次就会有第二次,只要见我在门道坐着,他就会经常来,开始还打招呼,后来时间长了,进门只是点点头笑笑,就直接去后院。有时看来实在不好意思,便停下来和我寒暄几句,无非是“上学了没有”“读几年级 ”一类没盐没醋的闲话。也可能我从小就“少年老成 ”,大人们不容易等闲视之吧。后来才知道,他叫张文义,是书店的二掌柜,大掌柜是光头,有家有室另有工作,平时不在店里。为了区分,旁人背后称张先生“分头三才 ”,家兄文中称他为“长发三才 ”,大掌柜自然是“光头三才”。面对面时没人这么叫,统称“三才”。 对每个人来说,如厕是小事,如厕是否方便却是大事。整条街上只有一座正式公厕,位于街道中段。街上的居民大多在自己院内如厕,只有路过的和个别院里无厕所的才上公厕。公厕和公用自来水站在一起,用自来水收费,公厕不收费,管水站的老头兼营厕纸收费。男厕所有一个小便池和四个蹲坑,蹲坑人多时则必须排。书店离公厕至少一百多米,离我家仅一步之遥。张先生每日一人照看书店,到我家院子如厕不走远路,极省时间,还可避免出现书店长时间无人照看时的不测之事。他自从认识我之后,“方便”的事就变得特别方便。 除了到门道做饭,外婆(我家习惯叫奶奶)主要在屋里做针线活或其他家务,不在院子多停留。偶然在院子见到张先生出入,便皱着眉头说 [1]我:“嫑把生人领到院子!”我答:“不是生人,是隔壁书店的三才。 ”外婆便不再言语,只是还皱着眉头。我虽然年纪小,帮外婆干家务活儿却是主力,烧火、倒垃圾、到水站抬水、到杂货铺买盐打酱油打醋,都是我。所以她平时不过分说我,如果我生气了,耍“小孩儿脾气 ”(尽管当时就是小孩儿),甩手不干家务活儿了,她还得好言相劝。所以 在允许三才到院子如厕这件事,外婆得由着我,不能严加禁止。如此一来,张先生来院里上厕所便成常态,家人习以为惯,视若不见。这应当算是我少年时社交公关的一个胜利。 三才书店成了我儿时的“天堂”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真是至理名言。从此,我和张先生成了忘年交。后来我到书店看书,他总是和颜悦色,笑容满面。书架上的书每个人都可以自己选取,但新书和受欢迎的“畅读 ”书,另放在他的身边,不能自取,得点名索要。当然,我来了,要看什么书,他会优先照顾。别人借书回家,要先交押金,归还时按天算账,对我不但不收钱,还允许我每次带几本书回家看。书店来了什么新书,张先生也总是很高兴地先告诉我。我每天在拉风箱时看书,看完马上到隔壁随意更换。老版《三毛流浪记》《三毛从军记》系列不用说,20世纪 50年代后陆续成套推出的《三国演义》《西游记》《水浒传》《杨家将演义》《聊斋故事》等等,我全部在第一时间看完,有的还反复看几遍。那时还出一些由电影截图编成的连环画,用电影台词做文字说明,看完便对看过的电影加深了理解和记忆,对没看过的电影增加了兴趣和渴望。其他同学看了电影,知其一不知其二,我却能知其三、其四,那种得意令人愉悦。更重要的是,有了连环画垫底,后来再读纯文字小说,感觉容易得多。 在家做完作业,我还爱照着连环画画画儿,当然水平和我哥不能比,他能模仿华三川、刘继卣、戴敦邦、王叔晖等名家画的连环画,各色人物惟妙惟肖,令人羡慕。但我那点水平,在班上同学中还算厉害。下课休息十分钟,同学们围上来,要我给他们本子上画关羽、赵云、岳飞,画青龙偃月刀、錾金虎头枪和青釭宝剑,还画赤兔追风马。为此,我到书店挑一些易于模仿的连环画悄悄在家练习,第二天再去显摆。当年能分辨清楚黄金锁子甲和镔铁连环甲、鱼鳞甲和人字形铠甲的区别。岳飞的铠甲就是人字形的,似乎是元帅的专属,元帅铠甲只露一个胳膊,另一边是战袍。关羽好像也是这种画法。黑色的乌骓马好画,但张飞不好画,掌握不住那金刚怒目的表情。我只能画斯斯文文的人,有人说,画家画出来的人都像他自己。 去街道垃圾站倒垃圾时,除了提家里的垃圾筐,我顺手捎上书店门旁的垃圾筐,偶尔也帮书店灌满一电壶(保温瓶)开水。有时在店里看书,张先生临时要离开一会儿,就托我照顾一下店铺,我便坐在他的座位上,为来看书的大人和小孩取书,收钱,俨然是个小老板。按同学的说法,三才书店成了我家开的。 每次来新书,书店一般一种进两本,张先生把其中一本的封皮撕下贴在招牌上,悬挂在醒目处,来人指名索要,他再从书架上取出。下一批新书来时,他才把上次撕下的书皮贴回原书。说来也怪,许多小孩望着招牌上的书皮,叫不出书名,只是说“给我取一下那本啥啥啥书 ”,他就能知道这孩子想要什么书,一取就准。我仗着自己认字多,在旁只管讥笑他们。 书店除了租借图书,还兼营糖果、炮仗和儿童玩具,有时还搞点博彩,虽是店主的生财之道,但足以吸引大小儿童把这里当成天堂。每到过年,附近街道穿新衣戴新帽、手握压岁钱的孩子都会聚拢过来,买糖的,买果丹皮的,买摔炮的,买孙悟空面具和金箍棒的,还有“戳彩 ”的——就是在用纸蒙着的方格里放置各种“奖品 ”,交两分钱任意戳一个格子,里面有张卷起的纸条,写着“硬糖一个 ”“弹弓一个 ”或其他小物品。有几个格子属于“重奖 ”,五分钱一戳,里面的东西要贵一些,如“手枪一个 ”“棒棒糖一个 ”,孩子们乐此不疲。格子里大多是“硬糖一个”,平时买一块硬糖是一分钱,戳彩得花两分钱,算是店主多赚了孩子的钱。也有几个孩子各要一本书坐在一起,偷偷交换,这样每人只掏一分钱就能看四五本书。算是孩子想办法让店主少赚钱。当然,这是书店不愿看到的,但孩子太多,张先生根本顾不上过来阻止。 三才书店给我的童年带来无穷乐趣和生活自信,我家几个兄弟也都和张先生亲密无间。我上中学之后,阅读来源变成了省图书馆、市新华书店和古旧书店,但两个弟弟还小,他们继续保持着这种亲密关系。说起来,张先生对我家兄弟个个都不错,令我们从小就得到温暖的文化 熏陶。这种熏陶,我哥称为“润物细无声”。 帮舅舅借阅文字小说书 二舅刚成年就去了青海柴达木油田工作,每年回西安探亲半个多月。他不爱讲话,白天喜欢一个人慢慢悠悠地转大街、看电影,晚上待在家里没事,知道隔壁书店除了连环画还有小说书,就问我能不能借到《福尔摩斯侦探案》。 我过去问,有,看哪本?一本一本借,都看。于是我先后借来《巴斯克维尔鬣犬》《血字研究》《四签名》等,都是 1949年前出版的老版单行本,繁体竖排,有些书上有比较恐怖的插图。他读完我接着读,大多看不懂,感兴趣的是《巴斯克维尔鬣犬》:“那坚硬的突岩、枝叶茂盛的沼泽地植物、让人毛骨悚然的夜半尖叫,一只闪着亮光的猎犬向人冲过来……”这场景会久久萦绕在你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二舅要的《归来记》书店没有,张先生便从其他人那里找来一本,再三嘱咐不要弄丢和损坏。我不知道二舅从哪里知道福尔摩斯的名字和这些书的名字的。三才家的小说书,都包着牛皮纸的封皮,怕书在传看过程中散开,拿锥子扎眼,用线绳订几道,和线装书的装订方式一样。后来才知道,这种保护方法对书的品相损害很大,为藏家所不屑。 第二年二舅探亲回家,这次点名要借张恨水的小说。他告诉我,张恨水原名张心远,喜欢谢冰心,追不到,就把名字改成“恨水 ”,恨水不成冰。后来知道这是江湖传言,张恨水明确说笔名源自李后主的名句“人生长恨水长东”。冰心也有专文澄清,并尊称张恨水为“前辈”。 张恨水是中国章回通俗小说的奇才,一生创作有一百多部小说,三千多万字,名作很多,有“中国的巴尔扎克 ”之誉。奇怪的是总被中国现代文学史忽略,可能是“天妒英才 ”。当年他的小说在报纸上连载时,每日排队买报等着看小说的人比肩继踵,蔚为大观,其影响远超过同时代任何一位小说作家。三才书店藏有全套张恨水的小说,大多是三四十年代出的各种单行本,也有上海文化出版社新出的《魍魉世界》等新版。我一本接一本地借,二舅一本接一本地看,读得飞快,一本看完,马上催我归还,借下一本,让我没有时间趁机浏览。只是借《八十一梦》时,书比较薄,我先抢着看完才拿给他。这本小说把猪八戒拉出来在梦中辛辣地讽刺时政,还能避过图书报纸杂志审查官的苛求,很有趣,很巧妙,很有智慧。 我问过二舅,要不要借新出版的小说。他抽着卷烟,笑着说:在柴达木把苏联和中国新出的小说都看完了,但那里没有老书,只听说过柯南 ?道尔和张恨水的名字,没想到三才书店应有尽有。是啊,这些书当时的新华书店都没有。 这些旧书三才从来不在明处摆放,都藏在阁楼上。阁楼十分逼仄,勉强能住人。我上去过,楼上的空间只能顺长放一张狭窄矮床,层高不过一米五,平时人只能坐在床边,无法站直。除了床,其余地方摆满了不允许公开阅览的古旧书,其中有民国时粗制滥造的武侠神怪荒诞字书和小人儿书,可能也有黄色书刊。这只是猜,没有亲见。 我上了小学四年级后就不再看连环画,开始从三才书店借读上海文化出版社竖排繁体《聊斋故事》《唐宋传奇选》等古典短篇小说简写本,还有林汉达编写的东周列国和两汉故事,后来就读《七侠五义》《小五义》《续小五义》之类的侠客小说。说来也怪,读后不甚喜欢展昭,反倒喜欢缺点百出的锦毛鼠白玉堂,他有小聪明,但很讲义气,称得上是侠肝义胆,可惜他在冲霄楼盗宝时被机关杀死,英年早逝。 下象棋是张先生唯一喜好 我一直不清楚张文义先生是哪里人。从冬到夏,他总是一身蓝布外衣,两颊带有“高原红 ”的血丝,肯定不是土生土长的西安人。见人总是很腼腆,说话斯文客气,完全不同于另一个“光头”三才。 “光头 ”三才蓄短髭,看样子练过拳脚,外形孔武有力,总是铮眉豁眼,说起话来生冷嶒倔,大家都不喜欢他。他好像姓王,就住在北四府街口,与书店不过十米。实际上他才是书店的主人,张先生不过是个伙计,但以兄弟相称。他每次来店里主要是给张先送饭,往往是一大碗“然面”,拿几瓣儿蒜,张先生吃起来狼吞虎咽,满头大汗。 回想起来张先生留的也不是什么分头,就是头发比平头长一些。分头有中分与偏分之别。电影上留中分的,不是汉奸就是流氓,偏分的也多是纨绔阔少或柔弱书生,如电影《青春之歌》中的余永泽。但张先生没有发型。到了冬天,他套上两只鼠毛护耳,围一条灰色毛线围巾,在脖子上一绕,胸前垂下一截,这才像个旧时商铺老板的样子,和电影《林家铺子》中的谢添相似,只是没有穿长衫长袍。 顾客少的时候,张先生戴上眼镜,也拿一本新书看,更多的是在小桌上摆一副袖珍的象棋盘,对着棋书打谱。除了杨官麟、胡荣华、王嘉良这些当代名家的棋谱外,还见他拿着线装的老棋谱看,肯定掌握不少“怪招儿”和“秘密武器”,一旦使出,招招要命,让对方缴棋认输。 书店有一副特大号的木制棋盘,棋子儿当然也大,拍起来啪啪作响,一旦叫将特别在“连吃带将 ”时能给对手产生极大的心理威慑。我也经常在一旁观战,发现拍棋的一方最后往往输棋,赢棋的一方则是默默地推着棋子儿走。 西安城里有的是象棋高手。会下棋的人经常彼此约战,来三才书店斗棋,这成为盐店街西头的一道风景线。棋摊儿就摆在我家门口,周边笃定围满了观战的人。吴承恩有一首关于描写围观围棋的诗,形容最是精妙:“四方豪隽会观局,丈室之间围再重。架肩骈头密无缝,四座寂然凝若梦。忽时下子巧成功,一笑齐声海潮哄。 ”如果有人先夸海口说要赢最后却输了,观战的必然起哄大笑。张先生也时时过来看一下进程,我问他谁能赢时,他只是笑而不语,回去继续照看书摊。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次盲棋大战。一位经常来的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店里拿一本连环画看,张先生蹲在街对面的棋盘前替他走棋,对手每走一步,张先生大声说“炮二进七 ”之类的招法,戴眼镜的放下书略加思考,说:“车五退一。 ”如此这般来回继续。 这种场面我是第一次见,真是惊呆了,有这样下棋的?这记忆力该有多强呀!最精彩的一幕是,戴眼镜的把书合起放回书摊,推起自行车,说一句:“卒五进一,缴棋! ”然后骑上车扬长而去,只见对手默不作声,表情狼狈不堪,围观者又爆发一阵哄堂大笑。 “缴棋 ”是棋局结束时双方把吃掉对方的棋子儿交还对方,先交还的便是表示认输。下棋时说“缴棋 ”是让对方认输,相当于喊“缴枪不杀 ”。王安石也有围棋诗:“讳输宁断头,悔误乃批颊。 ”是说下棋的人不肯轻易认输,下出了臭棋便会自批耳光,很生动。 自从看了这盘蒙目大战,我决计再不下象棋了,因为我今后不可能达到这个水平。达不到这个水平,下象棋还有什么意思?改学围棋算了,但那时我周围没有人会下围棋。 不知什么原因,张先生一般不和别人下棋。我只见过一次张先生和别人下棋,看形势张先生即将赢棋,只见他表情变得紧张而又激动,拿棋子的手抖个不停,和茨威格《象棋的故事》中描写的那个 B博士一模一样。打谱多而实战少的人下棋往往都这样,对局中出现与打过的谱有相同棋形而自己又十分熟悉的时候,往往心跳加快。这和考试发下卷子,发现自己猜中了试题的激动心情一样。 三才书店的最后绝唱 1966年 9月的一天下午,三才书店被一群戴红袖章的中学生强令在街道中间烧毁全部藏书,这个当口儿我正好在外地,没有亲见,事后听家兄讲述,十分痛心和愤懑。 这些学生可能来自梁家牌楼街的市二十七中,他们学校距离书店只有一百多米。不过,那时全国形势都一样,三才书店的书不是被这个学校就是被那个学校的学生焚烧,终归难逃一劫。可以想象到当时的场面:一群穿着绿色军装、戴着军帽的男女学生打着某某战斗队的红旗,高呼着什么无罪、什么有理的口号,突然包围了书店,几个领头人用手指着张先生大声训斥,其他人把书店的书搬下来,用脚践踏,乱七八糟地丢到街上,形成高高的书堆,过往的路人围成一圈,看着他们有人用火柴把书点燃,有的人还厉声骂着,用棍子拍打张先生,责令他亲自把其余的书都扔进火堆。不一会儿,盐店街西头便火焰熊熊,腾起一团黑烟升上天空,这些学生的情绪进一步被烈火激发,大喊着,推搡着,命令着,把书店楼上、楼下的带纸张的东西烧个精光。我哥眼见张先生把户口本也丢进火堆,经人提醒才赶快拿回。火焰熄灭后,这群学生还拿出一张传单似的东西大声朗读,内容是京城某总部的通告,勒令一切所谓成分不好的人立即滚出城市,哪里来的哪里去,立即生效。 这场被冠名某种行动的场面总算结束了,张先生肯定吓坏了,他绝对没想到平静了十七年的日子突然就这样消失了,以极恐怖的方式消失了,陪伴他二十多年、赖以生存的群书瞬间变成一团发烫的灰烬。烧书的学生中恐怕有不少人曾经来这里看过书,有的可能还只花一分钱就偷看了几本书,有的在这里摸了几次彩发现都是小奖品而怀恨在心吧?有的没钱看书就叫骂“三才洋来、上山打柴 ”而被赶跑过吧?张先生不知道做错了什么,只能赶紧收拾东西,连夜离开西安城。 一个在西安极有影响,和我个人、全家有紧密关系的三才书店就这样没有了,从 1956年到 1966年,整整十年的美好记忆突然变成一场噩梦。“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那几十个亲手毁掉西安这个文化田园的无知暴戾少年,汝今安在否?几十年过去,仍感觉青春无悔否?猜想这些人都已经老态龙钟,仍然没有丝毫罪恶感,还是一脸无辜的样子吧?有人说,他们也是“受害者”,施虐者和受害者能一样吗? 十几年后的一天,大约是 1977年,我在盐店街家门口看书,张先生突然出现在眼前,那情形,那感觉,简直和鲁迅在《故乡》中见到阔别多年的闰土、在《祝福》中见到被赶出四叔家的祥林嫂一样。 他还是长头发,但两鬓已经灰白,脸颊的“高原红”变黑了,似乎多日未洗脸。头顶和衣服上全是灰土,好像刚干完重体力活儿,样子显得十分疲惫,说话也有气无力。 多年前他第一次见我,曾怯生生地问能不能进院子上厕所,这次他仍是怯生生地问我:“你哥在不在? ”我告诉他家兄这会儿在南院门公社(后改称街道办事处)上班,没在家,他道声谢便匆匆离开。 后来才知道他是回来找工作的。我哥多年前便在南院门街办工作,此时已是“街办小令 ” —副书记、副主任。张先生打听到原来被驱逐回乡的人可以返城了,便从原籍赶回,又听说我哥在街道办工作,就想找他帮忙。家兄和书记商议后,就安排他在办事处传达室工作。办事处聘用临时工不用请示汇报,街办财政能够支付工资就行,不算违反规定。 我后来有次去办事处找我哥,经过传达室,张先生戴着眼镜正在读报,见有人来立即从窗户探头询问,见是我便笑容满面,带点紧张地说:“你哥在后面。 ”我离开时和他打招呼,他从屋里走出来,送我到大门外,说:“没事常来。 ”这是我和他最后一次见面。 一如家兄文中所述,街道办事处自己盖家属院,也给张先生分了一套两居室。他晚年的工作和生活都很安定,虽然没有孩子和亲人。张先生最后安静地在家里去世,办事处出面送终时,只见家徒四壁,仅有棋谱数册和生活用品而已。 家兄这是做了一件善事,也算是我家兄弟对他的一种报恩。只是没想到,西安的三才书店竟与我家如此有缘! 2000年前后,盐店街西头拆迁,我家也彻底地离开了。但时隔二十年,24号院仍是一片废墟,工程没有进展,还能让我和没在这里住过的外孙们看到老家原来的旧址,也算惬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