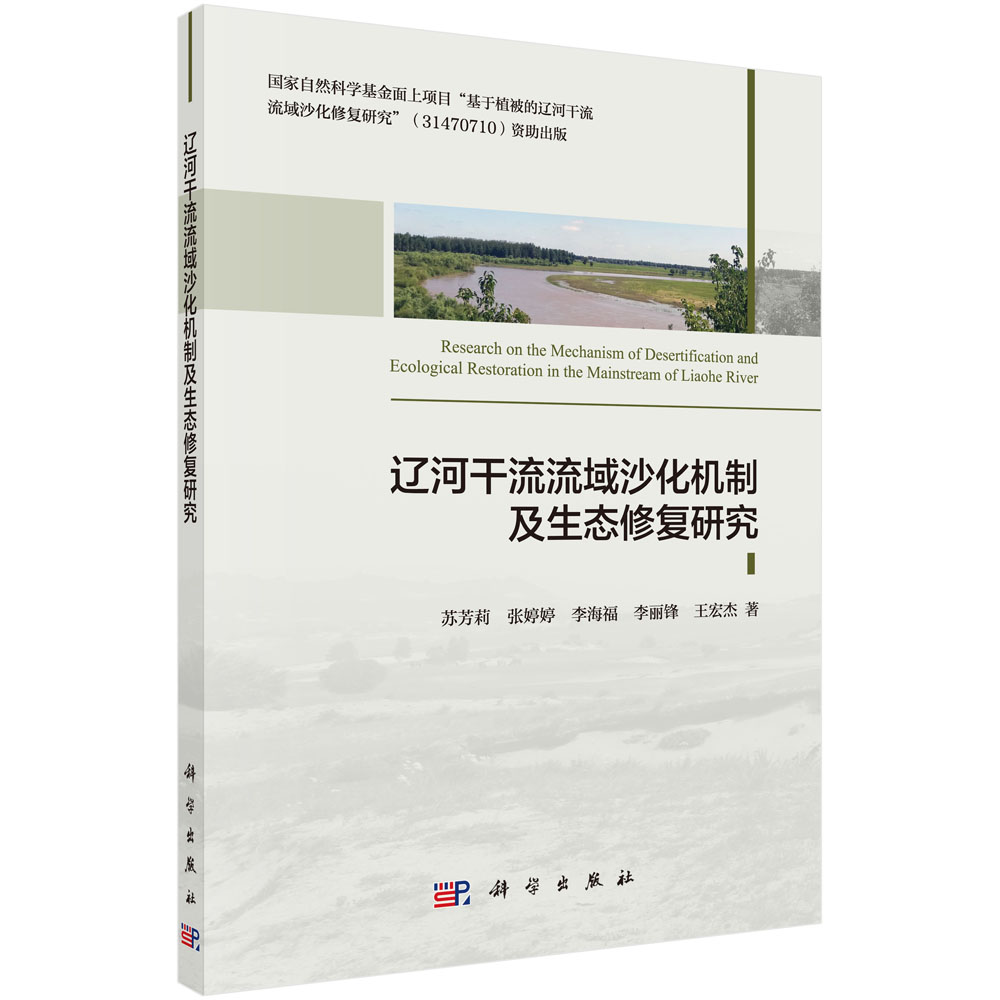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99.00
折扣价: 78.30
折扣购买: 辽河干流流域沙化机制及生态修复研究
ISBN: 978703061208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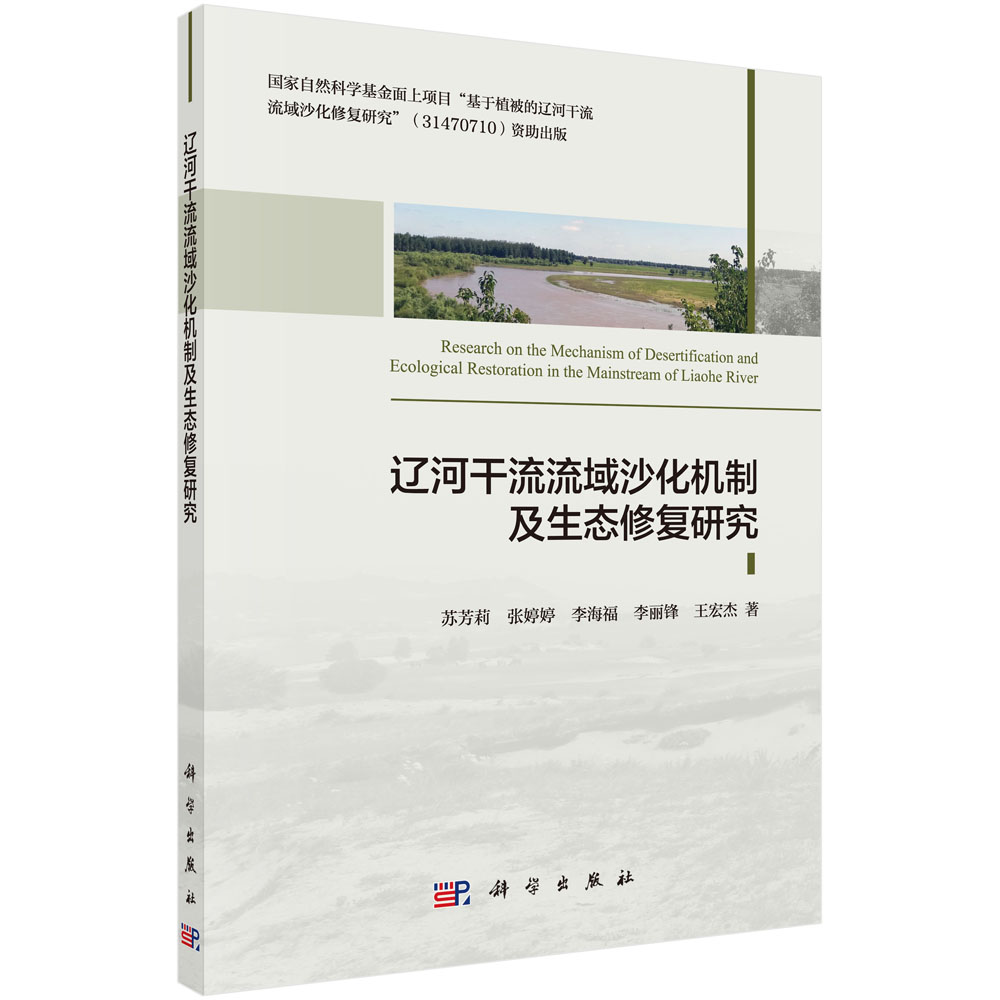
**章 绪论
河道是社会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承载着各自然要素间能量流、物质流和信息流的交换作用,发挥着通道、生境、“源-汇”等重要的生态功能。河道治理应在保证防洪、排涝及引水功能的同时,发挥上述生态作用。但我国河道治理“渠化”“硬化”现象突出,使得植被减少,水体的生态承载力和自净能力降低;生境的空间异质性减弱,生物多样性降低;硬覆盖阻断了水陆间物质与能量交换,破坏了生境条件和生态系统完整性;景观协调性差,不能满足现代人类亲近自然的要求。故亟需进行生态修复,提高河道稳定性,提升河流功能。
河流泥沙是塑造河道及河口形态的重要物质来源,也是引发河流问题的主要因素,对陆地及海洋生态安全均具有重要影响。河流泥沙含量过高引发河道淤积,险情加剧;携带的氮磷等营养物质导致面源污染及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日益严峻。但由于河流水沙规律极其复杂,且泥沙防控技术区域性差别极大,多沙河道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尚缺少系统研究。
辽河为全国七大江河之一,是仅次于黄河和海河的多沙河流,辽河干流水质污染及流域沙化问题严重。由于流域侵蚀,每年有大量泥沙及其携带的氮磷等营养物质进入河道,成为辽河污染不可忽视的因素,直接或间接造成辽河干流主河道游荡、河势不稳、水质多年不达标、河岸带植被稀少、生物多样性低等问题。河道虽经多年治理,但久治不愈,其重要原因是河流泥沙未得到有效防控,泥沙来源及防控机制不明晰。辽河干流具有独特的水资源匮乏与河道多沙并存特征,现有水沙理论不适于指导辽河干流泥沙防控,传统河道治理方式难以满足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需求,构建适于辽河干流的河道生态修复理论与技术体系是解决辽河问题的关键。本书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支持下完成,全面丰富了河流生态治理理论与技术,可为辽宁省委、省政府提出的辽河流域综合治理攻坚战提供技术支撑,为实现“山青、岸绿、水净、河畅”的生态目标及美丽辽宁提供保障。
**节 流域沙化修复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辽河水沙关系
辽河是辽宁的母亲河,辽河流域是辽宁省工农业发展最活跃的地区,因此,辽河与辽宁的社会、经济发展息息相关。据统计,辽河流域水资源总量约214亿m3,然而截至2001年实际供水量已经达到151.78亿m3,水资源利用率已经达到71%,大大超过了水资源开发利用的极限。高强度的水资源开发使辽河流域近几年面临水资源严重短缺、河道断流、水体污染严重、生态环境恶化等一系列问题,已经严重影响了辽宁老工业基地的建设。
辽河流域侵蚀严重,河滩裸露,植被覆盖度低,水土流失问题严重,辽河全流域水土流失面积9.5万hm2,占全流域面积的43%,主要分布在西辽河、东辽河及柳河、绕阳河上游,其中柳河每年进入辽河干流的泥沙就达2.0×107t,因此,辽河是多沙的河流,河流的含沙量仅次于黄河、海河,位于中国第三位。高含沙量使得河道严重淤积,影响河道行洪泄洪,危害岸上人民财产安全。
现有泥沙防控技术无法满足干流泥沙、面源污染物控制与生态恢复的需求。为改善河流水质使辽河保护区的生态环境质量得到根本改善,必须对辽河保护区进行生态治理。为了制定合理的生态建设方案,许多研究者或单位对辽河流域发育的动力过程、剖面塑造机制、演变规律以及泥沙交换进行了探讨和分析,并且这些分析大多以现有实测资料为基础,且以常规手段获得,具有一定的空间和时间的局限性,难以全面地掌握研究目标的空间分布和动态变化规律。为了更全面掌握保护区的悬沙分布、泥沙淤积和水资源变化情况,必须采用新技术、新手段,卫星遥感影像资料可以提供这方面的丰富信息,用卫星数据定性乃至定量研究河流表层泥沙运动规律和水资源情况已成为一种新型的、有效的手段。
传统的水体监测技术由于受到自然环境、仪器设备等因素的限制,具有一定的局限性。随着遥感技术的不断发展,MODIS、Landsat、NOAA、ASTER、RADARSAT、CBERS等卫星影像都被用来获取水体信息,并且在大面积水域动态监测、水质监测和洪水监测预报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水体遥感监测技术具有以下特点:
(1)宏观性强,可以进行大范围监测;
(2)效率高、信息量大,能同时获得多点位、多谱段的遥感信息,提高监测的效率[2];
(3)可以进行动态监测,建立水灾害预警系统,实行实时监控,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轻灾害威胁[3]。
不同物质有不同的光谱特征,相同的物质在不同的环境下光谱特征也不相同,因此,水体的光谱特征是进行水体遥感监测的依据。不同的反射光谱在遥感影像上有不同的图案、色调和纹理等反映,根据这些差异可以提取出水体的范围以及污染范围等信息。近年来,经过国内外学者的不断努力,遥感技术在进行水域面积动态监测和水体悬浮泥沙含量获取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一)遥感水域面积动态监测方面
Haralick等于1985年提出了色度判读法,即利用卫星绿波段、红波段和红外波段的综合信息确定水体范围[1]。Barton等利用AVHRR的第4波段的亮度,采用密度分割法识别水体并对洪水进行监测[2]。随着归一化差异植被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vegetation index,NDVI)的建立和应用,许多学者开始借鉴NDVI的成功经验,将波段组合后进行比值运算,目标物体类反射率强的作为分子,反之为分母,这样目标地物被凸显出来。McFeeters根据这一理念提出了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NDWI)法[3],这种方法成为水体提取的经典模型,随后的许多模型都是在该模型基础上进行修正或改编的,但是NDWI提取的水体信息中仍然包含有诸如阴影、泥沙、土壤等除水体外的其他信息。陆家驹等研究了TM影像并通过近红外单波段法、色度判别法和比率算法识别水体,对比分析了这三种方法的精度,指出比率算法既能识别出其他两种方法识别不了的小水体,又能优化较大水体的面积形状[4]。徐涵秋在归一化水体指数的基础上,对波段组合进行了修改,提出了改进型归一化差异水体指数(modified normalized difference water index,MNDWI)模型,并将该模型应用于不同的水体类型,经对比发现该模型在大多数情况下比NDWI提取效果好,并且MNDWI能较好地区分水体和阴影[5]。莫伟华等分析了MODIS与水体相关的波段信息,提出了一种新的混合水体指数模型,该模型对植被指数和MODIS第7波段做进一步组合,能有效地把水体从云层、植被和城镇等非水体中提取出来,并且他们对广西贵港市平龙水库进行了水体提取,精度较高[6]。
(二)悬浮泥沙浓度的遥感反演方面
国外许多学者很早就开始借助于卫星遥感的手段对水体悬浮泥沙浓度及其运动规律进行研究。Klemas等建立了特拉华湾(Delaware Bay)悬浮泥沙浓度的MSS遥感影像统计模型[7]。Stumpf等建立了监测中等浑浊度海湾悬浮泥沙浓度的实验系统,该系统的卫星数据源为AVHRR的CH1和CH2波段[8]。Froidefond等在2002年对法属圭亚那海湾的悬浮泥沙浓度进行了估算[9]。
地物反射的电磁波在传输的过程中受大气的影响较大,因此,在用遥感影像反演悬浮泥沙浓度时,需要考虑大气传输的影响。Gordon等建立了著名的Gordon关系式,该关系式能较好地消除或削弱大气对光的影响[10]。Mishra 基于 IRS-1C WIFS 遥感数据建立了孟加拉湾悬浮泥沙遥感反演模型[11]。近年来,国内悬浮泥沙遥感定量的研究主要针对近海Ⅱ类水体进行。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一些学者利用遥感影像和同步或准同步实测含沙量建立遥感反演模型,并对我国近岸河口地区的海洋悬浮泥沙进行了定量反演研究。恽才兴等基于MSS遥感影像和水体悬浮泥沙浓度地面实测值建立长江口处两者的统计相关关系[12]。陈夏法利用多时相NOAA卫星影像及同步实测水体悬浮泥沙含量,对杭州湾及其附近海域的水体表层悬浮泥沙浓度分布、变化和扩散等特征进行了分析[13]。吴传庆等利用MODIS数据对长江口及南北海域水体表层泥沙浓度进行了反演和分析,掌握了长江口的泥沙分布和运移规律[14]。梅长青等提出了利用泥沙指数来提取泥沙分布的方法,并利用陆地卫星ETM+数据得到了巢湖湖区的泥沙分布图,并对巢湖悬浮泥沙分布的环境背景进行分析[15]。奥勇等利用TM遥感数据与实测的 29个站点的海洋水色数据,建立了基于TM数据的曹妃甸近海区水体悬浮泥沙浓度的遥感定量反演模型[16]。随着MSS、TM、SPOT和AVHRR等遥感传感器的发展,国内很多学者利用含沙水体光谱反射率和地面实测水体悬浮泥沙含量相结合的方法,对长江口和杭州湾悬浮泥沙浓度进行了定量监测[17, 18]。许珺等建立了基于SPOT影像的水体悬浮固体浓度遥感反演模型,并且把该模型应用于淡水河和台湾基隆河[19]。陈晓翔等分析了气象卫星FY-1D数据和准同步实测数据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基于FY-1D的珠江口海域悬浮泥沙浓度遥感估算模型[20]。
二、辽河干流流域沙化评价
20世纪中叶以来,社会经济得到持续快速发展,不合理的人类活动及脆弱的生态环境相互作用导致具有全球性影响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沙尘暴肆虐,土地沙化面积不断扩大,严重危害着人类的生存。土地沙化每年对全球经济造成的损失超过400亿美元,我国的土地沙化形势非常严峻,沙化土地分布广,危害严重。沙化影响生态环境的建设,不断侵占人们的生活空间,严重制约着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土地沙化问题已不仅局限于传统的沙漠地区,我国七大河流流域均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土地沙化现象。江河流域土地沙化后,泥沙在流域内经起动、输移、沉积等加重水土流失。辽河属于我国的七大河流,是辽宁省最大的河流,流域面积接近全省土地面积的一半。辽河干流流域水土流失日益严重,土地沙化面积不断加大,分布有一定面积的半固定沙地、大面积的固定沙地、露沙地及沙化耕地,辽河干流流域的沙化土地已成为辽宁省的新沙源。国家林业局2015年发布的《第五次中国荒漠化和沙化状况公报》显示,至2014年,辽宁省现有沙化土地面积 5107k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 3.45%,较第四次监测公报减少388km2。土地沙化虽得到一定治理,但依然威胁着地方的生态安全与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流域沙化评价属于土地沙化评价的范畴。土地沙化评价是对干旱、半干旱和干旱亚湿润区的退化土地进行类型的划分与程度的分等定级。土地沙化评价的前提是建立土地沙化评价指标体系,核心是确定评价土地沙化程度的方法和划分土地沙化等级[21],土地沙化程度统计表及土地沙化分布图是土地沙化评价的最终成果。
(一)土地沙化评价指标体系
Lamprey是最早对荒漠化进行评价研究的,其综合植被图、航片和现场调查估算沙漠平移速率,结果表明撒哈拉沙漠每年平均向南移动5.5km,由此人类开始对荒漠化进行评价研究[22]。对土地荒漠化的评价更加系统,并将其作为体系提出的是Berry。Berry考虑到指标选取中的尺度问题,提出了全球、区域和地区荒漠化的鉴定指标系统[23]。1978年,Reining又把荒漠化指标具体化,H. Eregne则建立了一个包含社会经济、生物和物理指标的评价指标体系[24]。上述学者的研究以宏观的定性指标为主,实际应用中存在较大难度,但为世界荒漠化评价研究奠定了基础。1984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和联合国环境署制定的《荒漠化评价和制图暂行办法》从植被退化、荒漠化土地发展速度及内在危险性3个方面提出了评价.指标和评价方法,制定了相对完整的定量评价指标体系,从而开创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我国荒漠化问题的研究工作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对沙漠的研究,而荒漠化评价研究则是在1978年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成立之后[25]。国内.学者.对土地沙化领域做了大量的研究,不同学者选取的评价指标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