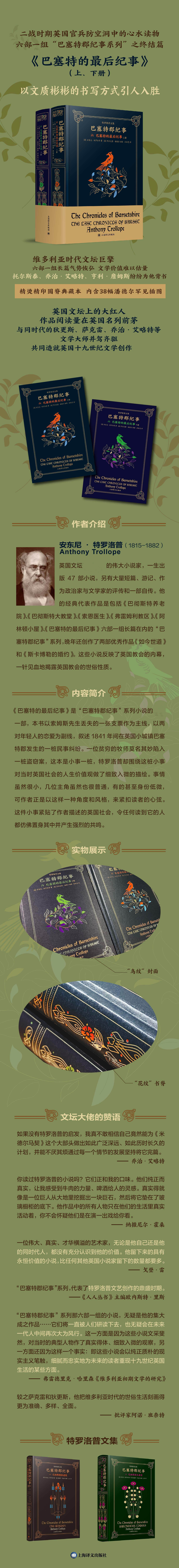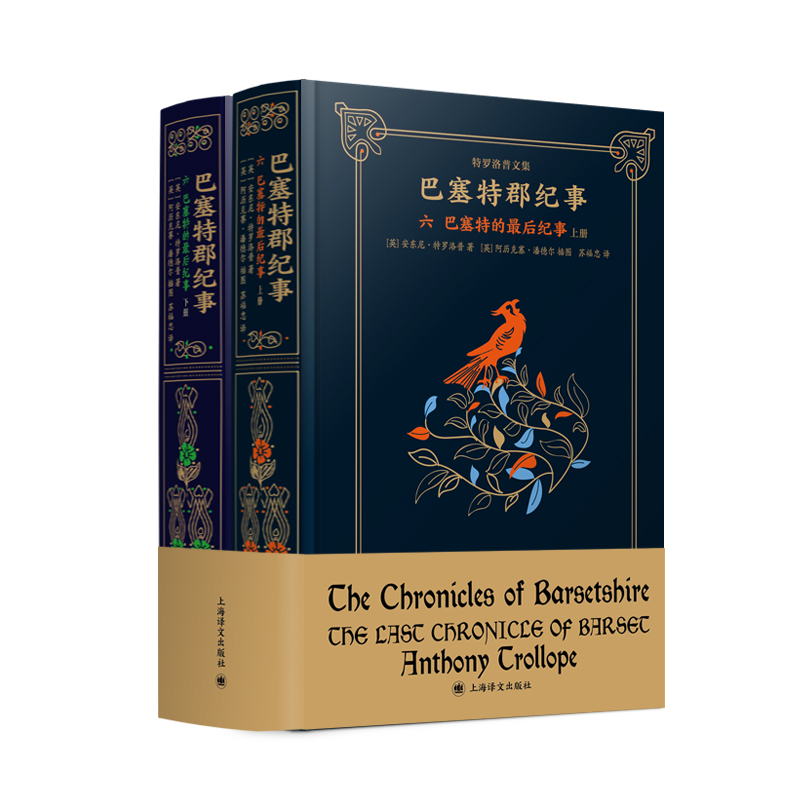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译文
原售价: 228.00
折扣价: 148.20
折扣购买: 巴塞特的最后纪事(上 下册)
ISBN: 978753278676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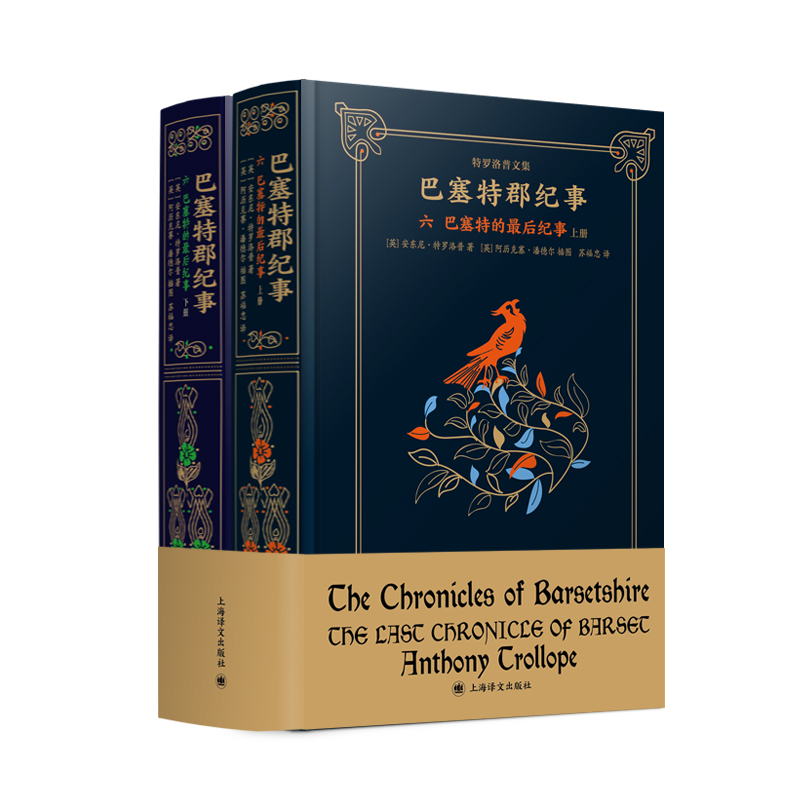
【作者简介】:安东尼?特罗洛普(1815-1882),英国声誉卓著的伟大小说家。一生出版47部小说,另有大量短篇、游记、作为政治家与文学家的评传和一部自传。他的经典代表作品是包括《巴彻斯特养老院》、《巴彻斯特大教堂》、《索恩医生》、《弗雷姆利教区》、《阿林顿小屋》、《巴塞特的最后纪事》六部一组长篇在内的“巴塞特郡纪事”系列,晚年还创作了两部优秀作品《如今世道》和《斯卡博勒的婚约》。这些小说反映了英国教会的内幕,一针见血地揭露了英国教会的世俗性质。
\"【精彩书摘】:上卷第一章他是怎么得到它的? “我也不能相信这事,约翰。”玛丽?沃克说;玛丽?沃克是西尔弗布里奇的代理人乔治?沃克的标致的女儿。“沃克和温思罗普”是这个事务所的名字,他们是有名望的头面人物,王国政府在巴塞特郡这一带必得有人去干的那种律师事务,都让他们包圆儿了;他们也受聘办理在那些地区十分显贵的奥莫尼乌姆公爵的地方事务,因此他们总是昂头叠肚,趾高气扬,全然一副外省的律师们的样子。他们——沃克家——住在这个市镇中间的一座大砖房里,经常宴请宾客,不过郡里的士绅却不怎么经常赏脸赴宴;在西尔弗布里奇,他们很有分寸地走在风尚的前面。“我是怎么也不能相信这事的,约翰。”沃克小姐又说。 “你不信也得信。”约翰搭着话,眼睛却没有离开他的书。 “一个牧师,还是这样一个牧师!” “我看这事没有什么值得费心嘀咕的。”约翰这次说话时,眼睛不再看书了,“一个牧师为什么就不能跟随便哪个人一样成了小偷呢?你们女孩子似乎总是忘记,牧师们不过也是常人罢了。” “我觉得,他们的品行会比别的人更好些。” “我根本不这样想,”约翰?沃克说,“我敢说,此时此刻,巴塞特郡负债的牧师远比律师和医生要多。这个人一向负债累累。自从他来到这个郡,我看他就从来不敢在西尔弗布里奇的海伊大街露露面。” “约翰,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可没权利说这话。”沃克太太接话说。 “为什么,妈妈,得到这张支票的那个屠夫,几天前威胁说要把账单在全县张扬,把该还他的那笔债如实说明,要是不能马上还债的话。” “弗莱彻先生更不知羞耻,”玛丽说,“他在西尔弗布里奇当屠夫发了横财。” “这有什么可非议的?一个人当然愿意把钱攥在手里,他已经给那位主教写过三次信,专派一个人接连六天去霍格尔斯托克解决他那笔小账。你看他到底要到这笔账了。当然,一个生意人一定要看紧自己的钱呀。” “妈妈,你认为克劳利先生偷了那张支票了吗?”玛丽问这个问题的当儿,走过来站到她母亲跟前,用焦急的目光看着她。 “我还是不表态的好,我亲爱的。” “可是人人都在议论这事,你总该有想法的,妈妈。” “妈妈当然认为他偷了,”约翰说着,又要埋头看书,“妈妈要有别的想法才怪呢。” “这话不公平,约翰,”沃克太太说,“你那些凭空想法不等于我的,也不能硬让我从嘴里说出来。整个儿这事是非常令人心酸的,你爸爸又正在查这件事,我觉得在这家里还是越少议论越好。我敢肯定,这也会是你爸爸的心情。” “我当然不会在爸爸面前说它的,”玛丽说,“我知道爸爸不愿意乱嚷嚷这事。可是,一个人怎么会压根儿不想它呢?它对我们所有在教的人,实在是太可怕了。” “我根本不这样看,”约翰说,“克劳利先生仅仅因为是个牧师,一点不会比别人特殊。我憎恨所有徒有虚名华而不实的玩意儿。在西尔弗布里奇,有不少人认为,仅仅因为这个人身居一种会使这一罪行比犯在别人身上更深重的位置,这事就不应该追究下去了。” “可是,我完全肯定克劳利先生根本没有犯罪行为。”玛丽说。 “我亲爱的,”沃克太太说,“我刚刚说过,我不愿意你再谈这事。爸爸马上就进屋来了。” “我不说了,妈妈;只是——” “只是!是的;仅仅只是!”约翰说,“要是有人呆在这儿听她说,她会一直说到摆餐桌的。” “你比我一句也没少说,约翰。”但是,约翰还没听见他妹妹说出来最后这些词儿,早已离开屋子走了。 “你知道,妈妈,不想这事是做不到的。”玛丽说。 “我信这话,我亲爱的。” “不过你熟悉他们吗?我至今从来没有跟克劳利先生说过话,也不记得过去见过克劳利太太。” “我很了解格雷丝,她过去常到普雷蒂曼小姐的学校去。” “可怜的姑娘呀。我真可怜她。” “可怜她!可怜这个词不恰当,妈妈。我为他们感到痛苦。可是,我心里没有存过一会儿他偷了那张支票的念头。那怎么可能呢?虽然他们家穷得厉害,因此负了债,可我们都知道他是个十分杰出的牧师呀。罗巴茨一家上次来这里做客,我听罗巴茨太太说,克劳利先生恪尽职守,兢兢业业,她过去还几乎没有看见哪个人能和他相提并论呢。罗巴茨家当然比任何人都更了解他们。” “人家说教长是他的好朋友。” “多遗憾吧,正当他有麻烦时阿拉宾一家眼下都离开了。”就这样,虽然沃克太太先头说过不再对这件事说长论短,这时母女俩还是接着讨论那个牧师的犯罪问题了。沃克太太,像别的做母亲的一样,和自己的女儿说起话来,比和儿子说话更容易自由起来。就在她们这样说着话时,做父亲的从他的事务所回来了,于是这话题就中断了。他是个介于五十和六十岁之间的男人,头发斑白,留得很短,身体有点发胖,但地位舒适和受人尊敬这两点一般情况下将赐予那种个人的风度,仍然看得出来。一个人被世人捧起来,他自己是很少不识抬举的。 “我累坏了,我亲爱的。”沃克先生说。 “你看上去是受累了。过来坐一会儿好去换装吧。玛丽,拿你爸爸的拖鞋来。”玛丽连忙向门口跑去了。 “谢谢,我的宝贝。”父亲说。然后,一等玛丽走开听不见说话时,他便在妻子耳旁小声说:“恐怕那个倒运的人是有罪的。我担心他是这样的!我真的担心!” “哦,天哪!他们会发生什么事呢?” “什么事吗?克劳利太太今天跟我说这事来了。” “是吗,她?你能跟她说什么呢?” “我开始告诉她,我还不能见她,请她别跟我说这件事。我极力想让她明白,她应该到别处去找人。但没有说服她。” “那到底怎么办呢?” “我要她来找你,可她不同意。她说你帮不了她什么忙。” “那她认为自己的丈夫有罪吗?” “不,当然不会的。她哪会认为他有罪!照我看,说破天说破地也没法儿让她想到那是可能的。她来找我,只是告诉我她丈夫有多么好。” “我倒喜欢她这样做。”沃克太太说。 “我也一样。不过,喜欢她又有何益呢?谢谢你,我的宝贝。也许,我哪天会给你拿拖鞋的。” 全郡轰动了,都在谈论乔赛亚?克劳利牧师这件所谓罪过一事——全郡,几乎全像西尔弗布里奇的沃克先生一家这样急切热烈。指责他的罪过,是说他偷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说他先从一个遗忘或丢在他家的皮夹里偷走,然后兑成现钱还到了西尔弗布里奇的屠夫弗莱彻手里,因为他欠人家的债。克劳利先生在那些日子里是霍格尔斯托克的终身副牧师;霍格尔斯托克是东巴塞特郡北端的一个教区,教区里谁都知道克劳利先生穷得家徒四壁,又是个不幸、忧郁、悲观失望的人,这个世界的种种苦难似乎总是以双倍重量压在他的身上。自从他的老朋友阿拉宾先生,巴塞特郡的教长,给他现在担任的这个小职务,他从来没有被人尊为牧师。尽管他不幸、忧郁、悲观失望,但他在那些与他同命运的穷人中间是个埋头苦干、自觉认真的牧师;因为在霍格尔斯托克教区除了寥寥无几的几位农场主,其余都是地位卑微的农田工人、制砖工人,以及诸如此类的百姓。克劳利先生眼下在霍格尔斯托克已经打发走了他生命的十八个年头;在过去的年月里,他十分努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坚持不懈地向他周围的人灌输了也许过多的玄义,但也演讲了一些有关舒适,有关宗教的东西。他在自己的教区变得为人爱戴,这点是他想不到的。他在哪方面都不是个能够使他自己受人欢迎的人。我前面说过,他是个忧郁寡欢、悲观失望的人。他实际上比这还糟糕;他一脸苦相,有时几乎到了神经不健全的地步。在以往的一些日子里,甚至他的妻子都发现很难对付他,还不如对付一个明确的精神病患者容易。这点在农场主中间也是众所周知的,他们在自己人堆里议论他们的牧师,就像是谈论一个疯子。但是在赤贫的穷人中间,在霍格尔恩德的制砖工人中间——一批无法无天、一醉方休和极端粗野的人——他却受到极高的尊重;因为他们知道他生活得很艰难,和他们的日子相差无几;知道他干得很苦,和他们的工作大同小异;还知道外界世界对待他十分严酷,如同对待他们一样毫不客气;他们还知道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明显的神圣的忠诚品质,有一种不顾世界的虐待而恪尽职守的精神,这种精神即使在逆境中也毫不妥协;因此,克劳利先生尽管有那种不幸的怪癖性格,但在他的教区里却很受人尊敬。就是这个人,他现在被指控偷走了一张二十镑的支票。 但是,在交待这桩所谓的偷窃公案的情况之前,关于克劳利先生的家庭是一定要说几句的。常言道,一个好妻子是她丈夫的一顶王冠,而克劳利太太对克劳利先生来说还远不止一顶王冠。对于这个人的全部精神生活——他在讲坛布道或牧师执教以外的所有那部分生活——克劳利太太一直是集王冠、御座和御杖于一身。她同克劳利先生一起忍受并替克劳利先生忍受了贫穷带来的种种痛苦和没有微笑的生活酿造的各种烦恼,这点也许不能直接说成是她的贞操吧。她和他有福同享,有难共患,而把分担这样的东西看作她义不容辞的职责;做妻子的不得不承担这些东西,因为她们知道嫁鸡随鸡,嫁狗随狗这个理儿。克劳利先生本来也许是个主教的料子,克劳利太太嫁给他时也许认为那样才是他的运道。但是他没有当上主教,眼下在他年近五十时还是个终身副牧师,一年只有一百三十镑的收入——还有一个家。而这正是克劳利太太一生的运气,她也就心安理得地承受了它。但是她又远远不只承受这点。她过去竭尽全力表现得心满意足,或者贴切点讲,竭尽全力做出心满意足的样子,尤其在克劳利先生最背时和最阴沉的时候。她深信克劳利先生神经不够健全,却努力不让他知道这点,一如往常地对待他,一个父亲在一个家庭里的尊敬应有尽有,并且像对待一个任性的病孩儿那样极有分寸地纵容他。在对待他们生活中所有那些可怕的烦恼时,她的勇气一贯超出克劳利先生。制作她的那块生铁已经百炼成钢,炉火纯青,只是那种炉火纯青的程度克劳利先生熟视无睹,欣赏不了。克劳利先生经常跟她说,她没有自尊心,因为她过去总是替他或替孩子们低三下四地接受别人的东西,接受那些非常需要却购置不起的东西。他跟她说,她是个讨乞鬼,并说活人与其饿死也不行乞。她默然承受了这种斥责,事后仍旧为他乞讨,自己却忍受饥饿之苦。过去的多少年来,她从不为他们的穷困感到无脸见人;而对克劳利先生来说,他们的贫困带来的每件小事,过去是一种存在的耻辱,现在还是一种活生生的耻辱。 他们生过许多孩子,活下来的还有三个。关于老大,格雷丝?克劳利,在以后的故事中我们将多次听到她的名字。她这时十九岁,据那些人说,尽管她家很穷,外面的穿着寒酸,身材单薄,看上去不够成熟和丰满,身上的线条也不够匀称,可她仍是那一带最标致的姑娘。她现在住在西尔弗布里奇的一所学校里,最近这一年当上了教师;在西尔弗布里奇,有不少人说十分光明的前程就要在她面前展开了,说科斯比洛奇的年轻的格兰特利少校在她那纤弱的脸上看到了美的光彩;格兰特利少校是个鳏夫,膝下有个小孩,但在西尔弗布里奇方圆一带的所有女人眼中仍是十分引人注目的男子,这似乎可以说,格雷丝?克劳利就要时来运转,和她家那无处不在的噩运进行对抗啰。鲍勃?克劳利比他姐姐小两岁,现在马尔博罗上学,家里打算让他从那里接着上剑桥大学,并由他的教父阿拉宾教长出钱供他深造。在这方面,世人又看到了时来运转的兆头。不过到那时,克劳利先生也说不上什么走运。一点不假,鲍勃在学校成绩优异,到了剑桥也许混得不错,也许在那里出类拔萃。但是,克劳利先生倒愿意这孩子在地里干活儿,不愿意让孩子靠这么刺眼的施舍方式上学。那时还有他的衣服问题呢!上学或进大学穿的那些衣服,他去哪儿弄钱给他置办啊?但是,教长和克劳利太太促成了这件事,压根儿没有征求克劳利先生的意见,这也是克劳利太太对付他的一贯办法了。这家还有一个小女儿,名字叫简,日子消磨在母亲的针黹案和父亲的希腊语之间,有时缝补内衣,有时学着往诗行上划格律——因为克劳利先生年轻的时候曾是一个通今博古的学者。 而眼下,这个灭顶之灾劈头盖脸地奔他们来了。可怜的克劳利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渐渐债台高筑而不能自拔,这在西尔弗布里奇和霍格尔斯托克两地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在很大一部分人眼里,阿拉宾教长不顾他的强烈反对,一直在接济他,为此他跟教长吵过嘴,或者一直想和教长吵嘴,尽管接济和钱有部分花在他自己手上,但他确是太想寻机争吵了。西尔弗布里奇的屠夫弗莱彻是他的一个债权人,他最近一个时期对待可怜的克劳利特别苛刻。这个人过去做生意也不是不讲通融,只是听了关于主教的良好愿望的种种传说,便到处嚷嚷说,霍格尔斯托克的这位终身副牧师早该表现出一种更高的自尊心,主动向一个富有的教友借债承情,而不再总和一个屠夫在金钱上纠缠不清。就这样,一个流言就四下传开了。不久,这个屠夫给主教——巴彻斯特的普劳迪主教接连写了几封内容相同的信;这位主教委托他的贴身牧师一个主教身边可以使唤一两名牧师做助手。这种牧师的职责有点类似私人秘书。答复了来信,有些微婉转地告诉了克劳利先生他对一个牧师吃肉而不付钱的具体看法。可是,这位主教说也好做也罢,却没办法让克劳利先生还那个屠夫的债。像克劳利先生这样一个人,收到普劳迪主教这样一个人的那些信件,这事本身就够让人难堪的了;可信毕竟来了,留下了一个个溃烂的创伤,不过后来这些信不了了之。最后,那个屠夫的肉店放风威胁说,如果欠的债在指定日期还不了,印好的账单就要在全郡四处张贴。西尔弗布里奇所有听说事的人,无一不生弗莱彻先生的气,因为谁过去也没有听说过一个生意人竟会采取这种措施;但是弗莱彻发誓说他决不让步,并为自己辩护说,六七个月以前,就是这年春天,克劳利先生在西尔弗布里奇还了一批账,可就是分文没还他——没还他这个不仅是克劳利先生最早而且是最持久的债主。“他三月从教长那儿得到一笔钱,”弗莱彻先生跟沃克先生说,“他还了格林十二镑十先令,还了面包师格罗伯里十七镑。”就是还面包师格罗伯里这十七镑面粉钱,激起了这位面包师的牛性,决心对这位可怜的牧师穷追猛打,毫不手软。“他还霍尔的钱,还霍尔特太太的钱,还更多人的钱,可就是不肯走近我的店铺半步。要是他哪怕来打个照面,我也不会对这事费这么多口舌的。”这样,就在那个指定的日期的前一天,克劳利太太来到了西尔弗布里奇,还了那个屠夫四张五镑钞票,共二十镑钱。到了这一步,屠夫弗莱彻算是一举成功了。 \" 1、《巴塞特郡纪事》代表着特罗洛普文艺创作的鼎盛时期。——《人人丛书》主编欧内斯特·里斯 2、巴尔扎克、萨克雷和特罗洛普是同一时代三位真正的现实主义大师。——哈利· 瑟斯顿· 佩克 3、你读过特罗洛普的小说吗?它的小说正配我的胃口——紧凑、充实,是凭借了牛肉的力量和啤酒的灵感写成的。特罗洛普的那些书正和牛排一样,是地道的英国货。——霍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