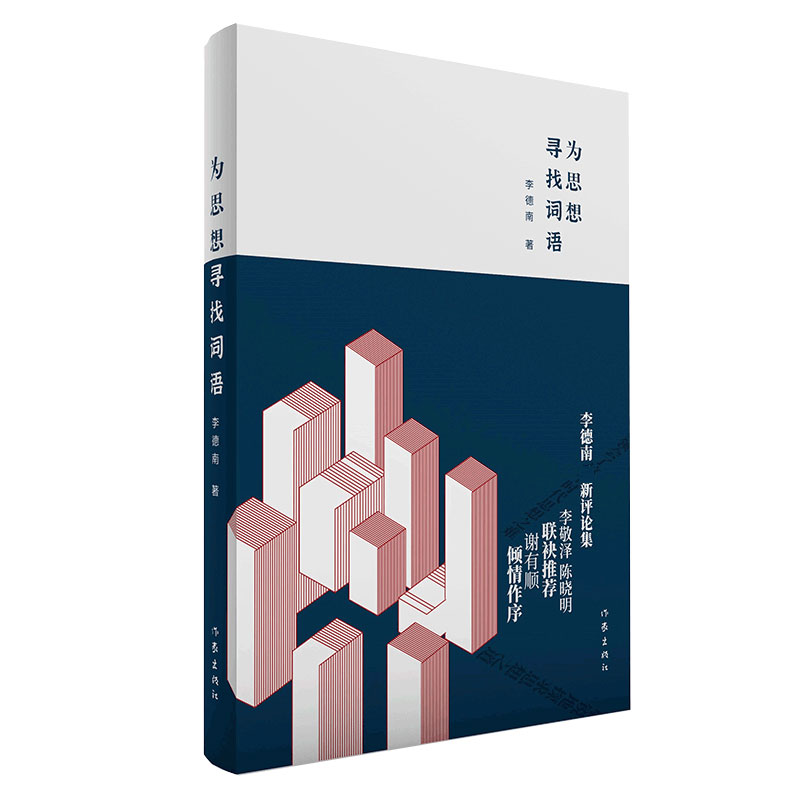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40.00
折扣购买: 为思想寻找词语
ISBN: 97875212134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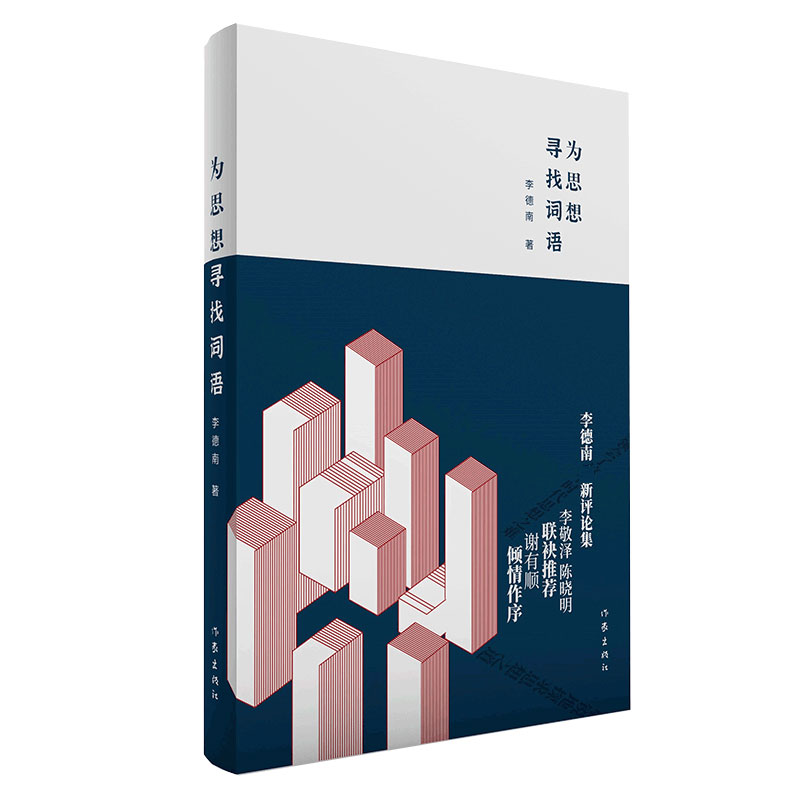
李德南,1983年生,上海大学哲学硕士、中山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广州文学艺术创作研究院青年学者、专业作家,兼任中国现代文学馆特邀研究员、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创意写作专业导师、广东省首届签约评论家、广州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著有《“我”与“世界”的现象学——史铁生及其生命哲学》《小说:问题与方法》《共鸣与回响》《有风自南》《途中之镜》等。曾获《南方文坛》年度优秀论文奖、广东省鲁迅文学艺术奖、“粤派学术”优秀论文奖等奖项。入选“广东特支计划”青年文化英才、羊城青年文化英才、“岭南英杰工程”后备人才、广州市高层次人才。
空间的凝视与思索 ——理解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一个角度 进入新世纪以来,城市文学的书写在逐渐增多,也出现了不少新的变化。其中,对空间问题的关注,成为不少作家的共同兴趣。他们或是以空间作为书写城市文学的方法,或是在写作中凝视各种形式的空间,通过思索空间的意蕴来拓宽、拓深个人对城市、人生还有新文明等领域的认知。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新世纪以来的城市文学和之前的城市文学相比,所涉及的经验范围有较大的拓展。这种拓展,又和空间的生产与拓展有很大的关系。在现代思想的视野中,空间本身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的动力机制派生于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和它们在形式上的重新组合” ()①。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则使得时间进一步是以空间的形式来体现的,很多问题都已经空间化了。列斐伏尔甚至认为,当今时代的生产,已经由空间中事物的生产转向空间本身的生产。“空间在目前的生产模式与社会中有属于自己的现实,与商品、货币和资本一样有相对的宣称,而且处于相同的全球性过程之中。” ()② 以文学作为考察对象的话则会发现,在以往的写作中,不管是城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大多是在中国的范围内,以城市—乡村的架构来书写人们的生存经验。然而在今天这样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地球本身也成了“村”,空间的距离进一步缩小了,新的生存经验已经撑破了以往的城市—乡村的架构,作家们也开始在中国—世界的架构中描绘他们眼中与心中的文学图景。 由此,我想到两篇同样命名为《故乡》的小说,一篇出自鲁迅,一篇出自蒋一谈。1921年,鲁迅写下了他的重要作品《故乡》。在这当中,我们首先可以读到这样一个故事:“我”——“迅哥儿”——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两千余里、有二十余年未曾回去的故乡。“我”是一个知识分子,这次回乡并没有多少好心情,因为回乡的目的是为了告别,是为了卖祖屋,“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 ()①。这里所说的“异地”,指的是中国的城市,不一定是大都市,也有可能是小城镇。至于具体是哪里,小说中并没有说明。时间到了21世纪,在蒋一谈的《故乡》中,所看到的已经是另一幅景象。蒋一谈的《故乡》的主角同样是一位男性知识分子,更具体地说,是一位文化批评家。此时他正置身于美国,在午夜遥想他的故乡。鲁迅《故乡》中的“我”之所以离开故乡,是为了到异地“谋食”;蒋一谈《故乡》中的“我”,则是为了去美国探望女儿和外孙女。而不管是回归,还是回归后的出走,两篇小说中的“我”的感受都是非常复杂的。鲁迅《故乡》中的“我”,似乎是因为无法忍受故乡的落后、贫穷与蒙昧而出走,涉及的是乡土世界和知识分子自身的启蒙问题。蒋一谈的《故乡》则注意到了各种新的生存经验:跨语际的话语交流的困难、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差异、民族主义和世界主义在新时代的冲突……由此可以看到,两篇小说的叙事模式虽有相通之处,但所涉及的主题与问题有非常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则与现实生活中空间的拓展以及相应的生存经验的拓展有很大的关系。 除了蒋一谈的这篇同题小说,还可以把徐则臣的《耶路撒冷》与鲁迅的《故乡》放在一起进行对读。这两篇小说里有一个相同的情节:回老家去变卖祖屋。“迅哥儿”变卖祖屋是为了扎根城市,是为了“到城里去”;初平阳之所以变卖祖屋,却是为了“到世界去”,是出于对耶路撒冷及其所蕴含的宗教精神的向往。在《耶路撒冷》与蒋一谈的《故乡》中都可以看到,小说所涉及的生存经验的范围显然扩大了。这种扩大,使得蒋一谈的《故乡》和《耶路撒冷》获得了某种独特性,从而与当下那些同质化的、无新意的作品区分开来。徐则臣和蒋一谈还都敏感地注意到新的问题,比如说,在一个全球化的时代,我们要重新定义故乡。当我们在新的世界视野或世界体系中思考故乡,故乡就不再一定意味着是乡村,而可能就是城市,甚至就是中国本身。故乡经验的生成,不再局限于中国内部的城—乡对照,而可能是来自中国与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度的比较。 另外,对空间的重视,也体现在深圳等新城市的城市文学写作热当中。我在读邓一光、吴君、蔡东、毕亮、陈再见等作家的作品时,注意到一个现象。他们的写作,都具有极其鲜明的空间意识。他们的城市书写,是以空间作为切入点的,也可以说,是以空间作为方法。他们之所以采用这样的书写方式,则和深圳这个城市的特点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深圳是一个在改革开放几十年中发展起来的城市,其历史线条非常简单,并不像北京、西安、南京那样有曲折的、深厚的历史。深圳的一切,看起来都是新的。它是一个绝对现代的城市。而对于这样的新城市来说,具体的书写方法和老城市也并不一样。对于北京、西安、南京等老城市而言,时间是比空间更为值得注意的因素,或者说,其空间是高度时间化的。北京、南京等老城市的魅力通常来自时间的流逝与积淀。围绕着这些城市而写就的作品,也往往是从时间或历史的角度入手,形成独特的叙事美学。王德威在为葛亮的长篇小说《朱雀》写序时,便首先是对南京的历史作一番追溯,在历史的视野中发掘并确认《朱雀》的魅力:“在古老的南京和青春的南京之间,在历史忧伤和传奇想象之间,葛亮寻寻觅觅,写下属于他这一世代的南京叙事。” ()① 邱华栋在回顾个人在北京生活的二十余年经历时,则谈到北京在现代城市改造中所发生的变化,看到了“老北京正在迅速消失,而一座叫做国际化大都市的北京正在崛起”。 ()② 然而,他并不认为老北京就此失魂落魄,而是认为“老灵魂”依然存在,“主要是存在于这座城市的气韵中。这是一座都城,有几千年的历史,纵使那些建筑都颓败了,消失了,但一种无形的东西仍旧存在着。比如那些门墩,比如一些四合院,比如几千棵百年以上的古树,比如从天坛到钟鼓楼的中轴线上的旧皇宫及祈天赐福之地,比如颐和园的皇家园林和圆明园的残石败碑。我无法描述出这种东西,这种可以称之为北京的气质与性格的东西。但它是存在的,那就是它的积淀与风格,它的胸怀,它的沉稳与庄严,它的保守和自大,它的开阔与颓败中的新生” ()③。金宇澄在其备受关注的《繁花》中,也正是从类似的一衣一饭等细部入手,来重构“老上海”的多重面孔。 在以前,一个城市的发展,往往需要经过漫长的时间积累,因此,从时间入手书写城市是具有方法论上的普适性的。张定浩在一篇尝试对“城市小说”进行重新定义的文章中所给出的第一条定义便是认为“城市小说是那些我们在阅读时不觉其为城市小说但随着时间流逝慢慢转化为城市记忆的小说”。 ()④ 他从接受美学的角度入手,认为城市小说所提供的阅读经验和城市居民的生活经验是一致的,“唯有游客和异乡人,才迫不及待地通过醒目的商业地标和强烈的文化冲突感知城市的存在,对那些长久定居于此的人来说,城市在一些不足为人道的细枝末节里。” ()① 这一认知很有见地。然而,张定浩提出的原则,对于深圳这样的新城市来说,又几乎是失效的。作为在改革开放中迅速崛起的新城市,深圳缺乏深厚的历史底蕴和醇厚的城市记忆。深圳是一座快速成形的城市,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部按了快进键的电影。它所经历的时间过于短暂,几乎是无历史感的,也是无时间的。相比之下,它好像只有今生,而没有前世。因着历史感的缺失,空间的效应则更为突出。 深圳作为一座城市的魅力,也不是源自时间而是源自空间,尤其是具有理想色彩的公共空间。很多人在想起深圳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时间,而是深圳的空间,是深圳的万象城、市民中心,是仙湖、红树林,等等。同样是和深圳这座城市的形成方式有关,邓一光、吴君、毕亮等作家在书写深圳这座城市时都会突出其空间因素,尤其是邓一光。迄今为止,邓一光已经出版了三部深圳题材的中短篇小说集。他干脆将写深圳题材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命名为《深圳在北纬22°27′~22°52′》,收入书中的九篇小说,有七篇的题目和深圳的公共空间有直接的关联:《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宝贝,我们去北大》《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万象城不知道钱的命运》《深圳在北纬22°27′~22°52′》《离市民中心二百米》《在龙华跳舞的两个原则》。只有《乘和谐号找牙》《有的时候两件事会一起发生》这两篇是例外的。中短篇小说集《你可以让百合生长》也同样如此,收入其中的十三篇小说,有九篇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标明了小说的叙事空间:《北环路空无一人》《你可以看见前海的灯光》《一直走到莲花山》《台风停在关外》《要橘子还是梅林》《出梅林关》《杨梅坑》《如何走进欢乐谷》《想在欢乐海岸开派对的姑娘有多少》。他的第三部以深圳作为主要的叙事空间的中短篇小说集则被命名为《深圳蓝》,十篇小说中也有三篇提到深圳或深圳的公共空间:《深圳河里有没有鱼》《深圳蓝》《与世界之窗的距离》。除了邓一光,毕亮也把他的一部小说集命名为《在深圳》。“在深圳”不仅标明了故事发生的空间,更指向一种独特的存在状态——流动的、迅速变化的、充满不安的城市经验,是毕亮这部小说的重要书写对象。作为一位自觉的、自知的城市书写者,他还将个人的另一部小说集命名为《地图上的城市》。 对于许多并无在深圳生活的经验、不熟悉深圳的读者而言,也许会觉得这种做法非常简单粗暴,写出来的作品会有些不自然,甚至是非常造作的,但是这种处理方式符合深圳的实际状况,也是对许多深圳人存在处境的直接揭示。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土著居民只有三万左右,此外的一千多万人口大多来自内地或广东别的地方,是成年之后才移居至此。他们之所以来到这座城市,首先是被这座城市的公共空间吸引。他们当中的绝大多数人无力在这个城市购买住房,尤其是众多打工者,通常住在狭窄的宿舍或杂乱的出租屋里。这些私人空间又不足以承载他们的“深圳梦”,因此,他们的所思所想与行动往往是在公共空间中展开的。 通过对公共空间与人的关系进行凝视与思索,从而展现新城市的生活现实,已经成为深圳作家讲述深圳故事的一种方法。大卫?哈维在《巴黎城记》等著作中,曾把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个人命运、城市地貌与建筑风格等融为一个有内在结构的思想体系,借此揭示空间的多重意蕴。深圳作家在以空间作为方法来写作城市文学作品的时候,也呈现出类似的立场,部分地采用了类似的方法——政治经济学式的考察与书写。比如说,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当中,邓一光就如哈维一样,重视探讨城市空间与社会公正的问题。正如哈维所一再强调的,空间并不只有物理属性,还带有政治属性与经济属性,因此可以从空间入手讨论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所写到的深圳市民中心位于深圳市中心区中轴线上,是深圳的标志性建筑,被称为深圳的“市民大客厅”。它实际上是深圳市政府的所在地。将市政府改称市民中心,则意在体现以下理念:第一,有效政府的理念——要求政府与其他非政府组织、市民一起形成复合的结构,政府与市民共享信息与文明。第二,开放政府的理念——市民中心的大型开放式平台使其开放功能得以凸显,市民中心以开放理念促进信息分享,其软硬件建设都体现政府的开放意识。第三,服务政府的理念——“服务政府”的本质是“有限政府”“法治政府”和“民主政府”,这些理念亦通过完善的服务系统得以落实。在写作这篇小说时,邓一光显然非常熟悉“市民中心”的种种空间意蕴并通过小说的形式与之展开对话。小说的主角是一对恋人,“他”与“她”都来自农村,通过奋斗都拥有了户口,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住在“离市民中心二百米”的地方,令“她”觉得骄傲、自豪,也增加了“她”对深圳的参与感与认同感: 她喜欢宽敞、亮堂、洁净和有条不紊的地方。怎么说呢,孕育她的地方是窄小、阴暗和混乱无章的,学习、成长和工作的地方同样如此。人们总说,一个人最终只需要三尺没身之地,但那是灵魂出窍之后的事。难道她只能在三寸子宫、五尺教室和七尺工作间里度过她的全部生命? 她应该走进更宽阔的地方。她迷恋成为宽阔之地主人的那种自由感觉。 ()① 李德南最新评论集 李敬泽 陈晓明联袂推荐 谢有顺倾情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