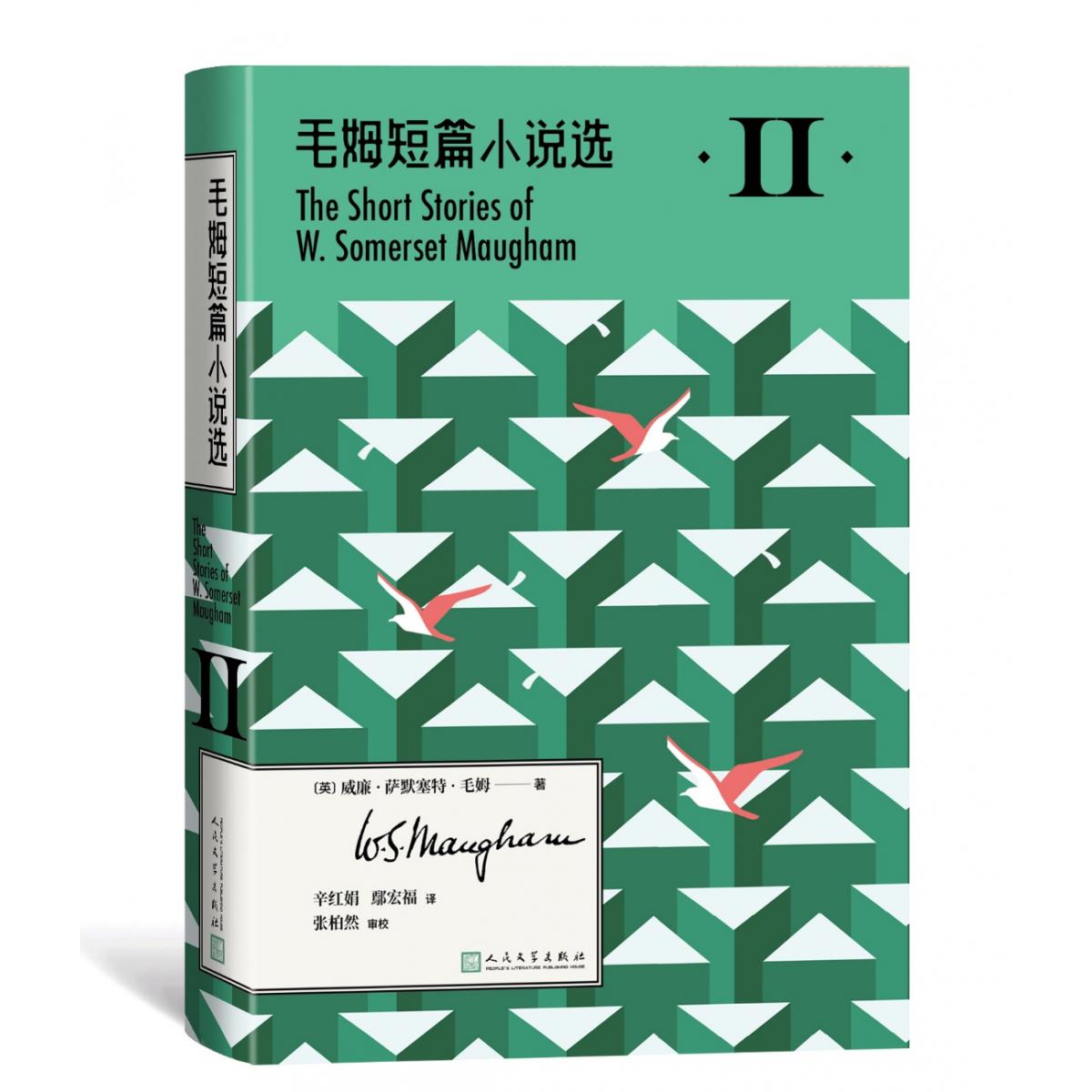
出版社: 人民文学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52.20
折扣购买: 毛姆短篇小说选II
ISBN: 978702017956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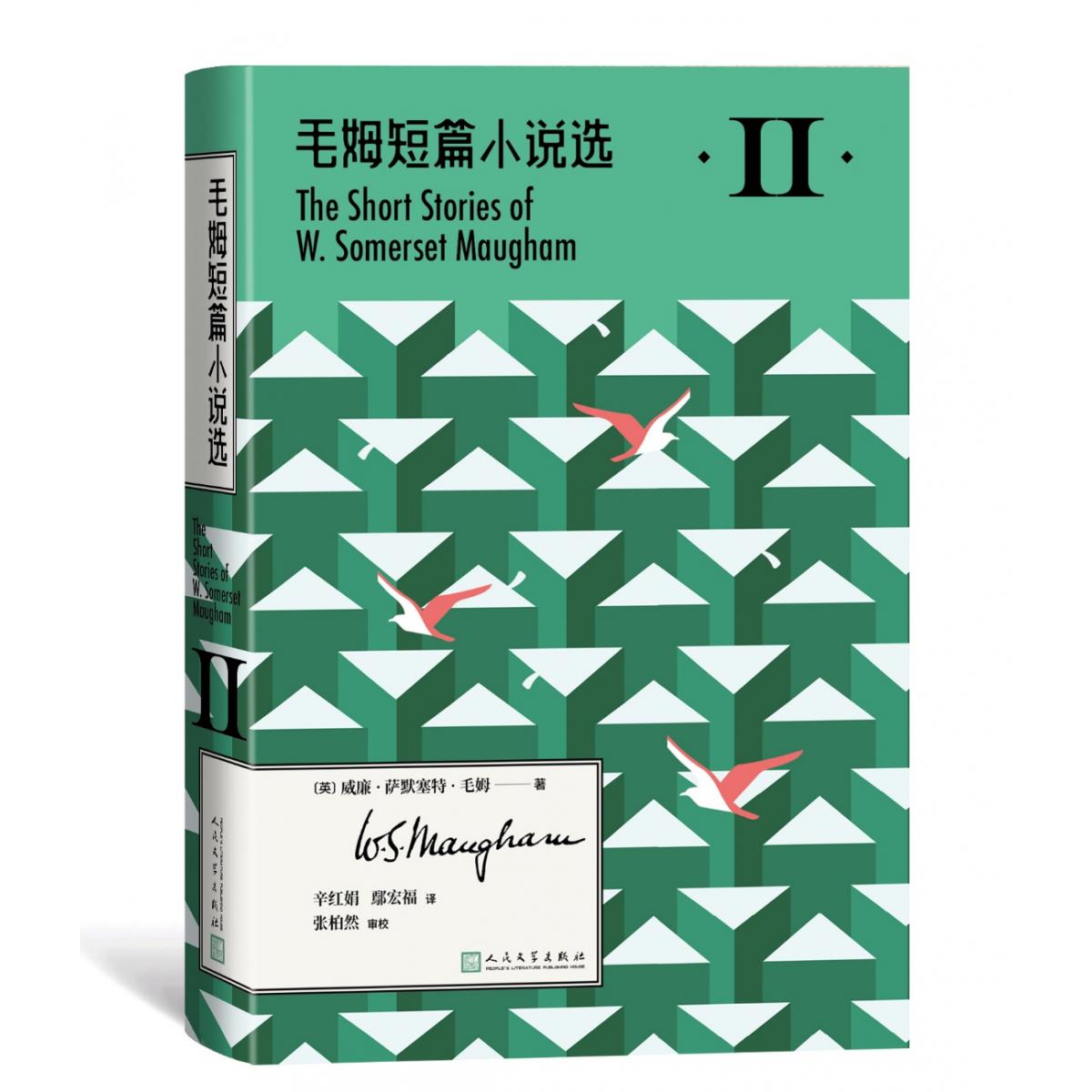
毛姆(1874—1965),二十世纪英国著名作家、英语世界最畅销的作家之一,是“盛誉下的孤独者”,更是“人世的挑剔者”。一生徜徉于三大文学领域,发表了二十一部长篇小说、三十二个剧本和一百二十余篇短篇小说,还写了大量的评论、随笔、游记和回忆录。他的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深受我国广大读者的欢迎和喜爱。
创作灵感 我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创作《阿基里斯雕像》的原委。既然这部作品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小说之一,我想,简要介绍这部作品产生的背景,必定会让文学领域的后学们很感兴趣。评论家预言该书将畅销不衰,若所言非虚的话,那么本篇所叙之事不仅能供人消遣,更能为将来史学家编撰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提供有益的参照。 当然,每个人都记得《阿基里斯雕像》出版时获得的巨大成功。几个月间,印刷工人废寝忘食,装订工人夜以继日,版本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们紧锣密鼓,完成书商们的加急订单。图书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每一种语言。最近,有消息称,读者很快就能读到该书的日语和乌尔都语版本。小说曾经在大西洋两岸的报刊上连载过,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代理人从这些报刊编辑身上攫取了高额利润。作品还被改编成戏剧,在纽约上演整整一个季度,毫无疑问,等这部戏剧在英国推出,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功。电影版权已经高价售出。尽管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所赚金额很可能跟传言(文学圈内)有出入,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她凭借这部书赚得的利润,足以保证这一生衣食无忧。 一部书很难同时得到公众和批评家的青睐。对于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来说,情况尤其明显(请允许我这么说)。迎合圈子诚然令她格外满足,评论家们不遗余力地吹捧她(而她确实也开始觉得自己实至名归),奇怪的是,公众对她的才华似乎浑然不觉。她出版的那些薄薄的作品,印刷精美,白色布纹装帧,甫一问世即被视为上乘之作,专栏定会刊发鸿篇巨论,仅在那些古老俱乐部尘封的图书馆中才能见到的每周评论对其极尽笔墨。饱学之士都读过她的作品,个个赞叹不已。然而,饱学之士并不买书,她的书因此并不畅销。如此久负盛名的作者,想象力如此奇特,文笔如此绮丽,却不为普通读者熟悉,说起来实在丢人。在美国,她几乎无人知晓;尽管卡尔·范维克滕先生曾经撰文指责公众驽钝,但公众依然反应平淡。她的一位代理人,对她的天才顶礼膜拜,曾经逼迫一位美国出版商:必须出版她的两本书,才授权他出版急切渴望的其他作品(毫无疑问,是质量低劣的小说),于是,这两本书才得以按时出版。这两本书受到出版社讨好似的赞誉,说美国最杰出的头脑欣赏她的才华。可到了第三本书,美国出版商(用惯有的粗俗方式)告诉这位代理人说,如果有钱,他宁愿投资杜松子酒。 自从《阿基里斯雕像》出版之后,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此前的作品被一版再版(卡尔·范维克滕先生再次撰文,悲痛而坚定地指出,早在十五年之前,他已经向读书界推荐这位不同凡响的作家),宣传得尽人皆知,高雅的读者无不知晓这些作品,无需我在此枚举。有了卡尔·范维克滕的两篇佳作,再做赘述无异于狗尾续貂。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很早即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十八岁,她就出版了处女作《一部挽歌》。此后,每隔两三年,她就会出版一本诗集或散文集(她对艺术怀有崇高的信念,不愿过于草率地频繁出版)。创作完成《阿基里斯雕像》时,她已五十七岁,到了受人尊敬的年纪。不难想象,她的作品数量卷帙浩繁。她为这个世界奉献了六本诗集,皆以拉丁文冠名,包括《幸运》《圣母马利亚》和《死生之际》,这些诗集都属庄重型诗体。她善于沉思,不愿涉足轻浮、荒诞的题材,独钟情严肃和厚重。她依然热衷于创作挽歌,十四行诗令她如痴如醉。她的非凡成就在于她复兴了抒情诗,这是今日之诗人久已生疏的诗体。可以断言,她的抒情诗《献给法利埃总统的颂歌》将在任何一类诗歌选集中占据一席之地。这首诗不仅韵脚响亮,对于法国大好河山的描绘更是惟妙惟肖。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描绘了卢瓦尔河的旖旎风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诗人杜·贝莱留下的印记,沙特尔大教堂镶嵌宝石的窗户和普罗旺斯阳光明媚的城市。她的赞叹之情尤为珍贵,这是因为,除了新婚宴尔之际从马盖特乘坐游船到过布洛涅,她再也没有去过法国其他地方。她晕船厉害,而且,这个广受欢迎的海滨胜地的居民听不懂她流利地道的法语,令她羞愧不已。她于是决定再也不去重复这种既不体面又不愉快的经历,从此抛弃了曾经在《圣母马利亚》里以庄重甜美的笔调反复歌颂的题材。 《伍德罗·威尔逊颂歌》中也有些精彩的段落。但是非常遗憾,由于她对这位杰出人物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决定不再重印这部作品。然而,我认为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经典力作是她的那些散文。她创作了多篇语言简洁、结构完美的美文,取材广泛,包括《萨塞克斯的秋天》《维多利亚女王》《死亡》《诺福克的春天》《乔治王朝的建筑》《迪亚吉列夫先生》和《但丁》。她还创作博雅、古怪的作品,介绍十七世纪的耶稣会建筑,论述百年战争时期的文学问题。正是她行文绮丽的散文,为她赢得了为数不多却绝对忠实的拥趸。这些崇拜者们认为她是这个世纪最伟大的语言大师。她自己也承认,她的强项在于她的风格,铿锵有力却不失生动活泼,语言典雅而又意味深长。她只在散文中展现了韵味十足但又张弛有度的幽默,令读者们难以抗拒。这种幽默不在于思想意蕴,也不在于遣词造句,而在于标点符号的精微修辞:电光火石之间,她发现了分号所蕴含的幽默潜能。因此,她大量使用分号,已臻炉火纯青的境界。她对分号的巧妙使用令人叫绝,你如果受过良好教育且幽默感强,根本不会滑稽大笑,而是欢畅地吃吃发笑,文化程度越高,笑得就越欢畅。朋友们说,她的幽默令其他所有类型的幽默显得粗俗不堪且夸张做作。多位作家都尝试模仿她,但皆以失败告终。无论你如何评价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都不得不承认她已经将分号的幽默意蕴发挥得淋漓尽致,任何人皆难以学到她分毫。 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住在距离石门不远的一栋公寓,交通便利,租金实惠。公寓包含一间临街的豪华客厅,一间供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居住的宽敞卧室,一间位于后面的阴暗餐厅,以及一间紧邻厨房、狭小简陋的卧室,供福里斯特先生居住。房租由福里斯特先生支付。每个星期二下午,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在豪华客厅里招待她的朋友们。客厅朴素而整洁。墙上挂着世界知名壁纸花样设计者兼画家威廉·莫里斯亲手设计的壁纸,还悬挂着朴素黑框装饰的铜版画,这些铜版画是在铜版画涨价之前就已收藏。家具是齐本德尔时期的,带折叠桌盖的写字台隐约保留了路易十六时期的特色。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就在这张书桌上写作。总要给第一次登门的客人介绍一番,多数人见了这张桌子都惊叹不已。地毯厚实,灯饰庄重。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坐在一张铺有红绸缎的直背老爷椅上。这张椅子并不值得夸耀,却是房内唯一舒适的椅子,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安然端坐,高高在上,与客人们保持着距离。负责倒茶的女仆,看不出年纪,沉默少言、无精打采。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从来不向任何人介绍她,但众所周知,女仆把为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分担倒茶之苦视作自己的特权。这样一来,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便能全身心投入聊天。不得不承认,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谈吐不凡。言谈并不轻松活泼,加之口头聊天时很难展示标点符号之妙,她的言谈虽然可能不那么幽默,却旁征博引、滔滔不绝,令人受益匪浅,不失生动趣味。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深谙社会科学、法律和神学。她阅读广泛,博闻强记,天生擅长引经据典,弥补了智慧的不足。三十年来,她或多或少结识过一些社会名流,于是,总有一大堆趣闻轶事与人分享。她自己也颇为用心,重复讲述的次数不致令人作呕。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善于吸引各行各业的人员,很可能会在她的客厅同时见到前任首相、报社社长和出任某大国的大使。我一直猜想,这些上层人物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觉得,来到这里跟一位作风正派、身份清白的文化人交往,不会招致非议。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对政治深感兴趣,我自己就曾听一位内阁大臣坦率地对她讲,她具有男性的智慧。她一直反对妇女选举权,但当妇女最终被赋予这项权利后,她开始考虑进入国会。令她头痛的是,不知道该加入哪派政党。 “总之,”她顽皮地耸动宽阔的肩膀说,“我不会自己创建一个政党。” 与众多严肃的爱国者一样,她分不清局势走向,她的政治观点模糊不清。最近,她明确转向认为工党是这个国家最大的希望。如果她能稳操胜券获得一个席位,她肯定会毫不犹豫地作为受压迫的无产阶级斗士进入公众视野。 她的客厅也常对外国人开放,包括杰出的捷克斯洛伐克人、意大利人和法国人,以及名不见经传的美国人。她绝非势利小人,她的客厅里见不到贵族公爵,除非这位公爵有特殊癖好;她的客厅里也见不到贵族夫人,除非这位夫人除了作为贵族之外,身上还出过这样或那样的小插曲引起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这位天主教徒的恻隐之心,诸如婚姻破裂、写过小说或是伪造过支票。她不怎么喜欢画家,画家大多腼腆寡言;也不喜欢音乐家,因为他们倘或有名,通常不愿演奏。而即便他们同意演奏,音乐也会妨碍谈天。人们想听音乐,大可去音乐会。她青睐更加微妙的音乐,心灵之音。她对作家,尤其是前途光明而目前寂寂无闻的作家,热情不减。她对崭露头角的创作天才独具慧眼,不时与她把盏品茗的知名作家,绝大多数在尝试写作阶段得到过她的鼓励,在写作生涯初期得到过她的指引。她的文学地位已岿然不动,根本不会对别人产生嫉妒之心。人们对她写作天分的赞美不绝于耳,她因此不会为他人所获得的成功而心生嫉妒。 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对文学后人的甄别能力自信满满,确信能做到公正无私。基于上述种种,不难理解她何以能够在荒蛮之风甚嚣尘上的国度成功打造法国十八世纪沙龙似的聚会清谈。人人都觉得,能够接受邀请“星期二吃面包、喝茶”是一种无上的荣耀。置身朴素的客厅,在肃穆的灯光下,往齐本德尔式椅子里一坐,你会恍然感觉自己正经历鲜活的文学历史。美国大使曾经恭维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 “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跟您喝茶,是不可多得的心灵盛宴,我有幸参加,真是荣耀之至。” 确实,类似的聚会清谈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品位卓尔,她对正确的事情必加以赞美,必做出精准的评判,时常令人叫绝。出席她的高雅聚会之前,我常会先喝上一两杯鸡尾酒解馋。事实上,我发现自己很难融入她的沙龙聚会。一天下午,我到她家门口通报,本来应该问开门的女仆,“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在家吗?”我却问道:“今天有没有礼拜?” 当然,纯粹是随口这么一问,不幸的是女仆吃吃笑了起来。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一位最忠实的崇拜者埃伦·汉纳威碰巧在走廊里脱鞋子。我还没进客厅,她就已经将我的话学给女主人听过了。我进去时,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用老鹰般的眼睛盯着我。 “你为什么要问今天有没有礼拜?”她愠怒道。 我解释说,自己纯粹是随口一问。孰料,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继续盯着我,眼神咄咄逼人。 “你是不是想说我的聚会……”她在寻找合适的词眼,“很神秘?” 我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可我无意在众多聪明人面前暴露自己的无知,于是认定自己唯一能做的就是奉承一番。 “亲爱的夫人,您的聚会就像您本人一样,完美无瑕,高雅神圣。” 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高大的身躯微微一颤。仿佛突然冲进开满风信子的房间,醉人的香气令她目眩神迷。她变得温和起来。 “你要是想耍幽默的话,”她说,“我想最好用在我的客人身上,不要跟仆人插科打诨……沃伦小姐会给你倒茶。” 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挥挥手,示意我这个话题告一段落了。但她却开始揪住这个话题不放,在接下来的两三年里,但凡需要向别人介绍我,她总不忘加上一句: “您务必好好跟他聊聊,他上这儿来只是为了赎罪。他到门口时总会问:‘今天有没有礼拜?’很逗,对吧?” 然而,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并不满足于每星期二举行一次的茶会。每个星期六她都会准备八个人的午宴:用她的话说,八个人最适合清谈,再者,她家的餐厅容纳不下更多的人。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吹嘘说,比起她久负盛名的午餐会,她为人所知的英国韵律学知识可就小巫见大巫啦。她对客人精心挑选,谁要是接到邀请,不单是受到抬举那么简单,简直就是受宠若惊。餐桌上的交谈比鱼龙混杂的茶会更加高雅,几乎所有的客人离开餐厅时都会对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能力信心倍增,对人性的信念也更加积极。她只邀请男客人,尽管她坚定地支持女性并且在很多地方愿意见到女人,但是她认为女人在饭桌上只会谈些家长里短,妨碍广泛的思想交流,她想让聚会不仅成为味蕾的享受,更是一次心灵的盛宴。不得不说,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午餐会有可口的佳肴、优质美酒和高级雪茄。凡是参加过文人聚餐的人都知道,这几样绝对非同寻常,文人们通常精熟于思考,可生活乏味。他们满脑子充斥着各种思想,鲜少会留意到羊肉尚未烤熟或土豆早已冰凉,他们喝喝啤酒就心满意足,认为红酒过于柔和,而咖啡过于浓烈。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很乐意别人赞赏她的食物。 ☆ 毛姆何许人也?马尔克斯、村上春树、乔治·奥威尔、张爱玲等人都是“毛姆作品爱好者”。 ☆ 这本小说“人类观察笔记”,以冷峻辛辣之笔写尽人生百态、世事浮沉,也可作为一本二十世纪风物志,可爱的乡间小镇、新兴的工业城市、炎热潮湿的海岛,迥异的风土人情,性情各异的活泼人物,定叫你爱不释手。 ☆ 精选名篇+上佳译文,晓畅自然,十分易读,且简洁风趣,质朴有力,原汁原味展现了毛姆作品的风采。
毛姆是二十世纪会讲故事的作家之一,被誉为“英国的莫泊桑”。他的短篇小说文笔质朴、脉络清晰,人物栩栩如生,情节跌宕起伏。本书精选毛姆秀的短篇小说,呈现一个世纪前英国海外殖民地的风土人情,描绘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人生百态,展露爱情、婚姻、家庭中的层层羁绊,冷峻剖析人性的虚伪、自私与脆弱。
书籍目录
| 目录 创作灵感 美德 带伤疤的男人 倒闭的妓院 乞丐 不可多得 蒙德拉哥勋爵 教堂司事 大班 患难识人 满满一打 简 疗养院 远洋客轮 轶闻 风筝 五十岁的女人 九月公主 权宜婚姻 一封信 边远任所 同花顺 在劫难逃 露水情缘 雷德
|
试读内容
创作灵感
我估计很少有人知道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创作《阿基里斯雕像》的原委。既然这部作品被视为我们这个时代伟大的小说之一,我想,简要介绍这部作品产生的背景,必定会让文学领域的后学们很感兴趣。评论家预言该书将畅销不衰,若所言非虚的话,那么本篇所叙之事不仅能供人消遣,更能为将来史学家编撰这一时期的文学史提供有益的参照。
当然,每个人都记得《阿基里斯雕像》出版时获得的巨大成功。几个月间,印刷工人废寝忘食,装订工人夜以继日,版本一个接一个,层出不穷。英国和美国的出版商们紧锣密鼓,完成书商们的加急订单。图书立即被翻译成欧洲的每一种语言。近,有消息称,读者很快就能读到该书的日语和乌尔都语版本。小说曾经在大西洋两岸的报刊上连载过,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的代理人从这些报刊编辑身上攫取了高额利润。作品还被改编成戏剧,在纽约上演整整一个季度,毫无疑问,等这部戏剧在英国推出,也会取得同样的成功。电影版权已经高价售出。尽管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所赚金额很可能跟传言(文学圈内)有出入,有一点却可以肯定,她凭借这部书赚得的利润,足以保证这一生衣食无忧。
一部书很难同时得到公众和批评家的青睐。对于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来说,情况尤其明显(请允许我这么说)。迎合圈子诚然令她格外满足,评论家们不遗余力地吹捧她(而她确实也开始觉得自己实至名归),奇怪的是,公众对她的才华似乎浑然不觉。她出版的那些薄薄的作品,印刷精美,白色布纹装帧,甫一问世即被视为上乘之作,专栏定会刊发鸿篇巨论,仅在那些古老俱乐部尘封的图书馆中才能见到的每周评论对其极尽笔墨。饱学之士都读过她的作品,个个赞叹不已。然而,饱学之士并不买书,她的书因此并不畅销。如此久负盛名的作者,想象力如此奇特,文笔如此绮丽,却不为普通读者熟悉,说起来实在丢人。在美国,她几乎无人知晓;尽管卡尔·范维克滕先生曾经撰文指责公众驽钝,但公众依然反应平淡。她的一位代理人,对她的天才顶礼膜拜,曾经逼迫一位美国出版商:必须出版她的两本书,才授权他出版急切渴望的其他作品(毫无疑问,是质量低劣的小说),于是,这两本书才得以按时出版。这两本书受到出版社讨好似的赞誉,说美国杰出的头脑欣赏她的才华。可到了第三本书,美国出版商(用惯有的粗俗方式)告诉这位代理人说,如果有钱,他宁愿投资杜松子酒。
自从《阿基里斯雕像》出版之后,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此前的作品被一版再版(卡尔·范维克滕先生再次撰文,悲痛而坚定地指出,早在十五年之前,他已经向读书界推荐这位不同凡响的作家),宣传得尽人皆知,高雅的读者无不知晓这些作品,无需我在此枚举。有了卡尔·范维克滕的两篇佳作,再做赘述无异于狗尾续貂。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很早即开始她的写作生涯。十八岁,她就出版了处女作《一部挽歌》。此后,每隔两三年,她就会出版一本诗集或散文集(她对艺术怀有崇高的信念,不愿过于草率地频繁出版)。创作完成《阿基里斯雕像》时,她已五十七岁,到了受人尊敬的年纪。不难想象,她的作品数量卷帙浩繁。她为这个世界奉献了六本诗集,皆以拉丁文冠名,包括《幸运》《圣母马利亚》和《死生之际》,这些诗集都属庄重型诗体。她善于沉思,不愿涉足轻浮、荒诞的题材,独钟情严肃和厚重。她依然热衷于创作挽歌,十四行诗令她如痴如醉。她的非凡成就在于她复兴了抒情诗,这是今日之诗人久已生疏的诗体。可以断言,她的抒情诗《献给法利埃总统的颂歌》将在任何一类诗歌选集中占据一席之地。这首诗不仅韵脚响亮,对于法国大好河山的描绘更是惟妙惟肖。艾伯特·福里斯特夫人描绘了卢瓦尔河的旖旎风光以及文艺复兴时期欧洲诗人杜·贝莱留下的印记,沙特尔大教堂镶嵌宝石的窗户和普罗旺斯阳光明媚的城市。她的赞叹之情尤为珍贵,这是因为,除了新婚宴尔之际从马盖特乘坐游船到过布洛涅,她再也没有去过法国其他地方。她晕船厉害,而且,这个广受欢迎的海滨胜地的居民听不懂她流利地道的法语,令她羞愧不已。她于是决定再也不去重复这种既不体面又不愉快的经历,从此抛弃了曾经在《圣母马利亚》里以庄重甜美的笔调反复歌颂的题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