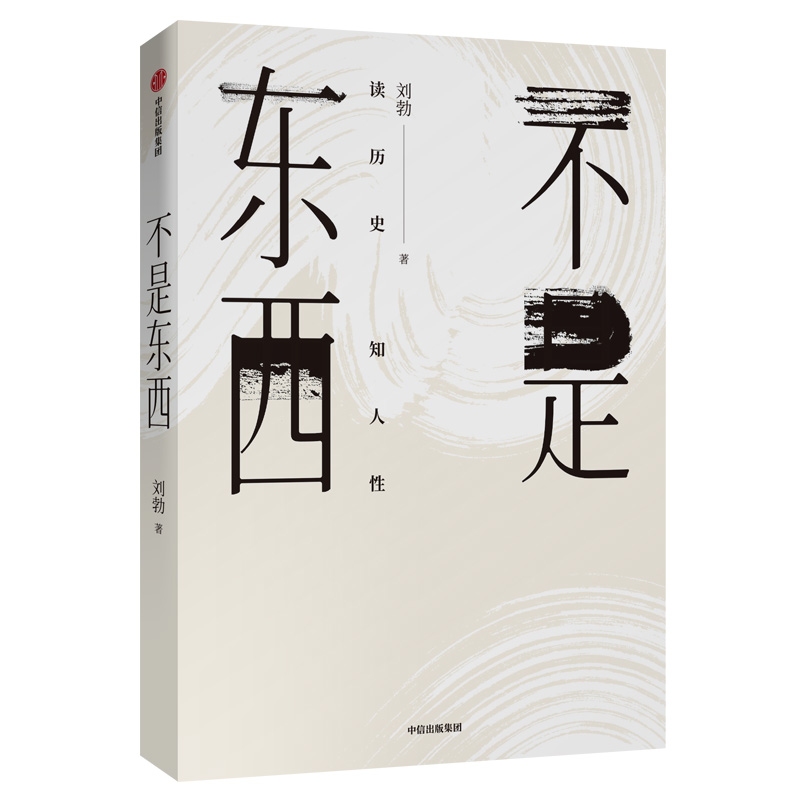
出版社: 中信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30.80
折扣购买: 不是东西
ISBN: 978752170857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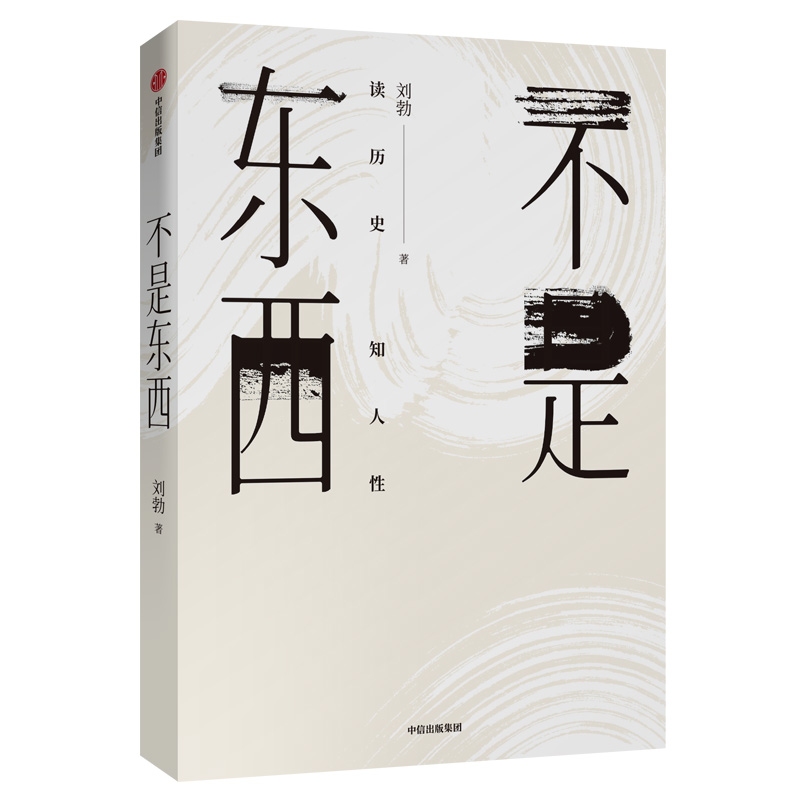
70后学者。历史文化随笔散见于《南方**》《读库》《**人文历史》《中堂闲话》。著有《小话西游》《失败者的春秋》《战国歧途》《***》《晋史笔记》(待出)等。
请四大名著的作者吃饭 四大名著里,有三部都是世代累积型的作品,换句话说,作者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甚至作者是谁,也没有那么重要。《红楼梦》是不是曹雪芹写的,也并非没有争议。 这篇小文,是由*通行的文本引出的感想。称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是从俗的叫法,不必较真。 《三国演义》吃的是权谋 请罗贯中吃饭,毫无压力。读《三国演义》很容易感*到,他对吃没什么兴趣,小说里也很少具体描写到吃。 其实,《三国演义》里饭局是很多的,但罗老师的叙述才能,全在写“局”,至于那“饭”具体是什么,如无必要,很少提及。 一开头,刘备和张飞相遇,到小酒馆里喝酒,然后遇到了关羽。这场戏里,下酒菜是不提的。 王允让貂蝉去**吕布,“貂蝉送酒与布,两下眉来眼去”,这时候当然也会劝吕布吃菜,吃的啥,也不写。 董卓死后,李傕、郭汜掌权期间,两个人互相伤害。李傕到郭汜家吃饭,回来后肚子痛,怀疑对方在饭菜里下了毒药。不知道郭汜请李傕吃的啥,李傕解毒的方法,倒是记下来了,“急令将粪汁灌之,一吐方定”。 汝南袁氏四世三公,自然是锦衣玉食。但袁绍、袁术兄弟平时都吃啥好吃的,《三国演义》不会浪费笔墨。只有吃不着的时候,才会记一笔。袁术兵败后,想喝蜜水,厨房回应说:“只有血水,安有蜜水!” 以吃货帝国的标准衡量,《三国演义》**是尊曹贬刘的。 刘备显然不是美食家,历**的刘备“喜狗马、音乐,美衣服”, 是个会享*生活的人,对吃也未必不讲究。但《三国演义》里的刘备**到晚忧国忧民,“食而不知其味”恐怕是伴随他大半生的体验。刘备依附曹*的时候,种过菜,但没见他吃。他种菜本是韬光养晦之 计,心思终究不在菜上。 刘备阵营里,张飞这种性格的人物,本来是很容易被塑造成吃货的。毕竟大碗喝酒也要大块吃肉,张飞家又以杀猪为业,对烹制肉食,自然很有经验。后世传播的三国故事,往往会大量补充张飞怎么好吃的细节。如张国良的苏州评话里面,《长坂坡》那场大戏,写刘备被曹*追上的前一个晚上,张飞把一桌酒席,不管是鱼是肉,连汤带水,装了一大皮袋——看来当时听书的确实多是底层重体力劳动者,不像我们**容易觉得恶心。后来倒是幸亏这袋泔水,分给赵云一半,赵云才有力气救回阿斗;自己吃了一半,才有力气一嗓子吓退百万曹兵。但这都是评话艺人的创作,《三国演义》中并没有写过。倒是诸葛丞相的口味,《三国演义》略有涉及。在南征孟获的故事里,诸葛亮为了给中毒的将士解毒,寻访隐士孟节。孟节款待诸葛亮的食物是“柏子茶、松花菜”,毛宗岗的批语:“百忙中却偏叙出隐士清冷之况,令人烦襟顿涤。”丞相初心中的食谱,大概也不过如此。后来司马懿诅咒诸葛亮,说:“食少事烦,其能久乎?”真正损寿的,应该还是事太烦心太累,以丞相的饮食偏好,每天吃几升饭,怕是已经在勉强自己多吃了。 所以,《三国演义》里的美食担当,也就只能是曹丞相了。 曹*爱笑,心情好的人多半胃口也好。司徒王允请大家吃饭,说起董卓专权,所有人都大哭。只有曹*说:“满朝公卿,夜哭到明,明哭到夜,还能哭死董卓否?”这顿饭,想来也只有曹*吃得香甜。 《三国演义》写吃*详细的地方,是曹*和术士左慈的对手戏。左慈变戏法,从一个铜盆里调出松江鲈鱼,又配上了蜀中的生姜。这个故事当然是《后汉书》《搜神记》之类的书里就有的,但那些书里的鲈鱼,有三尺来长,据@ 无穷小亮老师说,*可能是花鲈,也就是现在菜市场里常见的“海鲈鱼”。《三国演义》却改成了明清时*推崇的四鳃鲈。相应地,《搜神记》里曹*吃的是生鱼片,《三国演义》就改成了炖汤(烹)。 虽然,按照**的标准看,《三国演义》的写法未必*刺激食欲,但却是罗贯中老师写吃时难得流露出的创作欲。 总之,既然罗老师通常心思不在吃上,那么请他去**饭店还是下苍蝇馆子,可能没啥区别,只坐下来聊天就好。可以拿青梅煮酒,摆一盘*肋,炖汤的鲈鱼是花鲈也好,四鳃鲈也罢,哪怕换成美国大口黑鲈,他大约也不会像《舌尖上的中国3》的观众那么挑剔。但如果再摆上个空盒子,可能他老人家就压力山大了。 《水浒传》吃的是江湖 请施耐庵吃饭,鱼汤就不能这么马虎了。 施老师显然是生活在水边的人,但不是海边,所以提到海产品,泛泛的只说海味,不罗列具体的名目,但怎么拿淡水鱼炖汤,他显然很有心得。 智多星吴用想拉阮氏三雄入伙去劫生辰纲,套近乎的方式,是去讨要“十数尾金色鲤鱼,要重十四五斤的”。这大约是当时大鱼的标准。阮家哥儿几个表示很为难,因为他们生活的石碣村水浅,要十斤的也难,而大型锦鲤,都被霸占了深水区的梁山垄断了。可知至少仅就分量而言,现代淡水鱼养殖业,当然是可以傲视前贤的。 宋江*爱吃鱼,嘴巴也比吴用刁。所以在浔阳江畔,吃了几杯酒,想要“加辣点红白鱼汤”,而且只“呷了两口汁”,立刻吃出这鱼不是**现捞的,就不吃了。宋江的行为举止,在李师师这样的东京名妓眼里,固然还是“把拳裸袖(看来很热)”,很没体统,但和鲁达、李逵这样“原教旨”的好汉比,就已经算精致和矫情了。李逵迅速吃掉了宋江、戴宗嫌弃的鱼,还不满足,宋江吩咐切了三斤羊肉上来,李逵才说:“这宋大哥便知我的鸟意!肉不强似鱼?” 毕竟,肉才是梁山好汉的*爱。想想,尽管梁山泊以产大鱼出名,但山上生活的宣传语若是换成“大碗喝肥宅快乐水,大块吃金色鲤鱼堡”,英雄气概登时泄掉大半。至于吃什么肉,好汉们倒是不忌口。*鸭鹅这样的禽类,牛羊猪这样的家畜,在《水浒传》里都频频出现。马肉也一样没有放过,就连呼延灼的连环马,被钩镰*伤了之后,也被拿去做了菜马。 不过还是可以看出一个排序。羊肉、猪肉是*普通的,不论是小旋风柴进还是托塔天王晁盖,也包括宋江,在他们表面上还是守法良民的时候,哪怕广交天下的好汉,家里也只会杀猪宰羊,杀*宰鹅,很少有牛肉吃。前面提到的浔阳江畔的酒馆,因为是公开合法经营,所以也只有羊肉卖。 那时的法律规定,屠宰耕牛犯法,人们不一定严格遵守,但也不能肆无忌惮地践踏,吃牛肉,多少带点犯禁的快感。“花糕也似的好牛肉”,这句形容语,不是对牛肉有真爱,而是真想不到,写不出。 吃狗肉的犯禁程度比吃牛肉又重些,鲁智深在五台山附近的酒馆里想买酒肉吃,那段描写大概可以看出当时一般僧人的守戒状况。 五台山文殊院是大寺庙,管理严格,鲁智深亮出这个身份,就没有酒馆敢卖酒肉给他。 但他假装是行脚僧人,再去买,酒就到手了。店家回应说:“早来有些牛肉,都卖没了。”酒已经卖了,能多赚点肉钱也好,所以这不像是谎话搪塞。也就是和尚吃肉这事,其实并不罕见。 鲁智深闻到肉香,发现砂锅里煮着一只狗。店家道:“我怕你是出家人,不吃狗肉,因此不来问你。” 中国虽然本有吃狗的传统,但自从佛教传入之后,人们的观念还是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不吃的理由,和现在的爱狗人士可能刚好相反。佛经里常以狗喻贪婪、嫉妒、争斗种种恶行。所以不是“狗狗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它”,而是“吃狗肉,你不怕变得像狗那么坏吗”?接下来这段描写极生动: 智深大喜,用手扯那狗肉蘸着蒜泥吃,一连又吃了十来碗酒。吃得口滑,哪里肯住。店家倒都呆了,叫道:“和尚,只恁地罢!” 真是此人之肉彼人之毒,现代读者看了是觉得食指大动还是恶心反胃,不同的人反应怕也大不相同。 如果相信孙述宇先生的说法,《水浒传》是强人写给强人看的书,那请施耐庵吃饭的要点,大概也就明白了。酒肉管够就行,别的不需要太多忌讳,也没有太多讲究。只是有一点,如果不是胆力过人,吃饭的地点,一定要由你来挑。《水浒传》写大吃大喝,常有点口味怎么重怎么来的刻意。梁山好汉里有不少似乎挺喜欢在死人身边吃喝。 鲁智深、史进杀了崔道成、丘小乙一对恶僧恶道,但并没有救得了谁,被欺负的老和尚上吊死了,被掳来的女人投井死了。于是,鲁智深和史进就当着这些死人,跑到厨房做起饭来。 武松血溅鸳鸯楼,杀光在场所有人之后,在**壁上写下“杀人者,打虎武松也!”之前,注意力是在张都监、蒋门神他们吃剩的酒肉上,于是一连吃了好几盅酒。然后流亡途中,他杀了飞天蜈蚣王道人和一个道童,于是就接*被王道人抢来的女人的邀请,去吃人家没来得及吃完的酒席了。 真假李逵的故事里,黑旋风李逵杀死李鬼夫妇,吃着李鬼妻子煮的白米饭,正嫌弃没下饭菜,看见地上李鬼的尸体,自责地说:“好痴汉!放着好肉在前面,不会吃!” 所以,若换作是施耐庵写《三国演义》,曹*杀了吕伯奢全家后,他大概是不会让曹*马上就走的,就算不吃吕家人,曹*至少也会先把后院绑的那头猪吃了。 《西游记》吃的是食物 真心话,我特别想请吴承恩老师吃饭。读《西游记》很容易发现,这就是一位特别爱吃的老师。和《三国演义》对食物能不写就不写相反,《西游记》经常是逮着机会,不管情节需不需要,就来一段报菜名。 如小说开始不久,美猴王离开花果山学艺,猴子猴孙给他送行,开列的水果单子是: 金丸珠弹,红绽黄肥。金丸珠弹腊樱桃,色真甘美;红绽黄肥熟梅子,味果香酸。鲜龙眼,肉皮薄;火荔枝,核小囊红。林檎碧实连枝献,枇杷缃苞带叶擎。兔头梨子*心枣,消渴除烦*解酲。香桃烂杏,美甘甘似玉液琼浆;脆李杨梅,酸荫荫如脂酥膏酪。红囊黑子熟西瓜,四瓣黄皮大柿子。石榴裂破, 丹砂粒现火晶珠;芋栗剖开,坚硬肉团金玛瑙。胡桃银杏可传茶, 椰子葡萄能做酒。榛松榧柰满盘盛,桔蔗柑橙盈案摆。熟煨山药,烂煮黄精。捣碎茯苓并薏苡,石锅微火漫炊羹。人间纵有珍馐味, 怎比山猴乐*宁! 你说这种排列里有多高的文学技巧吧,倒也说不上。但一个吃货面对丰富的美食,那种从心底流露出来的欢喜,却分明是可以感*到的。 除了描写食物本身,他还特别善于写人物吃东西的状态。写猪八戒大吃,几乎场场出彩。在车迟国三清观,行者向猪八戒夸张地形容了贡品的数量和力量,“馒头足有斗大,烧果有五六十斤一个”,并不是什么**货,但对挨过饿的人来说却格外诱人。师兄弟三人坐下, 把贡品全部吃光,“ 那一顿如流星赶月,风卷残云,吃得罄尽,已此没得吃了,还不走路,且在那里闲讲消食耍子”。这是劳动者饱食后休憩的画面。 过去批点《西游记》的文人,对小说写吃,尤其是写猪八戒的吃常有不满,认为“都重复,都俗”。这大概是因为中国传统中,吃往往被赋予了重要的内涵。孔子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传说商朝的伊尹游说商汤,是把治国的道理放在做菜的道理中讲明白的;汉朝陈平分肉分得好,就要说“吾宰天下,亦如是肉矣”的大话……总之,吃不仅是吃,各种乱七八糟的大道理,都可以放进来乱炖。而《西游记》的特点就是,它往往写吃就是写吃,内涵也许欠奉,但看的人会饿。 至于天上的蟠桃宴、安天会之类,排场虽大,其实倒没甚看头,无非琼浆玉液、龙肝凤髓之类。这类描写,*重要的方法是在上流社会生活的基础上,进一步铺排渲染,溢彩增华。而这恐怕不是吴老师的长项,毕竟,他显然是中下层文人,王公贵族是怎么过*子的,他大概并不熟悉。即使写人间生活,他也是写国宴就比较平庸。比如女儿国国王对唐僧师徒盛情款待,那一顿饭菜如何,描写就平板僵硬,远不如写民间*常的吃食,来得饱满鲜活。 吴承恩老师还有个特别之处,他应该是不光爱吃,而且自己常下厨房。写唐僧遇到猎户刘伯钦,在他家吃饭有个难题:猎户家自然以肉食为主,“有两眼锅灶,也都是油腻透了”,做素菜也成荤的了,怎么给唐僧做饭呢?刘伯钦的老母亲出手了,“着火烧了油腻,刷了又刷,洗了又洗,却仍安在灶上。先烧半锅滚水别用,却又将些山地榆叶子,着水煎作茶汤”,然后才给唐僧煮饭。没有丰富的洗碗经验,可真写不出这么一段。 师徒四人都吃素,但《西游记》里*感天动地的一段做菜的描写,却是关于怎么蒸猪肉的。在狮驼岭,猪八戒被塞进了蒸笼,妖怪们则备下蒜泥盐醋,显然是准备第二天吃*能体现肉质好坏的白切猪肉。 奈何妖怪是个雏儿,明知道八戒难蒸,却把他安放在*下面一格。这时二师兄忧心忡忡:“哥啊,依你说,就活活地弄杀人了!他打紧见不上气,抬开了,把我翻转过来,再烧起火,弄得我两边俱熟,中间不夹生了?”中间夹生了叫苦的该是妖怪才对,你反正已经死了与你何干?这就是猪生自古谁无死,要留美味在人间,真真展示了一个美食家不惜用生命写就的情怀。 所以请吴承恩吃饭,*好是囤足食材,请到家里来吃。菜不要多,因为没准吃不了多少,他就忍不住自己撸起袖子下厨了。 《红楼梦》吃的是文化 请曹雪芹老师吃饭,是需要勇气的。 《红楼梦》写吃,内容太多,太丰富。说博大精深,是理所当然的评价。研究起来,很容易就能写成一部书。事实上就有许多学者已经写过了很多的书。我这千把字的篇幅,还真不知道该说点啥好。 我这样的俗人,本是看《**梅》里西门庆家那一根柴火就烧得稀烂的猪头觉得十分神往的。但看《红楼梦》里的精致菜肴,大多只能震惊于品位之高雅,烹制之繁复,越看越不敢吃了,思维也就不免跑偏。 比如说,现代的小仙女们要穿越到大观园去,香水还是要自带的,因为古代蒸馏技术不过关,制作的各种花露之类,浓度都不高,效果当然也不好。所以同一种花露,可以是香水,也可以是喝的饮料,如第六十回引发了风波的“玫瑰露”即是。反过来想,如果古代的这种不加区分延续到**,比方说各种色号的口红和火腿肠在一个柜台售卖,那效果倒也感人。 又比如说,妙玉喝水,要取梅花上的雪,她怎么就没有发现,雪融化后,会有许多肮脏的沉淀?毕竟,雪形成的*基本条件是大气中要有“凝结核”存在,而大气中的尘埃、煤粒、矿物质等固体杂质则是*理想的凝结核。也不知她有没有经常跑肚拉稀的毛病。 再比如王熙凤忽悠刘姥姥的**的茄鲞: 把才下来的茄子把皮签了,只要净肉,切成碎钉子,用*油炸了,再用*脯子肉并香菌,新笋,蘑菇,五香*干,各色干果子,俱切成丁子,用*汤煨干,将香油一收,外加糟油一拌,盛在瓷罐子里封严,要吃时拿出来,用炒的*爪一拌就是。 说得那么复杂,基本的口味,似乎还不如腌茄子加*精调香油。曾见王蒙先生的文章里提到,有人真的照做过,结果并不见佳。不知道诸位信不信,反正我是信的。 所以,我是自知不配请曹老师吃饭。若是碰到落魄后的曹老师,倒是可以请他吃个汉堡,也不妨说下这种廉价食品背后的工业生产流水线,比起茄鲞还复杂得多。这种流水线没什么品位,不过世界上“ 举家食粥酒常赊”的人,却因此少了许多。 骁勇善战的武将关羽,为何私下里偏爱读《春秋》; 明清时期公案小说红极一时,那时的基层官员都在忙什么,他们又如何自保; 无数女人耍尽心机用尽手段却求之不得的宫斗成就,汉代一个貌不惊人的女人窦猗房于不经意间全盘收获,大概没有什么比她的命运,*能解释“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夫唯不争,故天下莫可与争”之类的老子格言了; 欧洲中世纪的国王、同一时期的乾隆帝,大多喜欢在路上,原来他们心中都有一盘巨大的棋。 宋代史学家吕祖谦说:观史如身在其中,见事之利害,时而祸患,必掩卷自思,使我遇此等事,当作何处之。如此观史,学问亦可以进,智识亦可以高,方为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