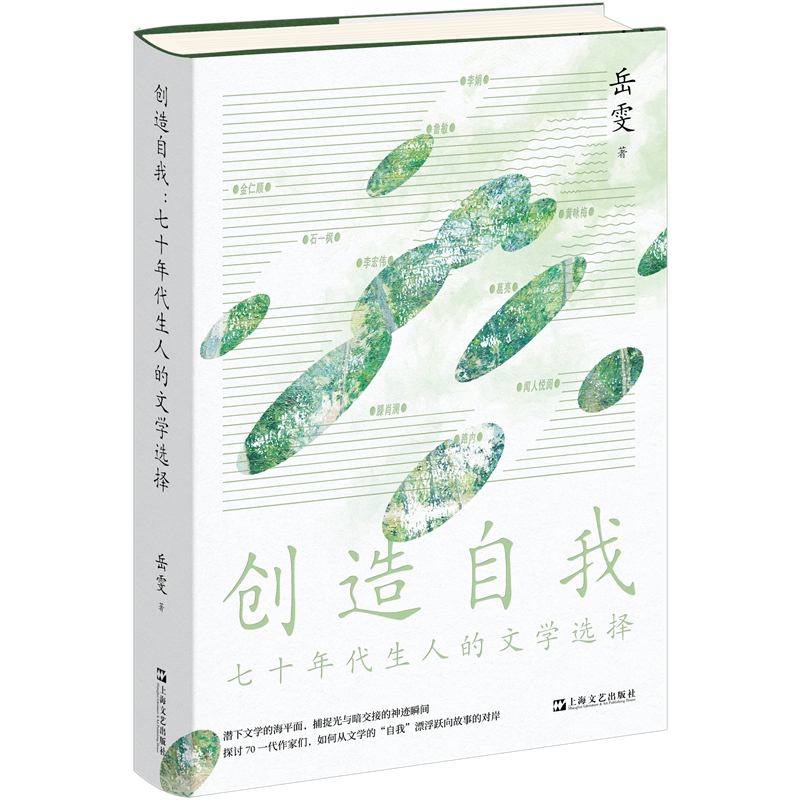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文艺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创造自我:七十年代生人的文学选择
ISBN: 97875321896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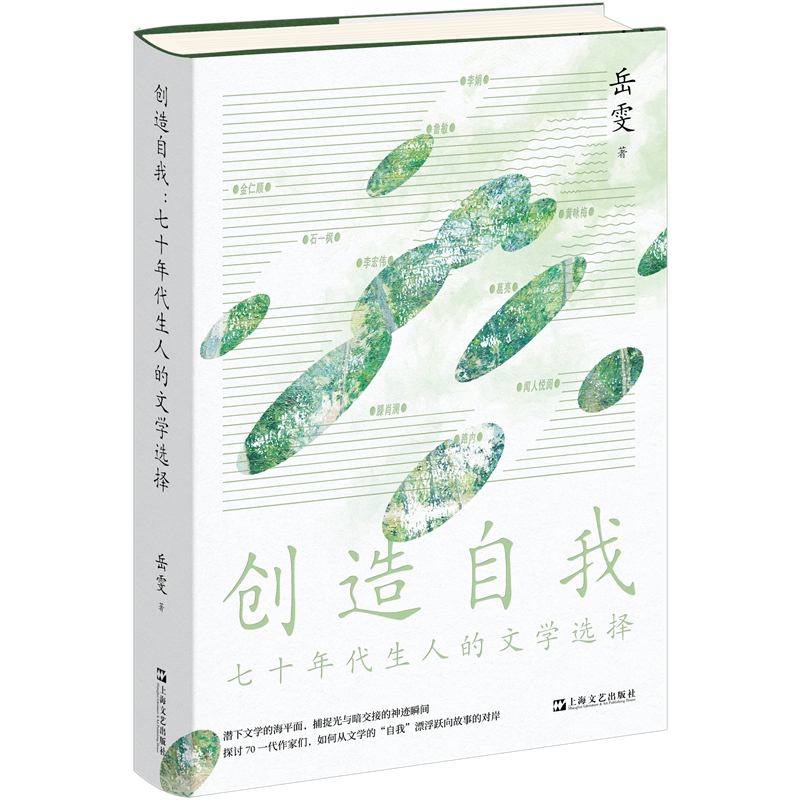
岳雯,文学评论家。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博士。著有《未尽集》《爱的分析》《抒情的张力》《沉默所在》。曾获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等奖项。
? 创造自我——李娟论 ? 三 据说,有人曾对李娟写作的持续性表示担忧,“写了十来年阿勒泰乡村旮旯里琐碎生活和纯粹自然之后,今后怎么写?”仿佛是为了回应这些质疑,李娟在《李娟记》中提出了反驳——“长久以来,我的写作全都围绕个人生活展开。于是常有人替我担心:人的经历是有限的,万一写完了怎么办?我不能理解‘写完’是什么意思。好像写作就是开一瓶饮料,喝完拉倒。可我打开的明明是一条河,滔滔不绝,手忙脚乱也不能汲取其一二。总是这样——写着写着,记忆的某个点突然被刚成形的语言触动,另外的一扇门被打开。推开那扇门,又面对好几条路……对我来说,写作更像是无边无际的旅行,是源源不断的开启和收获。”李娟将这一担忧理解为题材层面的枯竭。在她看来,随着生活之河的流淌,以记叙自我生活为己任的作家是有无限丰富的素材可供采撷的。实际上,这层担忧可以而且应该被从自我塑造这一层面去理解。也就是说,在消费时代,如果我们从作家和读者的关系去考量,那么,作家是生产者,读者是消费者。具体到李娟这一个案,读者是在接受“阿勒泰的李娟”这一文学形象的基础上实现对李娟作品的消费。但是,倘若这一文学形象数十年无变化,始终保持当年的“谐趣横生”,读者恐怕将对此产生审美疲劳。而事实上,这一预言正在慢慢显露它的形状。 在“牧场系列”之后,李娟的读者们在迎来灵动跳脱的随笔集《记一忘三二》之后终于等到了又一部主题性的叙事散文《遥远的向日葵地》。这部散文以“我妈”在南部荒野中种向日葵的经历为表现内容,“我妈”这一人物形象成为主角。在此之前,“我妈”这一人物形象零星地在《我的阿勒泰》和《阿勒泰的角落》里出现过,到了《遥远的向日葵地》中,她成为被集中表现的对象。这可以看作是李娟对于“自我”的一次尝试性扩展。“我妈”和“我”血脉相连,又分享了大致相同的生活经历。但较之于“我”的文艺式的敏感与自省,“我妈”更泼辣,也更强悍。因此,“我妈”成为被观照的对象,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对“自我”的观照。与此同时,“我”也获得了评述和言说的空间和余地。 这个“自我”依然怀抱着对人世和大地的巨大热情。这是李娟一以贯之的主题,也是她深切打动读者的地方。故事是从“我妈”独自在乌伦古河南岸的广阔高地上种了九十亩葵花地开始的。种地这一行为脱离了具体的经济生计的考虑,被充分审美化和象征化了。在李娟看来,种地,其实是在过真正与大地相关的生活。因此,种地过程中遇到的种种艰辛,都是向大地的献祭。“于是整个夏天,她赤身扛锨穿行在葵花地里,晒得一身黢黑,和万物模糊了界线。”“她双脚闷湿,浑身闪光。再也没有人看到她了。她是最强大的一株植物,铁锨是最贵重的权杖。她脚踩雨靴,无所不至。像女王般自由、光荣、权势鼎盛。很久很久以后,当她给我诉说这些事情的时候,我还能感觉到她眉目间的光芒,感觉到她浑身哗然畅行的光合作用,感觉到她贯通终生的耐心与希望。”这个“她”是“我妈”,也是李娟关于“自我”的想象。这一“自我”超越了日常生活,而闪烁着因为与大地相连而分享的神性的光芒。李娟越是着力书写人的力量感,人对于大地的蓬勃欲望,就越是要写出这欲望之后的虚妄。于是,我们看到,两年的艰辛劳作,第四遍播下种子,收获却是如此菲薄。甚至,劳作的人要付出惨烈的代价——在种地的第三年,在收获丰收的同时,“我叔”突发脑溢血,中风瘫痪,至今生活不能自理,不能说话。这样一个希望与悲伤同在,力量与虚妄相伴的故事似乎早就被写就。这不禁让人想起了刘亮程在《荒芜家园》里的感慨——“一年一年的种地生涯对他来说,就像一幕一幕的相同梦景。你眼巴巴地看着庄稼青了黄、黄了青。你的心境随着季节转了一圈又回到那种老叹息、老欣喜、老失望之中。你跳不出这个圈子。尽管每个春天你都那样满怀憧憬,耕耘播种;每个夏天你都那样鼓足干劲,信心十足;每个秋天你都那样充满丰收的喜庆。但这一切只是一场徒劳。到了第二年春天,你的全部收获又原原本本投入土地中,你又变成了穷光蛋,两手空空,拥有的只是那一年比一年遥远的憧憬,一年不如一年的信心和干劲,一年淡似一年的丰收喜庆。”如果说,刘亮程表达的是一种循环论的悲凉感,那么,李娟则在悲凉之中灌注了“自我”的神采,一如这本书中葵花的形象,既灿烂壮美,又蕴含着来自土地深处黑暗的不为人所知的力量。 这个“自我”信奉万物平等,对小动物们充满了友善的关爱。遥远的向日葵地的故事,是“我妈”耕种和收获的故事,也是大狗赛虎和丑丑的故事,是在荒野中成为土匪和泼妇的公鸡和母鸡的故事,是一个冬天养得膘肥体壮不再会游泳的鸭子的故事,是在茂密的葵花地里迷路整夜回不了家的兔子的故事……假如没有这些生灵,在荒野中独自耕种的人该多么寂寞;假如没有这些生灵的故事,属于葵花地的故事又该多么单薄。 这个“自我”对环境的破坏保持着一贯的警觉。我们还记得,在“牧场系列”中,李娟对牧人迁徙是为了保护环境的赞美。到了《遥远的向日葵地》,李娟在展现人的力量的同时,也意识到耕种是对大地的索取。当人为了经济利益,不顾土地的状况无休止地索取的时候,大地也会死去。李娟描述了“死掉的土地”,坚硬的,发白的,因为过度耕种而被废弃。而在李娟的精神秩序中,大地与人是同构的,大地被压榨,也意味着人的被压榨。大地的死亡,意味着人的死亡。 在李娟的书写中,经济与“自我”的关系被容纳了进来。在某种超越性的抒情以外,李娟意识到万事万物,特别是构成人类生活的最基础性的事物,都与“自我”有关。这使她跳出了以往单纯的乐观、肯定与赞美,开始生长出理性的种子。但是总体而言,在《遥远的向日葵地》里,我们读到的还是那个熟悉的李娟,那个在广袤的大地上书写着明亮的寂寞的李娟。那个“自我”是如此稳固与强悍,以至于在书写的时候,李娟无法挣脱其边界,从而开拓崭新的天地。到底还是那个“阿勒泰的李娟”啊。 沿着小径交叉的森林,李娟一路走到现在,似乎这是属于她的命定的道路,再也没有其他的可能。这让我想起她早年写的似乎被谈论得不多的《木耳》。《木耳》讲述了木耳的神奇出现与消失,以及它在人心中掀起的巨大波澜。在李娟的作品中,这一篇深具小说的气质。在这部作品中,“自我”挣脱了以往单纯的律令,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色彩。一开始,“我”和“我妈”是大自然生活的遵守者,“我们”与阿勒泰群山背面浩浩荡荡的森林平安相处。“我们”知道,在浩瀚幽密的森林深处,有生命的气息。这是一种对自然与生命发自本能的尊重与畏惧。尤其是在“我”跟着“我妈”采木耳的过程,这感觉越发分明。那种绿,仿佛是有生命的绿,感觉被这种绿所注视。所以,“我”才一步也不敢乱走,“全身的自由只在我指尖一点”。这是原初人与自然相处的状态。但是,随着木耳的出现,一切都变了。这里要追问的问题是,在一个从来没有木耳的森林里,木耳为什么会出现呢?对此,李娟有一个解释。她说,木耳是随着那些不得不最终来到阿尔泰深山的人们来的,而全球变暖的趋势,也恰好造就了最适合生长的气候环境。这一点非常有意味。也就是说,之前,阿尔泰深山因为地理环境的缘故,自成一体,自外于现代性和全球化的世界体系中,而现在,这一切改变了。木耳的出现就是一个征兆。这是变化的最根本的原因。 木耳的出现也使“我们”发生了变化——从自然秩序的服从者到被经济利益驱动的个体、大自然的索取者。在此之前,“我们”去森林,只是为了拾柴禾。森林供给我们所需要的那一点点资源。木耳的出现让我们意识到,自然有可能成为财富的来源。李娟的原话是,“就那么一下子豁然开朗了(似乎又在瞬间蒙蔽了些什么……)”。豁然开朗,是被现代性的经济体系启蒙的感觉。那么,“蒙蔽”指的是被眼前可见的利益所蒙蔽?由此我们看到,个人具有了强大的主体能动性。“我们”先是不辞辛苦地在森林中跋涉,发现、采拾木耳。尽管在劳动过程中,“我们”获得了关于森林和木耳的经验,但收获毕竟是微薄的。于是,“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小的经济体来实现进入大的经济体的努力。这是我们向牧人收购木耳的开始。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和牧人的关系也变得复杂起来。对于生活结构与我们截然不同的牧人来说,他们对于现代经济体系更是一无所知。“我们”是木耳的命名者,并赋予其价值。从经济秩序上说,“我们”优先于牧人。但是,也有牧人拒绝进入这一秩序中。比如,就有从西面沟谷里过来的阿勒马斯“只是用鼻子哼了个‘不’字”。这与哈萨克牧人的传统礼俗有关,他们热情地款待上门的客人,而拒绝任何形式的经济交换。 应该说,木耳被赋值的过程,也是其被人一拥而上,疯狂追捧的过程。更多的人来到了大山中,也带来了现代社会更为轻便,但与此同时对森林更具破坏性的因素。竞争变得越来越剧烈。这种剧烈程度甚至让发现它的人感到困惑——“我们也许清楚它的来处——无论是再秘密的藏身之地也能被我们发现,却永远不能知晓它今后的漫长命运。”与此同时,自然的秩序随着木耳的被赋值而彻底被改变了。只要是具有经济交换价值的事物都被人们疯狂地追逐。由此,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我”看到了人的欲望之可怕,也看到了在人的欲望之上更为强大更为坚决的意志。此时的“我”,变成了原始秩序的追忆者,怀念起那些没有木耳的日子,那些“没有希望又胜似有无穷的希望的日子”。“我”似乎全然忘记了,是什么撬动了变化的发生。木耳的消失就像它的出现一般神奇,生活仿佛又回到了原点。但是,这个原点,已经完全不同以往了。 在这部作品中,李娟依然要对她所经历的某种生活作描述,作解释。但显然,生活的复杂性远远超出了她所依凭的观念。当她让内心的散文家隐身的时候,一种从未有过的丰富与复杂就诞生了。但不知为什么,李娟没有沿着这条道路继续走下去。《木耳》孤零零地厕身于她的作品中,成为独异的所在。据说,“这篇她自己很不喜欢,虽然是真实发生的,但写作的刻意与苦心让她难受。她不喜欢沈从文某些文章,也是因为觉得他写得‘苦’”。这大约解释了李娟为什么没有沿着这条道路走下去。李娟的被接受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叙写了“生计之累”中的“生命之美”。这也构成了她的写作路径。从这个角度看,《木耳》蕴含了丰富的意味,不再是单纯明朗的美。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娟所创造的“自我”也决定了她的写作趣味与美学风格。 李娟曾经说过:“在大雪围拥的安静中,我一遍又一遍翻看这些年的文字,感到非常温暖——我正是这样慢慢地写啊写啊,才成为此刻的自己的。”对于李娟来说,写作既是创造自我的方式,也是参与世界实践的方式。在写作中,她成为“阿勒泰的李娟”;与此同时,“阿勒泰的李娟”也规定了她的写作道路。道路漫长,打破自我的限定对她而言可能是巨大的冒险。但冒险是值得的,因为一个有着持续创作活力的作家正诞生其间。 ?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李娟、鲁敏、金仁顺、黄咏梅、石一枫、李宏伟、葛亮、滕肖澜、闻人悦阅、路内这些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七〇一代,他们走出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的“大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进入被讨论的范畴,他们开始让“个人”不断地“换新颜”,以“叙事个人”的力量不断创造自我。 ? 在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自我”已经成为全球化、都市化在个人身上的投影,进而衍生为一个哲学命题。如何理解复杂的自我?七〇一代作家们用不同的“隐含作者”身份搭建桥梁,理解自我、表达自我、创造自我,建造起新的文学世界,获得某种程度的表达自由。 ? 《创造自我》是一本帮助我们走近七〇一代作家“文学自我”的密码本,从这本书,我们走近他们的写作;从这本书,我们得以观照当下、发现自我。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李娟、鲁敏、金仁顺、黄咏梅、石一枫、李宏伟、葛亮、滕肖澜、闻人悦阅、路内这些逐渐走上历史舞台的七〇一代,他们走出五〇年代、六〇年代的“大时代”,越来越多的作品进入被讨论的范畴,他们开始让“个人”不断地“换新颜”,以“叙事个人”的力量不断创造自我。 在充满流动性的现代社会中,“自我”已经成为全球化、都市化在个人身上的投影,进而衍生为一个哲学命题。如何理解复杂的自我?七〇一代作家们用不同的“隐含作者”身份搭建桥梁,理解自我、表达自我、创造自我,建造起新的文学世界,获得某种程度的表达自由。 《创造自我》是一本帮助我们走近七〇一代作家“文学自我”的密码本,从这本书,我们走近他们的写作;从这本书,我们得以观照当下、发现自我。
试读内容
——李娟(作家,著有《我的阿勒泰》)
——鲁敏(作家,著有《金色河流》)
——金仁顺(作家,著有《白色猛虎》)
——黄咏梅(作家,著有《小姐妹》)
——石一枫(作家,著有《借命而生》)
——李宏伟(作家,著有《国王与抒情诗》)
——葛亮(作家,著有《北鸢》)
——滕肖澜(作家,著有《心居》)
——闻人悦阅(作家,著有《琥珀》)
——路内(作家,著有《雾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