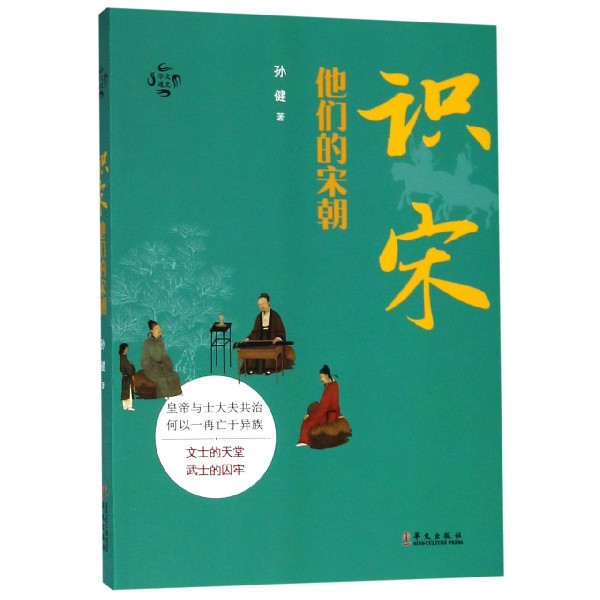
出版社: 华文
原售价: 48.80
折扣价: 28.90
折扣购买: 识宋(他们的宋朝)/华文通史
ISBN: 97875075511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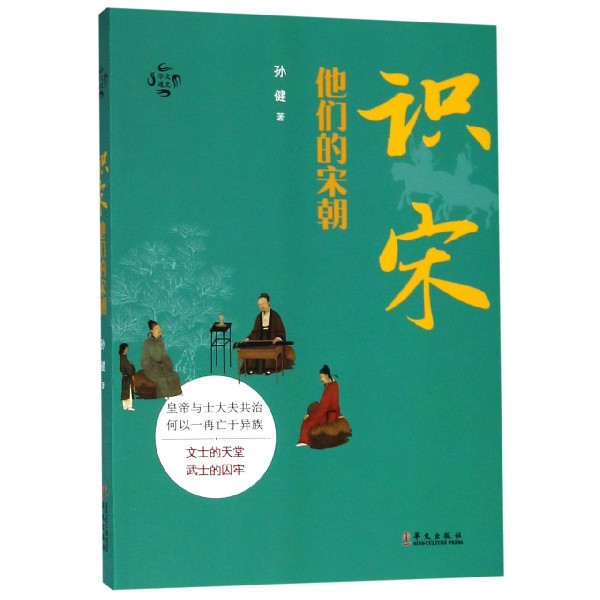
孙健:北京师范大学、比利时根特大学联合培养博士,现任职于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宋代政治史、海外汉学。著有《文献与学术:宋代典籍海外流传与欧美学界宋史研究》等。
序二 谈及中国古代历**的盛世,有人推崇汉唐,有人主张明清,“积贫积弱”的宋朝显然不在候选榜单之内。不唯如此,在很多人心目中,宋朝两次亡于异族之手,简直就是屈辱的代名词。然而与国人的苛责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如白乐*(Etienne Balazs)、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西方汉学家,却对宋代历史给予了很高评价。谢和耐注意到11—13世纪的中国在经济和学识方面的惊人发展,坦承在贸易、技术水平、政治组织、科学知识、文学艺术等诸多方面,欧洲都大大落后于中国。这种认识上的巨大反差,*使人们对如何看待宋代历史感到无所适从。 从长时段的视角看,宋代是中国历史演进过程中的重要转折时期,它是中央集权发展的里程碑,六朝隋唐以来的贵族政治被君主专制所取代。君主独裁政治下,皇位的传递是***重大的政治事件,对于接续五代而立的宋朝而言,这一问题*有其特殊的敏感性和紧迫性。五代乱世,功利主义的盛行和“君权神授”观念的转淡,催生出“无人不思为天子”的社会心理;皇位传递观念也因客观环境的逼迫而发生改变,“**多事,议立长君”成为时人的共识。宋**以“陈桥兵变”登上帝位,宋太宗继统也有篡位之疑,归根结底,它们都是五代传统的延续。但另一方面,随着**步入长治久安的轨道,无论是源远流长的家天下的传统,还是现实的政治环境,都在要求皇位传递从五代的“异常”回归“正常”。武功王之**、涪陵县公之贬死,是后人指摘太宗的两大失德之处,然而在道德批判的同时,不应忽略这两个举措背后的必要性,宋太宗在新的历史关口,以一种决*的态度扭转了五代皇位传递的“乱象”,推动了历史的转折。从宋**、宋太宗身上,折射出当事人走出五代、迈向治平的挣扎与艰难。 北宋末到南宋初,皇位传递出现另一个引人注意的现象,即由于禅位而形成的太上皇-今上的二元结构。正如杨万里所说,皇权“非可共理之物”,这一结构带来的不是权力的转移,而是皇权的分裂。它给现实政治造成巨大影响。徽、钦二帝间爆发尖锐冲突,错失出幸避敌的时机,父子双双沦为阶下囚。高宗的干预极大地削弱了孝宗的**,孝宗不时感*到来自臣下的轻忽,在潜意识的作用下也偶尔流露出对皇权*到侵夺的不满。太上皇和臣子从两个方向挤压着孝宗的帝王心理,他既要突显自己的存在,又对大臣充满不信任,因此宁愿事必躬亲,也不以责任臣下。当孝宗想把类似的权力结构再移植到他与光宗的关系中时,再次导致悲剧性的结局。光宗拥有*强烈的独占皇权的意识,在他心中,来自孝宗的压力,他自己要求独尊的意志,李后的挑唆,儒家伦理规范,数种力量一直处于激烈交锋中,给他带来毁灭性的结果。孝宗与光宗的父子关系,终因太上皇-今上的权力结构而被撕扯得四分五裂。五代乱世的根源之一是文武关系的失衡,武夫悍将左右政局,文教大衰。宋**奠定“文治”的政策导向,宋太宗进一步“兴文教、抑武事”,大量通过科举出身的文臣进入仕途,形成文臣治国的局面。寇准是宋朝培养起来的**代士大夫的代表,他敢于挑战皇权,“左右天子”,其担当意识为后人树立了一个典范。正因有类似寇准这样的榜样作为先驱,宋朝士大夫才理直气壮地说出皇帝是“与士大夫治天下”的豪言。王安石把宋代士大夫政治推向高峰,但他所主持的变法也使士大夫集团分裂为针锋相对的两个阵营,彼此间的争论愈演愈烈,终致互相倾轧。哲宗、徽宗两朝政治为朋*之争所充斥,数十年间没有任何实质有效的治国之政付诸实施。及至南宋,秦桧、韩侂胄、史弥远、贾似道相继秉政,权相政治几乎贯穿南宋政权的始终,南宋的政治生态*趋恶化,其统治濒临崩溃的边缘。 若以士大夫的自由度而言,宋代不但远超之前的汉、唐,也为其后的元、明、清三代所不及。思想的自由带来学术的发展,宋代士大夫不满汉唐学术章句训诂的刻板僵硬,认定能**汉唐注疏,直接把握古代圣贤的“文”与“道”,他们向经典寻求治世和思想精髓,义理之学应运而起。宋代学术纷繁瑰丽,北宋的荆公新学、温公学派、洛学、蜀学、关学,乃至南宋的湖湘、金华、永康、永嘉学派等,相互辩难,推动中国学术走向另一个**。诸多学派中,仅就对后世的影响而言,以朱嘉为代表的道学显然超出同侪。道学群体并非**专注于学术,而是有着明确的政治和社会使命,朱熹及其同道积极地参与**政治,其个人命运随政局变化而起伏。经历了诸多动荡挫折,道学由边缘走向学术中心,朱熹也成为道学的象征,曾经歧出多元的道学转变为程朱理学,不但奠定了尔后六七百年中国学术思想的走向,而且在整个东亚、东南亚地区的现代经济和社会建设中都产生了重要作用。 与士大夫政治伴生的是对武将群体的压制。“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是宋朝“祖宗家法”的核心原则,其中凝聚着宋朝统治者于五代乱世汲取的教训。以“杯酒释兵权”为代表的一系列政策措施,在人事和制度两个方面,扭转了武人干政、兴亡以兵之势,消除了困扰中原王朝近百年的重大隐患。经过宋初几代帝王“兴文抑武”的努力,社会价值评判标准发生根本性转变,*功战绩不再是衡量人才高下、功业声望的准绳,取而代之的是文学成就。 狄青的际遇折射出武人在崇尚文治的宋代的生存空间和生存状态,也反映出宋朝立国体制的某些深层次弊端。终于从唐末五代的窘境中脱身而出的文化精英们,不断强化着文学至上的理念,巩固其得来不易的领导地位。他们希望**性地消弭*权对政权的威胁,继宋初实现统兵权与调兵权分离、兵将分离之后,继续在制度上进行探索,至北宋中期形成以文臣为主帅、武将为部将的统兵体制。文臣为武将的活动范围划定了清晰的界限,并经由制度的强化上升为**意志,武将的生存空间*趋逼仄。五代时期颐指气使的武人们不复其猛悍之气,不得不在文臣的轻蔑乃至侮辱下退缩避让,小心翼翼地仰人鼻息。久而久之,武将的心态发生变化,处处表现出谦恭无能的姿态,宁愿有过,但求无功,以“释天子之猜疑,消相臣之倾妒”,这无疑是一种病态的政治氛围。宋室南渡,也带去了有关“祖宗家法”的集体记忆。苗刘之变、淮西兵变使高宗意识到将*事力量收归中央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岳飞之死则宣告南宋重回北宋以文制武的老路。 宋朝所处的环境与汉唐时期相比已经大不相同,相对于中原王朝而言,辽、夏、金都不再是附属性的民族政权,而已经成长为足以与中央政权分庭抗礼的少数民族王朝,因此与前朝相比,宋朝的内政和外交有着*紧密的联系。宋太宗两次北伐失败,北宋的国策随即转向消极防御、守内虚外。澶渊之盟虽开创了宋辽间百余年的和平局面,却在宋朝**引发了“天书降神”“东封西祀”等一幕幕闹剧,“一国君臣如病狂然”。及至南宋,**的对外政策*明显地***政局波动的影响。韩侂胄为求自固,打着收复中原失地的旗号发动北伐,却丧生于杨皇后和史弥远借机发动的政变。对韩侂胄的政治谋杀,是以正其开边之罪的名义进行的,也意味着新的领导集体必须在政策上与韩侂胄反向而行,宋金“嘉定和议”由此达成。宋理宗之立和济王之死使史弥远与道学群体决裂,道学集团力主灭金、拒*联蒙,史弥远愤恨之余,遂在外交政策上反其道而行之,一面与金维持不战不和的态势,一面与蒙古保持和好的关系。史弥远意图采用以夷制夷的传统策略,使金、蒙互相牵制,可当金朝灭亡已成定局后,南宋再想置身事外已不可能,除了与蒙古联合灭金外,已没有其他选择。 联蒙灭金申雪了赵宋百年之耻,就在金朝灭亡的前夕,史弥远也走到人生的尽头。史弥远之死并不意味着其政治影响力的终结,在后史弥远时代,渊默十年终于亲政的理宗急欲在南宋政治中打下自己的印记,备*史弥远压制的政治势力也要一展抱负,南宋遂展开以恢复中原为目标的“端平入洛”。“端平入洛”招衅纳侮,不但使南宋国力大损,而且带来一个比金朝*难缠的对手——蒙古。宋蒙间开始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争,南宋也走上覆亡之路。究竟是时势造英雄还是英雄创造了历史,是人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早年间的历史研究重视个体,中国传统史书中记载的多是重要人物的事迹,在西方影响深远的兰克史学也将政治人物视为改变历史的*重要力量。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史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的消失。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提出“人只是历史的泡沫”;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在《知识考古学》中宣称“人的死亡”,历史学家*加强调历史发展中非个人性的、结构性的因素。在笔者看来,两种倾向都不免有**之处,人和结构性因素之间不应该是相互否定的关系,历史的发展有其长时段的、结构性的因素,但并不否定人可以在其中自由、积极地发挥作用,两方面的结合才促使历史以那样的方式发生。因此这本书试图将人与结构性因素结合起来,观察个体在结构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本书以宋代政治史为叙述的主线,所选取的大多是两宋时期的政治人物,这是因为政治史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主干,能够为人们了解一个时段提供*直观的印象。通过对这些政治人物的考察,本书尝试呈现出宋代政治运作过程中的一些关键环节,如皇权的结构、士大夫政治、兴文抑武的国策、内政与外交间的互动等,进而能够对宋代的政治结构有进一步的了解,对宋朝呈现出来的特点以及这一时期的历史走向有*深切的体认。历史研究并不是非此即彼,解析历史理应也必须有多种不同的角度,“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本书呈现的线索只是笔者从特定视角出发对这段历史的理解和认识,是否有其合理性,仍有待于读者诸君的检阅。 太上皇-今上的政治格局:宋孝宗及其时代 高宗的禅让使皇位由太宗一系转回到**一系,除了*到当时 群臣的歌颂,甚至一向对高宗评价**苛刻的明代史家张溥也说: “彼一生行事,足告祖宗,质天地者,止有此耳。”但是在歌功颂 德背后,不能忽视禅位给南宋政权政治结构带来的深刻变化,它并 没有像形式上表现的那样实现权力的转移,而是造成了皇权的分 裂,形成太上皇-今上的二元权力格局,双方都需要在实践中摸索 彼此的权力边界。 禅让实现了帝尧公天下的儒家理想,使高宗的身份超升为与尧 并肩的圣王,高宗得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尊号:“光尧寿圣”。当 尊号由宰相和礼官拟定,交由侍从、台谏在都堂集议时,大臣们的 意见并不一致。持异议者认为,“寿圣”系英宗诞节之称,且已用 作佛寺之名。“光尧”寓意“比德于尧,而又过之”,似属过誉。 户部侍郎汪应辰就提出质疑:“尧岂可光?”高宗立即出面干预, 告诉孝宗汪应辰素来不喜欢自己。孝宗于是手诏“不须别议”,集 议大臣知势不可回,都签字同意,汪应辰不久便被外调。 孝宗能继承大统,**出于高 宗的赐予,对他来说,孝道不仅 是立德修身的儒家规范,*具有现实的意义,是他竞争皇位的** 资本。太上皇-今上的关系,是以太上皇的**和今上的顺从为基 础的。德寿宫就是由秦桧的旧第改建而成,隐然与皇宫对峙,形成 两个权力重心。高宗时刻强调着他不容触动的**。一次,德寿宫 一名卫士醉酒闯入钱塘县衙,咆哮无礼,被知县莫济施以杖罚。高 宗闻讯大怒,立刻谕令孝宗将莫济罢免。高宗一次在灵隐冷泉亭遇 到一位行者,自称本为某处郡守,因得罪监司而被废为庶人,高宗 答应为他向皇帝求情。数*以后,高宗又遇到行者,言及尚未得到 起复。次*,孝宗恭请高宗夫妇游园,高宗不笑不语,在孝宗百般 追问下才道:“朕老矣,人不听我言。”又说:“如某人者,朕 已言之而不效,使朕愧见其人。”孝宗随后召谕宰相:“昨*太 上圣怒,朕几无地缝可入,纵大逆谋反,也须放他。”于是尽复 该人原官。 孝宗朝的政治很大程度上笼罩 在高宗的阴影下,孝宗在即位赦 书中就明确表示,要继续听从高宗的指示,执行他的政策:“凡今 者发政施仁之目,皆得之问安视膳之余。”这是孝宗愿意服膺高宗 指导的公开承诺。孝宗**个年号“隆兴”,用意就是“务隆绍兴 之政”。对于安于旧秩序和既得利益的官员来说,这个承诺自然 *好不过。援尧舜故事上太上皇尊号后,他们*有理由请求孝宗像 舜协助尧那样,依从高宗的原则行事。孝宗也有模仿高宗的明显例 子,他即位后就设官收集建炎、绍兴以来所下诏旨条例,以便“恪 意奉承,以对扬慈训”。甚至视学的过程,也严格遵循高宗先例, “是为两朝盛典”。因此儒臣称孝宗于高宗“一政一事无不遵之 也”,“一字一画无不敬之也”。 高宗的政策不容妄议。一次,有言官批评秦桧专擅,这等于间 接批评了高宗。高宗将宫中一座建筑命名为“思堂”,然后宴请 孝宗。孝宗问及堂名的由来,高宗回答:“思秦桧也。”自此以 后 , 对秦桧的批评大大减少。秦桧身后之名需要维护,岳飞名誉 的恢复便要在低调中进行。尽管孝宗明白岳飞的冤屈和战功,也 只能有限地为他平反。淳熙年间,孝宗命有司为岳飞作谥,礼官 拟用“忠愍”:“危身奉上曰忠,使民悲伤曰愍。”孝宗以为用 “愍”字,则有批评太上皇失政的寓意,改为“武穆”。昭雪和 一切恩恤,都是以太上皇“圣意”的名义进行的,这些都是为太 上皇保留体面。 高 宗 退 位 之 际 , 与 孝 宗 达 成 共 识 , 孝 宗 每 月 四 次 至 德 寿 宫 朝 拜。一月四朝,表面上是儿子向父亲尽“温凊定省”的孝道,实则 具有重大的政治功能,它是高宗向孝宗发布指示、进行政治部署的 主要渠道。孝宗在朝拜德寿宫时,重要的朝臣奏疏都会送来,向太 上皇报告章奏和聆听意见都是习以为常的事。朝中的人事任免要经 太上皇首肯,新任大臣一定要先奏禀太上皇后再正式委任,殿试第 一甲的策文也要经太上皇过目。乾道八年(1172),孝宗听从言官 的弹劾,准许宰相虞允文辞职,但太上皇念念不忘虞允文在采石之 战中的功绩,反而令孝宗挽留他而把言官外调。 高宗退位御札宣称将所有*国要务全交孝宗处分,但由于各种原因,孝宗在相当大的程度上顺服于太上皇的**。孝宗把满足太 上皇的需索和富国强兵等量齐观,他特别新建“左藏封椿库”, 专门供养高宗和储备*资。高宗去世后,孝宗透露,此前德寿宫 缺钱,所以朝廷极力应付。孝宗要实行“永将四海奉双亲”的承 诺,就不得不将富国强兵的宏愿打折扣了。《宋史·孝宗本纪》称 赞:“宋之庙号,若仁宗之为仁,孝宗之为孝,其无愧焉,其无愧 焉!”然而清高宗却有不同看法,他说帝王之孝与庶人不同,一定 要把祖宗基业放在首位,南宋时祖宗旧疆已丧失大半,而孝宗不 思恢复中原、报仇雪耻,只能满足于膝下承欢的小节,不能称之 为孝。 本书以赵匡胤、赵光义、寇准、狄青、王安石等人为纲目,串联起两宋三百余年的历史,通过对人物行为的叙述及其前因后果的探寻,观照历史发展的变与常。本书不以解密、猎奇为意,聚焦于重大历史事件,条分缕析历史事件的台前幕后,揭开熟悉的历史的完整面貌。作者专*宋史,不空立论,言之有据,条理清晰,材料可靠,评价中肯。读完本书,你将对宋史有*全面、理性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