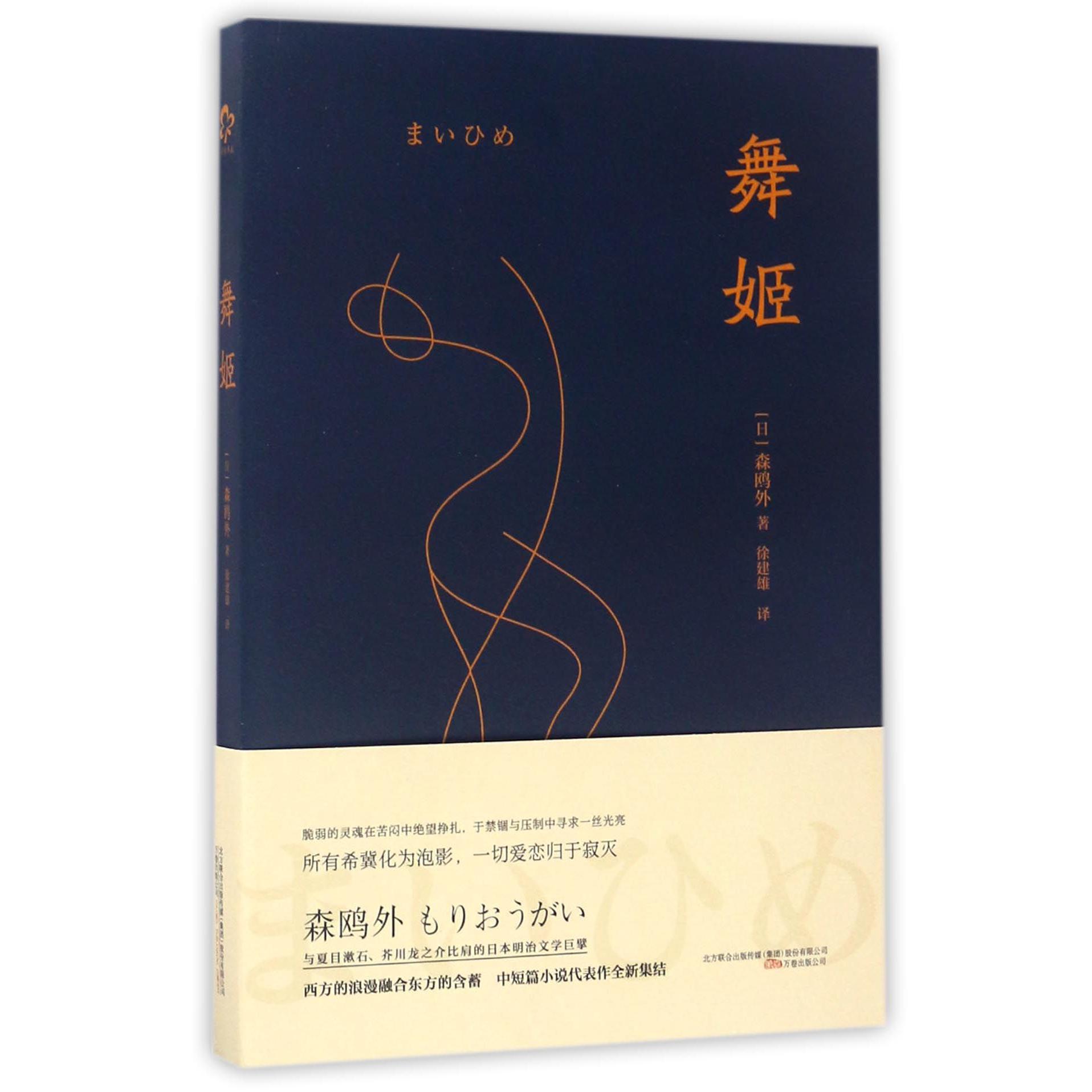
出版社: 万卷
原售价: 39.80
折扣价: 23.50
折扣购买: 舞姬
ISBN: 97875470451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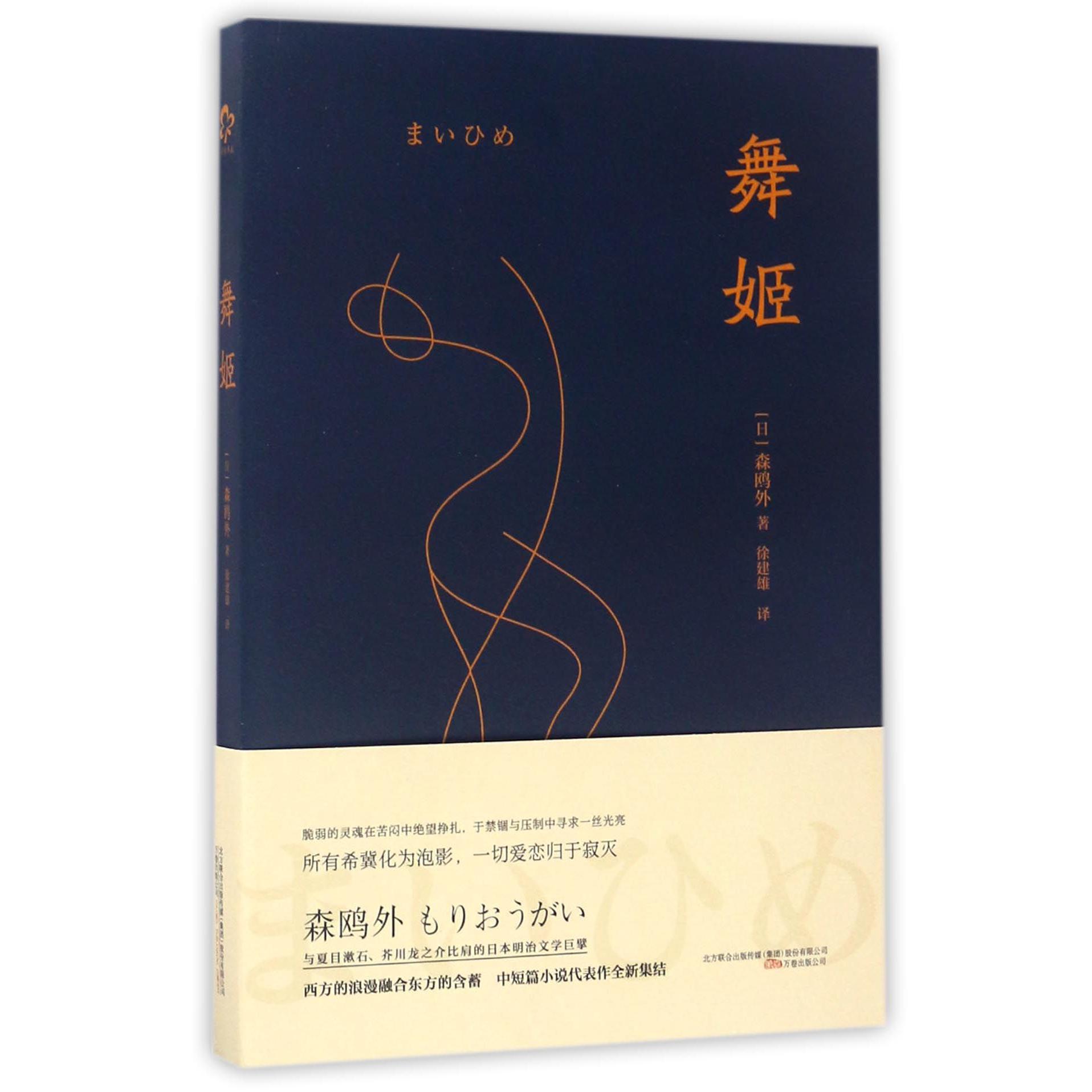
森鸥外(1862.2.17—1922.7.9),出生于石见国津和野(今岛根县津和野町),本名森林太郎,号鸥外,又别号观潮楼主人、鸥外渔史,*本文豪、翻译家,1881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医学部。 1**0年,发表**作《舞姬》,一举成名。后发表《泡沫记》和《信使》,统称“《舞姬》三部曲”,开创*本浪漫主义文学之先河。1909年,重启创作之途,不到四年间,创作了《修葺中》《沉默之塔》等四十余部现代小说。 从1912年至1921年的十年间,创作了《高濑舟》《寒山拾得》等13部历史小说和11部史传,名篇迭出。 1922年7月9*,60岁的森鸥外病逝于观潮楼。弥留之际,鸥外谢*了一切**赠予的荣衔。
啊,刚来德国之时,我自以为已经领悟了人生的 真谛,发誓决不做一个被动的、机械的人,可事实上 又怎样呢?不就像一只虽然被放出了笼子却还拴着脚 的小鸟,仅能扑腾几下而已吗?可我竟然沾沾自喜, 以为已经获得了自由。我根本无法解开拴在我脚上的 绳子。以前,这绳索的另一头*在我所属某省的上司 手里,如今呢?可怜见的,该是转到了天方大臣的手 里了吧。 我随着天方大臣一行回到柏林那天,正好是新年 元旦。在车站与大家告别后,我便坐上马车直奔家里 。由于当地有着除夕彻夜不眠,到了元旦再呼呼大睡 的习俗,所以家家户户都是静悄悄的。天气依然是冷 得要命,路上的积雪已经冻成了有棱有角的冰块,在 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光。马车拐弯驰进了克洛斯特街 ,停在了家门口。这时我听到了打开窗户的声音,当 然,我身在车内,看不到实际的景象。下车后,我让 马车夫拿着我的行李随我进门。当我正要走上楼梯时 ,迎面遇见了从楼梯上冲了下来的爱丽丝。她大叫一 声,一把搂住了我的脖子,将马车夫惊了个目瞪口呆 。他那张藏在大胡子中的嘴不知嘟哝了一句什么,我 没听清。 “啊,你终于回来了。你要是再不回来,我就要 一命归天了。” 事实上直到此时,我心里依然拿不定主意,思乡 之情和希望出人头地的功名之心还会时不时地盖过男 女间的爱情。然而,唯独这一瞬间,我抛开了所有的 烦恼,紧紧地拥抱着爱丽丝。爱丽丝将头靠在我的肩 膀上,并将喜悦的泪水哗啦啦地洒落在我的肩头。 “行李拿到几楼?”马车夫扯开嗓子像打锣似的 高吼一声后,便率先登上了楼梯。 爱丽丝的母亲出门来迎接,我塞给她一枚银币, 要她付给马车夫,自己便与爱丽丝手挽着手急不可耐 地走进屋去。进了房间之后,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只 见桌上放着许多白棉布和白花边之类的东西。 爱丽丝微笑着指着这堆东西说:“你看看我都准 备了些什么?”说着,她拿起了一块棉布。原来是一 块尿布。“你想想看,我心里有多高兴啊。这孩子生 下来后,也会有一对黑眼珠的吧。跟你一样的黑眼珠 。啊,我做梦都会梦见的黑眼珠。你是个好心人,这 孩子生下来后,你总不会让他姓别人的姓吧?” 她垂下了头又说道:“在给这孩子施洗礼的那一 天,我不知会有多高兴呢,到时候你一定又要笑我长 不大了。”说完,她抬起头来望着我,眼里噙满了泪 水。 回到柏林之后的两三天里,我揣想天方大臣一路 旅途劳顿,恐怕尚未恢复,故而没去拜访他,一直待 在家里。**傍晚,有个听差跑来说大臣要见我。我 去后,大臣十分热情,对我优礼有加,慰问过旅途辛 苦之后便问我是否有东归之意:“我虽然不知道你的 学问深浅,不过我想仅凭你的语言能力就已经足堪大 用了。我曾想,你在此地已耽搁*久,或许会有种种 牵累,后来我问了相泽,他说你并无此种麻烦,我也 就放心了。” 大臣说这话时的神情语态,简直叫人无法抗拒。 我明明知道这是不能应允的,可总不见得说“相泽说 得不对”吧,*何况此时我心中还冒出了一个强烈的 预感:机不可失!否则我将永远失去返回故国的良机 ,断*挽回名誉的途径,此生定将葬送于这座欧洲大 都市的茫茫人海之中了。啊!我拥有的是一颗怎样的 无*守之心啊!我居然一口应承,立刻答复道:“悉 听尊便。” 唉!纵然我有一张铁皮厚脸,回家面对爱丽丝时 又该如何开口呢?走出酒店之时,我心乱如麻,无法 言喻。我不辨道路,不分东西,只管闷头乱闯。也不 知挨了多少马车夫的骂,多少次惊慌退避之后才总算 没被马车撞死。过了好一会儿,我定睛看了看四周, 发现自己已经来到了动物园附近。我跌跌撞撞地坐到 了路边的长椅上,将烫得着了火似的、铁锤敲击般嗡 嗡作响的脑袋靠在了椅背上。就这样,瘫在长椅上一 动不动,如同死人一般。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我才重 新睁开了双眼。一看,已是深夜了,大雪纷飞,帽檐 上,穿着大衣的肩膀上,积雪已厚达三公分。 此时,大概已是夜里十一点钟了吧。通往莫哈比 特和卡尔大街的轨道马车的铁轨,已被大雪覆盖,勃 兰登堡大门旁煤气灯发着凄迷孤寂的光芒。我要站起 身来,可双腿早已冻僵,用手搓揉了许久,这才能勉 强行走。 由于两腿不听话,当我踉踉跄跄地走到克洛斯特 时,已经是后半夜了。至于我是如何一路走来的,自 己竟然一无所知。这是一月上旬的夜晚,林登大道上 的酒吧、咖啡馆客人进进出出的,十分热闹,可我却 浑然不觉。我满脑子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我是个 不可饶恕的罪人。 四楼的阁楼上还亮着灯,看来爱丽丝还没有睡觉 。透过昏暗的夜空望去,灯火灿烂,亮若星辰,却又 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中若隐若现,如同风中之烛一 般。进了大门之后,我顿觉疲惫不堪,浑身的关节疼 痛难忍。我爬一般地上了楼梯,穿过厨房,开门进了 房间。爱丽丝正坐在桌前缝尿布,一回头看到我后, 便“啊”地大叫一声。 “你怎么了?瞧你这一身,都成什么样了?” 难怪爱丽丝要大吃一惊了。此刻的我脸色白得跟 死人一样,帽子也不知何时弄丢了,头发蓬乱。由于 一路上不知跌倒了多少次,衣服上满是泥雪,还撕破 了好多处。 我想要回答却又发不出声,两腿瑟瑟发抖,站都 站不住,便伸手去抓椅子—所能记住的就到此为止了 。之后,便一头栽倒在地板上,人事不知了。 等我重新清醒过来,已是几个星期之后的事了。 其间,我高烧不止,满口胡话。爱丽丝则衣不解带, 尽心照料。有**,相泽找来了。于是,他发现了我 隐瞒着的一切。不过,在向大臣汇报时,他只说了我 的病情,其他的事情全都轻描淡写地遮掩过去了。 醒来后,当我**眼看到守在一旁的爱丽丝时, 不由得吓了一跳。她已容貌大变,像是换了一个人似 的。在这几个星期里,她掉了一身肉,瘦得形销骨立 ,布满血丝的眼睛眍着,灰色的脸颊也深深地塌陷了 进去。虽说由于得到了相泽的资助,每天的生计依然 能够维持,但这个恩人已在精神上杀死了她。 我后来才得知,爱丽丝见到相泽时,当她听说了 我对相泽的承诺,以及同意了那天傍晚大臣要我回国 的提议后,就猛地从椅子上蹦了起来,面如土色地大 叫道:“我的丰太郎,你骗得我好苦啊!”随即,便 当场晕倒了。相泽叫来了爱丽丝的母亲,两人一起将 她放到了*上。过了一会儿,她睁开了眼睛,但两眼 直愣愣的,一个人也不认得了。她喊着我的名字大声 咒骂,又揪头发,又撕咬被子。一会儿像是突然清醒 过来似的,慌慌张张地寻找东西。母亲拿东西给她, 可她一件件地全都扔到了地上。而将桌子上的尿布递 给她时,她就摸索着将其按到了脸上,泪如雨下,泣 不成声。 后来,爱丽丝虽然没再闹过,可她的精神已** 崩溃了,其智力也退到了婴儿的程度。经医生检查, 说是因刺激过度而得了一种妄想症,并且毫无治愈的 可能。本想送她去达尔道夫精神病院的,可她又哭又 叫的,就是不肯去。后来,她一直随身带着一块尿布 ,不住地拿出来看,每看一回都会啜泣半天。尽管她 不肯离开我的病*半步,可看样子她也未必真的认得 我。只是会时不时地像是突然想起来似的嚷嚷:“吃 药,吃药。” 我的病已经痊愈了。也不知有多少次,我抱着活 死人般的爱丽丝以泪洗面。 随大臣东归之际,我跟相泽商量后,给爱丽丝的 母亲留下了一笔赡养费,供她们母女俩维持生计,并 拜托她在可怜的疯女人生产时照料一切。 唉!像相泽谦吉这样的好朋友,在这个世界上恐 怕是再也遇不到了吧。可是,在我的内心深处,却至 今对他仍有恨意。 明治二十三年(1**0)一月 P22-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