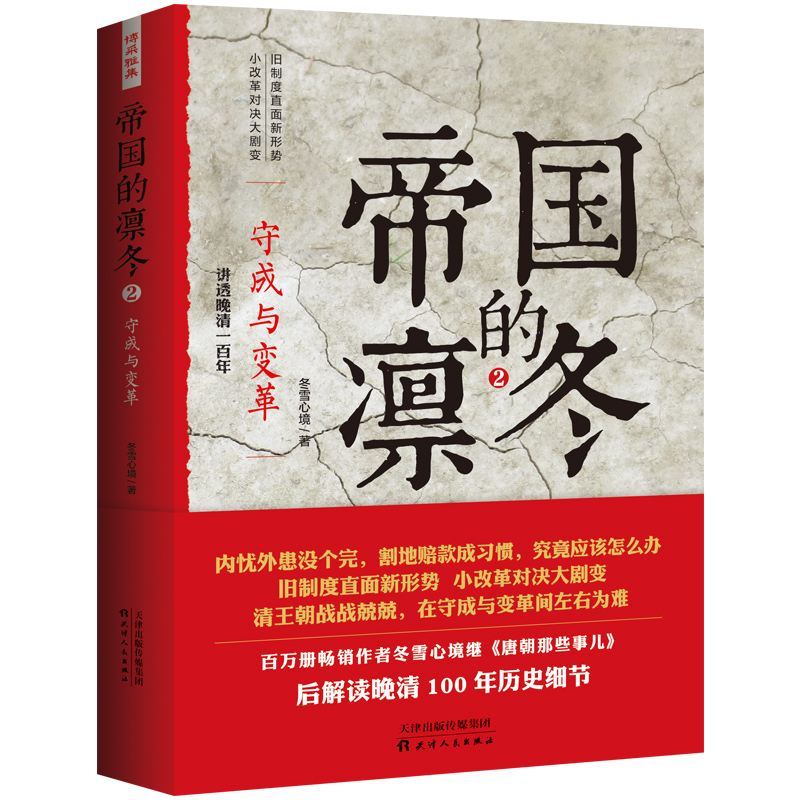
出版社: 天津人民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2.10
折扣购买: 帝国的凛冬(2守成与变革)
ISBN: 97872011500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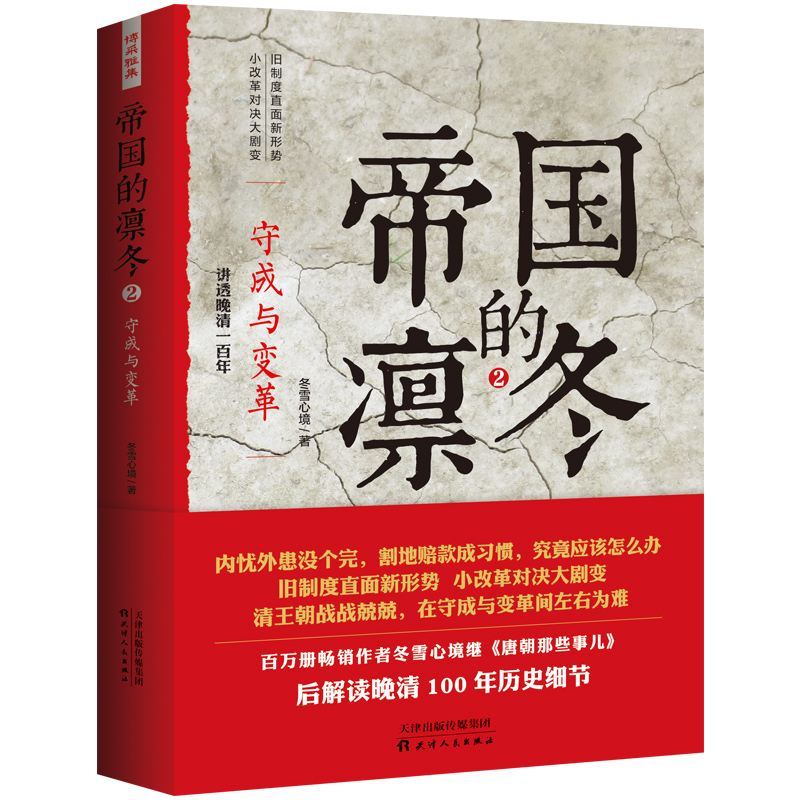
冬雪心境,原名李珩,天津人。现为天津作家协会会员,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十二频道《法律讲堂》文史版栏目主讲人,主讲《大唐第一宰相长孙无忌》《大唐宰相遇刺案》等系列节目。代表作有《唐朝那些事儿》全七册系列,《隋朝那些事儿》全三册系列,《帝国的凛冬》系列《武媚传》等。
1.垂帘听政 公元1861年11月7日,清内阁奉上谕宣布更改新年号,改“祺祥”为“同治”,取两宫太后共同执政之意,四天后宣布转年为同治元年,大清帝国由此进入了一个新时代。这也代表曾经以肃顺为首的八大顾命之臣被彻底从这个王朝的权力中枢清除干净。 新朝伊始,在帝国高层们看来,最先应该确立的是在特殊的政体下权力分配的问题。十月七日(11月9日),内阁奉上谕公布了两宫太后听政,以及处理各项政务和军务的程序: 各直省及各路军营折报应行降旨各件,于呈递两宫太后慈览,发交议政王、军机大臣后,该王、大臣悉心祥议,于当日召见时恭请谕旨,再行缮拟,于次日恭呈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阅定颁发;应行批答各件,该王、大臣查照旧章,敬谨缮拟呈太后,一并于次日发下,其紧要军务事件,仍于递到时立即办理,以昭慎重。 这等于是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重新分配了帝国政务的处理大权,两宫太后掌握审核权和决定权,奕?掌握议政与实施权。 权力分配问题解决后,接下来便是政务处理流程问题。当时翰林院侍讲学士杨秉章、御史林寿图列条陈述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事宜,提交廷臣会议详细阅览,几经修改补充完善,最终由亲王世铎领衔,将两宫太后召见朝臣礼节的一切办事章程,共同呈递两宫太后钦定。十二月二十六日(1862年1月25日),获得批准,懿旨宣布垂帘。 当时,关于垂帘听政章程一共拟定了十三条,其中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三点: 1.召见内外大臣时,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要同坐养心殿,两宫太后垂帘,议政王和御前大臣轮流派一人,将召见人员带领进见。 2.召见地方官员时,两宫太后和同治皇帝同坐养心殿,议政王、御前大臣带领御前,乾清门侍卫要排班站立,两宫太后垂帘设案,然后进呈召见官员名单,并拟谕旨同时注明。同时皇帝面前也要设案,也要进呈皇帝一份名单,其他一切礼仪同上。 3.任免官员时,除了朝廷重臣可以简化手续之外,应该将任免官员名单由议政王和军机大臣共同在接受两宫太后召见时进呈,由两宫太后最终钦定。 我们都知道,程序问题是依据权力分配以及当时的礼法而制定,而今权力分配是由两宫太后与恭亲王奕?所包揽,而礼法问题则是,因为两宫太后是女人,所以必须要“垂帘听政”,这是源于封建社会男女有别、内外有别的社会传统。 太后临朝始于西汉的吕后,唐代武则天也实行过垂帘听政,宋朝英宗皇帝的宣仁皇后也曾经垂帘御殿。大清帝国建立后,此前还没有太后干涉朝政的记录,而且前几代也有顺治和康熙年幼登基的局面,但都是亲王和大臣进行辅政,前者是睿亲王多尔衮,后者是以大臣鳌拜为核心的辅政大臣。咸丰皇帝临死之前本来设置的是八大臣辅政,算是效仿先辈们的做法,但是大清帝国政局却在他死了之后走上了另一条路。我们都明白历史事件是复杂的多面体,不仅有因有果,而且有时还一因多果或一果多因,同治时代出现的太后“垂帘听政”干预朝政,也是这种逻辑的反映。 咸丰皇帝临死之前那封分权的遗诏,是帝国政局转弯的根源。当然,我们不能说咸丰皇帝的做法是错的,但“垂帘辅政兼而有之”,授予太后阅折钤印权本身就为太后干政埋下了伏笔。八大臣也没能很好地遵守咸丰皇帝的遗嘱,没能与两宫太后、恭亲王奕?展开有效的合作,双方为了各自的政治利益,最终只能“兵戎相见”,打破了制衡的局面。 后世有人认为,垂帘听政的另一个诱因是慈禧太后的野心。据说慈安太后早年虽然由皇贵妃进位中宫,但性格软弱,凡事都由慈禧做主。对于这种说法,笔者部分赞同,毕竟此后大清帝国四十余年的实际领导者就是慈禧太后,如果她没有野心,无论如何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但我们同时也应该明白,“垂帘听政”如果扩展来看,绝不仅仅是一种礼法制度,而是一种适合当时帝国政务运转的行政体制。换句话说,至少是各方利益共赢后达成默契的结果。 体制的核心是:集体遵循的方式。如果从这个角度看,慈禧或许有野心,但在当时,她的野心还够不上影响国家体制的改变。 当时虽然定下两宫太后垂帘听政之制,但毕竟帝国先前没有过太后干政的事例,因此当务之急是要寻找相关的理论支持和历史依据。十月十五日(11月16日)谕令内阁将历代帝王政治及垂帘事迹汇总进呈,并且让南书房、上书房、翰林院等选择可以纳入国家法律的部分,汇成一册进呈。后来按照这个底本,编成了一部书,名叫《治平宝鉴》。 十月二十九日(12月1日),朝廷正式宣布两宫太后于十一月一日(12月2日)正式实行垂帘听政,也就是从这一天起,一直到1912年宣统退位为止,大清帝国实际上都是由女人当家。 据《穆宗实录》记载,当时垂帘听政大典举行得十分隆重而庄严,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垂帘,王公以下大学士、六部九卿在养心殿外集体行礼,而且通过时人的评论,也可以想见当时垂帘听政的庄严情景以及严谨威仪。 例如《曾国藩日记》(同治七年十二月十四日)记载他觐见的经过: 入养心殿之东间,皇上向西坐,皇太后在黄缦之内,慈安太后在南,慈禧太后在北。 《翁文恭公日记》(十一月二十四日)记载的随父觐见的过程: 黎明侍大人入内,辰正引见于养心殿,两宫皇太后垂帘,皇上在帘前御榻坐,恭邸立于左,醇邸立于右。吏部堂官递录头笺,恭邸接呈案上。是日引见才二刻许即出。 从上述记载看,垂帘听政的形式,潜移默化地让觐见两宫太后的人有一种莫名的无上的权威感,形式上保证了两个女人的主宰者地位,而且养心殿中垂帘听政的人员设置格局,也充分体现了“听政与议政”的权力分配。当然,对于两宫太后这两个女人而言,又有着不同的分工。 薛福成对垂帘听政有过一番评论: 是当时,天下称东宫优于德,而大诛赏大举措实主之;西宫优于才,而判阅奏章,裁决庶务,及召对时事咨访利弊,悉中窥要。东宫见大臣,讷讷如无语者。每有奏牍,必西宫诵而讲之,或竟日不觉一事。然至军国大计所关,及用人之尤重大者,东宫偶行一事,天下莫不额手称颂……西宫太后性警敏,锐于任事,太后悉以权让之,颓然若无所与者。后西宫亦感其意,凡事必咨而后行。 应该说两个女人各具特点,也各有所短。慈禧太后性格敏锐,善于处理政务;慈安太后由于身份特殊,而且本身德行深厚,因此德高望重。但是薛福成的评论也指出了,慈安太后因为慈禧太后把控政事似乎有些失落,幸好慈禧太后比较敏感,看出了慈安太后的失落,因此一改往日作风,积极与慈安太后相配合。 从薛福成的评论看,在大清帝国开启垂帘听政的最初阶段,两宫太后包括诸多大臣对于这种新兴的体制还有一个熟悉的过程,这里既有程序问题,也有人事配合问题,需要所有人去适应。从两个女人之间的配合也可以看出来,这个新兴的体制还需要不断地打磨。不过至少在那个时间段里,两个女人在处理国家大事的过程中是能互相合作、取长补短的。历史特殊的机遇,将两个女人的身份、地位、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也让经历了祺祥政变的大清帝国,重新找到一条特殊的生存模式,虽然它在不久的将来还会发生裂变。 2.议政重权 在刚刚确立垂帘听政体制的那段时间里,如果说两宫太后是这个体制的金字塔尖,恭亲王奕?就是支撑塔尖的基座。因为奕?在祺祥政变中出力最多,所以除了两宫太后象征最高权力之外,奕?获得了“议政”这项重要的权力。 为了表示对奕?的嘉奖,两宫太后在祺祥政变后特别下懿旨要优礼奕?,准其以亲王世袭罔替。然而,对这样的特殊优待,奕?是坚决辞让,甚至跪在两宫太后面前声泪俱下,认为这么厚重的待遇自己是担待不起的。最后,两宫太后不得已同意奕?的请求,暂时将这件事情搁置。 大清帝国的亲王是有世袭罔替的嘉奖传统的,但政权建立后,也只有当年打江山时的功臣—八个铁帽子王有这个待遇。两宫太后想给予奕?同等待遇,说明对他还是怀揣感恩之情的,因此奕?辞让之后,她们退而求其次,赏食亲王双俸以示优待。 事实上,奕?很清楚自己参与祺祥政变,将两宫太后推到政治前台,虽然立下大功,但真的还没有到可以接受世袭罔替嘉奖的程度。通过肃顺等人的遭遇,奕?或许已经看出,过分拥有权势不是件好事儿,更何况此时的奕?已经掌握了大清帝国的实际权力—要知道在那个时间里,两宫太后拥有的是名义上的最终裁决权,是一种身份地位的荣耀象征,奕?才是朝廷政务的真正决策者。 既然已经是国家的主宰者,奕?完全没有必要去追求世袭罔替的虚荣,后来的事实证明,皇权制度下,一切个人荣誉的承诺都不可靠—奕?虽然小心谨慎,但最终还是无可奈何地也走上了这样一条路。 奕?之所以可以成为这个帝国的实际主宰者,除了在祺祥政变中立下大功之外,还因为他的“北京派”也随他一同成为朝廷的当权派——至少在京师的官员几乎全都拥护他,而且在热河的官员中也有他的亲信,地方官更有不少倾向于他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让他可以在清帝国朝堂呼风唤雨——他的身后,站着西方列强。 后世的很多人认为,当时奕?可以算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代言人。之所以有这种观点,一方面在于咸丰皇帝北逃后,奕?身在北京,与外国的谈判颇有些献媚的感觉,而且奕?本身对洋人有一种莫名的好感,虽然他那时还并不完全清楚西方在各个方面已经领先于中华。 另一方面,大清帝国后来实行洋务运动,奕?确实是助推者。如果站在西方列强的立场,他们也确实要在中国找到一个合适的代言者,或者说在武力之外,找到一个可以帮助他们继续改变中国的助推器。 因此历史就赋予了奕?新的机遇。 早在咸丰皇帝身在热河的时候,西方列强看到帝国的决策者远在热河,而且不能被驯服,但北京的奕?却在接触的过程中,给他们留下了开明的印象,因此一致认为奕?能够成为他们与清政府有效沟通的新桥梁,而且有意打造一个以奕?为核心的,适合列强利益的新朝廷。 当然,在祺祥政变之前,西洋列强也明白奕?虽然算是清政府的全权代表,但真正的决策者咸丰皇帝却被另外一些大臣所包围(以肃顺为核心的八大臣),在咸丰皇帝去世后,这些大臣又坚决让奕?留在北京,不允许他前往热河奔丧。对此,列强们甚至产生想立奕?为皇帝的想法,当时英国驻广州领事罗伯逊就持这样的主张。 即使是那部分比较理性温和的西方人,也对奕?前往热河奔丧表示明确的支持,例如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给外交大臣罗素的信中这样写道: 恭亲王不顾阻挠他应召的各种阴谋终于到了热河。他向太后保证,我们在此并无可怕之处,这方面他对太后回京负完全责任。为了顺从恭亲王的意思,并证明我们是准备帮他把皇帝从那群险恶党徒手里解救出的,我和我的同僚们曾注意防止外国人冒犯皇帝一行入京的行列。 祺祥政变后,列强们对奕?的胜利表现出更大的热情,他们一致认为奕?走到大清帝国政治前台,能够改变清政府这么多年对西方人的“歪曲印象”,消除中国人对洋人的“恐惧”,并能借助奕?的力量,重新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树立起“良好的形象”。 列强的这种观点,充分说明奕?与他们的交情至深,至少在“洋人”们看来是这样,正像普鲁斯说的那样: “在过去的十二个月中,造就了一个倾心于并相信友好交往可能性的派别,有效地帮助这一派人掌权,这是一个非同小可的成就。我们在北京建立了令人满意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这个政府的顾问。” 由此我们可以明显看出,祺祥政变不仅仅是大清帝国内部的权力斗争,在权力斗争之外,同时包含着清政府的路线之争,或者说是对外政策之争。从某种角度而言,祺祥政变的胜利是两宫太后和奕?的胜利,却也是列强的胜利,标志着中外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西方诸国对华政策开始进行大幅调整,清政府对外也不再是一味地仇恨。 只有弄清上述关系,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大清帝国后来会有洋务运动,为什么在后来镇压太平天国的过程中,列强会站到大清帝国的阵营。 事实上,由宫廷政变导致的人事、外交等国家重大政策的变化,历史上不在少数,但彼时世界已经开始进入工业和殖民的时代,从此角度看,祺祥政变是影响中国历史走向的一次宫廷斗争,甚至说是一种观念的变革。 后世很多人认为,西方列强很看重奕?的议政权力,这种看法比较正确。议政是大清帝国形成政权初期的一种政治制度,那时候最高决策者是议政王大臣们,也就是说是一个集体在决策,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位时,任命八个皇子为和硕贝勒共议国政,体现出一种军事民主制度。 皇太极继位后,设八旗总管大臣各一人,与诸贝勒共同参与议政,从而降低了议政王的地位。雍正在位时又设立军机处,最终取代议政王制度。 看清朝“议政制度”的历程,到雍正皇帝废除议政王制度,说明议政王很容易分解皇权,到了恭亲王奕?的时代,没有设立议政处,便说明没有集体决策的考虑,但奕?在实际运作层面却拥有了议政权力,奏批发折子拟用“议政王军机大臣奉旨”字样,说明奕?当时的“议政”权力是朝廷的实权。 但是奕?的精明之处正在于,他知道自己的议政权力并没有制度作为依托,紧紧依靠两宫太后这两棵大树方是长久之计,而不是靠“议政王”这顶帽子来巩固自己的权势,更不用说世袭罔替,仅从这一点,就可看出奕?比肃顺等八大臣要高明很多。 奕?依靠两宫太后能够充分行使他的议政权力,这也才能让他在和西方列强打交道时赢得更多的好感,以及令自身获取更多的政治筹码。从奕?行使议政权力的过程看,他是充分研究了大清帝国建立以来议政制度变迁的。 在奕?拒绝世袭罔替的同一天,他上了一个名为《沥阵微忱请伥臣工于用人行政各抒所见》的奏折,论述了朝廷要想开创新风,必须要广开言路,让大臣们集思广益的重要性。 窃为自古大臣未有不开诚布公,集思广益,而可以任天下事者也。臣以西栋菲材,谊属天潢近胄,蒙皇上仰承母后皇太后、圣母皇太后懿旨委以重任。有可以安国家利社稷者,敢不尽心竭力,一秉公忠,与在廷诸臣认真办理,以期仰慰先帝天之灵,用酬委深恩于万一。然任大责重,且当此中外多事之秋,深恐一时见识偶疏,致滋贻误。臣虽不敢引嫌自避,亦何敢居之不疑?再三思维,唯有吁恳天恩,俯鉴臣受命袛惧之忱,明降谕旨,饬下中外大小臣工,嗣后于朝廷用人行政贤否是非,务当各抒己见,据实胪陈,以求折衷于至当。 这奏折体现了奕?对朝廷行政的建议,也是他对议政制度核心的理解,那就是强调为政要集思广益各抒己见,同时也是借着这份奏折向两宫太后表明态度,自己一定会尽心竭力不负重任。 两宫太后对奕?的想法和表态十分赞同,对他的功劳予以了充分肯定,对其议政地位也予以承认,而且还表示,希望奕?能够放手去干,力争扭转大清帝国二十多年来对外屈辱的局面。 我们都知道,在一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尤其是皇权制度稍显薄弱时,寻求能够支撑朝廷运转的强力大臣其实是一种权宜之计,因为皇权的唯一性决定了时机一旦成熟,它必然会不择手段地收回权力,在此之前甚至不惜充分放权。 但是除了两宫太后给予了奕?以议政大权之外,还有另外两个头衔也能充分体现出他的权势,其中一个是宗人府的宗令。宗人府是掌管皇族事务的机构。在封建社会宗法制度下,是以血缘关系区分家族关系远近的,宗人府的宗令是掌管皇族属籍等事务的,是确保皇族许多特权和待遇的机构,是维持封建宗法统治的权威机构,从这个角度看,这等于给予了奕?皇室族长权。 另一个头衔是总管内务府大臣。内务府是管理宫廷事务的衙门,是清朝直接服务于皇帝及皇族的专门机构。具体负责管理满洲上三旗,即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的全部军政事务,管理宫廷内部的人事、财务、礼仪、护卫、刑法、工程、农林、畜牧、渔猎以及日常生活的一切事务。 总管内务府大臣是内务府的最高长官,具体职责是办理宫内祭祀、朝贺礼仪,护卫后宫群妃出入,总理皇子、公主家务,宫内筳宴设席以及本府官员的考查、任免等,是一个有实权的职务,是皇家宫廷的大总管、当家人。 奕?身兼议政王、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三个职务,等于肩负着行政、军事、财务、皇族事务等大清帝国主要方面的各项权力,对于当时只有二十九岁的他来讲,真可谓是得天独厚,显赫一时。 当然前边我们说过,皇权的唯一性印证奕?这种诸多权力集于一身的情况,只能是一种客观形势的需要,也是客观原因造成了这种现象的存在,在短暂的时间内可以维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奕?必然会成为皇权第一个打击的对象。 夺权、洋务、剿匪、变法……百万册畅销作者冬雪心境继《唐朝那些事儿》后细微解读晚清100年,帝国的凛冬系列重磅作品,手术刀式解剖清王朝那段战战兢兢的变革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