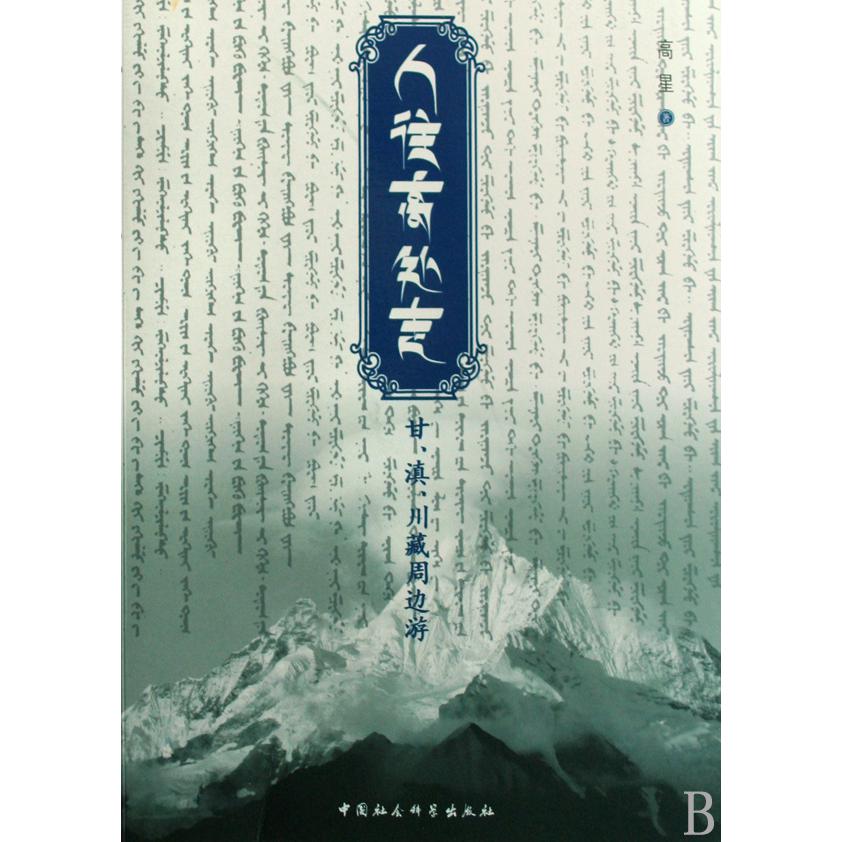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社科
原售价: 51.00
折扣价: 38.20
折扣购买: 人往高处走(甘滇川藏周边游)
ISBN: 97875004745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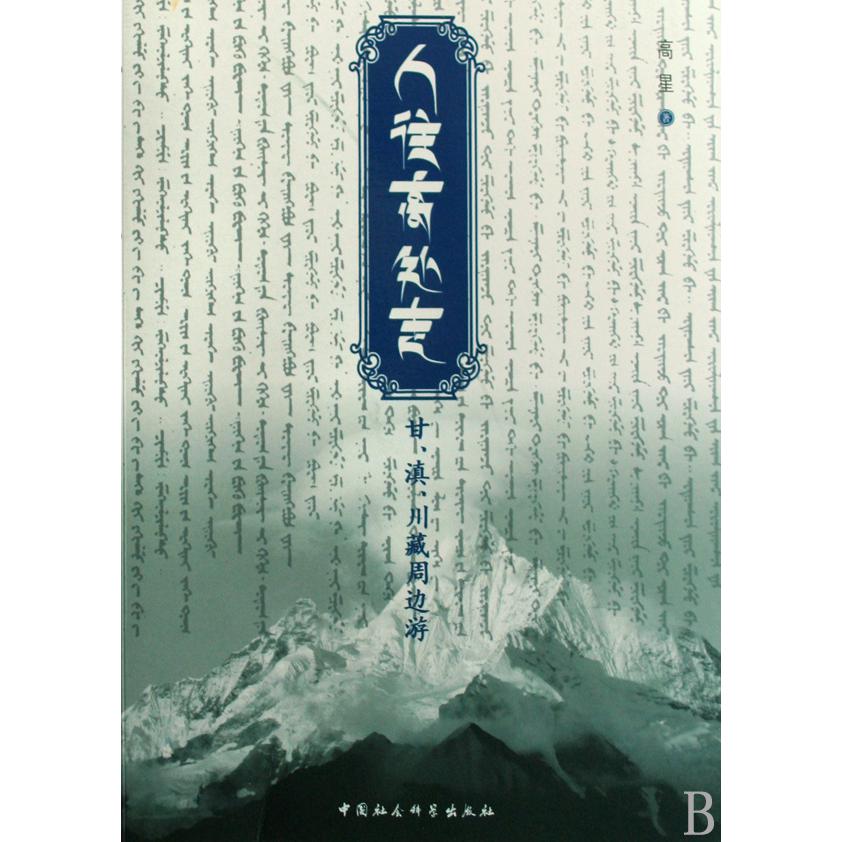
高星,某杂志美术编辑、摄影记者,喜四处游走,有收藏癖好。曾有多种图文书《执命向西》、《向着东南飞》及《中国乡土手工艺》(两部)等出版。
九寨沟的名气太大了。它所在的县原来叫南坪县现已改叫九寨沟县了 ,据说九寨沟就是因为沟里有九个藏族村寨而得名。 而那孔雀河、镜海、熊猫海、五花海、珍珠滩、五彩池、芒苇海、盆 景滩、火花海等导游图上所标的美丽艳俗的地名都是后人开发旅游时所命 名的,与九寨沟的原始风貌并无关系。九寨沟的九个藏族村寨分别是荷叶 寨、故洼寨、盘亚寨、树正寨、热喜寨、黑角寨、则查洼寨、尖盘寨、彭 布寨,而沟内的色莫女神山、达戈男神山、藏海龙里海、扎依扎嘎神山、 扎如马道、丹珠沟等这些并不被游人注意的名称倒是纯正的原始地名。任 何好看的风景都会轻易让人赏心悦目,使人陶醉,但对一片风景的深层挖 掘与理解,却能打动我的心,让风景走入我们的心胸。云可以拂拭我们, 水可以涤荡我们,这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感受,而不是仅仅停留在表面的一 饱眼福。 我一直都喜爱藏族风情民俗,推崇藏传佛教文化,而对雪域高原的风 景来说,总觉得是和藏族人生存分离不开的。它的纯净更像藏人的内心一 样洁净,就像奇丽的九寨风光更像藏族服饰的氆氇一样多姿多彩的惊艳。 据藏文历史古籍《多美宗教源流》记载,吐蕃王朝向东扩展时,由达 布和贡布率领的两个部落的军队驻守在今松潘、南坪、平武一带,没有被 召回,于是他们就世代定居下来,成为“安多”藏族的一部分。“阿坝” 这一地名便是由于当年这里的藏族人习惯称自己是“阿里娃”而形成的。 九寨沟属中羊峒番部,以九寨形成部落。 九寨沟一带的藏族大多信奉苯教,这和西藏地区的主流佛教教派黄教 有所区别。苯教是西藏土著宗教,属象雄时代。当佛教传人西藏之后,与 苯教发生冲突,使藏王赤松德赞不得举行公开考评,结果苯教失败,被迫 退缩到远离卫藏的地区。而九寨沟地处偏僻,并没有发生普遍的宗教改革 ,得以使苯教保留下来,形成了九寨沟地区宗教文化的一大特色,使其更 具原始宗教的风味。 由于时间关系,我只在九寨沟走访了一个村寨,和一座寺院。中午时 分我来到诺日朗北侧的则查洼寨,这个村寨虽距热闹的诺日朗旅游商场和 饭堂中心不远,但它没有一点诺日朗瀑布似的宣泄的涛声,在阳光下,只 有风马旗在风中轻摆,一切都非常沉静。几栋木楼建筑,依山而建,有的 已非常古老,略显破旧,而村后的山坡上,正是向阳的高山牧场,一些牦 牛在金黄色的草坡上慢慢地移动着脚步,而树林的边缘有断断续续的白线 ,那是残留的积雪和化冻的泉水。 路边一家红漆彩绘的大门吸引了我的注意,大门不仅有门楼,而且有 像北京四合院的蛮子门的拥墙及余塞板修饰。门扉画有老虎和豹的图案, 门沿上挂有木板刻印的经书及曼陀罗图案。看来也是一家非常讲究的人家 。进得院来,看见西屋二层的木裙板上画着一排藏传佛教的八宝图案,院 中堆放着一垛建筑材料,两个年轻的汉人向我热情推介屋里可拍的东西, 进得屋里发现屋中半边全是红漆彩柜,靠西的为佛龛,靠南的为生活用的 木柜,屋中有一铁炉,上面烧着奶茶,屋中柱子上也有彩绘。对面的墙上 画有一对白象,这是藏传佛教中的典型图案,可笑的是中间贴有一张谢霆 锋的招贴画及一张三好学生奖状。屋中的两个人正在看电视,并不注意我 在屋里上上下下拍照。后来他们向我介绍说,他们只是临时租住这里,因 为这家房子很多很大,又大多闲空,故引来许多在景区内维修、建筑的工 人在这租房。而这家的祖上一直生活在九寨沟,老人去年刚过世,而年轻 的夫妇在镇上经商,卖点旅游纪念品,挣点小钱。据说家中的老人原在村 寨中很有威望,在一些宗教礼仪活动中担当主持。 我在屋里拍到了许多画有精美图案的藏柜及诵经的佛龛,一般藏族人 家的佛龛是轻易不会让外人拍照的。在桌上有许多铜制的法器和酥油灯, 想必这是老人生前主持佛事的遗物吧。院中有一小白佛塔,上面留有煨火 的痕迹,这在藏族人家中是必不可少的。 这个装饰讲究的偏房,是用于待客和诵经的,正房的位置是一座三层 木楼,二层楼有走廊及平台,是住人的地方,三楼堆放草料和其他杂物, 底层作为牲畜圈棚。而榻板铺盖的流线型房顶,适合九寨沟多雨雪的天气 。这种三层木楼的功能分配适合于九寨沟半农半牧,人畜分居,粮草物资 储存,又有足够的肥料供农业生产使用。 扎如寺位于九寨沟沟口附近,由于游人较少,旅游公司改用小车接送 游客,虽不显眼,但这是一座已有千余年历史的寺庙。目前这座寺庙是崭 新的。它的辉煌是在29世活佛时期。20世纪50年代,南于阿坝藏区发生叛 乱,寺院遭严重破坏,1970年,在“农业学大寨”中又被推倒残墙开垦为 农田,并改造成果木园。1986年集资修复。 寺后有一堵黄土墙是当年老寺的遗迹,绿草旺盛,残墙倾废,与附近 新建的经堂形成强烈的反差。宗教的生命力就是如此,旧的永远依存于自 然景境之中,新的永远被描金涂红装饰得异常辉煌。扎如寺的门扉图案装 饰非常复杂、精细,并且没有重样的,这个现象甚至在西藏地区也不多见 ,町见九寨沟的经济条件还是可以的。寺院中的廊下坐着一位年老的僧人 ,手持一个转经轮,平和安详,似乎时间已与他无关,面对出出进进的游 人,依然故我。也不拒绝我为他拍照。 但让人担心的是开发带来的往往不是保护的原始文化的再现,往往是 一种繁荣之后的更大的丧失。如藏寨变成了宾馆;藏戏变成了卡拉0K及乱 点鸳鸯的粗俗游戏;拜佛成了保佑发财;藏餐成了风味快餐;在一种商业 利益驱动下的藏族文化生态旅游热,带来的往往就是人文景观的仿制品— —圣山吉地泛滥、寺庙泛滥、经幡泛滥、龙单泛滥、哈达泛滥、香格里拉 泛滥等,这是比白色污染更可怕的一种文化异化污染。 在离开九寨沟的路上,路边有许多藏族姑娘招手搭车,她们穿着民族 盛装,并刻意打扮了一番,一位叫桑格基茨的姑娘有幸搭上了我们的车, 这位开放爽朗的姑娘一上车便展开了具有穿透力的歌喉,唱起了藏族民歌 。据说所有这些搭车的姑娘都是如此,已成为一种人文景观,或是旅游节 目。因为她们一般一年到成都或茂县一两趟,就算出远门了,只有搭旅游 客车更方便,便练出了这种搭车的本事,乘客也图一个乐呵,因为所谓男 女对歌,女的赢了,男的就要留下来放牛,这不过像是游戏。桑格基茨被 我们戏称为“三妻”,但大方的她纠正着:这是不可以的,“包二奶”都 不行了,别说“三奶”了。看来她对外面的世界还是很清楚的。当然从她 各种流行的歌声中,从她在车卜很自然地卖起藏族饰品的行为中,我们都 可以看出这一点。其实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藏族妯娘有一天不再穿藏服 ,不再唱藏歌,甚至不再豪放直率,不再脸蛋通红,那才是可怕的。好在 桑格基茨并没有这样,在车过神…时,她从车窗向外面洒了许多甲马,祈 祷我们一路平安。 此时在北京的我,会默默地说上一句:你好!桑格基茨。 P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