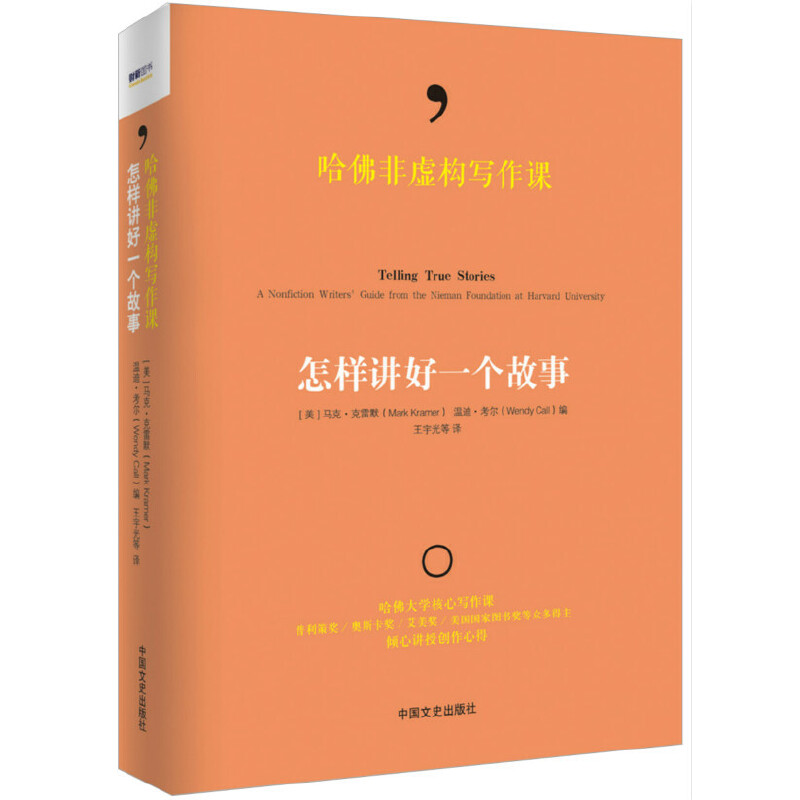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国文史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哈佛非虚构写作课(怎样讲好一个故事)(精)
ISBN: 978750346677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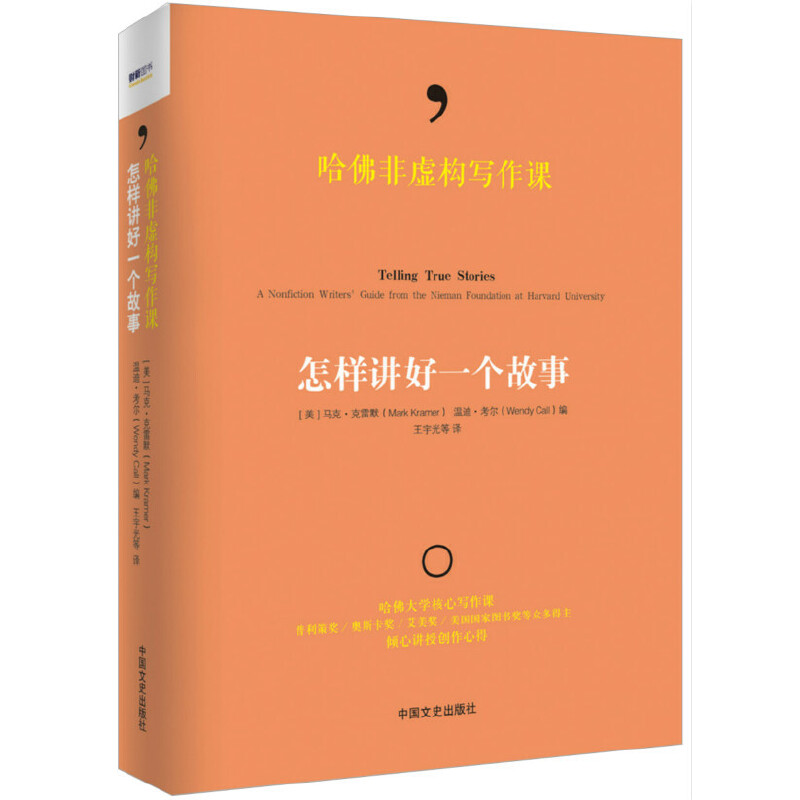
温迪·考尔(Wendy Call),驻西雅图的自由职业作家和编辑。她的叙事非虚构作品发表在六个国家的杂志和文集中。 马克·克雷默(Mark Kramer),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总监和驻留作家。
故事之重 雅基·巴纳金斯基 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动身。目的地,则是苏丹境内 靠近埃塞俄比亚边境的一个饥民营。在此之前,你已 经在电视里看到过那些可怕的画面,看到过那些腹部 肿胀着、受到饥饿折磨的婴儿。在他们的嘴里、眼睛 里,有成群的苍蝇爬进爬出,嫉羡着在那里还坚留不 去的最后一点湿润——那种坚留不去、直到生命逝去 才会消失的湿润。而现在,你已经置身于他们当中。 你是记者,为美国的一家地区性的——中西部靠上一 点——中型日报工作。你的任务,是写这么一个你从 来没到过的地方,一件你完全没有可能去理解的事。 至于你的读者们,他们一辈子也不会到这个地方,他 们也不知道这些事情跟他们有什么关系——也许写上 一张捐款支票除外。 现在,你到这个营地已经有几天的时间了。你每 天都在这里走动,绕过、跨过聚集在这里的10万人。 这些人之所以来到这里,是因为他们听说这里有水。 可是,等他们到达这里的时候,所谓的水,已经变成 只不过是干涸的河道里的一眼泥浆——而他们中的有 些人需要从埃塞俄比亚村庄走上三个星期,才能到达 这个营地。 你看着那个小女孩走到河边,在泥浆里挖动,让 碎布浸吸水分,再一滴一滴地拧到塑料水罐里。你坐 在诊疗处,那里等待就医的队伍,已经排了有上百人 。绝望的父亲们把他们的孩子塞给你,想着既然你是 一个“Khawaja”,一个外国人,你一定是一个医生 。你一定能帮得上他们。可你唯一要抛给他们的,却 是一个早准备好的笔记本和几个问题——这些东西, 突然之间,变得太过渺小。现实,早已经不是那个能 放在这些问题和这个本子里的现实。 你在营区的边界上游荡,来到那个巨大的“排放 区”。那些还足够健康,足够有力气走到这里的人, 会在这里解决他们的自然需求。在这些需求面前,那 一点点微不足道的人类的尊严,变得如此容易被遗忘 。女人们只用自己的裙子做一点遮挡就这么蹲下来, 她们的脸蒙着头巾。用这种方法,她们努力营造出某 种意义上的隐蔽所。 你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到石头多过土的山边,在 那里,男人们一群一群地刨着坚硬的地面,挖出深度 合适的坑,轻柔地安放着那些被寿布包裹着的身体。 这些坑确实不用很深,因为被埋葬的人都非常瘦。他 们每天都要埋葬75个人,有时候更多。多数都是婴儿 。 到了晚上,你退回到那些将这可怕的世界封闭起 来的草墙的后面。你瘫倒在一个小茅棚的吊床上面, 羞愧于你那小小的、短暂的饥饿,以及你那自私的恐 惧。你感激着这黑夜,因为这样你就可以有几个小时 的时间让眼睛什么也看不到,但是你的耳朵却仍然无 法停止去听。你听到咳嗽的声音、呕吐的声音、抽泣 和痛哭的声音。你听见嘶喊、生命愤怒的爆发,又有 75个人死去,你听见了那种咬牙切齿,又听着它“吱 呀”着直到沉寂。 然后你就又听到了另外一些东西:歌声。你听到 甜美的吟唱和深深的律动。每个晚上,一遍又一遍, 几乎总是在同一时间开始。你想你大概是产生了幻觉 。你怀疑你自己是不是因为恐惧而变得太不正常。人 在面对这种惨状的时候,怎么还能唱得出来?还有, 这歌唱又是为了什么?你躺在黑暗中,你在黑暗中怀 疑,直到睡眠仁慈地向你宣称它对你的占有。天光再 现,然后你睁开了你的眼睛。 我是1985年到的非洲,为《圣保罗先锋报》 (St. Paul Pioneer Press)报道埃塞俄比亚的饥 荒。在此之前,我从未踏足过北美之外的地区。 这歌声让我无法舍弃。我花了几天的时间,才弄 清它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了搞清楚这件事,我不得不 找了一个又一个翻译,直到最后,有一个人告诉我, 这是在讲故事。当埃塞俄比亚以及现在的厄立特里亚 (Eritrea)的村庄终于变得无法生存,因为干旱和 轰炸,他们会一起动身、成群结队,步行来到饥民营 。然后他们定居下来,住在他们能找到的不管多小的 棚舍里,按村落居住。只要可能,他们就会继续他们 的仪式。而其中的一个仪式,就是在晚间讲故事。老 人们会让小孩子们围拢过来,然后那歌声就响了起来 。 这实际上是他们的学校。就是以这种方式,他们 把他们的历史、文化和律法背负起来与他们同行。而 这,也可能是我第一次清醒地意识到:讲故事,作为 一种人类的活动方式,不仅强大,而且历史深远,也 不仅限于某个民族或者某种文化。确实,我们的童年 都曾有故事伴随,我们都是在故事中长大成人,但是 ,我们可曾暂停脚步,想一想这些故事如何与我们深 深相连,想一想它们到底具有怎样的力量? 哪怕是面对死亡,或者应该说,尤其是当死神降 临时,这些故事依然存活下去,从年长者传给年轻人 ,从上一代传给下一代。他们对待这些故事一如对待 那些珍贵的水罐,小心翼翼,唯恐破碎。事起事落, 人活人死,沧海桑田。但是故事却一直绵延不绝。 蒂姆·欧布里安(Tim O’Brien)写过一本《负 荷》(The Things They Carried)。苏丹之旅后, 几年过去,我偶然发现了这本书,而这本书也变成我 最喜欢的著作之一。在书里面他是这么写的:“因为 过去要进入未来,所以有了故事。因为在深夜里,你 会想不起你是怎么从原来走到现在的,所以有了故事 。当记忆被抹去,当你除了故事就再无任何可以去记 忆、可以被记住的东西的时候,因为要有永恒,所以 有了故事。” 托马斯·亚历克斯·蒂松 曾经和我在《西雅图 时报》(Seattle Times)共事过。我也问过他这个 问题:为什么人类需要故事。而他是这么回答的: 感谢上帝,世界上有故事。感谢上帝,有人有故 事可讲,有人讲出了故事,有人咀嚼这些故事,一如 这是他们灵魂的食粮——而故事确实就是灵魂的食粮 。故事让我们的经验成形,让我们得以不至于瞎着眼 走过人生的旅途。没有故事,所有发生了的事情都会 四处飘散,彼此之间毫无差别,没有任何东西会有任 何意义。但是,一旦你对发生了的事情有了某种故事 ,所有其他跟人之为人有关系的好东西,也就会出现 :你会笑,会敬畏,会充满激情地去行动,会被激怒 ,会想去让什么东西改变。 我的朋友兼同行凯瑟琳·蓝菲(Katherine Lanpher),她曾经为《先锋报》(Pioneer Press )写过,现在任职于美国广播公司(Air America) 。关于故事,她是这么跟我说的: 故事是人类共同拥有的联结体,不管你是去分析 教育税还是韩国政治。而在每件事的心脏处,都是一 个独属人类的元素,一个能通向世界上最美的三个字 的元素。那就是:“然后呢?”如果你回答这个问题 ,那你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 人们经常说,是语言让我们成为人。这个说法, 现在已经受到挑战,因为我们发现猿也有语言,鲸鱼 也有语言。我欢迎它们,欢迎加入我们这一族。而我 之所以不会因此而感到威胁,老实说,是因为我觉得 让我们成为人的是故事。而只有把故事一直讲下去, 我们才能保持自己为人。 故事,是我们的祷语。写故事、整理故事都需有 敬意,哪怕这故事自己桀骜不驯。 故事,是寓意之言。要带着意义去写故事、整理 故事,讲出属于你自己的故事。只有这样,每一个传 说才能超越它本身的边界,承载某种更大、更重要的 消息,每个故事才能成为我们的集体旅程中的路标。 故事,是历史。写故事、整理故事、讲你自己的 故事,要准确,要带着你自己的理解,要清楚地给出 语境,还有,要有对真相与真理的毫不动摇的献身精 神。 故事,是音乐。写故事、整理故事、讲你自己的 故事,要讲究快慢、律动和流向。如果这是舞步,你 可以加上起落转折让它们更激动人心,但不要因此错 乱了核心的节拍。读者是用他们心灵之耳朵去听的。 故事,是我们的灵魂。写故事、整理故事、讲你 自己的故事,需要带上你全部的自己。对于一个故事 来说,你要这样去讲它,犹如世间万物非于此则无存 其重。同时,对于讲述故事而言,所有的讲述也就重 在这里:你要如此去讲,犹如世间唯故事独存。P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