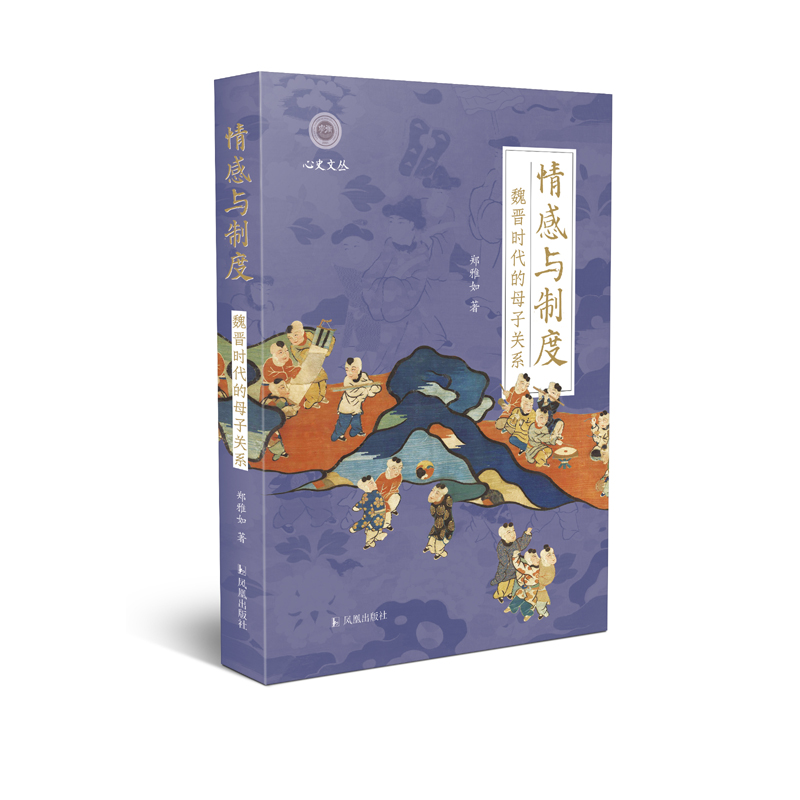
出版社: 凤凰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20
折扣购买: 情感与制度:魏晋时代的母子关系
ISBN: 978755063419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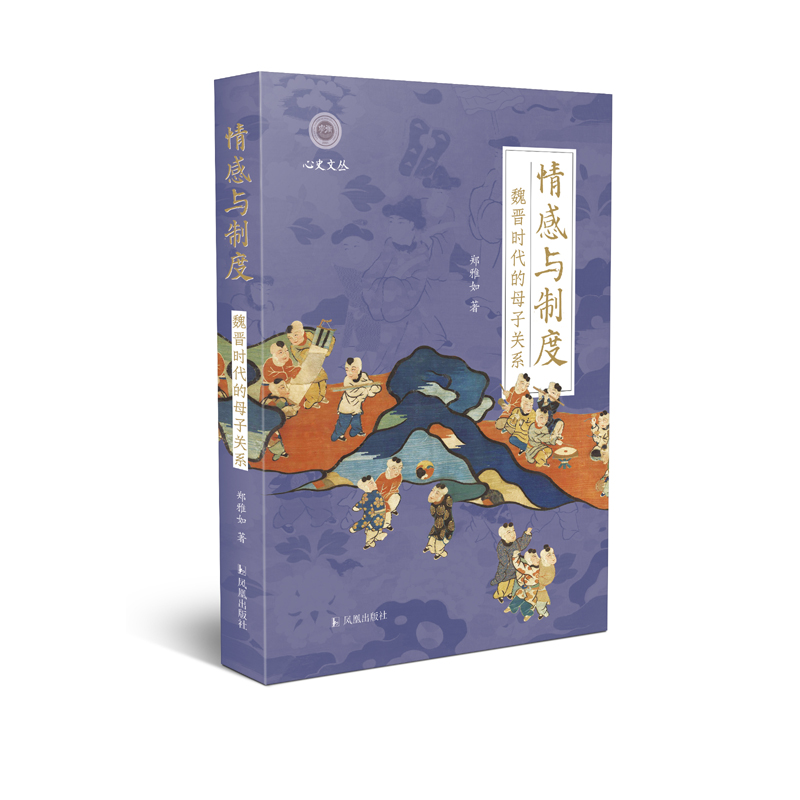
郑雅如,女。中国中古女性史专家,台湾大学历史学博士,师从李贞德女士。现任职于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在表文中于氏除了自述 陈情缘由,并针对贺率的 身份是“为人后”的说法,“ 备论其所不解六条,其所 疑十事”进行反驳,从自己 担任母亲之职、养育贺率 的经验出发,认为贺率应 该是自己的儿子。朝廷将 于氏所陈,交付群臣讨论 。四位发表意见的朝臣, 只有博士杜瑗站在同情于 氏的立场,认为养育之情 不可抹杀,贺率应为于氏 之子;其余以尚书张闿为 首的朝臣,皆从父系继嗣 制度的角度评论此事,认 为于氏养贺率是为贺乔之 后嗣,贺乔既有亲生血胤 ,则贺率当还本,即主张 以贺乔为主体来判定亲属 关系,完全忽视于氏为母 的经验事实。最后,事件 依旧以贺率归还本生定案 。 于氏上表的经过与内容 ,在现存史料中,仅见于 《通典·礼典》,杜佑辑录 这篇上表以及时人的议论 ,题名为“养兄弟子为后后 自生子议”。由此可见,后 世男性史家对这个母亲争 取养子为己子的事件,是 站在父系继嗣制度的立场 拍板定案。于氏力辩“养率 以为己子,非所谓人后也” ,以女性自己为母的经验 来认定母子关系,逸出了 父系继嗣制度的规范,而 被制度的维护者斥责“博引 非类之物为喻”, 见尚书张闿议,《通典 》卷六九《礼典二十九》“ 养兄弟子为后后自生子议” 条,页1913。凸显了在女 性经验与父系制度冲突的 情况下,女性的情感与经 验受到严重的忽视、扭曲 。从东晋至现代,一千六 百多年来,于氏与贺率的 关系,一直以于氏最不愿 接受的角度被后人诠释。 在二十一世纪的今日,我 们是否已有“能力”,从于氏 的角度理解她的声嘶力辩 ?女性“无子”的文化压力是 否依然存在?社会对母职 的看法是否依然充满父权 观念?值得我们深思。 于氏的表文中,一共出 现了四位母亲,依出现的 先后次序,分别是于氏( 贺辉、贺率的养母,贺纂 的嫡母)、薄氏(贺群、 贺乔兄弟的母亲)、陶氏 (贺辉、贺率的生母)、 张氏(贺纂的生母)。从 故事所见,这四位母亲在 同一家族中的地位和处境 显然很不一样。 在于氏的表文中,我们 看到贺群、贺乔的母亲薄 氏作为母亲所享有的威严 和权力,其地位俨然如贺 家的女家长,在许多家族 事务的决策上,拥有最高 的决定权。于氏无子不孕 ,承受庞大的家族压力; 养育贺率为子,又因为无 法在父系继嗣制度中找到 依据,而终不被承认;但 于氏身为贺乔的妻子,又 得以依据礼法自动拥有母 亲身份,成为贺纂的嫡母 。于氏与贺率母子关系的 解除,于氏与贺纂母子关 系的成立,在父系制度下 ,皆不是于氏所能自主。 贺辉、贺率的生母陶氏, 在丈夫做主的情况下,被 迫连续与所生二子割断亲 恩,扮演宛如生育工具的 角色;夫亡后,陶氏终究 又依恃父系家族的礼法夺 回亲子。贺纂的生母张氏 ,为妾的身份低贱,在家 内必须敬事嫡妻,但由于 于氏无子,贺纂成为贺乔 的嗣子,继承门户,张氏 有可能母以子贵,提高在 家内的地位。这四位母亲 中,陶氏为贺率的生母, 于氏为贺率的养母,一生 一养,两人皆自认是贺率 的母亲,彼此有争夺贺率 为子的冲突。对于于氏、 陶氏两人的母职经验,有 必要更详细地讨论。 P3-4 父权社会的人伦悲剧,三个母亲的生育困境。母子亲情被反复剥夺,“父至尊”与“母至亲”的艰难抉择。一本史语所中古女性史的经典著作,揭示父系家族传承的血泪真相。李志生、胡阿祥、仇鹿鸣、徐冲等专家学者倾情推荐,让历史告诉你,女性的未来应通往何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