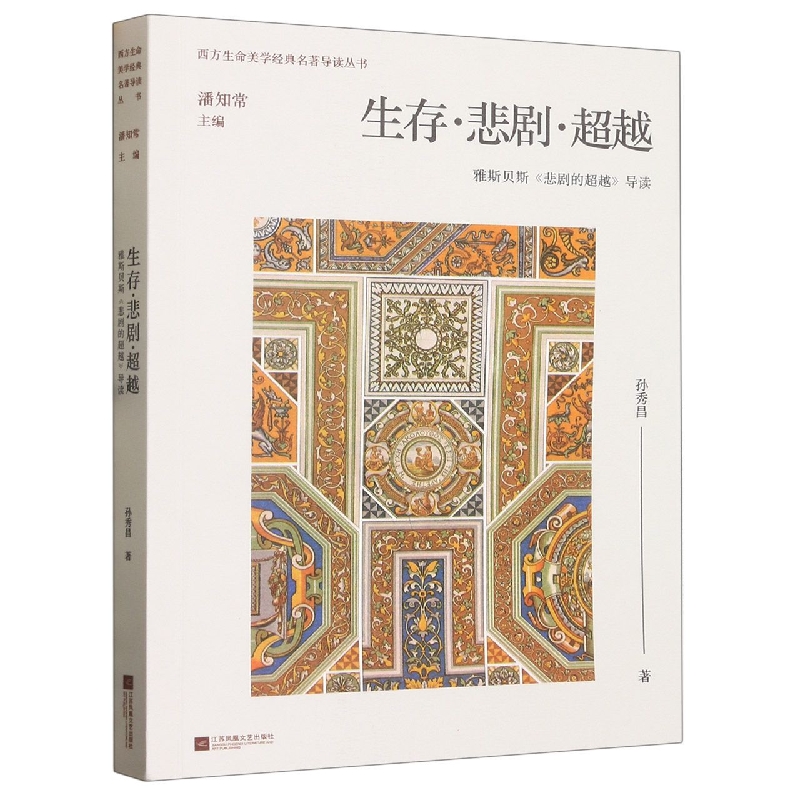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45.00
折扣价: 27.00
折扣购买: 生存悲剧超越(亚斯贝斯悲剧的超越导读)/西方生命美学经典名著导读丛书
ISBN: 97875594719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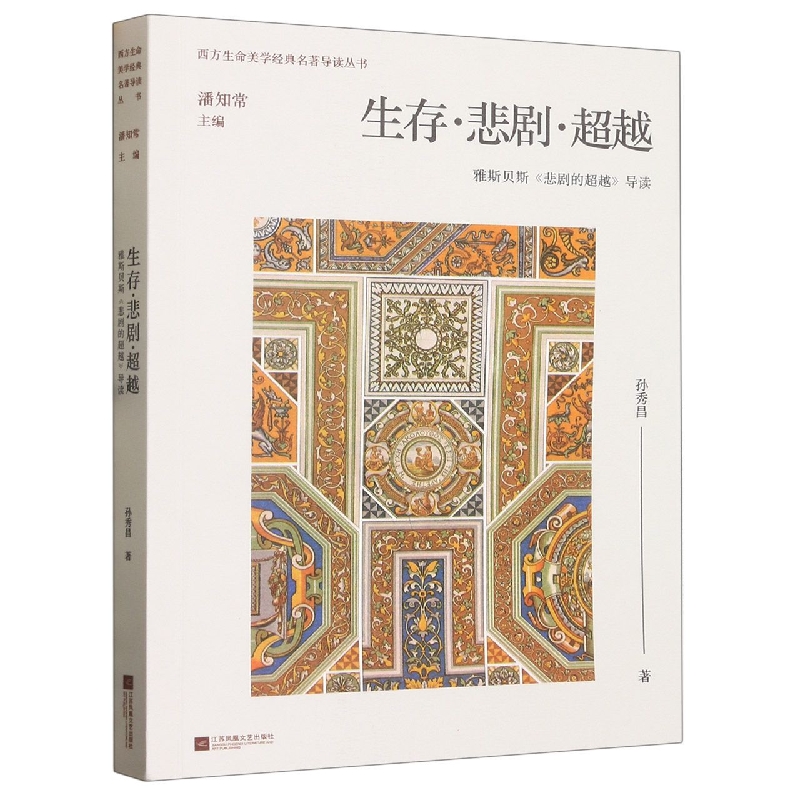
孙秀昌,中国人民大学文学博士,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存在主义美学、先秦美学思想史研究。出版学术专著《生存·密码·超越——祈向超越之维的雅斯贝斯生存美学》《问道于孔子》,以及译著《斯特林堡与凡·高》,编著《公孙龙子文献撮要》等,在《哲学研究》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绪论 雅斯贝斯与其悲剧论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给后世留下了一部论悲剧的文字——《悲剧的超越》。在详细解读这部著作之前,我们有必要厘清三个问题:其一,悲剧论与时代意识,意在揭示雅氏论悲剧的衷曲所在;其二,悲剧论与生存形而上学,意在阐析雅氏的悲剧论与其全部学说的内在关联;其三,悲剧论与真理论,意在说明这部节选自雅氏《论真理:哲学的逻辑(第一卷)》(1947年初版,简称《论真理》)一书的文字在其真理论中的位置,进而介绍其悲剧论的运思理路以及译本等情况。 一、悲剧论与时代意识 雅斯贝斯是一位秉具清醒的“时代意识”的哲学家。早在1931年出版的《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他就对“时代意识的起源”问题作过深入的探讨。在雅氏看来,“人对于自己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批判,与人的自我意识一同发生”。所谓“自我意识”,乃意指人的“生存意识”。作为自由选择、自我超越、运命自承的生存个体,“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己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基于这种考虑,雅氏始终对其亲在其中的时代精神处境有着真切的体验、敏锐的洞察和深刻的批判,他的著作在某种意义上可视为其对时代精神处境给出的诊断报告与疗救之方。就雅氏的悲剧论而言,他的“时代意识”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悲剧意识”与纳粹暴政之批判,二是“大众神话”之批判,三是“审美冷淡”之批判。 (一)“悲剧意识”与纳粹暴政之批判 雅斯贝斯的“时代意识”在《悲剧的超越》中具体体现为“悲剧意识”(awareness of the tragic,tragic consciousness),这从该书第一章的标题“悲剧意识”中便可见得出来。雅氏认为,“悲剧意识”是悲剧的灵魂并为悲剧奠定了基调。由富有生存论意义的“悲剧意识”来作考察,悲剧当然要表现困厄与灾难、失败与痛苦,但仅仅表现人的失败状况与痛苦意识的作品只能称作“泛悲剧”(“唯悲剧”“绝对悲剧”);相较之下,真正的悲剧乃是“对人显示于崩溃与颓败之中的伟大的量度”,也就是说,悲剧的旨趣在于将个体置于某种灵魂无可告慰的难堪处境下进而逼显出人的伟大来,就此而言,悲剧所展呈的困厄与灾难、失败与痛苦恰恰成为生存个体祈向“超越存在”(“整全的真理”)进而见证人的伟大的一个必要的环节与契机。 基于上述看法,雅氏批判了“泛悲剧主义”的悲剧观,认为那种仅仅表现人的失败状况与痛苦意识的“唯悲剧”(或“伪悲剧”)美化了个体所罹遭的痛苦,从中流露出一种妄自尊大、冷酷无情的情感基调,最终使悲剧沦为“极少数显赫人物的专利”。雅氏就此指出:“悲剧成了极少数显赫人物的专利——其他所有的人都必须满足于在灾难之中麻木不仁地归于溃败。于是,悲剧不再是全体人类的特征,而成为人类贵族政治的特权。作为特权的标志,这种世界观变得妄自尊大、冷酷无情,它通过迎合我们的虚假的自尊来骗慰我们。”这里所谓的“极少数显赫人物”,乃意指以炫示恐怖与残忍的非人乐趣为能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这类的人物看似具有某种超出常人的强力意志,事实上只是比常人更加傲慢自大、冷酷无情、狂热冲动而已;他们热衷于实体化信仰与偶像崇拜,然其根底处却透显出虚无主义与民粹主义的基调;更为糟糕的是,廉价的个人英雄主义极具煽动性与欺骗性,它善于通过迎合大众的“虚假的自尊”来骗慰人们,一旦大众在其魅惑之下将某个“显赫人物”(如希特勒式的独裁者)推到历史的前台,人间的惨剧也就同时上演了。历史一再证明,个人英雄主义与独裁特权的结合,乃是人类所遭遇的最坏的政治处境。鉴于此,雅斯贝斯把他那深邃的理论批判直指纳粹暴政期间发生了癌变的“人类寡头政治”与“实存”所面临的整体沉沦。 可以说,对纳粹暴政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犯下的罄竹难书的罪行的批判,正是雅氏在《论真理》一书中专门探讨悲剧问题的现实契机。在纳粹暴政期间,雅氏痛切感受到了独裁主义者的狂傲与残酷,希特勒之流以人间“上帝”的名义颁布着“真理”,唆使纳粹党徒对犹太人进行丧心病狂的集体屠杀,雅氏也因其夫人格特鲁德系犹太人而备受迫害,为了维护做人的尊严,他们二人甚至做好了一起自杀的准备。在这种难堪的处境下,悲剧与解救对雅氏来说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现实课题。雅氏在其《哲学自传》(Philosophische Autobiographie,1957年)中坦陈了这段痛苦的经历:“这部著者逐渐完整起来正是在我们经受最大痛苦的年代,正处于国社党统治和战争时期。我们不得不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这个国家看作一个罪恶的国家加以否定,而且甚至盼望它不惜任何代价地被毁灭。在这种时刻,我们在解决这个十分抽象的超脱世界的课题中感到了平静。在这些苦难的年代中,我们没有和所有德国人分担苦难,像我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但我们把被德国所迫害、折磨、屠杀的人作为我们真正的同患难者而分担苦难;在那样的年代里,哲学逻辑方面的著作是提出自己主张的一种形式。……我们被包围在强迫忍受和恐怖袭击的环境的封闭的静默中。我们几乎没有想到读者。我们为自己而写——除非能侥幸活到与我们的老朋友们重聚的时候。”这部著作委实是雅氏直面人生的苦难“提出自己主张的一种形式”,他把沉郁的愤懑化作理性的探讨,进而以一位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良知追问着真理问题、悲剧问题以及生存个体如何摆脱时代精神困境的途径。雅氏说自己在写这部书时“几乎没有想到读者”显然是发自肺腑的,这一方面出自他的学术自觉(“为自己而写”),一方面迫于当时的情境(当时的大众已被崇尚强力与强权的个人英雄主义氛围所笼罩,“读者们”纷纷跑掉了或哑默了);不过,若悉心探察的话,雅氏其实依然有其期待中的“读者”。多伊奇(Karl W.Deutsch)在《悲剧的超越》“英译本序”中就曾指出了这一点:“雅斯贝尔斯本人对于洞察力和同情心的关注,远胜于愤懑。作为一个心理学家和哲学家,虽然他并不怕作出判断、评价,但他更寻求理解。1933年以来,在德国和德国青年身上所发生的悲剧,有很多需要理解和同情之处:信守的盟誓、破灭的希望、英雄主义、痛苦和成千上万民众的忍耐——所有这一切都注定要归于崩溃、幻灭和失败。正是为了这幻灭的一代、失败的一代,雅斯贝尔斯才进行有关悲剧问题的著述。出自既是他们的又是他自己的悲剧经验而写作,作为一个伟大国家征服‘大业’的破产的见证人而写作,雅斯贝尔斯已经阐述了悲剧——关于悲剧的实质与意义——为世上所有的人们。”人之为人当有的同情心,足可使有着共同的悲剧体验的个体之间在灵府深处产生精神的共鸣——即便在濒临绝境之际,雅氏仍为自己留住了这一丝不至于绝望的希望;进而言之,他期待着悲剧所带来的“临界”体验能够唤醒读者们自由选择、彼此沟通、自我担待的“生存意识”。 (二)“大众神话”之批判 雅斯贝斯的“时代意识”还突出表现在他对“大众神话”的批判上。我们发现,自希特勒操控的纳粹党于1933年通过“国会纵火案”施行独裁统治以来,雅氏就在追问着这样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究竟是谁把这个狂热冲动、骄横狭隘、不负责任的民粹主义者与独裁主义者推到历史前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次年(1946年),雅氏在《罪责问题》一书中彻底反省了纳粹统治期间国家行动的罪责问题。“在他的著作《罪责问题》(Die Schuldfrage)里,他告诉他的同胞,他们无法推卸对纳粹政府的所作所为所担负的责任,因为大部分人都没有反抗,不少人甚至还在许多方面支持它。他说,也许在其他国家,政府和人民也应该对这场大灾难担负责任,然而,指责他人的过失并不能免除掉德国人民自己的罪愆——这罪愆需要完全的忠诚和长久、艰辛而彻底的内在更新方能革除”。对纳粹暴政所导演的人间悲剧,希特勒及其党徒须负直接责任与主要责任,这是不言而喻的,不过人们的反省若到此为止,仍无法避免此类悲剧的再次发生。基于这种考虑,雅氏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了滋生纳粹暴政的土壤——“大众神话”。 在雅氏看来,“大众”(mass man,亦译为“群众”)是一群被技术理性所模塑的功能性的人、功利化的人、无个性的人。正是这样一群自私自利、圆滑短视、消极被动的人,维系着现代社会机器的运转,进而成为大众秩序制造的又一个神话;也正是这样一群平庸懦弱、狭隘冲动、缺少理性判断与责任意识的人,在希特勒之流的煽动与唆使下,成为纳粹暴政的旁观者乃至参与者。雅氏在其《哲学自传》中对此作过深刻的揭示:“1933年后,未曾料想到的事情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人的能力用之于残忍的行为,智力上的天赋施之于欺骗,貌似善良的公民背信弃义,看来老实的人险恶狠毒,群众丧失头脑,自私自利、目光短浅、消极被动,这一切在现实中已成为事实,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的认识不得不经历一个大的变化。简单地说,过去甚至想都没有想到的事现在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现实的。历史像是经受了一次严重的冲击。但是如果再从世界历史的整体来考虑,就可以清楚地认识到:这些不可能的事在它们的根源上完全不是新的,它们只是得到了(特殊的)表现而已;虽然我们的理智已自觉到一定的程度,但时代的偏见使我们的目光模糊了。”雅氏在此反省的对象主要是德国“大众”(“群众”)的责任,这些大众因其“丧失头脑,自私自利、目光短浅、消极被动”,在事实上纵容了纳粹的暴行,甚至沦为纳粹暴政的帮凶。雅氏之所以说“这些不可能的事在它们的根源上完全不是新的”,乃是基于其清醒的时代意识与生存哲学立场对“大众神话”做出的理性批判。 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一书中,雅氏对“生活秩序的界限”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涉及“技术和机器成为群众生活的决定因素”“群众统治”“技术性的群众秩序与人的生活之间的张力”“对群众的崇拜”等问题。雅氏认为,在由技术和机器决定的大众社会里,大众秩序正以一种无名的力量构成不无霸权色彩的日常意识形态,而技术理性也正借着大众的名义在暗中操纵着这种“始终有着非精神和无人性的倾向”的大众秩序。雅氏就此指出,大众“是无信仰的迷信。它可以踏平一切。它不愿意容忍独立与卓越,而是倾向于迫使人们成为像蚂蚁一样的自动机”。于是,当大众秩序这一巨大机器得到巩固时,它便以虚构出来的所谓普遍利益、抽象整体及大众需要等名义消弭掉个体对本真自我的追求与对存在本身的探寻。丧失了生存之根的人“就是这样地被抛入了漂流不定的状态之中,失去了对于连接过去与未来的历史延续性的一切感觉,人不能保持其为人。这种生活秩序的普遍化将导致这样的后果,即,把现实世界中的现实的人的生活变成单纯的履行功能”。这些迷失本真自我的大众“看来是以享乐为目标的,而只在皮鞭的威吓下或在渴求面包或渴求更好的食品的驱动下才去工作”。大众社会许诺给人们愈来愈多的“面包”,但同时也在晃动着它那似乎带着关爱之情的“皮鞭”。在大众秩序笼罩下,一个人要想实现个体的自我意志,就必须同时满足多数人的需要;要想获取个人的权利,就必须同时为大众机器服务并不得不联合其他个体来维护它。由此看来,功能化的大众在利欲的熏炙下最易沦为满足自我欲望的工具,而这也正是单向度的大众统治所需要的。或者说,大众机器通过滋生、纵容与利用大众的欲望维持了大众机器的自动运转。这样一来,“群众秩序形成了一种普遍的生活机器,这机器对于真正人的生活的世界是一种毁灭性的威胁”。鉴于此,雅氏特意警告世人:“‘群众’这个词愚弄了我们,就是说,我们会被它误引到以数量的范畴来思考人类的方向上去:好像人类就是一个单一的无名整体。但是,群众在任何可能的定义上都不可能是那使人如其所是的本质的承荷者。……诉诸群众概念,是一种诡辩的手段,为的是维护空洞虚夸的事业,躲避自我,逃脱责任,以及放弃趋向真正的人的存在的努力。”“大众”其实是把囿于世界之中的“本能的我”(自我保存意志)偶像化成了上帝。技术迷信、个人崇拜、民粹主义等,追根究底,均与这种“大众神话”有关。可以说,正是这种“大众神话”最终为希特勒之流(恶魔般的政治明星)的自我“造神”运动及其犯下的“平庸的恶”(阿伦特语)提供了温床。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雅氏对“大众神话”及其“平庸的恶”的批判,并不是出自社会学意义上的所谓“贵族化”立场,毋宁说,这是作为哲学家的雅斯贝斯代表德国公共知识分子对日趋大众化、平庸化的思想界所作的理性审查与自我反省。雅氏发现,伴随富有理性传统的“德国精神”的不断衰落,德国思想界的格局变得越来越促狭、越来越独断,1933年纳粹终于在狂热的国家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怂恿下窃据德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一浪高过一浪的反犹主义思潮最终演变成了一场世界性的灾难,这场惨绝人寰的灾难也彻底终结了德国精神的时代。雅氏在其《哲学自传》中记述了自己对这场现实人生悲剧的反思以及对“什么是德国人”“谁是德国人”“什么是德国精神”等问题的理解:“对于包括我在内的少数人来说,在德国发生的事件意味着德国的终结。这从1933年起是可能的,而从1939年起则是确定无疑的。”在纳粹暴政期间,当多数人(包括不少所谓的“知识分子”)在强权的诱迫下出卖德国人的灵魂时,“什么是德国人”“谁是德国人”就成了问题。“1933年,我的妻子由于是一个德国犹太人而被德国所出卖,当她拒绝了她爱得或许比我更深的德国时,为了使她重新肯定德国,我明确而骄傲地回答说:就把我看作是德国”。“德国人”从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只在精神高卓的个体(如莱辛、康德、歌德、雅斯贝斯等)身上得以呈现。一个人即是“德国人”,这是雅氏哲学所内贯的生存逻辑。以个体的生命格范标示着人类精神高度的“这一个人”,他并不会囿于世界之中的任何一种“合法”的规定,而只把生存的目光投向内心祈向中的“世界公民”。雅氏坦言:“当我详细讲述这些思想时,我同时又从内心感到驱使我向往世界公民的动力在增强。首先作为一个人,然后在这个背景下才属于一个国家,我觉得这是最根本的。”可以说,正是这一出自理性精神的“世界公民”理念,使得雅氏敢于以哲学式的反抗主动承担起对自由的责任。他多次放弃去国“避难”的机会,最终选择留在这个已丧失道德根基的国家与每一个德国人一起承受人性的灾难,并难能可贵地“从来没有说过一句可能被理解为支持政府的话”;也正是期许于“世界公民”的理念,他在二战结束之后深刻反省了德国人的罪责问题。雅氏在一次公开表达对希特勒国家的看法时谈到:“当我们的犹太朋友被押遣走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上街示威,也没有大声呐喊。我们没有这样做,哪怕自己也遭杀害。相反,我们苟且地活着,其理由尽管是正当的,但却是那样的软弱无力,这个理由便是:我们的死亡无济于事。我们仍然活着,这就是罪过。”可以说,这既是雅氏在代表着德国人承担德国的罪责,也是他在代表着人类承担人类的罪责。 在《悲剧的超越》中,雅氏设专节探讨了“罪”的问题”,其隐衷仍在于追究缺乏责任意识的“大众”的责任,以便唤醒他们自主决断、自我超越、自我担待的生存意识。此外,在阐析“悲剧的基本诠释”时,雅氏对“唯悲剧”乃至“伪悲剧”之类的悲剧观进行了批判,从时代意识的角度看,这种批判便是雅氏对“大众神话”及其“平庸的恶”所作的最严厉的指摘。多伊奇在该书的“英译本序”中指出:“他揭露了希特勒和戈林时代变成德国偶像的‘通常所谓意志坚决的人’(the average so-called man of determination)的昏聩,这种人可能会在世界范围内的原子武器竞赛中再度成为许多国家的偶像——人因为不再能承担持久的责任而仓促地行动。‘那些除了决心之外一无所有的人’,雅斯贝尔斯提醒我们,‘他们坚定有力地保证,不假思索地服从,毫不质疑地蛮干——而事实上,他们陷入粗浅狭隘的幻觉里了’。他们的幻觉是‘一种狂野而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的智力低下的激情,表现出人类消极被动地成为自己本能冲动的奴隶’。”希特勒之类的大众“偶像”,其显著的特点是“蛮干”而“不再能承担持久的责任”,为“本能冲动”所役而陷于“智力低下的激情”。说到底,这样的人无宁是雅氏所批判的“实存”(Dasein/existence)意义上“显赫人物”,绝非他所希冀的“生存”(Existenz)层面上的杰出代表。对雅氏来说,“生存”固然在临界处境下也会采取决绝的“行动”,但生存的行动自始至终是与自由、选择、超越、责任相即不离的。为了避免“生存”畸变为“实存”(“大众”其实就是“实存”的别称),雅氏最迟在1935年出版的《理性与生存》一书中就开始有意识地为“生存”插上“理性”的翅膀,以便让“生存”始终行进在探问真理、祈向“大全”的途中,进而让“生存”承担起自由选择、自我超越、自我生成的责任。尤为可贵的是,雅氏在1938年出版的《生存哲学》一书的第二部分“真理论”中,首次明确提及莱辛的哲学悲剧及其散发的“理性的气氛”:“理性的气氛弥漫于高尚的诗作特别是悲剧中。伟大哲学家都有这种气氛。哪里还有哲学,哪里就还能觉察到它。有些个别人的身上,比如莱辛,这种气氛就很明朗,他们虽然还没有什么本质内容,却像理性本身一样对我们起着影响作用,而且我们之所以阅读他们的语言,完全是为了呼吸这种空气。” 对雅氏来说,真理乃是通向存在的道路,理性则是通向真理的道路,这样一来,彰显“理性的气氛”便成为真正的哲学永恒的使命与伟大哲学家之所以伟大的神髓所在。从雅氏所谓“哪里还有哲学,哪里就还能觉察到它”之类的断言中不难看出,“理性的气氛”在他那里是用作分判哲学“真正”与否的衡准的。依此衡准来作分判,那种丧失了理性气氛的哲学便被他逐出真正的哲学之列,而那种弥漫着理性气氛的“高尚的诗作特别是悲剧”则被请进了哲学的王国。正是在这层意趣上,雅氏在莱辛一类的艺术家身上感受到了真正的哲学精神,认为“我们之所以阅读他们的语言,完全是为了呼吸这种空气”。值得注意的是,雅氏在《论真理》中谈论“哲学悲剧”时,是以莱辛的《智者纳旦》为范例展开论述的,可以说雅氏的这种看法在他被纳粹政府禁止发表作品之前有幸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生存哲学》)中就已初见端倪了。 ·只有进入经典名著,才有机会真正生活在历史里,历史也才真正存在于我们的生活里,未来也才向我们走来。 ·这些生命美学经典名著是亘古以来的生命省察的继续。在它们问世和思想的年代,属于它们的时代可能还没有到来。它们杀死了上帝,但却并非恶魔;它们阻击了理性,但也并非另类。它们都是偶像破坏者,但是破坏的目的却并不是希图让自己成为新的偶像。它们无非当时的最最真实的思想,也无非新时代的早产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