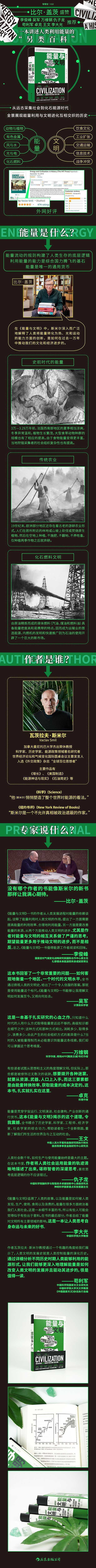出版社: 九州出版社
原售价: 110.00
折扣价: 71.50
折扣购买: 能量与文明(精)
ISBN: 9787510895401

瓦茨拉夫·斯米尔(Vaclav Smil),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学杰出荣休教授,他是一位科学家、历史学家,同时也是一名政策研究者。他是一位备受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推崇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经常现身世界经济论坛和气候变化国际圆桌会议,担任主要发言人,在能源、环境、食品、人口、经济、历史和公共政策等方面均有突出建树,并且非常善于进行跨学科研究。他著述颇丰,主要作品有《增长》《巨变》《美国制造》《能源神话与现实》《石油简史》等。2010年,入选《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杂志评选的“全球百位思想者”。2013年,比尔·盖茨在他的网站“盖茨笔记”(Gates Notes)上写下了如下文字:“没有哪个作者的书能像斯米尔的新书那样让我满心期待。”《科学》(Science)杂志则对他如此评价道:“他(斯米尔)悄悄塑造了整个世界对能量的看法。”
大多数历史学家都没有将能量当作必要的解释变量。即使是以坚持物质世界和经济因素的重要性而闻名的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也没有在他对文明的冗长定义中以任何形式提到能量: 文明首先是一个空间,一个“文化区域”,正如人类学家所说的那样,是一个场所。在这个场所里……你必须想象各种各样具备文化特征的“物品”,从房屋的形状、建筑材料、屋顶,到制作羽毛箭头这样的技艺、方言或当地族群、烹饪的口味、特定的技术、信仰的结构、做爱的方式,甚至包括指南针、纸张和印刷机。(Braudel 1982, 202) 据他的描述,材料、房屋、箭头和印刷机好像都是凭空出现的,不需要任何能量支出!如果人们试图理解塑造历史的所有基本因素,那么这种疏漏是不可原谅的——但如果我们注意到能源的种类、原动力以及能量使用水平并不能决定人类社会的愿景和成就,那么这种疏漏就是合理的。这种现实有其无可争辩的自然原因。诚然,能量转换对于所有生物的存活和进化都是绝对必要的,但这个过程的变种和差异又受到生物固有的性质的支配。 正如热力学定律一样根本,能量并非生物圈进化的唯一决定因素,也不是生命(尤其是人类行为)的唯一决定因素:不可避免地,进化是一个熵增的过程;但同时,也有一些物质投入是无法替代、无法循环利用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必需元素来支撑生物化学转化过程,一个弥漫着辐射的地球是无法支持碳基生命存在的。这些元素包括三磷酸腺苷(ATP)中的磷、蛋白质中的氮和硫、酶里面的钴和钼、植物茎中的硅以及动物的壳或骨头中的钙。表观遗传信息能分配能量,将它们分别用于生命的维持、生长、分化以及繁殖。这些不可逆的转变消耗了物质和能量,还受到土地、水和养分的可用性以及应对物种间竞争的需求和食物链的影响。 能量流会限制,但不能决定任何规模的生物圈组织。正如布鲁克斯和威利所说: 能量流不能解释为什么存在有机体,为什么有机体能够变化,或为什么有不同的物种。……有机体的内在属性将决定能量的流动方式,而不是相反。如果能量流对于生物系统是确定的,那么任何活物都不可能饿死。……我们认为有机体是具有遗传和表观遗传决定的个体特征的物理系统,它们以相对随机的方式利用环境中的流动能量。(Brooks and Wiley 1986, 37-38) 但这些基本事实并不能成为忽视能量在历史中的作用的理由。相反,这要求我们在合适的框架中对其进行讨论。在复杂的现代人类社会,能量使用显然更多是出于欲望和炫耀的目的,而不仅仅是为了满足物质需求。一个社会能够利用的能量规模明显会给这个社会的活动范围划定清晰的界限,却几乎无法告诉我们这个社会中人群的基本经济情况或精神状况。主要燃料和原动力是塑造社会的最重要因素,但它们并不能确定社会成功或失败的细节。当人们研究能量与文明的平衡关系时,这一点尤为明显。认为高能量使用等同于高水平的文明的观念,在现代社会普遍存在:我们只需要回想一下奥斯特瓦尔德的工作,或者福克斯的结论——“能量流动方式的每一次改进,结果都带来了文化机制的提升”(Fox 1988, 166)。 这种联系的起源并不令人意外。只有不断增长的化石能源消耗才能满足如此大规模的物质需求。更多的财产和更高的舒适度已等同于文明的进步。这种有失偏颇的看法抹除了世界上所有创造性成就——道德、智力和美学,这些成就与任何特定的能量使用水平或模式没有明显的关联:能量使用的模式和水平与“文化机制的提升”之间没有明显的相关性。这种能量决定论与任何其他还原论的解释一样,都是极具误导性的。 针对历史解释的挑战,乔治斯库-罗金提出了一个很好的类比:正方形的几何形状限制了它的对角线长度,而非它的颜色;同时,“正方形为何恰好是‘绿色的’,几乎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不可能被回答的问题”(Georgescu-Roegen 1980, 264)。因此,每个社会的物理行为和成就的领域 都会受到对特定的能量流动方式和原动力的依赖的约束——但即使是不起眼的地方,也可能达成精致的成就,但它为什么会出现,可能并不好解释。在大大小小各种领域中,我们都很容易为这一结论找到历史依据。 那些普遍且持久的道德规范都是由中东、印度和中国的古代思想家、道德家和宗教创始人在低能量社会中制定的。这些社会的一个特征是其中的大多数人只专注于基本生存。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如今仍能对现代事务产生巨大影响的两种主流一神论信仰)分别出现在2,000年前和1,300年前的干旱环境中,这种环境下的农业社会没有技术手段能将丰富的阳光转化为有用的能量。古典时代的希腊人经常提到他们的奴隶,他们明确地将奴隶等同于役畜(他们将奴隶称为andrapoda,即“像人一样行走的”动物;牛则是tetrapoda)。但希腊人给我们贡献了有关个人自由与民主的基本概念。自由和奴役同时发展是希腊历史最显著的特征之一(Finley1959),就如美国在共和国成立初期同时肯定人类平等和奴隶制一样。 当美国社会还在依赖木柴供能,宪法的主要起草人、第四任总统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 1751—1836)与第一任总统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 1732—1799)、第三任总统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1743—1826)一样都还是奴隶主,美国就通过了富有远见的宪法(“人人生而平等”)。19世纪后期的德国刚刚成为欧洲大陆主要的能量消费国,便拥抱了侵略性的军国主义,并在两代人之后进一步转向法西斯主义——而意大利和西班牙分别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成为独裁国家,当时他们的人均能量使用量是欧洲大陆国家中最低的,落后德国数代人。 艺术在其萌芽阶段,它的成就与能量使用水平、使用方式或特定种类无关:创造永恒的文学、绘画、雕塑、建筑或音乐,并不表示社会能量消费平均水平出现了相应的进步。在16世纪的头10年,佛罗伦萨领主广场上的一个闲人可以在几天内遇到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和波提切利等一系列创造力丰富的天才。这一现象绝对无法通过燃烧木材或驾驭牲畜(这些活动在当时的意大利、欧洲或亚洲任何其他城市都很常见)来解释。 没有任何能量方面的考虑可以解释为什么在18世纪80年代,格鲁克、海顿和莫扎特会聚集在约瑟夫二世时期维也纳的一个房间里。能量因素也无法解释19世纪90年代在世纪末的巴黎,一个人可以阅读埃米尔·左拉(?mile Zola)的最新小说,然后欣赏克劳德·莫奈(Claude Monet)或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最新的油画,在同一天里,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t)指挥乐团演奏了克劳德·德彪西(Claude Debussy)的《牧神午后》(图 7.11)。此外,艺术的发展没有显示出任何与能量时代相称的特征:法国南部新石器时代洞穴中的动物绘画、希腊和意大利南部古典神庙的比例、来自法国修道院的中世纪颂歌的声音,与胡安·米罗(Joan Miró)色彩缤纷的作品、丹下健三(Kenzo Tange)的建筑曲线、拉赫玛尼诺夫(Rachmaninov)音乐的魄力和忧思相比,现代气息丝毫不落下风,而且同样迷人且令人愉悦。 图7.11 卡米耶·毕沙罗的油画《蒙马特大道,春晓》,绘于1897年(来源:Google Art Project) 在整个20世纪,能量的使用水平与享受政治和个人自由关系不大:在能量丰富的美国和能量匮乏的印度,能量的使用都有所增加;而在储量丰富的苏联,能量的使用却受到了限制,在今天仍处于能量稀缺状态的巴基斯坦也是一样。二战后,苏联和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相比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使用了更多的能量,却无法为人民提供与西欧同等水平的生活质量。今天能量丰富的沙特阿拉伯的自由评级远低于能量匮乏的印度(Freedom House 2015)。 人均能量使用量和个人对生活幸福的主观感受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强联系(Diener, Suh, and Oishi 1997; Layard 2005; Bruni and Porta 2005)。生活满意度指数最高的20个国家不仅包括能量丰富的瑞士和瑞典,还包括不丹、哥斯达黎加和马来西亚等能量使用量相对较低的国家;日本(第90位)还排在乌兹别克斯坦和菲律宾之后(White 2007)。根据2015年世界幸福指数报告,墨西哥、巴西、委内瑞拉和巴拿马等能量使用相对中等的国家跻身前25名,领先于德国、法国、日本和沙特阿拉伯(Helliwell, Layard, and Sachs 2015)。 满足人类的基本需求显然需要一定水平的能量投入。但国家间的比较清楚地表明,随着能量消耗的增加,生活质量的进一步增益逐渐趋于平稳。那些更关注人类福利而非无谓消费的社会可以达到更高的生活质量,与浪费奢靡的国家相比,它们使用的燃料和电力只占很小一部分。日本和俄罗斯、哥斯达黎加和墨西哥,或以色列和沙特阿拉伯之间的对比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在所有这些情况下,能量流动的外部现实与内部动机和决策比起来显然是次要的。非常相似的人均能量使用量(例如俄罗斯和新西兰的能量使用量)可以产生完全不同的结,而截然不同的能量消费率也能导致惊人地相似的物质生活水平:韩国和以色列的人类发展指数几乎完全相同,然而韩国的人均能量消耗比以色列高出约80%。 在观察世界范围内的高能结构和进程的实际特征时,物理事实表象精神形象同样重要。由于它们在能量投入、材料投入和操作方面的普遍要求,美国中西部、德国鲁尔区、乌克兰顿涅茨克地区、中国河北省、日本九州和印度比哈尔邦的高炉从表面上看是几乎完全相同的。但如果考虑到所有的外部环境,它们实际并不相同。它们的独特性与它们起源于其中并持续运作于其中的文化、政治、社会、经济和战略环境的混合体有关,也与由它们冶炼的金属制品的最终用途和质量有关。 能量供应对人口增长的影响,是反映能量解释功能有用性十分有限的另一个关键环节。相对最可靠的长期人口重建(包括欧洲和中国的人口历史)显示,连续的流行病和战争所引发的扩张浪潮与危机构成了长期的缓慢增长(Livi-Bacci 2000, 2012)。18世纪上半叶,欧洲总人口大约是公元时代开始时人口的两倍;到了1900年,人口又增加了两倍多。营养的改善肯定是主要原因。但如果我们认为它是唯一的潜在因素(McKeown 1976),就与平均食物摄入量的仔细重建呈现的结果不相匹配了(Livi-Bacci 1991)。 《能量与文明》一书的作者从人类发展进程对能量的依赖谈起,诠释了能量利用对人类文明的作用,提出了一方面需要提高能量的利用效率、合理地利用能量,另一方面是要改善能量的来源,从两个方面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尤其是作者对能量与文明的相互关系做了严谨的思考,期望能量更多用于推动文明的进步,而不是相反。总之,《能量与文明》一书值得能源工作者阅读和回味。 ——李俊峰,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原主任、扎耶德未来能源奖终身成就奖得主 这本书回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何客观地衡量一个地区、一个时代的文明水平。全书通过俯视人类的文明史,给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答案,那就是使用能量这个标尺。《能量与文明》一书能够让我理解文明如何发展至今,又将向何处去。 ——吴军,计算机科学家 这是一本基于扎实研究的心血之作。只知道什么时代的人用什么方式取得能量是远远不够的,高级知识都在细节之中:这种方式和那种方式相比,消耗多少、取得多少、浪费多少,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方式的差异是什么?当时的人被能量限制而未必能意识到能量这条线索,我们却可以掌握这个思考维度。 ——万维钢,科学作家、得到APP《精英日课》专栏作者 有些读者试图从思想和主义的角度理解文明,但实际上,那些都是被修饰过无数次的说辞。想要拨开各种迷雾,就要从资源、武器、人口上入手。而这三要素都是由能量转换效率、获取能量的成本决定的。这本书,扎实就扎实在这里。 ——卓克,科普作者 能量是贯穿宇宙运行、文明演进、社会建构、产业创新的通行货币。这本《能量与文明》揭示的这个道理,令我震撼。全书糅合了历史学家、科学家、工程师、经济学家、社会学家的综合功力,帮助读者在一个全新侧面,重新了解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及与之互动的社会。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院长、国务院参事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员 人类社会数千年,如何生产与使用能量始终是最大的主题。在这本书里,作者将人类社会运用能量的轨迹清晰地描述了出来,堪称智者的深邃思考。喜欢思考底层逻辑的你不应该错过。 ——仇子龙,中国科学院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心高级研究员、神经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