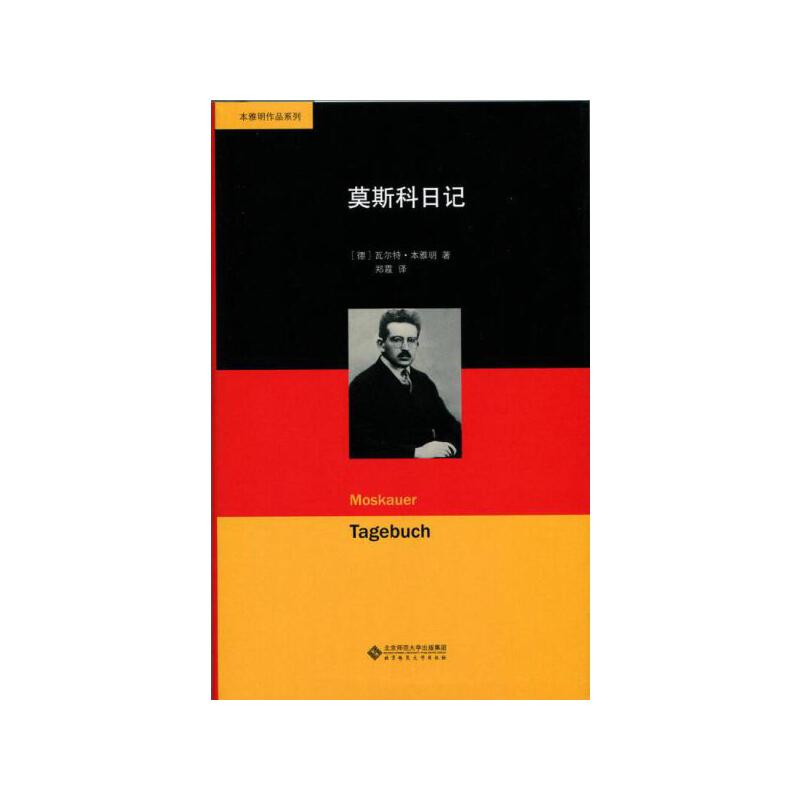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师大
原售价: 42.00
折扣价: 26.90
折扣购买: 莫斯科日记(精)/本雅明作品系列
ISBN: 97873031747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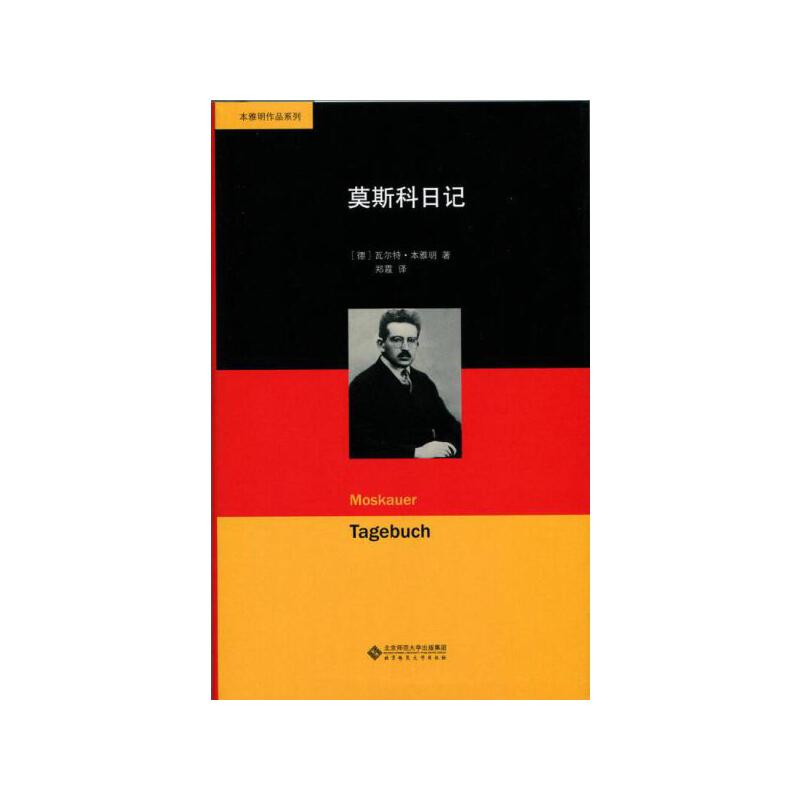
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1892—1940),德国文学评论家、思想家和哲学家,被称为“欧洲最后一位知识分子”,其写作徘徊在绝望与希望之间、大众与神学之间,从而获得了某种暧昧的伦理学态度。代表作有《拱廊计划》《德国悲剧的起源》《单向街》《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等。
今天我见不到阿丝雅。疗养院里的情况很严峻。 经过长时间的谈判,昨天晚上他们才允许她出院,而 今天早晨她并没有如约来接我。我们原本打算去给她 买布料做裙子的。我来这儿才一个星期,就不得不像 预料的一样,见到她的难度越来越大,更别说单独相 见了。——昨天上午,她急匆匆地来了,情绪激动, 她那像往常一样不安的神情更令人感到不安,好像害 怕在我的房里待上一分钟,害怕面对我似的。我陪她 去了一个委员会的办公大楼,她受到该委员会的传 唤。我告诉她前一天晚上我得到的消息:赖希有望在 一家非常重要的杂志社得到一个剧评家的新职位。我 们走过萨多瓦娅大街。总的来说,我说得很少,她则 兴奋地大谈她在儿童院与孩子们打交道的工作。我第 二次听她讲起儿童院的一个孩子被另一个孩子打破了 脑袋的事。真奇怪,我现在才明白这个非常简单的故 事意味着什么(这件事有可能给阿丝雅造成不良后果 , 不过医生认为那个孩子有救)。经常会发生这种情况 : 她说什么我几乎没听见,因为我非常专注地看着她。 她陈述了自己的想法:孩子们必须被分成小组,因为 无论如何都无法同时应对那些最野的——她称其为最 有天分的——孩子和其他孩子。令普通孩子感到非常 充实的东西却令那些野孩子感到无聊。很显然,正如 她自己所说,阿丝雅在和野孩子打交道的过程中获得 了极大的成功。阿丝雅还谈到自己的写作情况:为一 份在莫斯科出版的拉脱维亚共产党报写三篇文章。这 份报纸通过非法途径到达里加。对阿丝雅而言,她的 文章能被那里的人们阅读是非常有用的。那个委员会 的大楼位于斯特拉斯诺伊大街和彼得罗夫卡大街交汇 处的广场边。我边等边在彼得罗夫卡大街上来来回回 走了半个多小时。她终于出来了,我们去国家银行, 我要换钱。今天早晨,我感觉充满了力量,得以简洁 而平静地谈论我在莫斯科的逗留以及在此期间的微乎 其微的机会。我的话给她留下了印象。她说,那位救 治她的医生曾明确禁止她待在城里,并要求她去一家 森林疗养院。可她却留了下来,因为她害怕森林里令 人悲伤的孤独,也为了等待我的到来。在一家皮货商 店前,我们停了下来。我们第一次经过彼得罗夫卡大 街散步时,阿丝雅也在此停留过。店里的墙上挂着一 件漂亮的皮衣,上面缀着五彩的珍珠。我们进去问价 钱,得知这是通古斯人的手艺(而非阿丝雅所猜想的 “爱斯基摩”服装)。皮衣开价二百五十卢布,阿丝 雅 想买下它。我说:“假如我买下它,我就得马上离 开。”不过,她让我允诺日后送她一份能伴其终生的 大 礼。去国家银行要从彼得罗夫卡大街穿过一条拱廊 街,街上有一家古玩代销店。橱窗里陈列着一个“帝 国风格”的橱柜,镶嵌工艺异常精美。继续走向拱廊 街的端头,只见人们在木制陈列架旁拆装着瓷器。我 们走回公交车站的路上,度过了非常美妙的几分钟。 随后,我去见了卡梅涅娃。下午,我在城里乱逛。我 不能去见阿丝雅,克诺林在她那儿。此人是位重量级 的拉脱维亚共产党人,最高审查委员会的成员。(今 天也不能去见阿丝雅;我写此日记时,赖希单独在她 那儿。)我的下午结束于斯塔列施尼科夫大街的法国 咖 啡馆,面对着一杯咖啡。——关于这座城市:拜占庭 教堂的窗户似乎没有形成自己的风格。给人一种魔幻 的印象,没有亲切感;那些普普通通、毫不起眼的窗 户从拜占庭风格教堂的尖顶和大厅临街而开,就像住 宅楼的窗户一样。东正教的神父住在这里,就像和尚 住在寺庙里一样。圣巴西尔大教堂的下层部分倒像是 一座华丽的贵族宅邸的底楼。教堂穹顶上的十字架看 起来却像矗立云霄的巨大的耳环。一一奢华就像患病 的嘴巴里的牙垢一样附着于这座贫穷困苦的城市: N.克拉夫特巧克力店,彼得罗夫卡大街上高档的时 装店以及毛皮间摆放着的冰冷、丑陋的瓷花瓶。—— 这儿的乞丐不像南方的那么富于攻击性:在南方,衣 衫褴褛的叫花子会一个劲儿地纠缠不休,这好歹是残 存的生命力的体现;而这里的叫花子却是一帮垂死之 人。破烂的铺盖卷占据着街角,在那些外国人做生意 的区域尤甚,就像露天的“莫斯科大战地医院”的床 铺 一样。电车上的乞讨有另外的组织形式。有些环线车 在线路上停留的时间较长,要饭的就趁机溜上车;或 是一个孩子站在车厢的角落里开始唱歌。然后,孩子 捡起戈比。很少看见有人给钱。乞讨已经失去了社会 良知这一最强大的基础,比起同情心,社会良知更容 易打开钱包。——拱廊街:与其他任何地方不同,这 里的拱廊街有着高低不同的楼层,廊台往往空空荡 荡,和教堂里的一样。农民和阔太太们穿着大毡靴走 来走去。靴子看上去像内衣似的紧贴腿肚,就像紧身 胸衣一样叫人觉得万般难受。毡靴是双脚的华丽行 头。还是说说教堂:它们大多似乎无人照管,空荡 荡、冷冰冰,就像我在圣巴西尔大教堂里面看到的那 样。祭坛上只剩下零星的火光照向雪地,不过,这火 光却在遍布木头售货亭的城里被完好地保存着。白雪 覆盖的窄巷子很安静,只能听见卖服装的犹太人在轻 声叫卖。他们的摊位旁是个卖纸的摊子。女贩置身于 银色的箱子后面,遮着身子,露出脑袋,面前摆放着 挂在圣诞树上的银丝条和填衬着棉絮的圣诞老人,好 似一位蒙着面纱的东方女子。我发现最美的摊子在阿 尔巴茨卡娅一普罗夏基街上。——几天前,在我房里 和赖希谈论新闻业。基希(埃贡·埃尔文·基希)曾向 他透露过几条黄金规则,我还新拟了几条:①一篇文 章必须包含尽可能多的人名;②首句和尾句一定要 好,中间则无关紧要;③将由一个名字所唤起的想象 作为对这一名字进行真实描述的背景加以利用。我想 在此和赖希合作写一部唯物主义百科全书的纲要,他 对此有很棒的主意。七点过后,阿丝雅来了。(不过 , 赖希跟着一起去了剧院。)上演的是斯坦尼斯拉夫斯 基 执导的《土尔宾一家的日子》。自然主义风格的舞台 布 景非常出色,表演却不怎么差也不怎么好,布尔加科 夫的戏完全是一种鼓动造反的挑衅。尤其是最后一 幕,其中,自卫军“皈依”布尔什维主义,不仅戏剧 情 节乏味,而且思想观念虚伪。共产党反对此剧的上演 是有道理的,可以理解。至于这最后一幕是像赖希所 猜测的那样迫于审查而附加上去的还是原本就有,都 不影响对这出戏的评价。(这里的观众明显有别于我 在另外两家剧院所看到的。似乎没有一个共产党人在 场,哪儿都看不到黑色或蓝色的衬衫。)我们的座位 不 在一起,我只在演出第一场景的时候与阿丝雅相邻而 坐。随后,赖希坐到了我旁边,他觉得翻译太累了, 阿丝雅会吃不消。P27-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