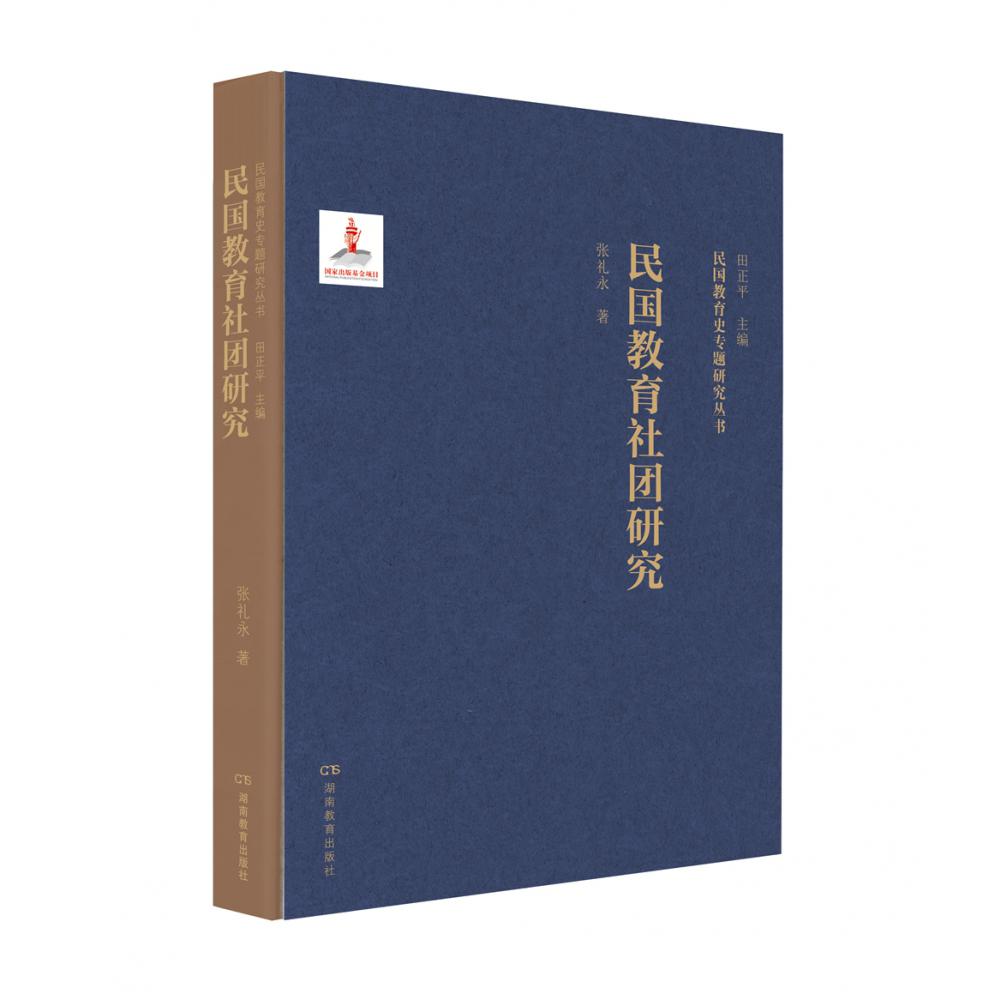
出版社: 湖南教育
原售价: 136.00
折扣价: 88.40
折扣购买: 民国教育社团研究(精)/民国教育史专题研究丛书
ISBN: 97875539653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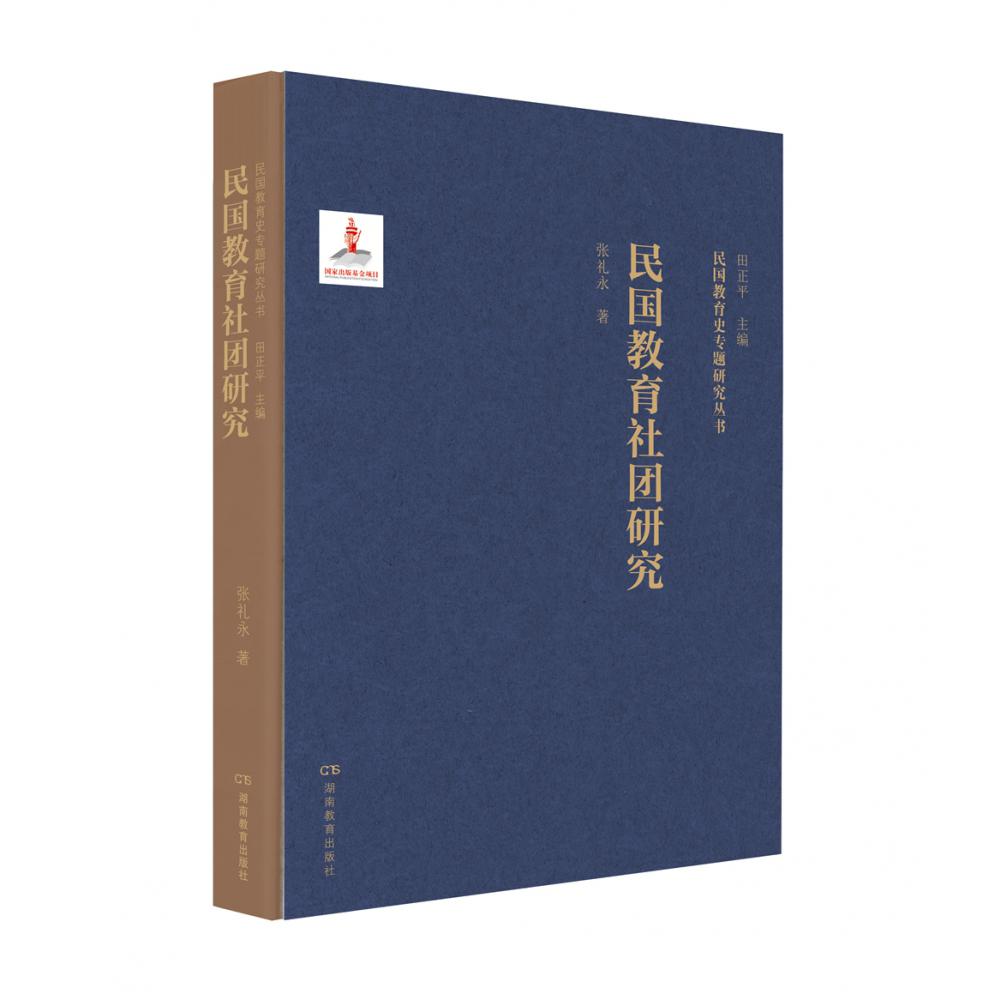
张礼永(1983- ),男,江苏扬州人,教育学博士,现为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发表论文50余篇,著有《民国教育社团研究》《共和国教育?筚路蓝缕》等。曾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十二五”国家青年课题一项,负责上海市高峰学科建设计划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专著项目一项。曾获“宝钢”优秀学生奖以及上海市教委“晨光”人才计划资助。
民国初期的教育行政者鉴于国家情形,对于清季兴学时兴起的教育会制度,加以保留并进行了改造,教育会中人,不仅继续推动地方教育事业的进步,而且还谋划联合起来组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以此促进全国教育事业的同步前进,在中央教育行政及省级教育行政式微之时,该联合会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后人称赞它对“吾国教育,贡献甚大” 。其实它也可以看作是从另一种形式上继承了清末兴学的一大教育遗产。 一、现实的需求与既有的成例 民国初年的教育行政者决心保留教育会这种组织形式,并予以改造,以适应新时代教育建设的需求,于是颁行了《教育会规程》,规定其以“研究教育事项,力图教育发达为目的” ,分为城镇乡、县和省教育会三种,并且“互为联络,不相统辖”,以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 (一)民初中央教育行政的更迭频繁 民国初年,蔡元培被任命为教育总长,他为了发展教育而邀请留学日本专攻教育的范源濂(字静生)相助,当时蔡、范之间曾有一番推心置腹的对话。蔡对范说道: “现在是国家教育创制的开始,要撇开个人的偏见、党派的立场,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国民党里不是寻不出一个次长;我现在请先生做次长,也不是屈您做一个普通的事务官。共和党随时可以组阁,您也可以随时出来掌邦教。与其到那时候您有所变更,不如现在我们共同负责。教育是应当立在政潮外边的。我请出一位异党的次长,在国民党里边并不是没有反对的意见;但是我为了公忠体国,使教育部有全国代表性,是不管这种反对意见的。听说您们党里也有其他看法,劝告您不要自低身份,给异党、给老蔡撑腰;可是,这不是为了国民党或我个人撑腰,乃是为国家撑腰。我之敢于向您提出这个请求,是相信您会看重国家的利益超过了党派的利益和个人的得失以上的。” 蔡元培为国民党党员,范源濂为共和党党员,蔡邀请范相助时,国民党里有不同意见,共和党内也有异样的声音;但蔡毫无党派的观念,不愿将教育部视为国民党的地盘,专用党内人员,再加上他一心发展教育的愿望和热忱,打动了范源濂。 二人在商量教育部部员组成时,也是持“公忠体国”的态度,蔡元培回忆到:“我那时候只有能者在职的一个念头,竟毫没有顾到老同志的缺望,到正式组织时,部员七十人左右,一半是我提出的,大约留学欧美或日本的多一点;一半是范君静生所提出的,教育行政上有经验的多一点,却都没有注意到党派的关系。” 对于这样的人员组成,民初著名记者黄远生评价道:“教育部新旧杂用,分司办事,已确有规模……俨然有建设气象。蔡鹤卿君富于理想,范源濂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 据范源濂回忆:“合作期间,部里的人都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讨论很多,却没有久悬不决的事。一经决定,立刻执行,所以期间很短,办的事很多。” 但是蔡元培与袁世凯的政治主张不同,无法长久合作,而且蔡发现“政府中显分两派,互相牵掣,无一事可以进行” ,在唐绍仪同袁无法共事辞去国务总理后,蔡元培不愿再作“伴食”之阁员,邀集同盟会成员农林总长宋教仁、司法总长王宠惠、工商次长王正廷一同辞职。袁派认为这种行为是“拆台”,于是极力挽留,但蔡“持之甚坚”。 在给新总理的辞职信中表示:“到部视事,亦至迟以14日为截止之期。” 民国初年,政治纷争,政潮起伏,变化莫测。蔡、范二人虽有“公忠体国”之心,想着“给教育立一个统一的智慧的百年大计”,但是二人与袁世凯一派终究合不来相继辞职,由此拉开了北京教育部不断更换教育总长的序幕。 与今天很多人的认知不同,教育社团对民国时期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不少今天的我们习以为常的教育理念、教育规范,实际上正是由这些民间的教育社团在那个由封建教育向近现代教育转型的时期提出、制定、推行,并为随后的教育管理者所沿袭采纳,多方合力塑造了我们今日教育的面貌。而随着时代向前发展,这些民国时期红极一时的教育社团又走向沉寂,湮灭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渐渐离开人们的视野。研究民国教育社团,不仅是对一段教育史、学术史的系统性回顾与总结;了解它如何在短暂的数十年间登上教育舞台并大放异彩,同样对于我们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实践具有重大参考价值。在这个意义上,《民国教育社团研究》一书的历史意义与其学术意义同样值得读者细细品味、鉴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