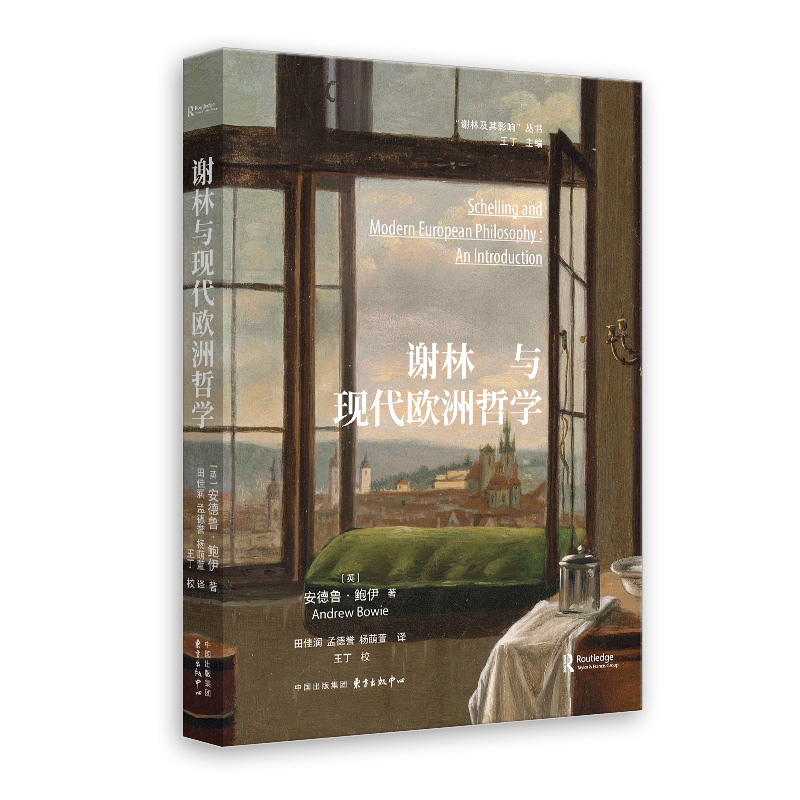
出版社: 东方出版中心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3.60
折扣购买: 谢林与现代欧洲哲学
ISBN: 978754732328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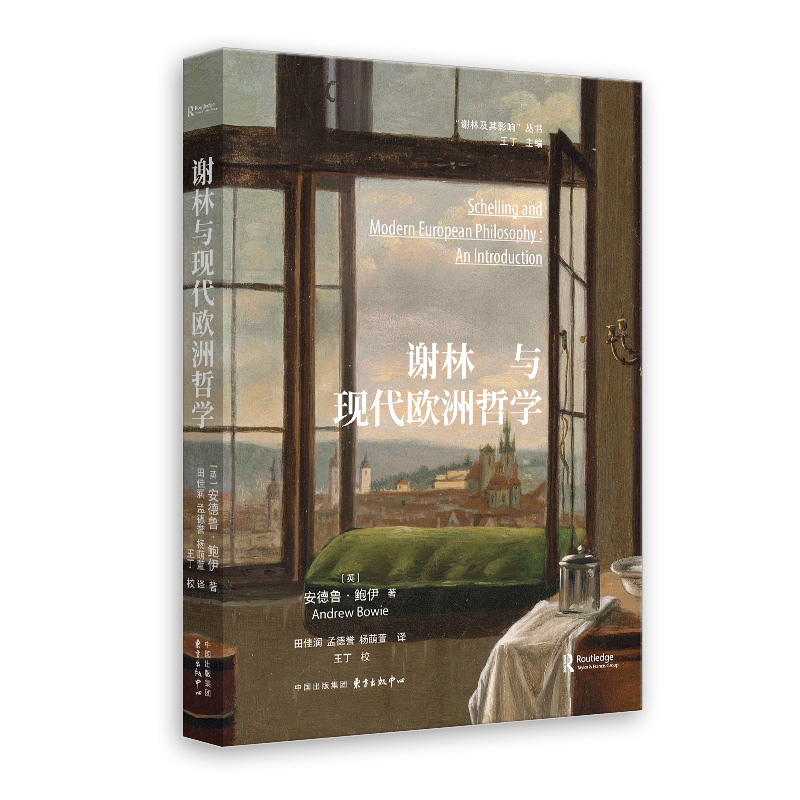
安德鲁·鲍伊(Andrew Bowie),伦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哲学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德国观念论、德国美学等,著有《谢林与现代欧洲哲学》《德国哲学导论》《从浪漫主义到批判理论》《美学与主体性》《阿多诺与哲学的终结》等。
弗里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1775—1854)在近现代哲学史上的重要性直到最近才开始被理解。长期以来,谢林晚期作品的重要性都被德国唯心主义的衰落掩盖,导致他仅仅被视为黑格尔的先导。我要为下面这点辩护:鉴于当代对“西方形而上学终结”以及“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关切,谢林的思想需要被重新评估。新近的绝大多数英文谢林研究一直把谢林看作黑格尔的附庸。这意味着他要么作为黑格尔批判的靶子,即黑格尔批判自己先前的哲学无法克服“直接性”、无法在哲学中阐明存在和思维关系的靶子;要么仅被视为黑格尔理论演进中的一个插曲:在这种叙事中,在尼采和海德格尔开启了从西方形而上学中解放的真正进程以前,黑格尔都被视为哲学王国中一切事物的权威。在接下来的内容里,我力图表明,谢林不仅仅是黑格尔的批判对象。事实上,谢林通过揭示黑格尔哲学的缺陷,为阐明现代哲学中的关键结构作出了贡献,这些批判甚至对当今哲学议程的设定有着极大的帮助。谢林的主要观点在其晚期哲学中最容易得以透视,对黑格尔的批判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这些内容主要可以参看我为剑桥大学出版社翻译的《近代哲学史》(On The History of Modern Philosophy)讲座(Schelling 1994),以下我将把它称为“讲座”。我的目标在于,结合新近那些建立新的理性概念的尝试,以及联系后现代思想的理性概念批判这两方面,重新审视谢林哲学思想,促进对谢林哲学的理解。 在1831年黑格尔去世前,他的哲学长期宰制着哲学界。而待其去世,对他哲学大规模、多方面的攻击才纷至沓来。然而很少有人意识到,谢林对这些攻击的贡献有多么重要。事实是,在1841至1842年期间,一些青年黑格尔派成员就参加了谢林在柏林的讲座——当时谢林接替了黑格尔的哲学教席,或者通过他人的讲座笔记了解了一些讲座内容以及谢林早期对黑格尔的一些批判。显然,谢林被他们视为是“未来哲学”(费尔巴哈)的另一个敌人,尤其源自他晚期生活中被确认无疑的保守主义倾向——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恰如其分的判断,因为谢林即使以诸多方式冲击很大一部分唯心主义概念,但他仍然对唯心主义抱有信念。在唯心主义的哲学史传统中,最重要的阶段是最高和最终的阶段。这意味着,那个阶段必须在自身中把握之前的所有阶段。从费希特开始,德国唯心主义者的共同目标,不外乎是终结形而上学——根据康德对独断论形而上学的批判来理解“绝对者”(这个争议极大的术语含义将在后面变得清楚明晰)。为了实现这种理解,哲学家必须确保他自己的哲学是最后一个可能的哲学。对于晚期谢林来说,这就是他的“肯定哲学”。它将通过展示理性体系自我奠基的不可能,来超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从而导向一个新的基于历史的哲学宗教。谢林确实超越了黑格尔,但他也没有实现更高的综合:现在,谢林的一些晚期思想被重视,正是因为它们揭示了那个由黑格尔建立的形而上学的不可能性。 无须多言,属于谢林和黑格尔哲学时期的雄心壮志已成过眼烟云。鉴于同黑格尔一样构建总体哲学的失败,我们现在更可能会去思考“后哲学”是什么样子。正如理查德·罗蒂所说,如今的情况是,我们“发现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德里达以及像我这样的德里达实用主义评论者,都争夺着成为历史上第一个真正激进的反柏拉图主义者的地位”(Rorty 1991b p.96)。罗蒂引用了米歇尔·福柯的观点,认为哲学家现在面临的关键危险是,无论我们走哪条路,我们注定会发现黑格尔在路的尽头耐心地等待着我们的到来(同上),因为试图超越形而上学的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也总是预先假定着同样的概念。形而上学的概念本身就不断显示出它辩证地依赖于它要克服的东西。谢林正是最早试图避免“不知不觉地成为黑格尔”的哲学家之一。在这个意义上,谢林受到了最早提出“哲学的终结”的人,即青年黑格尔派的追随。而“哲学的终结”这个概念在最近又变得耳熟起来。 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提出了谢林—黑格尔构成的这一“星丛”在哲学史上的重要性:“我觉得,我们的处境和黑格尔的第一代弟子并没有本质差别”(Habermas 1988 p.36);“在哲学上我们始终都是青年黑格尔派的同代人”(同上书,p.277)。哈贝马斯认为,现代形而上学的思维模式可以追溯到笛卡尔和康德,“直到黑格尔那里仍然生机勃勃”,其特征在于“同一性思想、理念论和强大理论概念在意识哲学中的转型[作者注:在实践之前的意义上]”(同上书,p.41)。因此,哈贝马斯和海德格尔的观点一致,即现代哲学的特点是赋予主体以首要地位,并试图通过自身的活动来确定对象世界的真实本质。因此,超越“主体—哲学”的模式构成进入后形而上学思维的途径。但在谢林晚期的哲学中,谢林显然不符合哈贝马斯所概述的现代形而上学构想,甚至在他早期哲学的某些方面,谢林提出了一个完全不同的视角。因此,值得一问的是,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终结”,无论是在形而上学终结的传统意义上,还是在以“后形而上学思维”的名义克服形而上学的当代意义上,是否还可以通过重新审视谢林来更好地得到理解。 在英语世界,晚期谢林的声誉似乎使他在这样的背景下不太可能成为人们进行研究的候选对象。毕竟,他的许多晚期哲学都被猜测是受到雅各布·波墨(Jakob Bhme)和其他一些神秘主义者影响,这些学说被理解为将基督教转化为一种在哲学上可行的宗教的尝试,即尼采所谓的“大众柏拉图主义”的一种尝试。即使是晚期谢林的同时代人,比如克尔凯郭尔以及马克思的朋友阿尔诺德·卢格(他们1841—1842年在柏林听了谢林的讲座,那时谢林获得了曾属于黑格尔的教席)也认为谢林是无望的。克尔凯郭尔曾说:“我已经完全放弃谢林了。”(引自Schelling 1977 p.455)卢格说:“认为谢林仍然是一位哲学家是最愚蠢的事情。”(同上,p.464页)如果真有如这些有影响力的思想家所认为的那样,晚期作为哲学家的谢林已经消失了,为什么我们现在还要重新唤起他呢? 在后经验主义科学哲学氛围中工作的科学史学家不难像马克思一样,对青年谢林作出肯定评价。他们认为进行自然哲学研究的谢林是一个重要的人物,他对自然的“生产性”(productivity)和其内在的极性(polarity)的思辨性阐述,在紫外线的发现、能量守恒原则的提出以及电磁学的发现中起了重要作用(参见:例如Kuhn 1977 pp.97-9; Cunningham and Jardine 1990)。即使如此,他们也没什么理由去关注晚期谢林的“讲座”、《神话哲学》和《启示哲学》等作品,而这些作品占据了谢林自1820年代末期以来的大部分精力。当然,当时间到了19世纪40年代,自然科学研究开始受到物理主义和实证主义的影响,它们使得作为现代科学公开实践事物的一部分的自然哲学被有效扼杀了。谢林的晚期工作很少涉及自然科学,而当涉及时,结果也往往令人失望。他将注意力转向神话和神学,这一事实也常常被看作谢林无法构建一个完整融贯的哲学体系的又一证明,这一长伴谢林一生的指责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中早就被人熟知了。 荣获众多好评的谢林导论,清晰重构谢林关键哲学论证 ·摆脱传统的德国古典哲学,在后现代思潮中重新定位谢林 ·填补学科空白,哲学爱好者和研究者不容错过的经典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