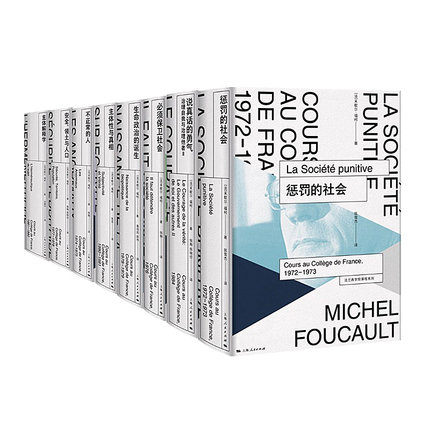
出版社: 上海人民
原售价: 550.00
折扣价: 0.00
折扣购买: 福柯法兰西学院课程系列 共8册
ISBN: 978720815508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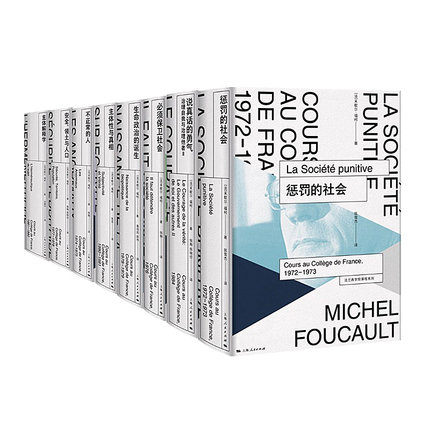
米歇尔 福柯(1926年10月15日-1984年6月25日),法国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对文学评论及其理论、哲学、批评理论、历史学、科学史(尤其医学史)、批评教育学和知识社会学有很大的影响。
**课时 忘记自我的危险—苏格拉底拒*干预政治—梭伦面对庇西特拉图—苏格拉底的精灵—死亡的危险:阿尔吉努萨伊(Arginuses)战役中的将军们和萨拉米斯的莱昂(LéondeSalamine)的故事—德尔斐神谕—苏格拉底对神谕的回答:核实和调查—任务的对象:人们对自身的关心—苏格拉底说真话的顽强—真正意义上伦理“直言”的出现—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从道德上建立了对自身的关心。 在上次提到政治“直言”的危机、至少是政治体制作为直言可能出现的场所的危机后,我**想开始研究伦理场域的直言,以及说真话的实践,而想这么做显然就得从苏格拉底出发,他当然是宁可直面死亡也不愿放弃说真话的人,但他不会在讲坛上、议会里、民众面前行使说真话的权利,不加掩饰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苏格拉底是有勇气说真话的人,能为了说真话接受死亡的风险,但只是在反讽提问中实践对内心的拷问。 [自]伦理场域的直言与政治直言分离[之后],就与后者形成对立,为了研究伦理场域直言的建立,我想谈谈两篇文章。**篇出自《申辩篇》:在这篇名作中,苏格拉底说,之所以他没打算在城邦里承担政治角色,那是因为一旦他从政,就可能面临死亡。 后一小时我们会读第二篇文章,[出自]《斐多篇》(Phédon)——是苏格拉底**的临终遗言,要求他的门徒以还债的形式,给阿斯克勒庇俄斯(Esculape)献上一只公鸡,[当他]托付这项献祭[时],补充说:想着啊,别忘了,别疏忽。两千年来,任何哲学史家、评论家即便对此感兴趣,也从未加以解释或阐述。杜梅齐尔(Dumézil)分析的正是这一篇,我认为在上次**你们读的那本书中,他找到了答案。不管怎样,在这两篇文章之间(**篇是《申辩篇》,苏格拉底说:我没有“从政过”(我们**的说法),我没有走到讲坛上,因为如果我这么做,很可能就死了;在第二篇中,苏格拉底愉快地接受了死亡,要求以公鸡的形式给神灵还债),说真话涵盖了整个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该传说处于说真话及其招致的死亡风险的关系中。这就是我想跟你们讲的问题,要加以探讨。 首先是《申辩篇》。我首先要提到一个观点,现在暂时搁置留待后用。是[关于]《申辩篇》的头几行。至少柏拉图是这么讲的:苏格拉底的话属于司法性话语,像所有好的同类话语那样,不管怎样他开头就是一大堆辩护词,[这么说]:我的对手们在撒谎,我说的是真话。因为这是在法院里面对指控者时,能说的*少的话。我的对手们在撒谎,我说的是真话。第二点,苏格拉底说:我的对手们善于言辞(deinoilegein),而我则相反,他说,我说话简单直接,毫无技巧和准备。这还是传统主题。而他也补充——这在此种话语中也不算稀奇:他们善于言辞,而我说话简单直接。何况他们如此能言善辩,以至于他们希望让大家相信,能言善辩的人是我。他们这么说正是在撒谎:我,我不善言辞。如果在这种修辞形式中,在这种**传统的司法话语表达形式中,他没加入某个概念的话——苏格拉底说:我的对手们在撒谎,他们能言善辩,如此善于言辞以至于到了几乎让我“忘记自己是谁”——因为他们(hup’aut?n),我几乎忘记了自己(emautouepelathomên),这话就根本不值得详细分析。如果你们愿意,我希望我们能够记住这一观点,它有点儿像留待后用的松鼠存粮,以便对我们之后提到的那个人致敬。我只希望你们能够记住的是,对手们、其他人说话方面的灵活熟练,能够让人忘记自我。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能够从反面推理出对面的相关命题。如果能言善辩导致忘记自我,那么说话简洁、毫无准备和修饰、直接的真话,因而是“直言”的真话,会把我们引向我们自身的真相。 第二点我也希望提请你们注意,被称为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的,一系列文章可被归作一起,包括《申辩篇》(诉讼)、《克里托篇》(Criton)(苏格拉底和克里托在监狱中对可能越狱的讨论)以及《斐多篇》(记述苏格拉底的*后时刻),开头提到在整个传说中都很重要的东西:忘记自我的风险。从开头(“他们差点儿让我忘记自己”)到结尾应该加以评论的(“别忘了我”),整个传说探讨的就是自我的真相和忘记自我之间的关系。在此影响下会上演对苏格拉底的诉讼、苏格拉底对可能出逃和可能获救的讨论,以及*后苏格拉底之死。我们暂时就此作罢,把这一观点留待后用。 现在我想着手刚才提到的那篇文章,出自《申辩篇》31c,问题是:应该从政吗?或者*确切地说:为什么苏格拉底,他没有从政呢?刚刚就在这一段之前,苏格拉底解释了为什么他去找雅典公民们,为什么他要管这些事(我们以后还会分析),为什么他要照管他们(“在每个人身边扮演父兄的角色”)。因此他像父兄那样照管雅典人。说了这话后很快,他就反驳自己如下:但是,“为什么,不吝惜在这里那里针对每个人提出我的建议、差不多什么事情都管的同时”,我却不敢公开地(dêmosia),在民众面前对他们讲话(anaibain?neistoplêthos:从严格意义上讲,走上讲坛以便对民众讲话),给城邦提建议(sumbouleueintêpolei)呢?又一次用了技术性的词。Sumboulein,是议会、城邦讨论机关的术语。为什么我不敢公开地走上讲坛,参与城市、城邦的决策呢? 一项政治角色,某人起身站立,和民众说话,参与城邦事务的讨论,讨论这一问题显然提到了本应该给“直言”留出空间的民主体制的图景。苏格拉底提到的,就是这个可能的政治直言者形象,不顾危险,无视威胁,愿意为了城邦的利益而站起来。他可能会冒着死亡的风险,说出真话。这里我们可以回顾在古希腊文学中经常被讲到的,梭伦的故事、举动和态度。在亚里士多德的《雅典人宪法》**4章、普鲁塔克的《梭伦生平》和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èneLa?rce)的著作中都能找到。雅典人正失去自由,因为庇西特拉图树立个人**,开始以自己之名行使对雅典人的**权力,行使所谓的专制,在这一时刻,见证了年轻的庇西特拉图上位的老梭伦,决定来到公民大会。庇西特拉图通过给自己配备个人卫队,公开了其行使专制的意图,这是希腊城邦公民传统的夺权手段:在身边聚集一支个人卫队。针对这一事件,梭伦来到公民大会。他作为普通雅典公民来到议会,但穿甲带盾,通过这一举动表明了正在上演的一幕,庇西特拉图给自己安排一支个人卫队,将公民视作敌人,而他有朝一日会与之斗争。如果君主表现出运作一项军事权力,以武力威胁其他公民,那么[反过来]很正常,公民会全副武装地前来。因此梭伦穿甲带盾地来到公民大会。他要批评公民大会刚批准庇西特拉图为自己配备个人卫队,梭伦对同胞们说:“我比那些没明白庇西特拉图不良居心的人们要聪明,比那些明白了却因害怕而保持沉默的人要勇敢。”这里你们看到梭伦的双重直言:对庇西特拉图的直言,因为他通过[完成]穿甲带盾、全副武装来到公民大会的举动,[由此]表明庇西特拉图正在做的事情。他揭示了正在上演一幕的真相,同时对公民大会发起真话,批评那些没明白的人,也批评那些明白了却保持沉默的[人]。梭伦正相反,他要说话。梭伦说出揭示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真话,批评了同胞们之后,公民大会却回答说梭伦实际上正在发疯(mainesthai)。梭伦反驳道:“如果我疯了,你们过一段时间就会知道,[……]那时真相将会大白。”此处你们有一个很确切、很典型的例子,当然是由果溯因建构起来的实践“直言”的例子。 苏格拉底不愿担当的正是这种直言实践,他不愿扮演的就是这一角色。他不敢公开地走到民众面前,为城邦提建议。苏格拉底不会成为梭伦。而问题是,苏格拉底如何解释下列事实:他不会成为梭伦,不会到讲坛上去,不会公开地(dêmosia)说出真话。苏格拉底给出的不扮演这一角色的理由很有名。他听到一个熟悉的声音,来自神灵或魔鬼,时不时会听到,对他说话,在他正要这么做或者本来能这么做的时候,这个声音从不给予他正面意见,从不对他说应该做什么,[而是]不时被他听见,不让他做某事。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就是这样的事。为什么这个声音被他听见呢?为的就是不让他从政。他像父兄般照管公民们,这个声音却不让他以政治的形式去照管他们。这一禁令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信号?为什么这个声音不让苏格拉底实践政治上的直言,而此时他本来能赋予其真话这种形式、这一场景和这一目的? 针对这些问题,苏格拉底列出一些考虑,乍一看,可能会以为它们太简单,纯粹是为了解释这一禁令,或者说只是解释魔鬼的声音发给他的这个负面信号。这一表面上的解释,就是民主直言的不良运作,或者*一般地说,政治直言的不良运作,在牵扯到政治体制时,想要实实在在,充分**地扮演“直言”的角色,人们就会感到无能为力。为什么呢?很简单就得归因于所冒的风险。这便是我打算认真思考的:“如果早先我投身政治,那么我估计已经死了很久了。”你们是否记得,上次给你们读过的这段话。苏格拉底补充道:“噢,听到我对你们说真话,请不要生气[米歇尔?福柯:真话是:如果我当年从政,我可能就死了]:哪怕是因为他出于高贵的理由,勇敢地反对过一丁点儿事,可能是反对你们,也可能是反对整个公民大会,哪怕是因为他努力阻止过城邦中一丁点儿非正义和非法的行为,那么没有任何人能够免于一死。”如果我们很快地读这段话,情况就很清楚:我没有从政,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当年从政,如果走过来对你们说话、说真话,那么你们可能就把我处死了,就像你们处死所有其他人一样,那些人曾勇敢地试图阻止城邦内非正义和非法的行为。只不过我们要看得*加仔细,尤其得看苏格拉底给出的例子和解释。其实,为了支持这一断言——在公民大会对民众说真话时,或者仅仅在想要笼统而直接地照顾城邦利益时,会冒有死亡的危险,苏格拉底给出的例子很奇怪,同时还自相矛盾,因为它们既是例证又是反驳。 说这些是例证,因为在这些情况下可以看到政治体制,不管是民主的、专制的还是寡头的,都阻止或试图阻止那些为主持正义或合法性而说真话的人。但这些也同时是反驳,因为可以看到,恰恰苏格拉底在其援引的两个**具体的案例中,没有接受这一要挟和威胁。他直面了这两种情况,愿意冒死亡的风险。事情是这样的。当我们希望在民主制度游戏中说真话时,确实会置身死亡的风险中,苏格拉底借鉴自身经历和生活,给出一个**具体的例子。事情发生在公元前406年,根据轮流执政规则,苏格拉底当了执政官——这并非某种个人行为,并非苏格拉底本人主动找麻烦,而是他所在的部落轮到行使执政权了。此时刚开始了一个诉讼,起诉阿尔吉努萨伊(Arginuses)战役中打胜仗的雅典将军们,出于很多原因没在获胜后收拾尸体——这在当时既属于亵渎行为,也是一种有点可怕的政治举动。我们暂不详细解释。因而在公民大会中,有人提交了对阿尔吉努萨伊之战将军们的申诉。那么苏格拉底做了什么呢?“只有我这个执政官同你们作对,阻止你们违反法律,只有我投了反对票。”事实上公民大会还是给阿尔吉努萨伊之战的将军们判了刑,将军们被处决,千真万确。尽管整个公民大会都赞成判刑,苏格拉底说:我“投了反对票”。“那些[赞成处决将军们的;米歇尔?福柯]演说家声称准备起诉我、逮捕我,而你们[指雅典民众;米歇尔?福柯]还叫嚷着鼓励他们这么干,但这都是徒劳;我认为我的义务是站在法律和正义一边,无视危险,而不是因为害怕坐牢、被处死,和你们串通一气,迎合你们的意愿。”这里有个例子很好地证明,在民主中要想说真话,捍卫正义和法律,就得冒死亡的风险。但在指出确实存在这种风险的同时,苏格拉底也表明实际上他直面了风险,扮演了典型的政治直言者的角色。的确,直言是危险的,但苏格拉底也确实具有勇气直面直言的风险。他有勇气去说话,有勇气在公民大会前给出反对意见,而公民大会试图让他闭嘴,追捕他,可能会惩罚他。 在这个带悖论色彩的例子(证明民主中的直言是危险的,但也是苏格拉底接受这一风险的例证)之后,苏格拉底从雅典历史的另一阶段,从另一种政治体制中,又援引了一个例子。他援引的是一个持续较短的时期,公元前5世纪末,雅典人处于30人寡头的统治下,这是一个专制而血腥的政府。苏格拉底表示,在一个专制、寡头的制度中,说真话会和在民主制中同样危险。但他同时也指出,这对他来说没有区别,以及他是如何冒险说真话的。他提到,当时那30个专制者想要逮捕一个叫萨拉米斯的莱昂(LéondeSalamine)的公民,但其实此人被冤枉了。30个专制者要求4个公民去逮捕这个人。苏格拉底被指派到这4人之列。其他3人都去逮捕萨拉米斯的莱昂[米歇尔?福柯:苏格拉底提醒他的指控者们说]:“在这一情况下,我不是通过言辞而是通过行动(oulog?all’erg?)表示,我视死如归(emoithanatoumeleioud’hotioun;我提醒你们注意melei[这个表达法],经常会碰到;米歇尔?福柯),但我希望不为非作歹也不犯神,这是我首先考虑的[米歇尔?福柯:再次用到melei:toutoudetopanmelei]。” 一个既相对又相反的例子。说相反是因为此时处于贵族、寡头政体中;说相对是因为在这个体制中,“直言”也不可能实现,但苏格拉底以同样的方式接受了风险。你们看到问题是怎样的。苏格拉底刚才说:为什么说到照管公民,我却从没管过,不愿意公开地(dêmosia,公开地,走到讲坛上去)照管他们呢?因为这么做的话我会死。他给出了例子证明其实尽管危险,他还是接受了危险和死亡,那么他怎么能又为了解释其态度而这么说呢?能否说在这样的条件下,不良政治运作导致直言者所冒的死亡的危险,说真话可能面对的死亡,是苏格拉底没有投身政治舞台、从未在民众面前讲话的真实理由?为了彰显真相和正义,他两次(民主制和寡头制下)都接受了死亡的危险;在这篇正在上演的《申辩篇》中,他恰恰就在解释并将会用整篇文章解释,他不畏死亡;他怎么能够这么说:我没有从政,因为如果从政我可能就死了。问题是:这些危险能否成为他有所克制的真实理由?问题的答案既是肯定又是否定的。显然是否定,我坚持认为如此,并非因为畏惧死亡、逃避死亡,苏格拉底才放弃了从政。但也可以说:是肯定的,正因为这些危险他才有所克制,但并不是怕死,而是如果他当年从政死了,就不能为自己和雅典人效力,文章里就是这么说的。苏格拉底没有愿意以政治直言的形式说真话,原因不是畏惧死亡,不是出于个人及其死亡的关系考虑。不是这种个人关系,而是某种有用性关系,某种牵扯到他本人和雅典人的关系,这层有用的、正面的、会带来益处的关系才作为真实理由解释了:政治体制给真话施加的威胁阻止了苏格拉底以政治形式说真话。魔鬼的声音通过负面信号、通过呼喊,要劝告苏格拉底的正是:小心,别死。并不是说死亡是应该避免的痛苦,而是苏格拉底死了,就不能做正面的事。不能对他人和自己,建立某种宝贵、有用而有益的关系。因此这一魔鬼的声音,在苏格拉底本该走到公民大会前去时,让他离开了致死的政治,这一信号的结果或者功能是,合理地保护苏格拉底去完成这一正面任务,履行他接受的责任。 这里指的是神交给苏格拉底的任务:防范政治上的无用风险。不要忘记(后面我们会回到这一点上来),整个苏格拉底之死的传说都被打上了一些神灵干预的印记。这就是神灵干预,在苏格拉底可能实践政治直言的时候将其中断:神灵干预保护的究竟是怎样的任务呢?整个《申辩篇》或者至少其**部分,都在界定、描述这项有益的任务,应该得到保证使苏格拉底免于一死。该任务就是行使、实践说真话,应用某种说真话的模式,这种模式和政治舞台上有生存空间的说真话模式不同。那个声音向苏格拉底传达了这一嘱托,或者*确切地说使他远离了以政治形式说真话的可能,该声音标志着在政治上说真话的对面,建立起另一种说真话,即哲学上说真话:你不是梭伦,你应该是苏格拉底。魔鬼的声音指出,相对于政治上的说真话,这另一种说真话实践的本质上、根本(fondamentale)而基本(fondatrice)的区别,那么这种说真话实践是什么呢?《申辩篇》**部分整篇都在讲这个,我认为可以用三个时刻,勾勒出另一种说真话,苏格拉底如此小心地吝惜这种说真话。 说真话的**时刻,位于和神灵的关系、和阿波罗的关系以及和预言的关系中。你们看到,这并不是无关紧要的。苏格拉底的朋友凯勒丰(Chéréphon)去问德尔斐的神:哪个希腊人比苏格拉底*博学?你们知道,这个问题并非由苏格拉底提出,神的答案是:没有人比苏格拉底*博学。当然和神所作的一切答复一样,这个回答是谜一样的,得到答案的人永远都不会很确定真的明白了与否。苏格拉底就没有明白。和(几乎)所有听到这些来自神灵的谜一样话语的人一样,苏格拉底自问:Tipotelegeihotheos(神说了什么,遮遮掩掩地:ainittetai)。但应该马上指出,在神灵遵循惯例给出谜一样的答复后,苏格拉底自问这个传统的问题以找寻神所说的意思,他并没有给自己找一个可谓阐释性的方法。他没有努力去破解隐于其下的意思,没有试图去猜测神所说的话。苏格拉底解释了此时所做的事,**有趣。他说:凯勒丰问题的答案传到我这里,我不明白,就问自己:神究竟是什么意思?我就开始寻找。这里用的词是zêtein(你们会找到zêtêsis这个词)。他开始寻找,而又一次,寻找不是为了阐释、破译。不是要给神可能想表达的意思加注解,神可能以预言的形式、半真半假的话语形式隐藏了他的意思。苏格拉底着力寻找的[目的]是,弄清楚神谕说的是不是真话?苏格拉底想证明神谕的内容,坚持要对其予以核实。他用一个典型而重要的词,指出寻找(zêtêsis)的模式。就是elegkhein,意思是:责备、反对、询问、讯问某人,反对某人说的话,以便弄清楚所说的话是否站得住脚。某种意义上说,对其提出争议。因此苏格拉底不会阐释神谕,而是要对神谕提出争议,加以讨论,予以反对,以便弄清楚它是不是真的。正是为了核实神谕而不是要阐释它,苏格拉底将会四处游历,经历一个过程(古希腊文是“planê”),才*终知道预言是否真的无懈可击(anelegktos),以及是否真是建立在真相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