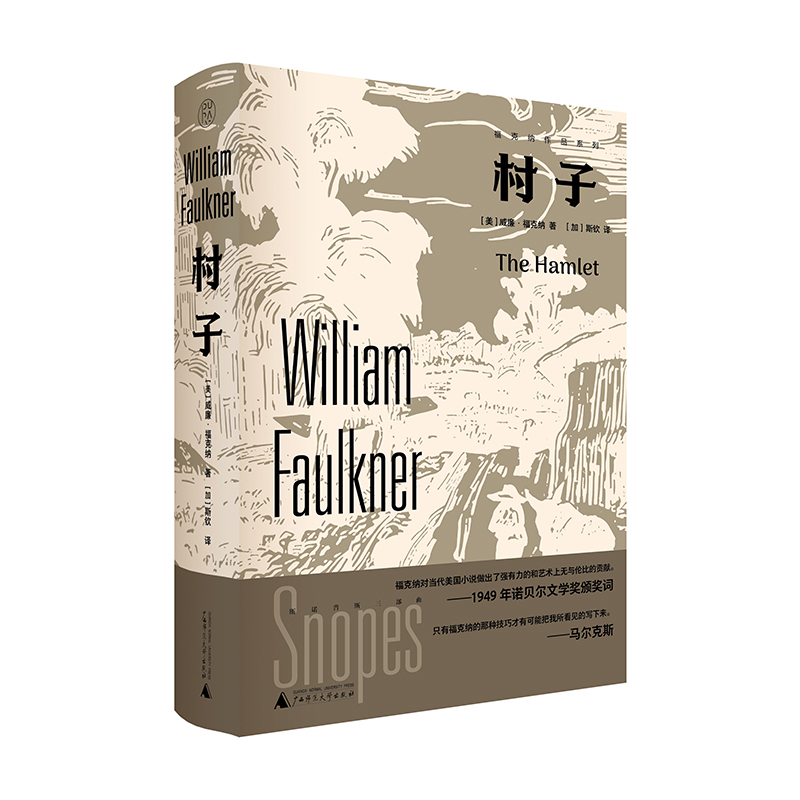
出版社: 广西师大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3.10
折扣购买: 福克纳作品系列 村子
ISBN: 978755987001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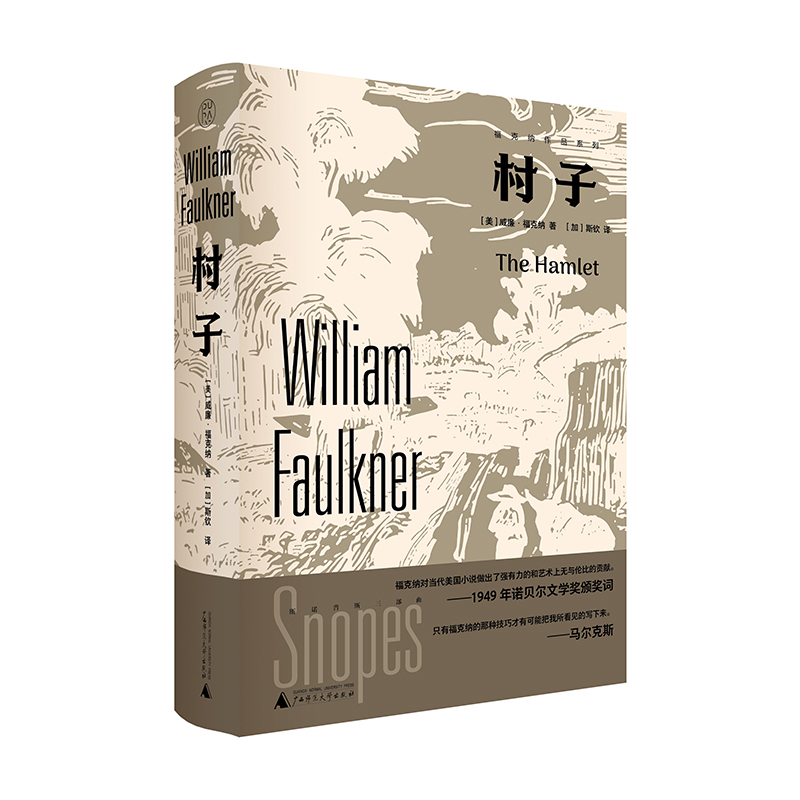
作者: 威廉·福克纳(William Faulkner,1897—1962),美国文学史上具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代表人物。1949年因“他对当代美国小说做出了强有力的和艺术上无与伦比的贡献”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福克纳以小说创作闻名于世,他为人熟知的诸多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讲述了发生在虚构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故事,被称为“约克纳帕塔法谱系”。主要作品有《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圣殿》《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等。“斯诺普斯三部曲”作为福克纳晚期作品,对“约克纳帕塔法谱系”的主题具有很重要的强化和升华作用。 译者: 斯钦,先后在澳大利亚悉尼大学以及加拿大的乔治布朗学院(George Brown College)和圣力嘉学院(Seneca College)学习,旅居海外多年。2018年至今翻译出版了《野棕榈》《婚礼的成员》《谁见过那风》《小镇艳阳录》《闲适富人的田园历险记》《伤心咖啡馆之歌》《两种孤寂》等作品。
第一章 当弗莱姆·斯诺普斯第一次来到瓦尔纳的店里当店员时,尤拉·瓦尔纳还不到十三岁。瓦尔纳有十六个孩子,尤拉是老幺,是家里的宝贝。她十岁时身高就已经超过她母亲,不满十三岁已经出落得像个女人,胸脯圆润,一点都不像青春期女孩儿或者少女那种小巧坚挺的胸脯。她的模样很容易让人想到酒神时代的象征物——阳光下流淌的蜂蜜,丰收的葡萄在山羊蹄子的践踏下汁液四溅的场面。这女孩儿似乎是一个生活在真空玻璃瓶里等着慢慢长大的女孩儿,天生带一种只有雌性哺乳动物身上才有的与世无争的懒散劲儿。 这一点她和瓦尔纳很像,虽然懒散在瓦尔纳身上体现为一种优哉游哉打发日子的姿态,但在尤拉身上,懒散成了一种实实在在的不爱动弹的特点。还在婴儿时期她就很少活动,即便活动,范围也仅限于从桌子到床,从床到桌子这么一小块地方。她很晚才学会走路,有了摇篮车后下地玩耍的次数就更少了。那辆摇篮车是方圆百里第一辆也是唯一一辆摇篮车,既笨又沉,几乎和一辆狗拉车一样大。尤拉躺在摇篮车里被人推来推去,她一天到晚躺在这辆车里,一直长到伸直两条腿车子已经盛不下了,必须由一个大人很吃力地从车里把她抱出来时,父母才强制性地戒掉了她对这辆车的依赖。不能坐婴儿车后她开始依赖椅子,一天到晚坐在上面。也许这姑娘从小就已经明白自己哪儿都不想去,人生的每一阶段毫无新意,每个地方也和其他地方毫无二致,所以养成了走到哪儿都要人抱的习惯。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她五六岁。那时候她母亲不愿意把女儿一个人留在家里,走到哪儿都要带着,于是她跟着母亲去了很多地方,说得更确切点,她其实是被家里的黑人奴仆背着去了许多地方。母亲,她,和那个背她的黑人仆人的身影常常以这样一幅画面出现在大路上——瓦尔纳老婆身披披肩,穿一件星期天做礼拜穿的衣服走在最前面,她的身后是背着尤拉的黑人仆人,因为身上背着一个人,黑人仆人走得有点艰难,而他背上背着的那个长胳膊长腿、腿脚当啷着悬在空中的姑娘就像一个被劫持的萨宾妇女 。 家人给尤拉买了很多玩偶娃娃。她把它们放在自己座椅旁边的椅子上,很少搬来搬去。玩偶们大同小异,看模样几乎没什么差别。瓦尔纳让铁匠仿照尤拉一到三岁时坐的那辆摇篮车的样子另外给她打了一辆小型摇篮车,专门让女儿放玩偶娃娃。新的摇篮车做工粗糙且看着一点都不轻巧,但对住在法国人湾的村民来说这是很了不得的事,因为以前他们可没听说过(更没见过)谁家会专门请人给孩子打一辆专门放玩偶娃娃的摇篮车!尤拉把娃娃全部放在那辆小型摇篮车里,自己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守着,但她很少摆弄那些娃娃。一开始家里人以为她之所以对那些娃娃冷漠可能是因为智力发育迟缓,要不就是她还小,还没朝着女人的方向成长,可是不久他们就发现真正的原因是这孩子根本不愿意动弹一下。 从一岁到八岁这段时间她几乎是在椅子上度过的,只有吃饭或者全家大扫除这样的事情才会让她从椅子上下来展展筋骨。在瓦尔纳太太的要求下,瓦尔纳让铁匠给女儿打制了几件迷你版的家庭用具——几把小扫帚和墩布,一台小铁炉——希望女儿可以用这些东西学习一下持家的本事,顺便多走走路。可是当他们把这些小东西放在她眼前时才意识到,这就像是给一个老酒鬼端来一杯冷茶,毫无作用。她很少找人玩,也没有形影不离的女伴,她似乎也不需要她们,在其他女孩儿身上常见的,为了团结起来对付和她们差不多大小的男孩儿或者大人而彼此之间形成的短暂亲密关系,在她身上从来都看不到。她只是懒懒地待着,样子让人想到待在母亲子宫里的胎儿。也许她出生时心智和肉体便彻底撇清关系,或者这两样东西根本不情愿结合在一起,所以选择了独自来到这个世界,而不是以相互陪伴来到世间并一同成长的方式;要不就是她的心智和肉体来到世间时已经发育得不对等,一方大一方小,大的把小的裹在里面。“没准儿这孩子长大了反而淘气得像个男孩子似的!”瓦尔纳这样说。 “长多大?”尤拉的哥哥乔迪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像是在冒火,很短,一闪而过。他就是这样,很容易被激怒。“像她这样长,哪个男人等她?等五十年吗?人不是橡树,可以等五十年,要我说没等到她缠上橡树,它已经烂了!被人当成柴火烧了!” 当尤拉长到八岁时,哥哥乔迪认为她该去上学,瓦尔纳夫妇也有这个打算,但什么时候送女儿上学,夫妇俩迟迟未定。瓦尔纳是村民推选出来的学校信托人(也许是因为这个原因,瓦尔纳才不反对送女儿上学),是学校里说一不二的人物,甚至可以决定法国人湾学校的存亡。在那些已经当了爹妈的村民看来,这间学校早晚都会成为瓦尔纳家的产业,既然这样,他们觉得瓦尔纳把女儿送到学校上学是早晚的事,再不济也会让他女儿在学校里待上一阵子。瓦尔纳人精一个,收租子算利息时一毫一厘都不会让,他怎么会错过利用自己在学校的地位让女儿上学的机会?瓦尔纳老婆对女儿上学这事儿倒是不怎么上心,作为这一地区最会持家的主妇之一,她孜孜不倦地打理着这个家,收纳熨好的床单被罩,整理货架和储存土豆的地窖,在熏肉房里悬挂鲜肉条,其他人很难从繁重的家务活中感到愉悦,但她却乐此不疲。虽然嫁给瓦尔纳的时候她多少识几个字,但还达不到能够阅读整本书的水平,因为底子薄,所以四十年过去,她没有养成一丁点读书习惯,她更愿意从活人嘴里听到对事件、传闻和消息的描述,然后自己添加点议论或者从道德方面评判一下。在这个女人看来,女人识字纯属多余,光凭看书做不出一手食材搭配得当的菜肴,佳肴美食是从实践里来的,是通过搅动勺子以及品尝勺子里食物的咸淡磨出来的。一个认为自己只有去学校学习后才能算清楚家庭开支账目的女人,永远都不是一名合格的家庭主妇。 尤拉八岁的那年夏天,他的哥哥乔迪突然对念书这事儿重视起来,他强烈要求自己的妹妹去上学,但是三个月以后他后悔了,而且后悔得很厉害。他不是后悔说服爸妈让妹妹上学,而是后悔坚持让妹妹上学导致他付出了代价。这代价太大了,大到他一辈子都对这件事耿耿于怀。尤拉从一开始就抗拒上学。不是因为上学就得和其他人待在一间屋子里而不想去,实际上她并不抗拒学习,这可以从她总共上了五年的学得到证明,不过,如果把她学到的知识折算成小时,再把小时折算成年月日的话,她从学校里学到的那点知识充其量可以折算成天数,而不是年月数。她抗拒上学是因为不愿走路,从瓦尔纳家到学校只有不到半英里远的路程,就这么一点路程,她也不愿意走着去。很多孩子住得比她远多了——他们的家离学校的距离是瓦尔纳家距离学校的三到五倍——但人家照样风雨无阻每天走着去学校,可尤拉不,她的理由很简单:不愿意走路。但她不吵不嚷,更不拳打脚踢又哭又闹地反抗家人的安排,而是不声不响地坐在家里的椅子上,脸上的神情像一匹倔头倔脑的小母马!而小母马的主人因为考虑到虽然现在这匹马因为年龄小还不值钱,但保不齐明年身价就一飞冲天,也不敢随便就用鞭子抽它。看见女儿这样,瓦尔纳大手一挥,劝自己老婆说:“那就让她待在家里!虽然在家她也懒得动动手指头,但看着别人干活儿也不是不能学到持家本事。反正我们也不指望她能为这个家做什么,只要她能平平安安地长大,找一个好心眼有本事的男人,跟着对方过日子就行!只要那人知道谋事儿,不给咱们和这个家惹麻烦就行,这比啥都强!如果女儿能找个有钱人就更好了!万一哪天乔迪吃不上饭了,沦落到去福利院生活的地步,还能指着他们拉他一把!她若是真找到一个有本事的男人,我和你就把房子、商店和家当交给他们管理,然后咱们两个放放心心地出去看世面去!最起码也去一趟圣路易斯,到世界贸易大会参观一趟!如果喜欢的话,我们就买个帐篷,多住几天!” 乔迪还是坚持让妹妹上学,尤拉还是负隅顽抗, 理由是她不愿意走路。她坐在家里的椅子上,不哭不闹,像一个柔弱的小女人,在她面无表情的脑袋上方,是她又吼又叫、吵得不可开交的母亲和哥哥。最后母亲决定让家里的黑人仆人(小时候总是他背着尤拉跟着瓦尔纳太太走乡串亲,只是这一次不是背,而是用马车接送)接送女儿上学。于是每天一大早,黑人仆人赶着马车走半英里的路把尤拉送到学校,然后等在学校外面一直到下午三点学校放学把尤拉接回家里。两个星期后这个办法被喊停,原因是瓦尔纳老婆认为这种做法好比把二十加仑的水生生烧成一碗汤,浪费巨大。她对儿子下了一道命令,说如果他非得坚持妹妹上学的话就得自己承担起这个责任,并提醒他说既然他每天都要骑着马往返于家和杂货店之间,完全可以捎妹妹一程,先把她送到学校然后再返回杂货店工作。母亲的提议自然引发了乔迪的抗议,他对着母亲又吼又叫,声言自己不同意这么做。一旁的尤拉还是不声不响地坐在那里,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但是之后的每个早晨,村民们看见尤拉手里拿着家里人给她买的油布书包坐在阳台上,等哥哥乔迪骑马接她上学。乔迪来到阳台边儿上,大声喊妹妹过来,尤拉站起身,走到阳台边缘,骑到马上。从此以后,接送妹妹上学的任务就落到了哥哥乔迪的肩上——他每天早晨把尤拉送到学校,然后回来做自己的事情,到了中午再去趟学校接她家,吃完午饭后再把她送到学校去,之后他便等在学校门口,一直到下午放学再把妹妹接回来。一个月后,乔迪决定不干了,他告诉妹妹自己只负责从店里骑马送她回家,她得自己走从学校到商店那两百码的路程。他以为尤拉会反抗,但出乎意料的是,尤拉很爽快地答应了。可是乔迪的这个方案只施行了两天就作废了。第三天下午,尤拉一条腿着地被乔迪夹在胳膊底下拖回了家,刚进家门乔迪就冲到正在客厅里干活儿的母亲面前吼道:“难怪她答应得那么痛快!难怪她同意自己从学校走到店里!”他的声音因为生气抖得很厉害,“要是你每隔一百码安排一个男人在大路上站着,她肯定能同意自己一个人走回家里!她就是只母狗!只要经过男人身边,她就不安分了!离着十英尺远你就能闻到她身上那股骚味儿!” “你少胡说八道!”瓦尔纳太太说,“少拿这种事烦我!是你非要她上学的!我养了八个女儿,个个都是正经姑娘!话说回来,一个二十七岁的单身汉比姑娘的妈还了解她的女儿,这话我也不是不明白!所以,如果你想让你妹妹退学的话,任何时候都可以,我和你爸不会反对。让你带的肉桂带回来了吗?” “我忘了。” “记着今晚带回来,我急着用。” 从那天起尤拉不再自己走着去哥哥店里 《村子》以法国人湾乡村为背景,讲述了弗莱姆·斯诺普斯利用一系列手段逐渐征服了代表南方文化的村子法国人湾的故事,较为传统的叙事手法交织着作者独特的对意象、想象、象征等方面的艺术表现,形成了颇具特色的艺术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