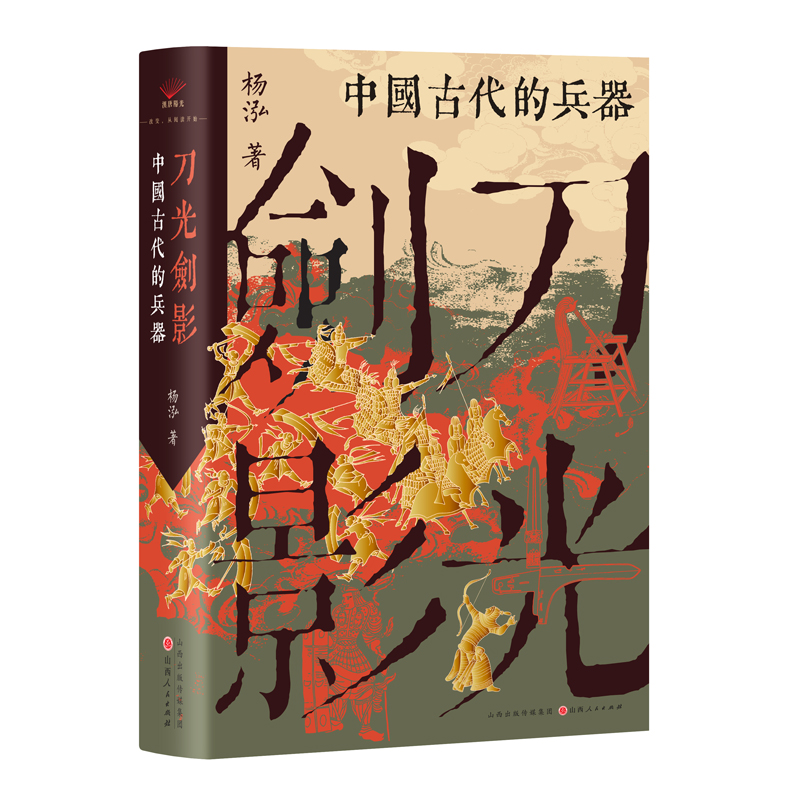
出版社: 山西人民
原售价: 98.00
折扣价: 64.27
折扣购买: 刀光剑影:中国古代的兵器
ISBN: 978720313466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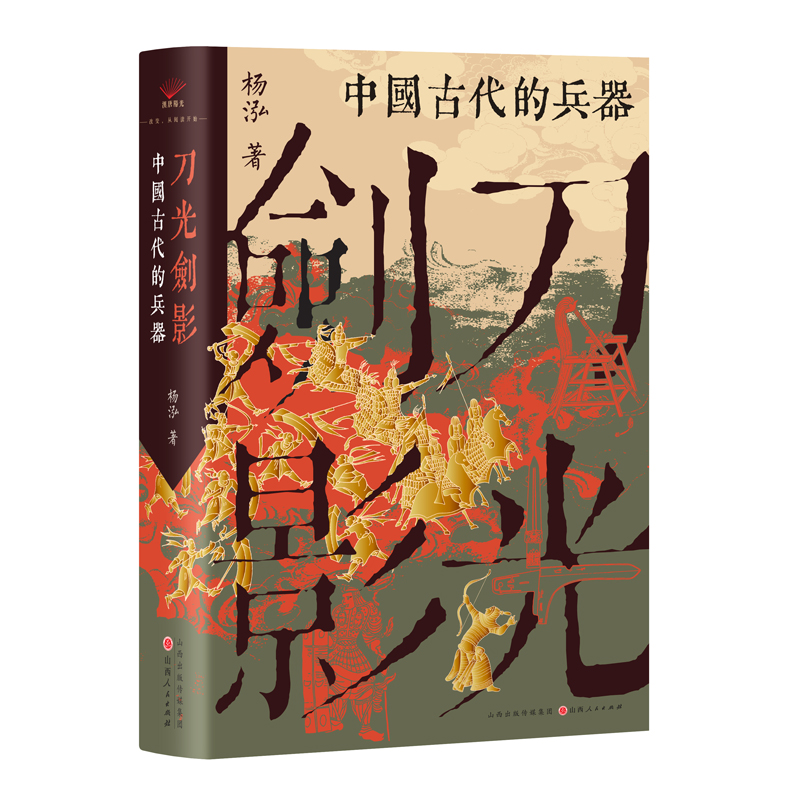
杨泓:1935年生于北京。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主要从事中国汉唐考古、中国美术考古和中国古代兵器考古的研究,其研究领域涉及古代物质文化史的方方面面,除了深耕兵器、车马器、家具器用外,对佛教文物、壁画、雕塑等也有非常研究。
步、骑兵的发展对兵器的影响 谈起东周时期步兵和骑兵的发展,必然要联想起“毁车为行”和“变服骑射”两则历史故事,而这两则故事又都是与对边疆的古代民族作战有关。 “毁车为行”,发生于公元前541年。《左传·昭公元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大原,崇卒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阨,以什共车,必克。困诸阨,又克。请皆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五乘为三伍。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为五陈以相离,两于前,伍于后,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由于山戎及群狄的军队是步兵,又在大原的山区作战,晋军战车兵的缺点暴露无遗,所以不得不采取魏舒的主张,临时放弃不适于山区作战的战车等笨重装备,让战车上的战士下车徒步作战。许多不肯放弃车上战士高于徒兵身份的人,以荀吴的宠臣为代表,不肯接受改为徒兵的命令,只有将他杀掉示众,才顺利地将战车兵改编成步兵,排成五个互相呼应的阵。狄人看到晋军临阵才把战车兵改成步兵,感到很好笑,结果轻敌致败,没等狄人排成阵势,就遭晋军迫近攻击,狄人大败。但这只是统帅依据战场地形及敌我态势,为了取得这一战斗胜利选用的权宜之计,出奇兵以制敌,并不是此后晋军就真全部“毁车为行”,撤除战车兵,改以步兵方阵为军队主力兵种了。所以认为这次战斗就是成建制组建步兵的开始时期,恐怕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很可能打败狄人以后,那些战车兵依然回到自己的战车上去,晋军仍是以战车兵为军队主力。迟于这次战斗几乎半个世纪,即公元前493年的铁之战,就仍是一场典型的车战。那次战斗中赵简子和为他御车的邮无恤和车右卫太子蒯聩的表现,则被认为是车战中三个乘员的楷模:“简子曰:‘吾伏弢呕血,鼓音不衰,今日我上也。’大子曰:‘吾救主于车,退敌于下,我右之上也。’邮良曰:‘我两靷将绝,吾能止之,我御之上也。’驾而乘材,两靷皆绝。”这也并不奇怪,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装备、编制、战术和战略,首先依赖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交通状况。这里起变革作用的,不是天才统帅的‘悟性的自由创造’,而是更好的武器的发明和士兵成分的改变。”当几十个分立的诸侯国终于兼并成了七个,中国历史迈入战国时期,社会性质不断发生变化,各国纷纷变法,核心内容之一就是要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仅靠士以上阶层组成的战车兵,直是步卒,还有水军和战船。当吴王夫差引兵北上争霸,主力亦为步兵方阵。因此适于步兵近战的格斗兵器——剑,以吴越所铸造的最为精良。 “变服骑射”,是赵武灵王于公元前307年开始实行的,目的是对付“三胡”,即东胡、林胡、楼烦。“三胡”都是善于驰马射箭的游牧部族。赵国原来的主力部队是驷马战车,笨重的战车难于对付轻捷的骑士,处处被动挨打。为了争取主动,赵武灵王不得不考虑学习敌人的长处,改变传统的上衣下裳的服制,改穿“胡服”,也就是脱掉宽袍大袖的袍子,穿上裤子与窄袖短服,以便于骑马射箭。赵武灵王欲胡服的主张,虽然得到楼缓、肥义等大臣的支持,但以公子成为首的王公贵族极力反对,赵武灵王力排众议,亲去说服公子成,终于出胡服令,组建骑兵,获得了对三胡、中山的战争的胜利。赵武灵王曾宣言:“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乐,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贤者察焉。世有顺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虽驱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但是赵武灵王最后的结局是颇为悲惨的,被公子成、李兑围于沙丘宫饿死。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以后,赵国军队的主力依然是战车兵和依附它的步兵。即使到赵武灵王变服骑射七八十年以后,名将李牧重组赵国军队时,还是以战车兵一千三百乘为主,以骑兵一万三千匹为辅,而在军队总数中,骑兵所占的比例也不过8%。终战国之世,骑兵的比例仍不多,前引苏秦、张仪等的说辞中所列各国军队,秦有兵员百余万,只有骑万匹;燕有数十万军队,只有骑六千匹。均不及兵员总数的1%。 战国时骑兵数量虽然不多,也没有成为军队的主力兵种,但作为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兴兵种,已经发挥着与其他兵种不同的重要作用。依仗轻捷迅速的特点,常常担负着突然冲击、迂回包抄、断敌粮道、追歼溃敌等任务。当时还认为“夫骑者,能离能合,能散能集,百里为期,千里而赴,出入无闲,故名离合之兵也”,认为“用骑有十利:一曰迎敌始至;二曰乘敌虚背;三曰追敌散乱;四曰迎敌击后,使敌奔走;五曰遮其粮食,绝其军道;六曰败其津关,发其桥梁;七曰掩其不备卒,击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烧其积聚,虚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系累其子弟”。同时为了加强主力部队的机动性,往往将车骑组编在一起,“轻车锐骑”配合战斗。在军事著作中,也开始有了关于骑兵的论述。竹简本《孙膑兵法·八阵》中就讲述了车骑参与战斗的情况,并指出根据不同的地形,兵力布置也应有变化,“易(平坦)则多其车,险则多其骑”。 骑兵的发展又与供骑乘的成套马具的完善分不开。但战国时期的乘骑马具还较原始,也显示着骑兵处于尚待发展的初始形态。在考古发掘中获得的有关战国时骑兵的形象资料,目前只有陕西咸阳塔儿坡秦墓(28057号)中出土的两件绘彩灰陶骑马俑(图4-7)。那座墓的年代估计在秦惠文王至秦武王时期,也就是公元前337—公元前307年之间,其时正与赵武灵王变服骑射相近。且秦人历史上善养马,又与赵国同样需对抗戎狄人的侵扰,出现骑兵自在意料之中。这组陶骑俑制工较古拙,但还能从其观察当时马具的一般情况,可以看出辔头由额带、鼻带、颊带构成,大致与当时驾车辕马的辔头相同,因缺乏细部刻画故未绘出马镳,但推测当时也是以铜衔与骨镳控御马匹。值得注意的是骑士直接跨在光背马上,并无坐垫,恐非失误忘绘,而是反映当时乘马马具尚较原始。在洛阳金村出土铜镜背面的骑士刺虎图像中,骑士蹲踞在马背上而非跨骑,且足作兽爪状,虽带有神异色彩,但马背上绘出鞯或坐垫,胸前有鞅带,较塔儿坡秦俑马具稍显完备(图4-8)。 正是由于战国时期,特别是到了战国晚期,随着步兵和骑兵的日益发展,生产大量适合于步兵和骑兵使用的兵器和防护装具,成为各国当务之急。步兵必须装备适合一个人体力负担,并能长途行军的兵器和防护装具,《荀子·议兵》所讲魏氏之武卒的装备,应反映着当时步兵的标准装备:“衣三属之甲,操十二石之弩,负服矢五十个,置戈其上,冠胄带剑,赢三日之粮,日中而趋百里。”至于骑兵,除了适于跨马战斗的成套马具外,还需要适于马上作战的格斗兵器和防护装具。格斗兵器要配合马上格斗而长短适宜,更要与马速冲击相配合。防护躯体的铠甲更要长短适宜便于骑乘,盾牌同样要求其尺寸和形制合于跨马战斗。原来供车上战士使用的成组合的长柄格斗兵器,以及厚重而长大的皮甲,都只适于在马车运载的条件下战斗,虽不适合徒步战斗,有些还勉强可转用于步兵,但那些供车战用的长柄成套青铜兵器组合,特别是长大厚重的皮甲,却根本无法转用于骑兵部队。改造已形成固定模式的车战兵器,十分费力。刚刚诞生的钢铁兵器,恰好与步兵和骑兵同时走上战争舞台,而且由于材质和制作技术等各方面的原因,主要靠锻打的钢铁兵器,很难与用铸模成型的青铜兵器保持完全相同的外貌细部特征。例如将铁剑锻成铜剑侧刃两度弧曲的形貌,就是一个难题。所以有必要对传统兵器的外形,进行适于锻制技术的修正。这种修正,恰好与当时各国极需大量装备步兵和骑兵的格斗兵器相契合,因此成批量生产的钢铁兵器,正是为了装备步兵和骑兵。从燕下都44号墓出土的人骨和兵器,可以看出那正是一处埋葬阵亡步兵将士的丛葬坑,出土的铁戟、矛、剑,外形已与同类青铜兵器有很大不同,正是适合步兵近战格斗的兵器。 1.当下很多古装影视剧中,尤其涉及战争场面时,都会有兵器,眼花缭乱,读了本书后,就会明白,这些奇奇怪怪的兵器都是今人的臆造。 2.兵器都是用在战争,所以了解了古代兵器,也就了解了古代战争。 3.本书内容除了涉及兵器外,对兵制也有论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