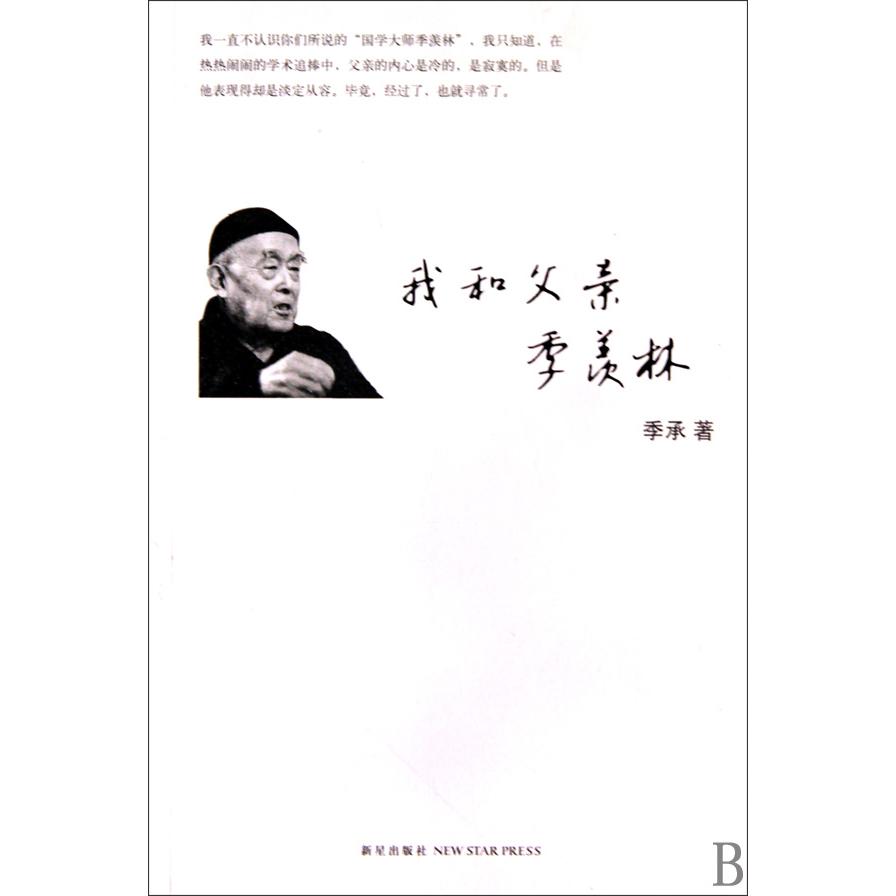
出版社: 新星
原售价: 32.00
折扣价: 22.89
折扣购买: 我和父亲季羡林
ISBN: 97878022592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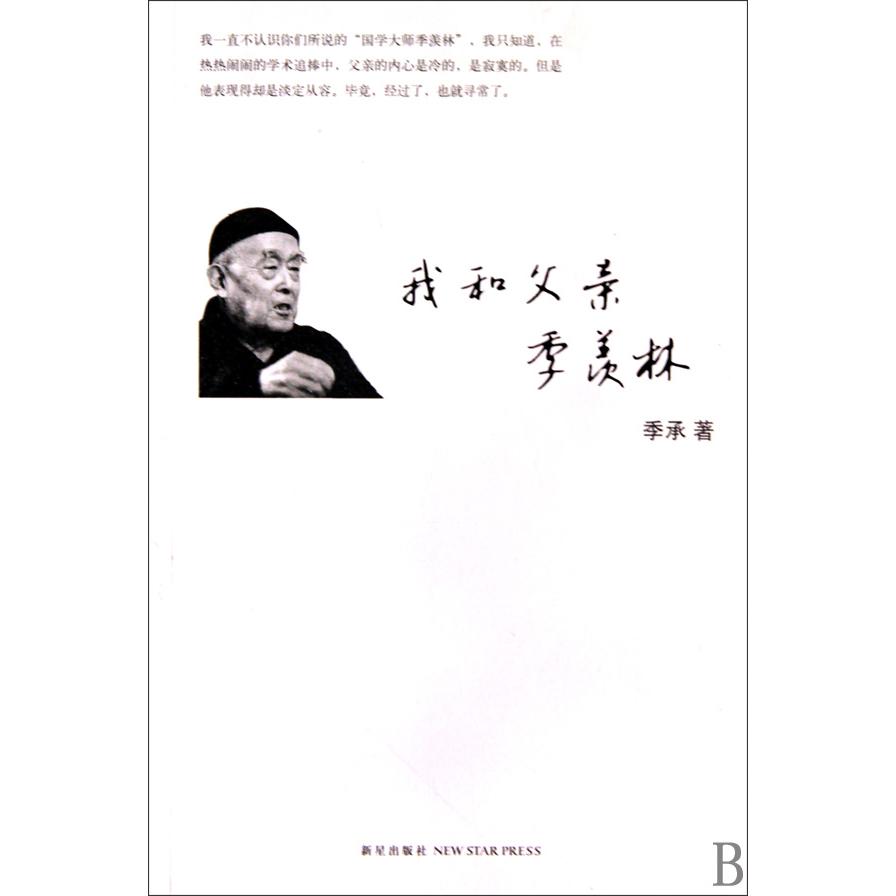
季承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高级工程师,曾任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建设指挥部领导人,中国新技术开发公司及中科院辐射技术公司总经理等职。作为首个中美合作项目“高能物理”的核心人物,1979年被派往美国,负责与美国五大高校的合作项目。 与李政道有近三十年的合作,并应李政道之邀曾任其主持的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顾问一职。并著有《李政道传》一书。 生活中,季承拥有另一个身份:学者季羡林之子。
当然,他那时候并不知道,不去邮局做职员,而去读大学,这一辈子的 前程就会大不一样。那时候,父亲虽然胸无大志,但也不愿意在邮局里度过 一生。当时,一般家庭大半不要求子女深造,读完了小学、初中,最多是高 中,就去谋个小职员的职业,最好是去铁路、邮局、税务、银行等部门,因 为那是“铁饭碗”,然后生儿育女,终了一生。当时,即便是当上职员,有 了工作,也是“混”日子。人们在街上相遇,除了问“吃了吗”,“哪儿去 ”,更多的是问“在哪里混”,现在听起来真是不可思议。 在清华大学凹年的学习生活,父亲没有详细地叙述过,但可以在他稀少 的叙述和《清华园日记》里了解到一些情况。他选择了西洋文学这一专业, 也以一篇论述德国诗人荷尔德林(F·Holderlin)早期诗作的论文取得学士学 位。父亲的日记里记载,他几乎每天都在读荷尔德林。因此,我对于父亲对 荷尔德林感兴趣,甚至以此作学士论文很好奇。为此,我去查阅荷尔德林的 资料,知道他是一位著名的德国抒情诗人,生活于18至19世纪。他的早期诗 歌受克洛普施托克和席勒的影响,洋溢着革命热情,多以古典颂歌体的形式 讴歌自由、和谐、友谊和大自然。但是他的价值却是在他去世一百多年后, 也就是20世纪中叶,才被发现的,那正好是父亲在清华求学的时期。 从这里可以看出父亲当时的思想状况。父亲那时也许正梦想着成为一个 诗人,恐怕也有一些革命热情,但是却没有投身革命的勇气和打算,否则, 他应该接受胡乔木的建议加入共产党。至于做诗入,父亲好像没有明确说过 。从他的日记看,读大学的时候,父亲没有写过什么诗,也没有做诗人的志 向,倒是开始写起了散文,并对自己是否会成为一个散文家有着憧憬。另外 从他一生写作的情况来看,除去生命后期的一首《泰山颂》之外,他从没有 再写过更不要说发表诗作了。这说明,父亲爱诗但不擅长写诗,有诗人的感 情但没有诗人的表达能力。所以荷尔德林的影子,在父亲大学毕业以后便消 失了。他虽然以《泰山颂》获得“世界桂冠诗人”的头衔,但大家都知道, 那只是一场误会。对于为什么爱诗又不写诗,最后也没成为诗人,我曾问过 父亲,我说,您那么喜欢荷尔德林,喜欢中外诗歌,为什么您没有写诗,没 有成为诗人?父亲回答,我太喜欢诗歌了,但写不好,不敢写,写散文比较 得心应手。 回过来再说父亲在清华大学学习的事情。对他产生深远影响的不是他所 选的西洋文学专业,却是外系的两门课程。一门是历史系陈寅恪先生(就“ 恪”字的读音我曾问过父亲。他说,陈先生在德国学习的时候,他自己填表 ,德文的拼音是“ke”,所以应该读作“ke”)的“佛经翻译文学”,是旁 听课;一门是中文系朱光潜先生的“文艺心理学”,是选修课。在读大学期 间,父亲在写作散文方面已有所建树,发表了《年》《黄昏》《寂寞》《枸 杞树》等文章,受到好评,但小说写得少。他和吴组缃、林庚、李长之被誉 为“文学四剑客”,文学天赋初露锋芒。四年清华园的学习,对父亲说来, 与其说是增长知识,不如说是开阔眼界,在众多人师级教师的熏陶下,他当 然想去做一个作家或文人,可是,摆在父亲面前的首要问题却是寻一份职业 ,养家糊口,维持家庭生计,回报其叔父婶母的养育之恩。至于当教授,他 连想都没有敢想过。 那时候,毕业即失业,找丁作是一大难题。父亲有幸谋得了济南高中国 文教员的职位,得以安定一时。一年的教师生涯,使他能够养家糊口,暂时 满足了叔祖父对他的期望,也使他初尝世事,体会社会的百味。中学教员的 薪水颇丰,但父亲却没有放弃出国留洋镀金的打算。他除了按月给家里一定 数量的生活费,还悄悄地积攒略费,打算以自己的力量实现出国梦想。谁也 没有想到,一年后,父亲通过考试成了清华大学与德国大学交换的一名研究 生,不久就到德国留学去了。 父亲和母亲于1929年结婚,1933年他们有了女儿婉如,1935年有了儿子 延宗。延宗就是笔者本人。1934年,叔祖母去世。1935年,叔祖父续娶陈绍 泽为妻,是我的第二位叔祖母。但是,我和姐姐‘直都叫她祖母或奶奶。这 里有一一个插曲,是父亲去世前不久才对我说的。父亲对叔祖父有看法,对 他这么快就续娶年纪比他小很多的女子一举不甚赞成,不愿意参加这一婚礼 ,所以在婚礼之前,便借口要去德国留学离开了济南。其实,当时离规定的 出发日期还有很长时间。父亲在从德国回来之前都没有见过这位婶母。十余 年之后,父亲从德国回来,得知婶母为维持季家生存立下了大功,顿时后悔 ,便写信称赞婶母是季家的“功臣”,从此开始了和婶母和谐相处四十几年 的漫长历程。 我们家的故事从这里算开了头,可一下子就没有了我父亲——他到德国 留学去了。谁曾想,他这一去就是十一年!父亲走的时候,我姐姐两岁,我 只有三个月。 在德国十一年的生活,父亲已有过较为详尽的叙述,我不再赘述。那么 ,在济南的我们这一家的情况怎么样呢?P15-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