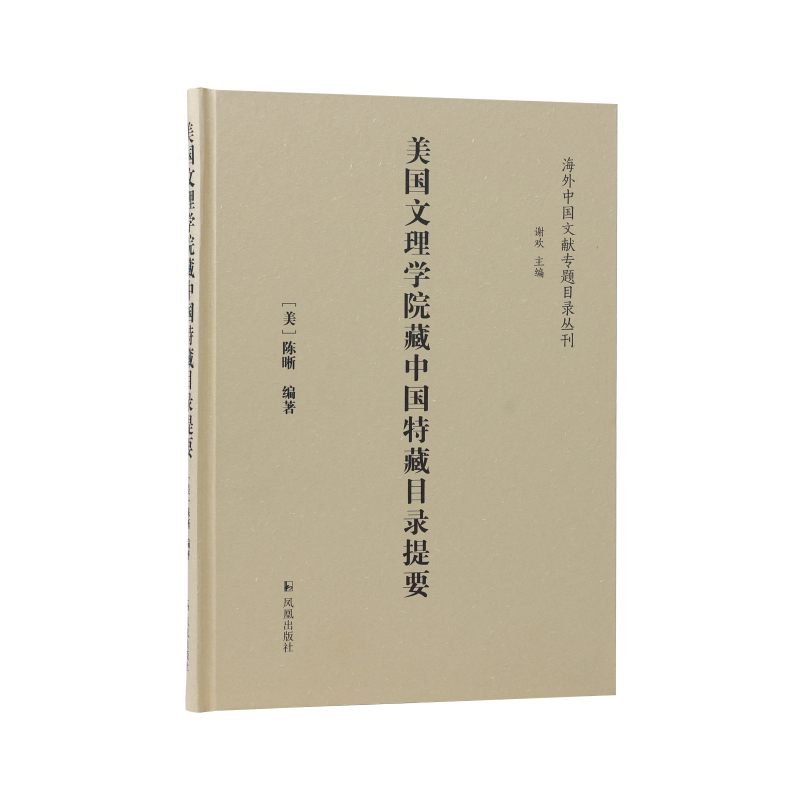
出版社: 凤凰
原售价: 168.00
折扣价: 114.30
折扣购买: 美国文理学院藏中国特藏目录提要(海外中国文献专题目录丛刊)
ISBN: 978755064106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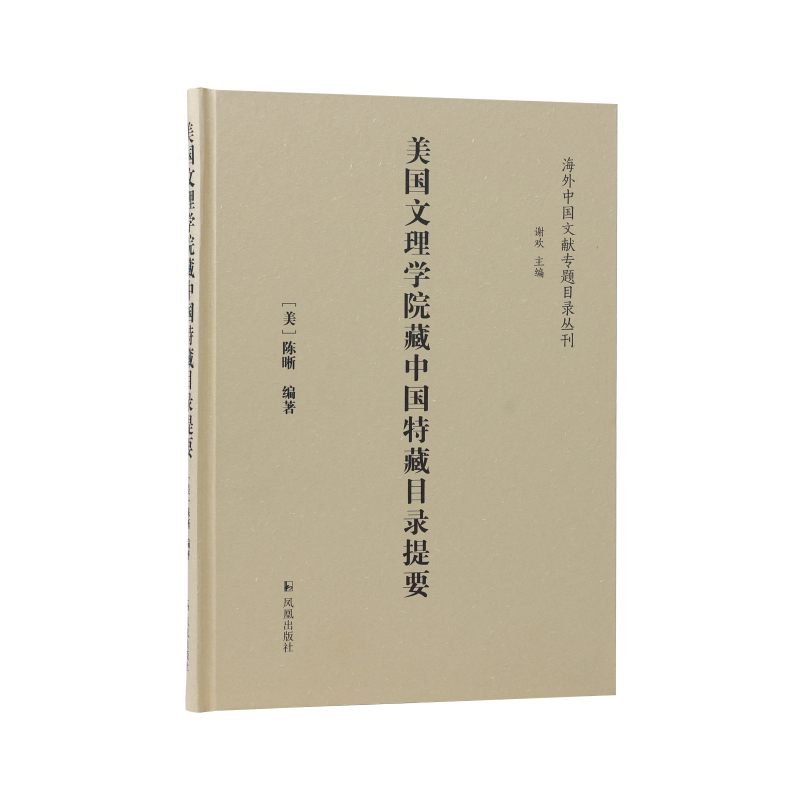
陈晰,任职于美国高校图书馆,主要研究方向为图书馆学、近代东亚史料整理与研究、中国近代社会史研究、版本学与目录学等。
(一) 海外中国文献的内涵及范围 所谓海外中国文献,是指在中国以外的与中国有关的各类文献,具体而言,在以下方面与“域外汉籍”有所区别: 1. 语种。除了汉文文献,还包含英语、日语、法语、德语、俄语等语种书写的与中国有关的文献。 2. 文献类型。相较于域外汉籍侧重于图书(或古籍),海外中国文献所涵盖的文献类型更为广泛。如按照出版形式划分,除了图书,还包括档案、期刊、报纸、舆图、学位论文等各类文献;按照文献加工程度划分,除了图书、期刊、报纸等一次文献,还有很多关于中国的书目、索引等二次文献;按照文献存储介质划分,可分为纸质文献、视听文献(如哥伦比亚大学收藏的近代中国人物口述档案),而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浪潮的加剧,在不久的将来,各种电子文献必将成为海外中国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 3. 年限。现有的域外汉籍界定通常都是以20世纪为限,对于20世纪以后的文献基本不予关注,而海外中国文献的年限范围则较长,时间跨度可以从马可·波罗—利玛窦时代即西方开始相对有系统地关注中国以来,一直到当下,这一时期产生的文献都属于海外中国文献的研究范围。 4. 学科覆盖。海外中国文献的学科范围较之域外汉籍更为宽广,在传统人文科学的基础上,延伸至各类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 (二) 海外中国文献的特点 从上述对于海外中国文献的定义及范围的界定可知,海外中国文献具有四个特点: 其一,以中国为核心。海外中国文献范围广、类型多、时间跨度长,但是其核心特征必须是与中国有关。何为“中国”?这是近年来学界的一个热点话题。从主权归属来看,“中国”是包括34个省级行政区的独立主权国家;从文化来看,通常而言,凡是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中国”。而海外中国文献中的“中国”,更多的是从文化角度来定义的,凡是内容涉及中国的历史、地理交通、风土人情、生活方式、宗教信仰、文学艺术、制度法律、语言文字等,都属于海外中国文献范畴。 其二,跨文化性。文献是文化的重要载体与表现形式,而海外中国文献,尤其是那些西人撰写的或者中国人用外文书写的文献,不仅是中国文化的延伸,更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融合的结晶,具有跨文化的属性。即使是那些纯粹的中文古籍,身处海外图书馆、档案馆,被用西方的方式进行收藏、分类、编目,其身上早也具备了所在区域的文化特征。 其三,多样性。从上述对于海外中国文献的语种、类型、年限的界定可知,海外中国文献具有多样性的特点,这一点自20世纪中后期以来尤为明显。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中国问题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2010年在接受采访时曾指出,到2010年左右,美国大学和智库大概有3000人在研究中国问题梁怡、王爱云:《西方学者视野中的国外中国问题研究——访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教授沈大伟》,《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4期。,这些人研究范围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其产生的文献在类型、涵盖范围等方面非常多样化,而这仅仅是美国在2010年左右的数据。随着全球化、信息化的发展,海外中国文献多样性的特征将会愈发明显。 其四,零散性。伴随着多样性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零散性,从上文对于海外中国文献文种、类型等的界定来看,海外中国文献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尤其是档案、舆图等,分布较为零散。除了明确以中国为主题的文献,还有相当一部分内容是分散在各种文献类型中的,如图书章节、期刊文章、报纸文章等。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美国报纸为例,在二战期间刊发了大量和中国有关的报道,这些新闻报道对于研究中国抗战以及二战时期的中美关系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这些新闻报道由于分布零散,给系统整理、研究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三) “域外汉籍”与“海外中国文献”的关系 从上文对于域外汉籍和海外中国文献的定义来看,域外汉籍无疑是海外中国文献的一部分,而域外汉籍研究同样也属于海外中国文献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两者还是有所不同。域外汉籍研究,其研究对象主要为汉文典籍,更确切地说是东亚汉籍,属于传统汉学(Sinology)研究范畴,其重点在于探讨中国文化对于东亚文化圈的影响,其本质反映的是学术研究从“中国之中国”走向“亚洲之中国”。而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中外各种交流的愈发频繁、紧密,传统汉学研究逐渐被更为广泛的“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所取代,海外中国文献研究在域外汉籍研究的基础上更加注重档案、期刊、报纸、舆图等资料,关注的重心也从“古典的”“单向式”的研究发展为“古今结合”“中外双向互动式”的研究。从某种程度而言,海外中国文献研究兴起的背后,折射出的是全球化时代的学术研究,即所谓“世界之中国”1901年,梁启超在《清议报》第90期、第91期发表《中国史叙论》(署名“任公”),其中在第91期刊发的该文第八节“时代之区分”中,梁启超提出了中国历史时代的三段划分,即“第一上世史。自黄帝以迄秦之一统,是为中国之中国……第二中世史。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第三近世史。自乾隆末年以至于今日,是为世界之中国”。梁启超在《中国史叙论》中提出的“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与本文所指含义有所区别,本文中只是借用梁启超提出的概念,表达中国学术研究之走向。 来自美国文理学院的珍贵中国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