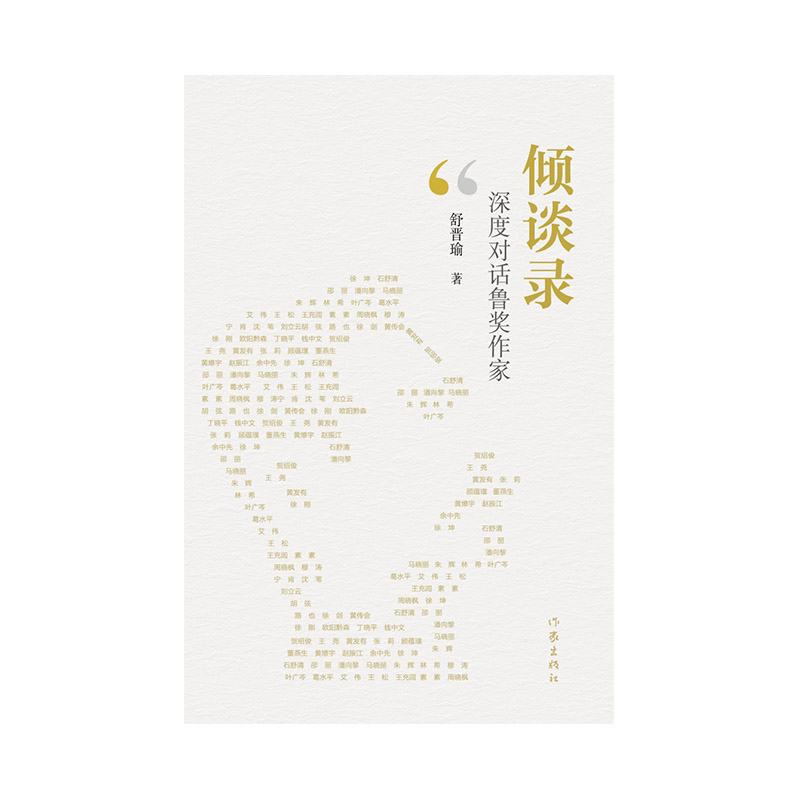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7.20
折扣购买: 倾谈录:深度对话鲁奖作家
ISBN: 978752122468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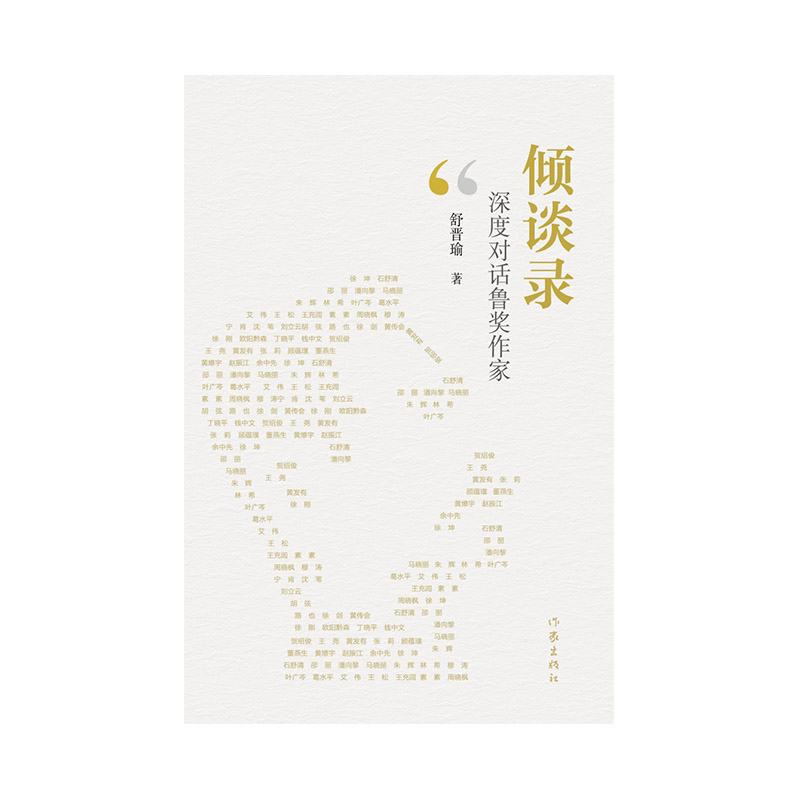
舒晋瑜,毕业于中国新闻学院。自1999年供职于光明日报报业集团中华读书报社。著有《中国女性作家访谈录》《风骨:当代学人的追忆与思索》《深度对话鲁奖作家》《深度对话茅奖作家》《以笔为旗:与军旅作家对话》《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等。曾获中国第六届报人散文奖、第四届丰子恺散文奖。
"与时代同行,为生民立传 徐坤 1965年3月出生于沈阳。作家,文学博士。现任中国作家协会《小说选刊》杂志主编,中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文化名家。已经发表各类文体作品五百多万字,出版《徐坤文集》八卷。代表作有《先锋》《厨房》《狗日的足球》《神圣婚姻》等。曾获老舍文学奖、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长篇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以及《人民文学》《小说月报》等文学期刊优秀作品奖三十余次。长篇小说《野草根》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7年十大中文好书”。部分作品被翻译成英、德、法、俄、韩、日、西班牙语。短篇小说《厨房》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 采访手记 “一直是短发,戴一副不断变换样式的眼镜,仔细看,她的短发讲究,总需要及时修理,打扮得利落而入时。她酒量大、酒品好,任何时候都是体面地坐在那里,比男子更有气魄……” 在作家邱华栋简笔素描式的勾画中,徐坤就这么生动地跃入眼帘了。印象中,徐坤总是笑眯眯的,说话不疾不徐,让人如沐春风。但是她的文字与思想日渐成熟,作品也在逐渐走向阔大与深沉。 徐坤是在写作中成长的。她评价自己年轻时的文章很幼稚,但有激情,敢冲撞,想当前锋,想射门,有快感;年老时的文章,技术纯熟,但倦怠,围着球门子转,兜圈子,看热闹,就是不往里进球,知道射门以后会有危险后果出来。 尽管这么说,她的作品还是陆续与读者见面了。2022年,八卷本的《徐坤文集》记录了徐坤从事文学创作三十余年的旅踪屐痕。文集囊括了徐坤的长篇小说四卷,中短篇小说两卷,散文及学术论著各一卷。徐坤将自己的第一部文学评论著作命名为《双调夜行船》,想必是因为学者和作家的双重身份。文学创作起步时,她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所的一名青年科研人员,短短两年时间,《白话》《呓语》《先锋》等中篇小说的问世,使她一度成为文坛熠熠生辉的明星。她研究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犀利地透视世纪末人文精神的衰落,叩问知识分子的灵魂,探寻欲望与挣扎背后的心灵,也温情款款地书写亲情、友情和爱情。 2022年年底,徐坤又出版了长篇小说《神圣婚姻》,是一部带有鲜明的徐坤风格的作品。读完之后,你会觉得,徐坤又回来了,那个写《厨房》《狗日的足球》的徐坤,那个洒脱智慧的徐坤,给我们讲述新时代的北京故事,讲得神采飞扬,讲得酣畅淋漓。小说探讨的主题切近生活肌理,不仅写出了知识分子的坚守,也写出了对市民阶层与城市精英、知识分子与海归青年遭遇的审视。小说融入了她丰富的生活经验、生命体验,富有魅力的叙述语言,张弛有度又简洁凝练的叙事风格。这也是她认真思考、呕心沥血打造的一部符合新时代特征的长篇,篇中每个人物小传,她都写下了几万字的笔记。 她希望充当寻常百姓的代言人,为生民立传,同时也希望能真实记录自己所生活的这个时代,记录世事迁徙和风起云涌的变革,以及其中的人心嬗变。 作家王蒙曾称徐坤为“女王朔”,其先锋姿态与女性视角令人耳目一新 问:您曾说过对自己影响最大的是随社科院同行下乡锻炼的那一年,回来就按捺不住地要写小说。能具体谈谈是怎样的影响吗? 徐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刚毕业进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一身学生气,带着年轻人成长过程中普遍的叛逆和冲撞精神。八十年代的结束和九十年代的开始,对于中国的改革开放进程来说,是一段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刚参加工作不久,我就随社科院的八十几位博士硕士一起到河北农村下放锻炼一年。远离城市,客居乡间,忧思无限,前程渺茫。在乡下的日子里,我们这群共同继承着八十年代文化精神资源的二十来岁的青年学子,经历浅,想法多,闲暇时喜欢聚在一起喝酒清谈,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看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播放中关村淘回来的各种国外艺术片,在高粱玉米深夜的拔节声中,在骤雨初歇乡村小道咕吱咕吱的泥泞声里,凌虚蹈空探讨国家前途和知识分子命运,虽难有结论却兴味盎然。回城以后,这个小团体就自动解散,然而,在乡下探讨的问题以及与底层乡村民众打交道时的种种冲突和遭际却一直萦绕我心,挥之不去。终有一天,对世道的焦虑以及对于前程的思索,催使我拿起笔来,做起了小说——相比起“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做学问方式,激情与义愤喷发的小说更能迅捷表达作者的情绪。 问:中篇小说《白话》让您一举成名,《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等刊物几乎同一时间刊发您的系列小说。您如何评价那一时期的创作风格? 徐坤:在1993—1994两年间,我以《白话》《先锋》《热狗》《斯人》《呓语》《鸟粪》《梵歌》等一系列描写知识分子的小说登上文坛,文化批判的锋芒毕现,又都是发表在《中国作家》《人民文学》《当代》这三家大刊物上的,立即就引起了读者和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年轻时的写作,十分峻急,仿佛有无数力量催迫,有青春热情鼓荡,所有的明天,都是光荣和梦想。仿佛可以乘着文字飞翔,向着歌德《浮士德》中“灵的境界”疾驰。 问:《先锋》刊发于1994年第6期《人民文学》时,评论家李敬泽首先以“欢乐”形容它,说“如果说以艰涩的陌生化表现世界并考验读者曾是一种小说时尚,《先锋》对世界、对读者却摆出了亲昵无间的姿态”。评论和作品相得益彰,读来特别过瘾。您还记得当时作品发表后的情景吗? 徐坤:相当激动!接到通知稿子采用后,就天天等着《人民文学》第6期出刊。那时我在社科院亚太所工作,住在学院路,总去学院路的五道口新华书店看看杂志到了没有。前一次去五道口书店还是排队去买《废都》。5月底的一天,终于看到了有卖,只剩下一本了。赶紧买下来,拿起杂志一翻,哇!第6期整个卷首语都说的是《先锋》啊!天哪!我只是个新人哪!我还是第一次上《人民文学》啊!我是投稿过去的啊!跟他们一个人也不认识啊!这是谁写的啊!这么会写,表扬得这么的好!激动得我啊,立刻,骑着自行车就直奔了王府井新华书店,因为知道那里的书报杂志到得多。十多公里的路,没多久就骑到了,也不觉得远。到了王府井书店,一下子买光了店里的三十本刊物!那时的杂志是三块钱一本,花了我九十块钱,差不多是一个月的工资。 问:那时候人们对文学的虔诚和激情,很令人羡慕啊! 徐坤:是啊!那期的卷首语,我几乎是能够背下来,还曾一笔一画抄到了本子上。后来才知,是个跟我一般大的年轻人写的,叫李敬泽,刚升任了小说组的主任。那是他写的第一篇卷首语,“《先锋》是欢乐的;如果说以艰涩的陌生化表现世界并考验读者曾是一种小说时尚,《先锋》对世界、对读者却摆出了亲昵无间的姿态。它强烈的叙述趣味源于和读者一起开怀笑闹的自由自在;它花样百出的戏谑使对方不能板起面孔……”寥寥六百字,将近三十年,关于《先锋》的评论也有千百篇了,我认为竟没有一篇能超过它。 问:王蒙先生说您“虽为女流,堪称大‘侃’;虽然年轻,实为老辣;虽为学人,直把学问玩弄于股掌之上;虽为新秀,写起来满不论,论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您是怎样理解的? 徐坤:那是王蒙老师发表在1994年《读书》杂志“欲读书结”专栏上的文章。我理解他的本意,一是震惊,刚进入九十年代没几天,年轻人写的东西已经变成这样后现代了;二是希望文坛多出几个王朔,不管是男的还是女的,都能够以年轻的话语,冲撞的身姿,把进入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坛特殊的沉闷的日子捏出个响来;三是希望年轻写作者除了戏谑、解构、嘲笑外,能不能再稳健庄重些,能有一些建构的思想意见表达。他的话让我深受教益。从此以后就逐渐收敛起锋芒,努力在文章中做一些文化建设性的工作。 在北京作家协会期间,对于徐坤是创作上的拓展和深化。《野草根》《八月狂想曲》等都是这一阶段完成的 问:早期的写作,您以知识分子题材为主,后来您写《厨房》《狗日的足球》《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爱你两周半》《野草根》等,不断关注着女性的生存状况,书写她们独特的生命体验。这种转变的契机是什么? 徐坤: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刚开始写小说那会儿,不考虑男女,只是按先贤先哲大师们的样子,追寻文学审美的传统精神之路,写《热狗》《白话》《先锋》《鸟粪》,写我熟悉的知识分子生活,探究人类生存本相,相信能成正果。后来,某一天,女权主义女性主义潮涌来了,急起直落,劈头盖脸。忽然知道了原来女性性别是“第二性”,西蒙娜·德·波伏娃告诉我们,子宫的最大副作用,是成为让妇女受罪的器官。 《厨房》写于1997年,距今已经有二十七个年头。依稀能记得,原先想写的是“男人在女人有目的的调情面前的望而却步”,写着写着,却不知最后怎么就变成了“没达到目的的女人,眼泪兮兮拎着一袋厨房垃圾往回走”。之后,《厨房》的主题给批评家演绎成了“女强人想回归家庭而不得”,所有同情方都集中在女性身上。 《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写于2005年,距今也已经十九年。2005年的夏季,不知在哪家厨房待腻了钻出来放风的那么一对男女,开始在大庭广众之下的居民区的午夜广场上发飙。他们把社区跳健身舞的街心花园广场,当成了表演弗拉门戈、拉丁、探戈舞的舞台,男女每天总是着装妖艳,嘚瑟大跨度炫技舞步,像两个正在发情的遗世独立的斗篷。最后以女方在大庭广众之下摔跟头收场。 问:您有没有想过把《厨房》和《午夜广场最后的探戈》两篇小说放在一起比较一番? 徐坤:《厨房》和《探戈》是两篇中间跨度有近十年,却又横亘了两个世纪的小说,前后放在一起考察时,连我自己也不禁悚然一惊!十余年来,竟然用“厨房”和“广场”两个喻象,用“拎垃圾”和“摔跟头”的结局,把女性解放陷入重重失败之中。小说的结局都不是预设的,而是随着故事自己形成的。但愿它不是女巫的谶语,而只是性别意识的愚者寓言。 十年一觉女权梦,赢得人前身后名。乐观一点儿想,“厨房”和“广场”的意象,如果真能作为跨世纪中国女性解放的隐喻和象征,二者的场面也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不光活动半径明显扩大,姿态和步伐也明显大胆和妖娆。如果真有女性的所谓“内在”解放和“外在”解放,我真心祝愿二者能够早一天统一。既然,中国女性的解放之路,从“厨房”已经写到了“广场”,那么,下一篇,是否就该是“庙堂”了呢? 《野草根》被评价为女版的《活着》。三代女性始终在生活的夹缝中挣扎奋斗、狂欢跳跃,如风中摇曳的野草生生不息 问:您的长篇小说《野草根》被香港《亚洲周刊》评为“2007年十大中文好书”,这部作品在文坛获得诸多好评。 徐坤:当年这部小说被评为“2007年十大中文好书”,但在今天看来价值也是被低估了。《野草根》堪称女版的《活着》。小说讲述的是那个动荡年代,三代女人在各种艰苦环境下的坚持与隐忍、不断与命运抗争的故事。知青于小顶、于小庄与后代夏小禾三个女人的卓绝成长与红颜薄命,围绕她们身边的男人们的暴戾、颓败与倾情,构成广袤东北大地上四十年的最为壮观的风俗风情画和最为激越的命运交响曲。 作品的地域背景放到我的出生地东北沈阳,时间跨度则从“文革”知青下乡到当下,笔触深入底层女性的成长、情感、事业中,而真正的指涉却是对女性命运的观照。不管命运如何多舛,三代女性始终在生活的夹缝中挣扎奋斗、狂欢跳跃,她们宛如那随风摇曳的野草,根系深深扎在泥土里,生生不息,盎然丰沛。 问:我觉得《野草根》书中的情节、东北风俗,根据梁晓声同名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人世间》很相像——如果拍成像《人世间》那样的电视剧的话,您觉得谁来演合适? 徐坤:要说合适的演员,那得首推俺们大连姑娘秦海璐,长着一双桃花眼的周迅,老戏骨宋春丽,风头正健的抚顺小伙于和伟。《野草根》有望成为继电视剧《人世间》之后,又一部打动几代观众的爆款剧目。 第一,“时代·女性·命运”是这部《野草根》最为重要的主题;第二,“挣扎,奋斗,不屈”是这部《野草根》最强大的主基调;第三,“人间百态现实,时代变革发展”在剧中有最好的体现;第四,浓郁的东北风情,催人泪下的年代故事,三代女性的命运,吸引老中青三代观众有沉浸式观影体验;第五,绝世独立的大女主、红颜薄命的女配、桀骜不驯的女新新人类、刚愎强悍的东北老太太……这些人物形象,都给演员表演提供了极大的空间。 问:《野草根》以追忆和倒叙的方式讲述一个家庭三代女性的故事,折射近半个世纪里残酷的女性命运。这部作品的创作源于什么? 徐坤:2006年五一长假,我应邀回沈去看沈阳世博园,也顺路回家探望父母。回来的路上,表妹为让我多观些风景,特意多绕了些路,将车子一路从棋盘山和东陵山间的森林里穿过,最后竟将车子拐到了东陵山野的墓地上,说这儿离姥姥姥爷的坟不远了,我领你顺道去看看吧。 她的姥姥姥爷也就是我的爷爷奶奶,我们徐家去世的几个亲人都葬于此。这还是我头一次在这个季节里来扫墓。一见到奶奶那座栽着柏树的坟我就哭了,泪如泉涌。手抚着墓碑,是热的,似觉有奶奶的体温在上面,分别之日竟像昨天!那一刻我真觉得奶奶好像还活着,她知道我们来看她,也能听到我们在跟她老人家说话。我和小表妹都是奶奶一手带大的,我在奶奶身边一直长到十五岁,考进辽宁省实验中学后才住校离家,对祖母的感情远胜过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我总是在思乡的梦里和她老人家频频相见……那天的墓地方圆几十里几乎没有人,静寂无边。只有隐约的远山、青葱的绿草、夏季的风声和脚下的坟茔与我们为伴。站在芳草萋萋一望无际的墓地,我的心里霎时涌起无尽的惶惑和迷茫,生与死的问题头一次如此鲜明地涌上心间。 我当时想的问题跟《野草根》书里夏小禾想的并不一样,我想的竟是:再过几十年,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我也不过就是回到这里来吧?到时候也埋在这里的祖母和亲人们的身边化作一抔黄土吧!那时候埋葬我的是谁?又会有谁来扫墓看望?二十年或者三十年是个很快的时日,倏忽即逝,很快就来。那么,我们如此辛苦地打拼奋斗又有什么意思?活来活去的意义究竟何在? 回北京后,我仍然久久不能平静。就这样,原本要做的有关世博园的欢乐文章被搁下了,我开始写《野草根》,写生与死,写底层人民蓬勃的生命力,写中国人生生不息的生命哲学中的原动力。 问:您为什么选择知青一代和她们的子女的故事来写? 徐坤:《野草根》因为沈阳而引发创作联想,通篇又是以沈阳为背景展开,主要线索就是于小庄母女二人的命运。书中设计了一个生命的轮回:让知青于小庄在二十九岁芳华死去,如今站在墓前悼念她的女儿夏小禾也恰好是二十九岁。 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年龄段的人来写?因为我考虑到在当下中国的人口成分构成中,知青一代人和他们的子女们正构成中国社会的基本力量。我重点要写的夏小禾这一代“新新人类”一族的生存状态,由此而上溯,先定下夏小禾的年龄身份,然后逆向推理,找出她的母系家族谱系,由此带出了母亲、姨妈、外婆这几个主要人物以及附带着的一些男人。然后选择从母亲于小庄下乡的1968年写起,将近四十年的时间跨度,写了三代生活在底层女人的命运。 2001年,徐坤的《厨房》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它像一首悲歌,却只能在如水的夜晚任热泪汹涌 问:您的《厨房》在2001年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还记得当时获奖的情景吗?您知道这篇作品参评吗? 徐坤:当时的鲁迅文学奖,才是刚设立这个奖项的第二次评选,动静还没有闹得今天这么大,报得很安静,我自己也不知道谁给报的奖,应该是首发这篇作品的《作家》杂志报的吧。 问:关于当年鲁奖评选,您还知道些什么? 徐坤:啥也不知道。那时候风气很正,大家对文学都怀有一颗初心,评奖就是评奖,安安静静,公公正正。" " 一位优秀的记者,首先应该是一位优秀的读者,最好还是一位优秀的学者。晋瑜符合这两个标准,她不仅研读了大量文献,而且对采访对象的“底细”了如指掌,提出的问题质量很高,具有挑战性,真正让采访变成对话。 ——全国政协副主席、民进中央党务副主席 朱永新 舒晋瑜并不完全以记者的身份在采访,更多是以研究者的身份介入其中,给予作家高度的理解和同情,她的访谈呈现了作家们丰富独特的内心世界,也有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整体把握。 ——中国作协党组成员、副主席、书记处书记 吴义勤 晋瑜所做的事情,简缩成一句话,其实就是在发现好书和好作家。她打通了新闻报道和文学评论之间的通道,成为中国文坛最热心最深情的一个关注者,成为中国文学事业发展的一个积极参与者。 ——作家 周大新 舒晋瑜无疑是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对话第一人,无论是她对话对象的范围,还是对话话题的延伸性,以及与之完成对话的人之数量,几乎都无人能及。更重要的是,她视对话为评论的一种特别形式。一种“我与你”交相呼应的方法,一种现代评论谱系中被忽视的日常,在对话中被重新拾起。 ——诗人、评论家 何向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