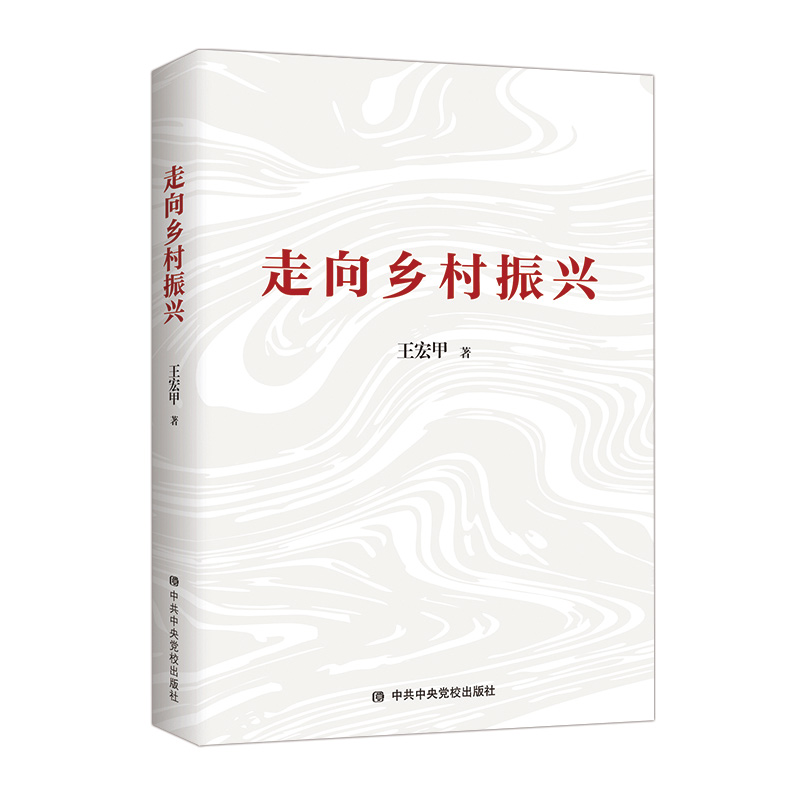
出版社: 中央党校
原售价: 68.00
折扣价: 41.30
折扣购买: 走向乡村振兴
ISBN: 978750356998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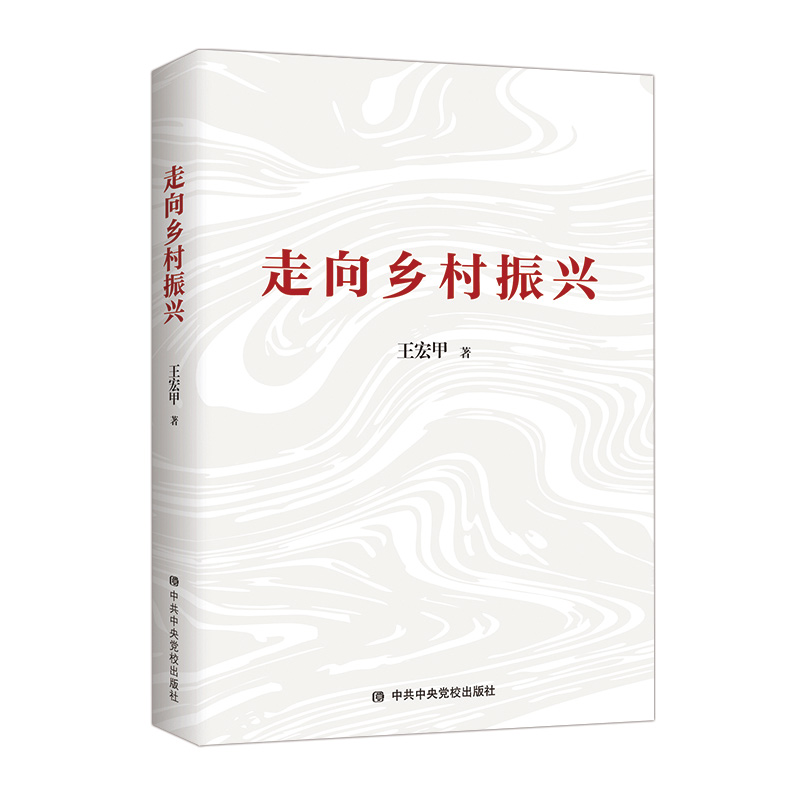
王宏甲 当代文学家、著名学者。福建南平建阳人。中国作家协会报告文学委员会副主任。1993年起享国 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中宣部全国宣传文化系统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曾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鲁迅文学奖、徐迟报告文学奖、冰心散文奖、中国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等。著有《中国天眼:南仁东传》《世界需要良知》《让自己诞生》等作品。
青年就是前途(节选) 张凌回来了! 他会留下来吗? 眼里是漫山一片片高矮不齐的苞谷,枯黄的。他知道今年又是关键时候遇旱,靠天吃饭的苞谷没有收成,苞谷秆还那么凄凄地立在地里。这是2014年底,这是他的家乡。 家乡名叫箐口村,属毕节市大方县猫场镇。猫场镇还是明初奢香夫人主政时设的赶集乡场。大方那时候是贵州宣慰府所在地,奢香夫人是最高长官。她按十二生肖给辖区的大村设赶集日,有赶马场、赶牛场、赶虎场……虎猫同科,日久乡民觉得虎不如猫亲,把虎场改成了猫场。奢香夫人设赶集日使村寨有了商品交易的场所,设赶集日的大村也变成了镇。 张凌生于1985年,童年时跟一群“爹在外打工的”孩子玩。他长到八岁,娘送他去读一年级。村里有小学。小学有瓦房,一共两间,大约四十平方米,分四个班上课。这是1993年了,小学校年久失修,一下雨,屋顶要用塑料袋(不是塑料布)补漏。下大雨,水漫进教室,张凌和同学们都穿着破解放鞋站在水里听课。老师也站在水里。 没有课桌。一块木板,两边架着砖头,课本就放在木板上。凳子是砖头垒的。在这环境里他读完了六年级。接着到猫场中学读了三年初中,再考到另一个乡的中学读了三年高中,然后奇迹般考上了大学。录取通知单,是去猫场赶集的亲戚带回箐口村的。那天,张凌还在山坡上跟爹一起拾掇苞谷地。 “张凌考上大学了!”消息传遍全村。箐口有八个自然村,那挺远的自然村也有妇女抱着孩子来看张凌,看他的大学录取通知书。 “我们张凌中状元了!”这可是箐口村开天辟地的事。 张凌的爸妈招呼着挤到屋里来的乡亲,家里的碗不够盛水招待客人,就用水瓢打水直接给客人喝。山里的狗也知道发生了喜庆的事,远远近近地跑来在屋里进进出出。 乡亲们走后,天黑了,张凌的爸妈发愁了,上大学要钱,缺钱咋办……爸妈早就存钱了,存啊存,存了多年,有两千多块钱了!在爸妈看来,这有好多钱了。可是通知书上说,学费要6000元!上学还要吃呀,上哪去找这么多钱? “幺……”爸的声音在黑暗中说,“不读了吧,咱读不起。” 次日天蒙蒙亮,张凌就坐在苞谷地里看天空。双脚踩在雨水里做作业的童年一幕幕闪现……还记得高考完了不敢想能够考上,马上回村到地里干活,可是……他惦记着日子,离9月开学不到十天了,他感觉没希望了,突然录取通知书来了,他眼泪都出来了。可是现在……家里有一头牛,卖了牛,家里耕地咋办?不行。再没有别的可以卖了。亲戚们也都穷。无论如何找不到这么多钱……太阳出来了,他还在苞谷地里坐着。 “幺。”妈的声音。他没有察觉到妈已经走到他身边了, “幺,好歹也念不少书了。别怕,打工去。” 他知道妈在家里什么都能干,什么都不怕。他也想到了打工,村里那么多人都去打工了。他站起来,跟妈回去了。 “张凌不去念大学,要去打工了。” “为哪样?” “没钱念。” 这消息再次传遍全村。村里人再次来到他家。最先来的是一个老太太,看去老,只有60岁。她拿出一个折叠得很小的东西,打开是一张十元的人民币。她拉过张凌的手,放到他手里:“幺,带上。” “我永远都记得她那天的眼神。”张凌说,她只说了三个字,是那种不容你不去念书的语气。他不知道她的姓名(后来张凌要在本子里补记上她姓名的时候,才知道她叫谢发秀)。 接着来的乡邻把5元、10元、3元……最多的30元,放到他家的一张破桌上。两天时间,乡亲们捐了2600多元。 读了这么多年书,就这两天,穷乡亲给张凌打开了一个从前没看到的世界。家乡,家乡,从那时起他再忘不了这是他的家乡! 仿佛不容你自己选择,仿佛这不是你自己的事,这是村里人要你去上大学!爸妈要重新考虑儿子的上学问题了。 爸说:“猫场还有亲戚,再去借点,凑上。不行就卖牛!” 张凌有三姐弟,姐嫁人了。弟弟张梁出生于1990年,才读完初二。妈把小儿子叫到跟前:“幺,你念书不如你哥,别念了。十六岁了,你去打工供你哥上学。” 就这样定了。 离村那天,村里许多人都来送行。张凌穿一件妈洗得干干净净的衣裳,那是爸从猫场镇上的铺子里花19块钱买来的。 张凌告别家人和乡亲,踏上去读大学的路。山路两边,漫山的苞谷一步步留在身后。一路上,他泪流满面。 村里距离大方县城有65公里,他走到猫场镇,坐中巴到了县城;再坐大巴四个半小时到遵义。遵义有火车,他上了绿皮火车,没坐票,蹲在厕所间门口,火车走了38个小时才到北京。 他离家的时候,爸没卖牛。但他走后,爸就把耕牛卖了,养起两头母猪,让母猪下崽,卖小猪崽供他的生活费。弟弟也离家跟人去浙江打工,搞模具,不久右手被压碾,拇指、食指、中指都没了,无名指和小拇指也严重畸形。这件悲惨的事,他很久以后才知道。弟弟获赔了8万元。爸用这笔不幸的钱,除了继续给小儿子治手,就用于支持大儿子读完大学。 大学四年,他只回家一次,寒暑假他都去打工。看到弟弟那只残废的手,他落泪了,下决心今生一定要与弟弟同甘苦。 2010年大学毕业了,他找不到工作。睡过大街大单位的门洞,睡过地下通道。身无分文了,一连三天没吃饭了。不得不卖手机。他有个长虹牌手机,卖了80块钱,买馒头吃,喝自来水。喝着自来水,他想,读了一肚子书,现在比来上学时还穷。不行,不能让读的书荒废。继续找工作,找到了一家私企打工。 “北漂了一年。”他说不是没想过回家,可是回家能干什么。想到离家那年爸妈乡亲期望他要有出息的目光,他两手空空怎么回家?大学时他读物流管理,有一门课程《市场营销基础学》,他对其中的“借鸡下蛋”“白手起家”很感兴趣。2011年底他回贵阳与贵阳的一个人合伙开了一家做营销策划和广告的公司。 “我是无产阶级,只能走这条路。”2012年11月他自己开了个独立的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两年都没有挣到钱,“只是挣了曲折,挣到经历。” 但是,曲折、经历和磨难都是有价值的,因为贯穿了奋斗。应该说,大学所学是有用的,毕业后他进了更为有用的“社会大学”。张凌说他用了一种术语叫“饥饿营销”的方法,2014年1月12日,他的团队在遵义市凤冈县卖海尔电器,三小时卖了400多万元。13日,在兴义市又是三小时卖了400多万元。至此,他的“营销策划和广告”获得突破性成功。这一年把营销做到了省内外多地。他赚到了钱,用160万元在贵阳市买了房,还买了车。 这年12月26日,张凌把小车开回家乡来了。从猫场镇到箐口村还是泥巴路,天下雪了,雪化了路上都是泥泞。车开到距离村子还有七公里的地方,实在进不去了。只好打电话让村里人来帮忙。村民来了,来了一群。 雪停了,风呼呼地刮着山路两边林子里的树叶。崭新的小车和烂泥路,十四个小伙子,用绳子把小车拉进了村。 2017年9月,我初次到箐口村。站在它高高的山岗上,我想我看到了张凌那年的抉择确实难。我走过很多山村,第一次知道了不能用“漫山遍野”来形容这个村,因为它只有山,没有野。 全村最大的一块平地只有三亩,也只是相对平。没有河,也没有小溪。如果说有,从村外小路一个拐弯处看下去,能看到它在很深很深的山谷下,去山谷下挑水要走两个小时。这样我就理解了张凌说的:“吃的水,还是屋檐水。”就是下雨时从屋檐下收集起来的水。 “漫山还是苞谷。”张凌说,他去看小学,“还是原来那么小,更破了。有210个学生,大部分是跟爷爷奶奶生活的。没有操场,没有图书室……”学生们看着他,没有一个人说话。 他捐了三万元给每个学生做一套校服,每人一个书包,还在学校一个小小的场地上捐了篮球架。全村70岁以上的老人有6人,他给每人一千元。这是他自从离家去读大学那一天起就放在心里的一个心愿。 村民们又兴高采烈地聚到他家,来看出息了的张凌和他的小汽车——这是小汽车头一回来到箐口村。远村的妇女也抱着孩子来了,许多狗又在屋里进进出出。 张凌渐渐感到自己的内心在倒海翻江。他记不清自己是不是想过大学毕业要返回家乡,乡亲们也没有希望他回乡的意思。他们还说,等张凌在贵阳买了更大的房子,张凌的爸妈、弟弟都可以搬到贵阳去住了。还有老奶奶对孙子说:“好好念书,长大了像张凌叔,去贵阳买大房子。” 是啊,他已经在贵阳买了房,结婚,妻子也是个大学毕业生,孩子2014年7月在贵阳出生。他还能返回箐口吗? 箐口小学那些看着他没说一句话的孩子来到他的脑海,除了捐校服还能帮他们什么?村里还是非常穷,漫山都是枯死的没有果实的苞谷,水泥路还没有通村。夜雨一下,到处都是烂泥地。弟弟那只手还常常犯疼,半夜里用那只疼手敲打着床沿,那声音在静夜中一下一下撞击着张凌的心。此刻他的妻子和女儿在贵阳的席梦思上睡着了吧……这个只有虫鸣之声的村庄,直到2017年全村513户201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就有238户853人,贫困发生率41.16%,而毕节全市农村的平均贫困发生率已经下降到13.2%…… 读书是为什么?为了逃离家乡? 贫困铺满了家乡的白天和黑夜。 也许正因为贫困,因为家乡非常贫困以不回来吗? “想了三天,想透了。”张凌说。 就这样,张凌决定回家乡。 回来干什么? 已懂做企业的张凌想,先要选择一个有经济效益的产业。读书告诉他,要善于利用优势发展产业。家乡有什么优势吗?箐口村前有个硫黄厂,烧硫黄的烟往天上飘,天下雨降下来是酸雨。日久山上不长树,只长茅草。家乡既没绿水,也没青山。 书本也告诉他,微酸性土壤适合猕猴桃生长。接着发现,猕猴桃适应的海拔高度以1000-1600米为宜,箐口村山地的海拔在1500米左右,正合适。还知道了猕猴桃喜半阴环境,适合“寡日照山区”,箐口山地日照时间一天只有四小时左右,也合适。他还知道了,世界上消费量最大的前26种水果中,猕猴桃的综合考评名列前茅,被誉为“水果之王”。这些因素集合起来,他选择了种猕猴桃。我们也可以由此获得一个启发:重要的不是你有没有优势,而是你能不能把劣势转化为优势。 张凌家只有十来亩承包地,即使全部种猕猴桃,收益再好,也不是他回乡的理想。去动员伯伯、叔叔种:“所有的资金我来投,你们管种管收就行了。”可是他们都不种。 “那东西能吃饱?” “那就我种给大家看?”他不相信在村里组织不起人来,他去挨家挨户做宣传,终于组织起32户,种了270亩。 猕猴桃要三年才挂果。第二年还看不到收益,但木质藤本长起来了,漫山绿色。2015年夏,村民都惊诧:这东西在这里长这么好!还没挂果的绿色藤叶开始摇动村民的心。 “张凌做事,错不了。” “人家做公司都赚钱的,还能亏了?” 2016年1月,村里扩种了300多亩。 这年8月8日,村里发生了一件事,村民张青祥的妻子被高压电电死了。供电局的高压线从村寨的房屋顶上过,张妻拿梯子到二楼天台上取物,那梯子是铝质的,碰到了高压线,瞬间就被电击身亡。这大不幸,农村人会认为是自己不小心所致。张凌说,高压线这么低从屋顶上过,没有保护措施,供电局有责任,要向供电局索赔。可是谁去找供电局?张青祥是特困户。没人去。 张凌看到了,贫困在他的家乡不止表现在缺钱少物,文化知识贫乏,乡亲和乡村距离现代社会都多么遥远。回村这些日子他已感到,村民知识贫乏不知保护自己不只是这件事,但这件事非常典型。高压电从民房屋顶上通过,线布得这么低,县城供电局的人也缺乏知识吗!瞬间失去妻子的张青祥原本是特困户,现在连丧事都不知道办。张凌和村民们帮着办了丧事,他对张青祥说:“我去给你讨公道。” 张凌一次次去县里找供电局,花了两个月时间。最后一次,他带着张青祥去领到了赔偿的13万元。这件事更重要的是,县供电局由此对全县农村高压电进行了一次风险排查,对不合规的线路予以修改。而用电安全、饮水安全等防风险措施,是农村脱贫攻坚的一项重要内容,造成危害就会加深农民的贫困。 张凌带着张青祥讨回赔偿,全村都轰动了。所有人都说村里多么需要张凌这样的干部。可张凌是个“群众”,连党员都不是。2017年3月村委换届。张凌被村民们选为村主任。4月初,毕节市布置学塘约经验。张凌去了塘约三次,第三次是带了32个农民一起去看的。箐口人说,这是要真学。 张凌说:“我读《塘约道路》,看到‘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非常感动!”他说细想自己的村,什么是穷村?有三点,一是人没有组织起来,二是产业没有选准,三是精神没有焕发。只要这三点没改变,这个村就不可能脱贫。 张凌说的三点,没有使用一个贫困数据,但他抓住了本质,看到了精神的重要。塘约村组织起来的标志是“村社一体”。张凌有办公司的经历,他与村支书李兴国商量:我们办个村集体公司,把全村人组织在公司里,办成“村企一体”。也就在这时,张凌听到市里要求办“脱贫攻坚讲习所”,他立刻就办了。村民太需要补充各种知识。这是毕节村一级最早创办的农民讲习所。 4月28日,张凌去注册了一个公司,取名“新梦想种植专业合作社”。箐口有八个自然村寨,九个村民组,每个组建一个合作社,另建一个养殖合作社,还建一个工程队和一个运输队。一个公司把这十个合作社、两个队,统一管理起来。村政还建了三个协会:基金会,老年协会,残疾人创业协会——由张凌的弟弟张梁把全村33个残疾人组织起来。 接着是人员分工。很特别的是:65岁以上的老年人,不分男女不再务农,能做事的负责带入学前的小孩(包括别人的孩子),搞清洁卫生。他们的工作,因“村企一体”统一核算而有劳动报酬。这使箐口村破天荒地相当于有了“托儿所”。 产业方面,扩大优选的种植品种:樱桃和李子。增加土鸡养殖和养蜂。在猕猴桃山地套种黄豆。猕猴桃需要氮磷钾,套种黄豆相当于给猕猴桃施氮肥。在张凌身上,人们看到,上学和毕业后继续自学都是有用的。不能让知识荒废,要让知识“落地”。 看到塘约村有“一建四改”,张凌回村订立了“三建七改”。“七改”第一点是改思想,依次是改厨房,改厕所,改沟渠,改道路,改圈舍,改炉灶,由新成立的工程队实施。与此同时学塘约“红九条”村规民约,箐口村订立了“红十条”,也就是“十不准”,合起来称“三建七改十不准”。 这些都经过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并告诉大家一个原则:入社自愿,退社自由。结果,村民入社踊跃。我不禁想,其实农民思想并不保守,农民在涣散而无奈的贫困生活中已经期望很久,当有人召唤有人组织,就有人来集合。 再说“七改”的哪一项都需要先搞环境卫生。村里牛羊粪、鸡屎狗屎随地拉,雨天同烂泥混在一起,你不踩下去没别的路可走。一个环境卫生问题,在上过几年大学的张凌看来,它其实就是城市和贫困农村一道巨大的鸿沟。张凌组织搞卫生,搞了里里外外的卫生才能改厨、改厕、改灶,这个“配套工程”挺奏效,全村都发动起来了,小学老师称之“环卫风暴”。这年夏季,箐口村在猫场镇开展的卫生治理大评比中获得全镇第一名。 村庄环境发生变化,有人建议应该建个村寨大门,可是村集体经济还是“空壳”的,有人建议大家捐款修建。张凌起初不同意,后来想,左文学也曾经发动村民捐款修桥,这里面有一种“齐心协力”,于是同意了。时值学校放暑假,在外读师范学院的大学生张涛回家,来捐一百元。家有大学生的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村里说好不让贫困户捐的。张凌不收。可是张涛说:“我是箐口村一分子,有这份义务。”相持不下。张涛说:“我是我自己!你应该理解。”作为也读过大学的张凌,能听懂一个大学生的话,他收下了。这事传开竟有捐过钱的人来再捐,说是为孩子捐。 “你的孩子不是刚出生吗?”张凌说。 “那也是箐口村一分子。”对方说。 没想到这个头一开,陆续有父母来为孩子捐钱。当我看到张凌记录的捐款名册时,我不知天下别处还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我看到名册上,第一个2017年出生的捐款者名字是:张雨欣。表上2017年出生的孩子有9人。还有一岁半到三岁的孩子11人,还有学前班、幼儿园的孩子,以及从一年级到高三到大学的学生。还有两个在外省就读中学的学生,总共88人。最少的捐10元,捐最多的是个幼儿园的孩子,名叫张芷齐,捐了520元,据说这个数字的意思是“我爱你”。我不能不感动!重建一个有希望的家乡,这就是村庄的父母和爷爷奶奶对刚出生的孩子们寄予的期望! 就这样,三天捐了35600元。这些钱是不够的,这件事重要的不是钱。十五天后,寨门高高地耸立在村前了。 “农民需要一个精神焕发的村庄。”这寨门已是箐口村民精神面貌的体现。孩子们知道这件事,从此进出村庄,知道仰望。即使将来读书读到远方,想起家乡的寨门,心中会没有波澜吗? 2017年6月22日,周建琨来到箐口村。张凌领着周书记登山爬坡看了将要挂果的猕猴桃,看了养蜂基地,看了村庄改造。周书记一路看着,一句话都没有说。 一直走到一个展板前。展板上呈现的村组织结构同常见的不一样,常见的把“党组织”标示在最上方,这个图把“党组织”放在中间,四周是村企一体的公司、合作社等等。周书记看了一下张凌,似乎问:怎么想的? 张凌说:“我们叫它‘酿蜜模式’,中间这个是蜂王,蜜蜂都围绕着蜂王。蜂王代表党建引领,公司、合作社都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酿造甜蜜生活。”周书记微笑了一下,然后说:“走了这么久,你不邀请我去你们村部坐一下?” 村部很小,挤在村民房子的中间。于是坐院坝。村民自己带凳子坐到院坝来了。张凌后来告诉我:“村民来了七十多人,周书记坐下来跟村民交谈了两小时十六分钟。”周建琨对张凌说:“村部太小了,你要考虑建个大的,要有‘阵地’。” 座谈中,张凌讲了目前有个困难,“村民组织起来,开始干事情了,但村集体是‘空壳’的,没钱付工资。” 周书记说:“跟大家商量商量,能不能借鉴以前生产队记工分的办法,先记上账,年底再给,看行不行。” 我且忽略周书记还讲了什么。张凌说他记得,周书记临走时对他说:“你干得不错,换一种生活,农村是大有作为的地方。” 猕猴桃树在挂果了。 张凌开始筹措销售,并以“箐口”谐音去注册了一个“沁口”商标,用于箐口村产业的一切绿色产品。 第一批32户人的猕猴桃收成了,产量4.2万斤,四天就卖完了。“不够卖。”张凌说,销往北京、上海、浙江、山东,还有本地。我说,不够卖,为啥卖到那么远?他说:“一个地方不多给,培育市场呀。” 初次挂果产量是最少的,但也获得32万元,除去成本,每户分到5600元。最让农民放心的是:这项产业是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统一品牌,统一采购。农民搞种植养殖都愁卖,现在他们不用愁。分钱那天,种了猕猴桃的和还没种的都非常高兴。这算是尝到了“集体的甜头”。 “我们的猕猴桃特别甜,很好吃。”张凌告诉我。 “你是对自己的东西偏爱吧。”我说。 “不是自吹,我们拿去检测,箐口猕猴桃达到11个糖,一般的是9个糖。”他还说,“采购价,我们一斤卖8元,采购上万斤才7元,其他地方一般是5元左右。” 现在不用动员,猕猴桃又扩种到1200亩。产品还是供不应求。张凌在讲习所里算给大家听:猕猴桃第四年一棵树最低可以收成10斤,每斤卖8块钱,一棵树就是80块钱。一亩地可以种70棵,就是5600块钱。过几年就到了丰产期,科技书上说,丰产期的最高纪录,一棵有产300斤的。我们的摘100斤没问题,那一亩地就可以卖出56000块钱。 我对这个数字不敢相信:“确切吗?” 张凌回答:“我们的猕猴桃,丰产期一棵树的产量,一般在100斤到220斤之间,我说摘100斤肯定没问题。” 现在农民对“张凌说的”,几乎都信。张凌说:“猕猴桃的生命周期有80年到100年,到丰产期,我们就好比把土地变成了‘绿色银行’,每年收取的利息比银行高很多,本钱都在地里,能收成一百年。”农民们听了,真是脸上笑开了花。 这好像是梦想,更是选准的产业、科学的种植技术和组织方式在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我很想对他乡的农民兄弟说,看看土地有这么高的价值,在土地流转中要好好盘算盘算,是流转给哪个大户,还是流转给像箐口村这样组织起来的村集体。 这个大学生对新时代农民讲习所特别青睐,这是他可以把自己的知识传授给乡亲们的地方。村里有老太太把剪纸贴到讲习所来,它就像合作社社员的家。张凌对农民说,猕猴桃也是有公有母的,一棵公树,配十二棵母树。授粉的时候,蜜蜂不帮忙,自然授粉不如人工授粉。最好的授粉期只有四天,要是你自己种自己的,你人工授粉忙不过来,就耽误了。所以我们还是要组织起来,集体干这件事。 一步步开拓前进的箐口村,成规模地扩展种植猕猴桃、樱桃、李子,以及养蜂、养鸡等产业,并同步推进村庄建设,其变化之大之快,让前去参观者感觉它像这片土地上的异类。 其实,这个深度贫困村发生的一步步变化,都离不开这个村寨的孩子去读书后返回家乡,还因为这个归乡的孩子及时地积极地响应市委号召,走组织起来共同致富的道路。 1 、一部来自八年脱贫攻坚一线的乡村调研报告,重点记述在脱贫攻坚中衔接乡村振兴。 总 书 记指出,在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历史关口,巩固和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需要全党高度重视的一个关系大局的重大问题。《走向乡村振兴》重点记述了若干特困地区和先进市、县、乡、村在脱贫攻坚中衔接乡村振兴的典型实践。作者四年来跑了全国20多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的300多个自然村寨,这是一部“用脚写出来的”乡村调研报告。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实践经验,在书中融会贯通。书中“经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人物的实践体现出来的,许多故事感人至深,催人泪下。 2、从“试验区”走向“示范区”,五级书记抓脱贫促乡村振兴,竭诚贯彻新发展理念。 贵州毕节是我国唯一的“开发扶贫、生态建设”试验区,那里的贫困程度之深,曾令人震撼。总 书 记多次对毕节试验区工作作出重要指示,称毕节试验区是“脱贫攻坚的一个生动典型”,要求毕节“着眼长远、提前谋划,做好同2020年后乡村振兴战略的衔接”,“努力把毕节试验区建设成为贯彻新发展理念的示范区”。贵州省及毕节市全力贯彻,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做法在实践中诞生:“新时代农民讲习所”“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留下一支永远不走的工作队”等等,均形成可资借鉴、可供学习的经验,具有重大示范意义。 3、 加强党对农村工作的全面领导,引领农民发展合作经济和集体经济。 总 书 记曾说:“党管农村工作是我们的传统,这个传统不能丢。”本书重点记述了毕节和烟台两地党组织引领农民走合作化道路,发展壮大集体经济的实践。毕节和烟台,一个在西部,一个在东部,两地实践证明,把农民组织起来走共同致富之路,在贫困地区可推行,在经济发达地区也可推行。“党支部领办村集体合作社”,解决“一户农民的单打独斗问题”;“乡镇党委统领合作社”,解决“一个村的单打独斗问题”;县委统领县乡村三级联办合作社,县委书记由此被推到“一线总指挥”岗位。 4、一部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之作。党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实践,都是当今学 习 党 史的重要内容。 本书以大历史观看近代以来的乡村问题,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看乡村振兴,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看中国共产党百年实践的伟大成就。“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今天,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乡村振兴不只是乡村的事,仍然需要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进乡村振兴。书中讲述的中国共产党领 导 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时代的脱贫攻坚战中,英勇奋斗,克难攻坚,取得的辉煌成就,既是当今学 习 党 史的重要内容,也是向党百年华诞的献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