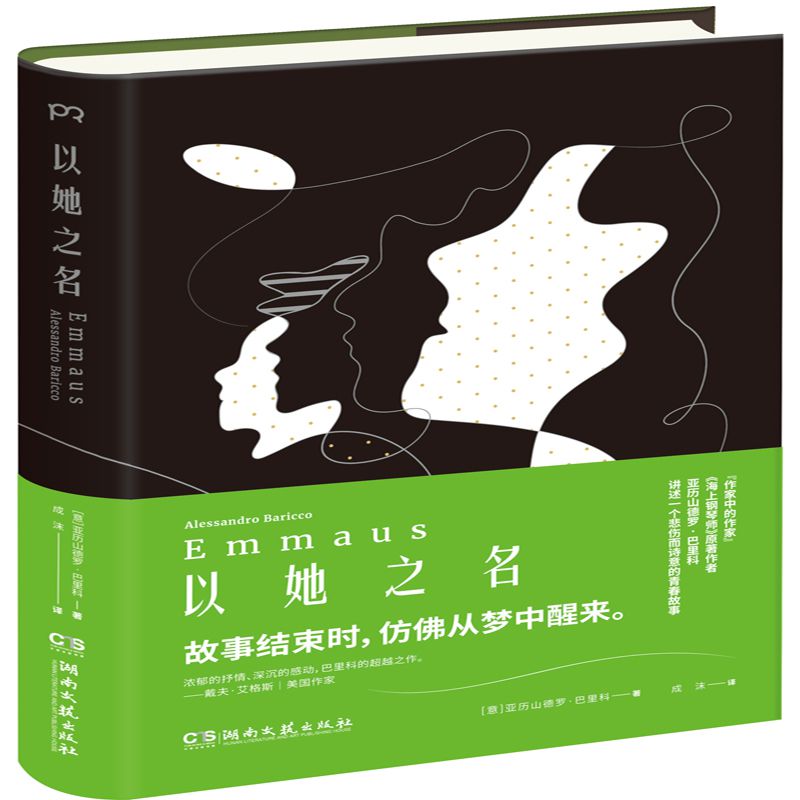
出版社: 湖南文艺
原售价: 48.00
折扣价: 28.80
折扣购买: 以她之名(精)
ISBN: 9787540484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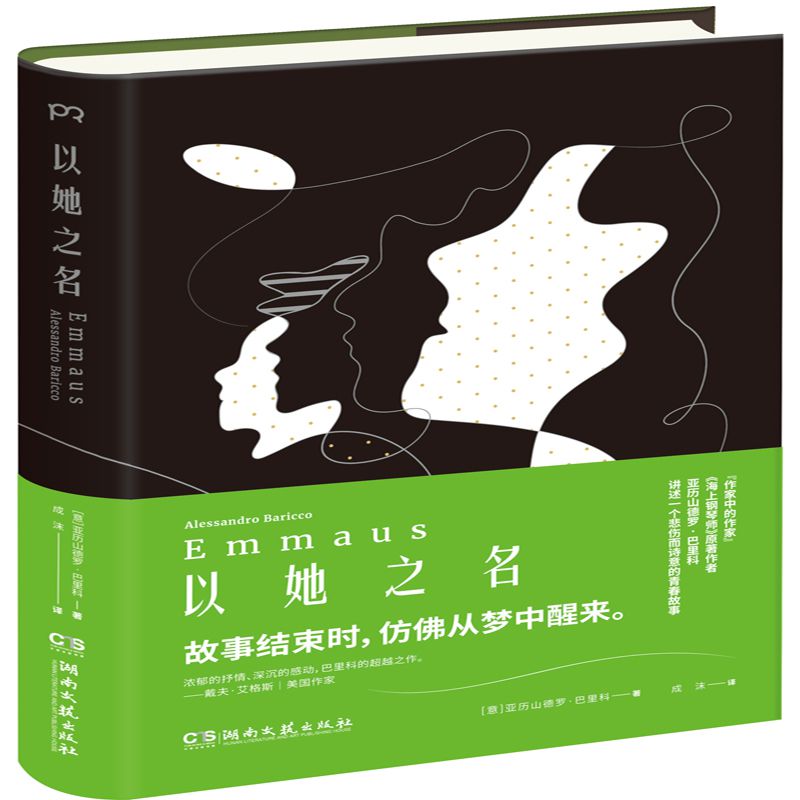
[意大利]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Alessandro Baricco) 1958年生于都灵。1991年,**作《愤怒的城堡》获得意大利坎皮耶罗奖、法国美第奇外国作品奖。1993年,《海洋,海》获得维多雷久文学奖和波斯克城堡文学奖。1994年,《丝绸》荣登欧洲各国畅销榜单,2007年被改编成电影,由凯拉·奈特莉主演。1998年,《海上钢琴师》被知名导演朱塞佩·托纳多雷改编成电影。2016年,巴里科以其全部创作荣获罗马尼亚特兰西瓦**图书节奖颁发的小说大奖(Marele Premiu al FICT)。 他还是导演和表演者,曾自编自导影片《第二十一课》。 巴里科的作品有着浓烈的艺术与童话气质,富有实验性与音乐感,浓缩了人类美好而温暖的情感,既古老又新鲜,既传统又现代。他被美国《图书馆杂志》称作”作家中的作家”。 在我的小说里,有很多天真的东西。我说的”天真”是那种没有被世俗和厌倦污染的东西。我喜欢挑战那些伟大的作品,我推崇万古流芳:这是对抗死亡的一种方式。 ——亚历山德罗·巴里科(接*《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说) 译者:成沫 罗马大学罗曼语文学博士,同济大学中意学院、人文学院教师,主要研究领域包括欧洲中世纪文学、意大利文艺复兴、但丁与彼特拉克等。
正文P027—035 我们上了桥,都给吓着了。在骑车回家的时候,我们意识到天色已晚,于是用力地踩脚踏板。我们什么都没说。鲍比拐弯回家了,然后是圣托,剩下卢卡和我。我们紧挨着对方,踩着脚踏车,沉默不语。 我之前说过,卢卡是我*好的朋友。我们只需一个手势就可以互相理解,有时一个微笑就够了。在女孩进入我们的生活之前,我俩共同度过了生命中几乎所有的下午——至少我们是这么认为的。我知道他在想什么,有时候可以在他张口之前就说出来。我可以在人群中一眼认出他,只要看他走路的样子——他的肩膀。我看起来比他年长,我们看起来都比他大,因为在他身上仍保留着孩子的某种特征——在他的细小骨骼、白皙的皮肤中,以及在他的脸上——他的脸精致而英俊。他的手、细长的脖子、干瘦的腿也显得孩子气。但他并没有意识到这些,我们没有意识到——如我之前所说,我们很少在意外貌的美丽。我们的世界并不需要这个。就这样,卢卡拥有美丽却不利用它——像一场迟到的约会。在很多人看来,他是个给人距离感的人,女孩子们喜爱那种距离,她们称之为”忧伤”。但是,和其他人一样,他只是单纯地想要快乐。 几年前,当我还是十五岁的时候,某个下午,在我家里,我和卢卡躺在*上看有关F1赛车的杂志——在我的卧室里。*边就是一扇窗。窗户开着,正对着花园。我的父母在花园里。那是个周*,他们在聊天。我们没有留神听,而是看着杂志。但从某一刻起,我们开始留神倾听,因为我的父母谈论起卢卡的母亲。显然,他们没有意识到卢卡也在那里,于是谈论起他的母亲。他们说她是一个十分能干的女人,真是可惜,遭*如此不幸。他们说上帝让她背负了一个可怕的十字架。我看着卢卡,他微笑着向我示意,让我不要动,不要弄出声响。他好像兴致正浓。我们在那儿继续听着。外面,在花园中,我的母亲说,与一个病成这样的丈夫一起生活一定是件可怕的事,那该会是多么痛苦的孤独。然后,她问我的父亲治疗进行得如何。我父亲说他们什么都尝试过了,但真相是,他们永远不会摆脱那些东西。他说,只能祈祷他不会在某**下定决心摆脱一切。他说的是卢卡的父亲。我为他们说的那些话感到羞愧。我回头看卢卡,他向我示意,像是在说他什么都没听懂,不知道他们在谈论什么。他把一只手放在我的腿上,希望我不要动,不要出声。他想要听下去。外面,在花园中,我的父亲在谈论一种被称为”抑郁”的东西,这显然是一种疾病,因为与药和医生有关。有一刻,他说,这对妻子和孩子来说,真是太可怕了。可怜人。我母亲说。她沉默了一会儿,又重复了一遍”可怜人”,指的是卢卡和他的母亲,因为他们要与病人生活在一起。她说人们只能祈祷,要是她,她也会这么做。然后我的父亲站起来,两个人都站起身,回到屋里。我们本能地低下头,把目光移回F1赛车杂志上,害怕房门会忽然打开。但那没有发生。我们听见我父母的脚步声,他们沿着走廊,走向客厅。我们在那里一动不动,心怦怦地跳。 我们得离开家,但并不顺利。我们走到花园,母亲出来问我准备什么时候回来时,发现卢卡也在。她喊出他的名字,好像是在跟他打招呼,但声音中充满惊慌——她之后什么话也没能说出口,不像平常总能聊上几句。卢卡转向她,跟她道晚安。他说得很有教养,用他*平常的口气。我们在假装这件事上都异常在行。我们出门时,母亲仍在那里,站在过道上,一动不动,手里拿着一本杂志,食指夹在书页中。 我们并排走着,有一阵子什么也没说。有什么藏匿在我们的思想中,我俩都怀有心事。要过街时,我抬起头,看看有没有汽车驶来。那一刻,我也看见了卢卡。他两眼通红,低着头。 我从来没有想过他的父亲生病了——纵然奇怪,但事实上,卢卡也从没有这样想过。由此可以看出我们是怎样的人。 我们对父母有种盲目的信心;我们在家里所看到的都是正常而平稳发展的事,以及代表心态健康的各种礼仪。我们因此崇拜父母——他们把我们从任何不正常中挽救回来。因此不存在这样的假设——他们自身处于不正常的状态,比如一场疾病。不存在生病的母亲,只有疲倦的母亲。父亲从不失败,只是偶尔焦躁不安。不幸——我们不愿触及的,时不时以疾病的形态降临,它们总有个名字,但在家里我们都闭口不提。 在我们看来,这很正常。 如此,不知不觉间,我们继承了面对悲剧时的无能,以及对命运的钝感:因为在我们的家里,不好的事情是不被接*的,这样可以拖延那些一旦被触发就会无限期膨胀的、真真切切的悲剧的发生——我们就是在这样看似平静实则危险的沼泽中长大的。这是一块荒谬的栖息地,由被压抑的痛苦和每*的禁忌构成。但我们无法意识到这有多荒谬,因为我们是沼泽里的爬行动物,我们只认识那一片世界:沼泽对于我们来说是正常的。就这样,我们消化大量不幸,并把它们当作生活的必然,而不曾怀疑有伤口需要愈合、有破碎的身心需要缝补。同样,我们忽略丑闻,因为我们出于本能,将身边人对自己的伤害视为对*常生活不期而至的补充。比如说,在教区电影院的黑暗中,我们感觉到神父的手搭在我们的***,却没有愤怒,而是急忙得出结论——显然,事情就是如此,神父把手放在那里,我们不需要在家里提到这件事情。那时我们十二三岁。我们没有把神父的手移开。在随后的星期*,我们从同一双手中领取圣餐。我们以前能那么做,现在仍然能——为什么不把压抑转化为优雅,把不幸化为生命中的一抹色彩呢?卢卡的父亲从来不去体育馆,他*不了挤在太多人中的感觉。我们知道这点,并视之为令人敬重的举止。我们一直认为他有一种难以言明的贵族气质, 因为他的沉默。我们一同前往公园的时候,他走路缓慢,不时发出笑声,就像在做出某种让步。他从不开车。在我们的记忆中,他从来不抬高嗓门说话。在我们看来,如此种种都是他高贵尊严的表现。我们从未察觉在他周围的所有人都有种独特的欢乐—确切地说,是勉强的欢乐。我们从未在意,因为我们将这种独特的欢乐视作一种尊重—实际上,他确实是一位在**工作的官员。我们认为他跟其他父亲一样,只是*难以理解。这么说吧,*加陌生。 晚上,卢卡坐在他父亲的身边,在沙发上、电视机前。父亲将一只手搭在他的膝盖上。卢卡什么都没说。他们什么都没说。时不时地,父亲紧紧地抓住孩子的膝盖。 “那是一种病”是什么意思?**,我们一起走在路上时,卢卡问我。 我不知道,**没概念,我说。我说的是实话。 继续谈论下去没有意义,我们很久很久都不再提起它。直到那天晚上,四人从安德雷待过的桥上回来,*后只剩下我们两个。在我家门前,我们停下自行车,一只脚撑在地上,另一只踩在踏板上。父母在等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总是在七点半吃晚饭。我得走了,但我能看出卢卡还有话要说。他把身体的重心挪到另一只腿上,将自行车朝另一侧倾斜。然后他说,他靠在桥栏杆上的时候弄明白了一件事——他记起一件事,并且弄懂了它。他稍停了一下,看我要不要走。我留在那里。在我们家里,他说,吃饭时总是很安静。你们家不一样,鲍比和圣托家也和我们家不一样,我们家吃饭时是不说话的。我可以听见所有的声音,叉子刮盘子,水倒进杯子里。尤其是我的父亲,他一言不发。总是这样。然后我想起父亲有多少次在吃饭时一言不发地站起来——我们还没有吃完,他便站起来,打开门,走到阳台上,掩上身后的门,站在那儿,靠在栏杆上,就在那儿。许多年来,他一直这样。我和妈妈会抓住这个机会——我们会聊天,妈妈会开个玩笑,或站起身拿一个盘子、一个瓶子,或问我个问题,诸如此类。透过玻璃窗可以看见我的父亲,背对着我们,有点驼背,俯身在栏杆上。这么多年来我都没有想过这件事,但**晚上,在桥上的时候,我想到他去那里是要干什么。我觉得我父亲去那里是想跳下去。他没有勇气这么做,但他每次起身,都是带着这个念头到那儿去的。 他抬起眼睛,因为他想要看着我。 和安德雷一样,他说。 就这样,卢卡成为我们中**个越界的。他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他不是个不安分的小伙子。他碰巧待在一扇打开的窗前,大人们不谨慎地说话;然后,他间接地听说了安德雷的死。这在他——我们——的国度上刻下了裂痕。头一次,我们中的一个人跨越既定的边界,怀疑其实并不存在什么边界,也没有避风的港湾。他带着羞涩的步伐,开始步入无人之境。在那里,”痛苦”和”死亡”都有明确的意义——由安德雷念出,由我们的父母以我们的语言书写。他在那片土地上看着我们,等待我们的跟随。 正文P103—110 我知道这个故事,是鲍比跟我说的,包括所有的细节。他告诉我这些,是想向我解释,很可能一切早就在发生了,缓慢地发生,宛若地质变迁。但站在山间的石子路上时,他突然间明白,一切都结束了。他指的是我们**了解的某件事情——我们会用不太恰当的方式来形容它:失去信仰。这是我们的梦魇。在前行的每一刻,我们都知道这事如同*食,随时可能发生——失去我们的信仰。 无论神父给我们多少教诲,关于这件事情,只有通过*初的信徒的经历才能*好地去理解。当时只有几个人,耶稣基督身边的人,在骷髅山上的第二天,把他们的导师从十字架上卸下。他们聚集在一起,惊慌失措。要知道他们身上背负着巨大的悲痛,因为失去了所珍视的,但也仅此而已。那时候,他们中没有人知道,死去的不是一个朋友、一位先知、一名导师,而是上帝。那是他们当时没有理解的事。显然,他们也无法想象,那个人就是真的上帝。他们聚在一起,在那**,在骷髅山后,单纯地纪念一个亲密的人、一个无可替代的人—他永远地离开了。但是圣灵从天上降落在他们身上。突然间,帷幕被揭开,他们懂了。与他们一同行走了多年的那个上帝,现在他们认出来了。那一刻,生命中每一个微小的细节都回到他们的脑海中,带着耀眼的光芒,深深地照进他们的心灵,直到永远。在福音书中,那种洞开是由一个美丽的隐喻来形容的:圣灵降身的他们忽然能够说出世界上所有的语言——一个众所皆知的奇迹,与先知、占卜者的形象联系在一起。这是不可思议的理解力的印记。 因此,按神父的教诲,信仰是个赠礼,来自上天,属于一个神秘的国度。也因此,它是脆弱的—像是幻觉,也如幻觉一般无法触摸。它是超自然的。 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向来遵从教会的信条,但也了解另外的故事,而那些故事来源于生养我们的温顺的土地。在那儿,我们不幸的家庭以潜移默化的方式,让我们继承了某种无法改变的本能——相信生命是一场无尽的体验。他们传递给我们的习俗越是简朴,每**,他们从地下对我们的呼唤便越是深远—呼唤一种无尽的野心,一种期待,几近毫无理性的期待。从孩童时期起,我们便带着明确的目的向这个世界靠近,要使它重新归于伟大。我们认为这个世界应该是公正的、高贵的,为了它变得*好而不懈努力,在创造的道路上勇往直前。这使我们成为反抗者,成了不一样的人。世界于我们而言,大体上就是一份枯燥而耻辱的责任,**不符合我们的期望。在那些不信者的生活里,我们看见应*谴责的*常生活;从他们每一个行为中,我们察觉到那些拙劣的模仿,模仿我们所梦想的美好人性。任何不公——每一份痛苦、恶毒、卑劣、残酷——都是对我们这份期待的冒犯。没有意义的道路,每一个失却希望及高贵灵魂的人,对我们也是冒犯。每一个卑贱的行为。每一个迷失的瞬间。 因此,在相信上帝之前很久,我们就相信人——在*初,这本身就是一种信仰。 像我之前所说的,信仰在我们体内发动了一场战争——我们反抗,我们与众不同,我们疯狂。他人喜欢的,我们觉得厌恶;他人鄙夷的,我们觉得珍贵。无须多言,这一切让我们兴奋。我们带着想要成为英雄的想法长大——尽管是奇异的一类,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英雄——我们不喜欢**或暴力,或是残暴的抗争。我们是阴柔的英雄,渐渐卷入赤手空拳的争斗中,满怀着孩童般的纯真,以让人恼怒的谦虚战无不胜。我们在世界的齿轮间昂首爬行,但迈着缓慢的步子——就像拿撒勒的耶稣那样迈出谦卑而坚定的步伐。他在公众的注视中走过整个世界,在创立信仰的教义之前,首先确立一种行为规范。如历史所示,谁也无法战胜他这种行为规范。 在这个颠倒的传奇史诗的深处,我们发现了上帝。这是自然而然的过程。我们如此笃信每一个造物,因此自然地开始想象创造—我们以上帝之名称之为智慧行为。因此,我们的信仰不是充满魔力的、无法控制的事,而是顺理成章的推论,将我们所继承的本能无限延伸。为了寻找意义,我们渐行渐远,而旅途的终点就是上帝—完整的意义。这很简单。我们失去这份简单时,求助于福音书,因为在那里我们从人向神的过渡永远地依照一个固定的模板,反抗的人之子与**的神之子合而为一,融会成一具血肉躯体、一位英雄。在我们的世界中可能被看作疯狂的事,在那里则是启示,完结的命运—**的符号。我们从中挖掘出没有棱角的坚信—我们称之为“信仰”。 丢失信仰的事时有发生。而当我使用”信仰”这个表述时,并不准确——它仿佛是一种魔法,但与我们无关。我不会丢失信仰,鲍比也不会。我们还没有找到它,所以不会丢失它。没有信仰与失去信仰**不同,毫无神奇魔力。在我的脑海中,信仰的丢失就像一面墙的粉碎——结构中的一角脱落,一切因此崩塌。因为石墙是坚固的,但石墙上总有脆弱的连接、不稳固的支撑。时光流逝,我们确切地了解到那一处究竟在哪里——那是将会出卖我们的隐秘的石子。那里,就是我们放置英雄主义、**情感的所在。在那里,我们拒*他人的世界,我们所鄙视的世界,带着出于直觉的坚信;在那里,我们知道并且声明,他人的世界是没有意义的。只有上帝能让我们满足,其他任何事都不行。但并不总是如此,并不总是。有时候,我们会满足于别人一个优雅的举止,或是迷恋一个美丽的世俗词语。生命闪光,在错误的命运之中;有时候,是罪恶中的高贵在吸引我们。一束光透过,而我们没有察觉。石子般的坚信破裂,一切随之倾塌。我在很多人身上看到这个过程,我在鲍比身上目睹了。他跟我说,在我们周围,有着许多真实的东西,而我们看不见,但它们就在那里——它们拥有意义,不需要上帝。 给我举个例子。 你,我,我们是真的存在,并不是在假装存在着。 再举一个例子。 安德雷,甚至是她周围的人。 你觉得那样的人有什么意义吗? 是的。 为什么? 他们是真实的。 而我们不真实? 对。 他想说的是,在意义缺失的时候,世界仍然继续。在混乱中存在一种美,有时候甚至是一种高贵,而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比如一种我们从未想到过、但切实存在的英雄主义——某种真理的英雄主义。如果你凭着自己的眼睛,在注视着这个世界的时候认出了它,哪怕只有一次,你便会迷失——于是,你将面对另一场战争。在成为英雄的确信中成长,而我们在传说中被纪念。上帝像是个天真的权宜之计,消失了。 鲍比跟我说,山中的那条石子路,当时在他看来,突然变成城堡的废墟。**没有办法在上面行走,他说。 我们看着他渐行渐远,但并不是看着他的背影;他的眼睛仍注视着我们,他的朋友们。他还会回来的,不会太久—我们这样以为,不曾想过会看着他真的消失。但他不再去医院的瘦鬼那里或其他地方了——我们曾一起去的地方。他来教堂里和我们一起演出过几次,之后就再也没来。我在键盘上弹出贝斯的声音,但它和鲍比在贝斯上弹出来的根本不是一回事。重要的是,没有了他,我们的成长变得不同。我们的成长,没有了他——他的成长有一种轻盈,我们的没有。 有**,他回来跟我们说起他和安德雷的演出,问我们是不是真的愿意去看。我们说,是的。我们去了,而这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译后记 故事发生在意大利,这曾是一个传统而又保守的天主教**。小城之中,大家互相认识,每天出门时会友好地打招呼。这是地点的前提。如故事中所说,传统与守旧的力量仍异常强大,人们数十年如一*地在固定的摊点买菜,每**去参加教堂的弥撒。与此同时,外面世界的影响开始体现,夜生活、**品,以及性自由。教堂对年轻人的影响力越来越弱,流行文化的大潮汹涌而来。这是时代的前提。 年轻人的眼睛没有错过任何细节,他们将所看到、听到和感知到的一切不加分辨地吸收,并视之为生活的常态。他们被夹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努力遵循父母的生活模板,同时抵抗又拥抱外面世界的**。他们同时面对文化的精华与糟粕,必须做出选择。这样的选择让他们恐惧,迷失了信仰。 那份信仰的根基是意大利天主教,基督教流派中*为保守和根深蒂固的一支。如同原书名“Emmaus”(意为“以马忤斯”,出自《路加福音》24:13,耶稣基督死后复活并在以马忤斯向人现形)所揭示,神父、父母向年轻人讲解的福音书故事深深刻在他们的心中。每周去教堂聆听弥撒,参加教区集会,忏悔与祷告,这些习惯的力量有着拯救的作用,让他们躁动的心获得平静。拉撒路的死而复生、圣母的贞洁与母性的光辉、耶稣复活的奇迹,以及他的殉难,拯救了人性,赦免人类的罪恶。如同故事中的“我”所说,年轻人翻阅福音书,寻找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页。借助”继承而来”的文化与**传统的力量,他们试图解释在自己身上发生的一切,以及安德雷的存在。 这份**信仰构成他们正在成形的世界观的一半,而另一半则来自一个几乎**对立的“那些人的世界”——不信者、富人的生活方式和“动物凶猛”的现代文化。与我们的世界里的年轻人一样,在这个同样古老的千年农耕文明中成长的年轻人,面对这个新的、无法解读的世界时,孤立无援而不知所措。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 1. 当代欧洲小说大师、《海上钢琴师》作者巴里科的经典作品,被认为是其写作生涯的**之作。 2. 美国摇滚乐团魔力红(Maroon 5)主唱亚当·莱文挚爱的小说。他说:”《以她之名》营造的紧张氛围使我三次将它放下,让眼睛放松,并做下自我调适。比较之下,我的世界实在平淡,过于标准化了。” 3. 1个女孩,4个男孩,一段危险而诗意的青春故事。浓郁的抒情,深沉的感动,读完后,仿若从梦中醒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