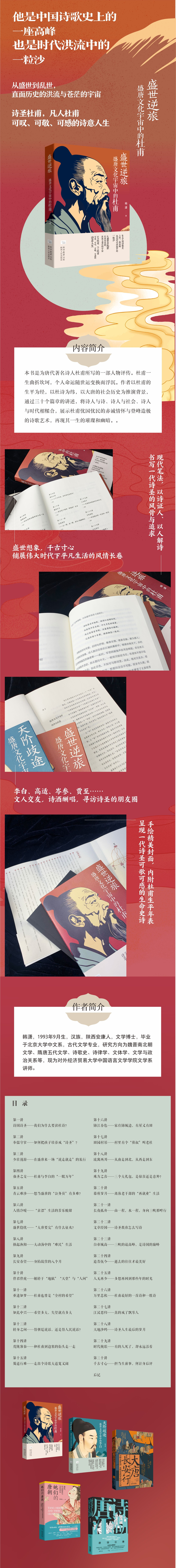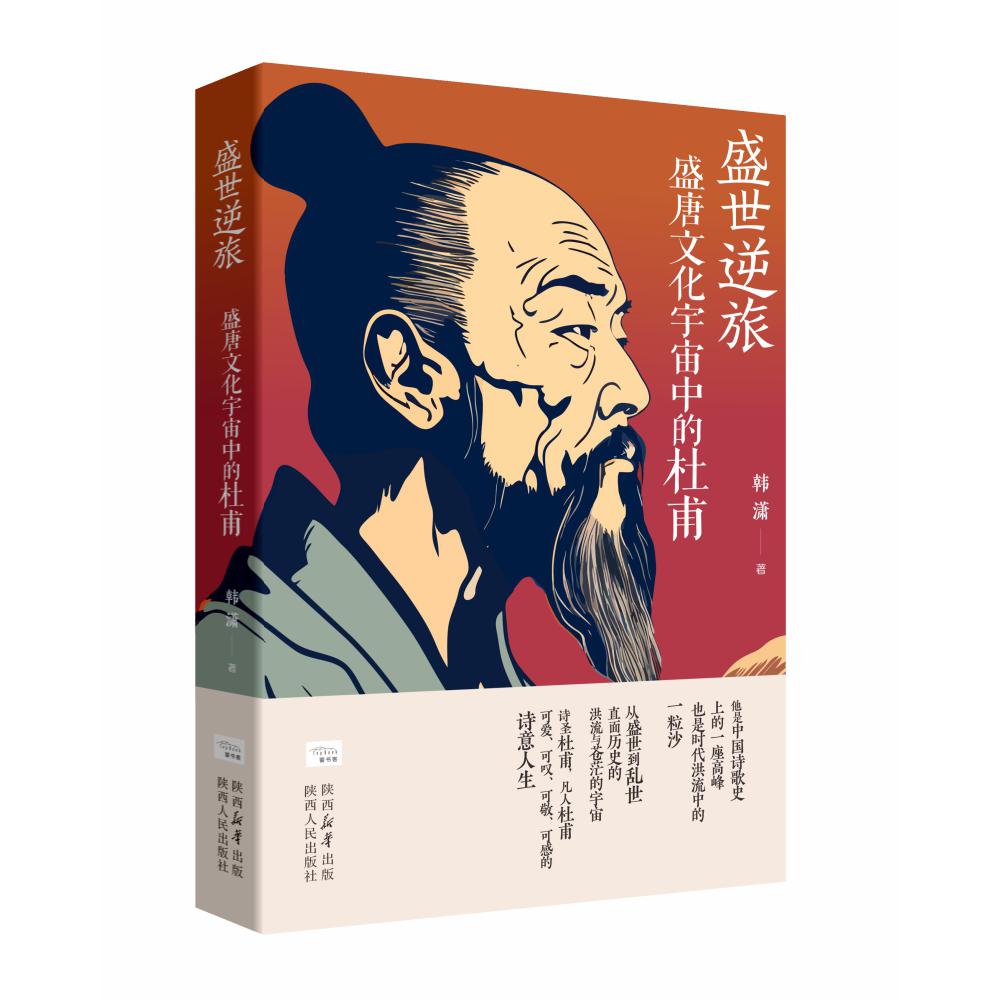
出版社: 陕西人民出版社
原售价: 69.80
折扣价: 41.20
折扣购买: 盛世逆旅:盛唐文化宇宙中的杜甫
ISBN: 97872241474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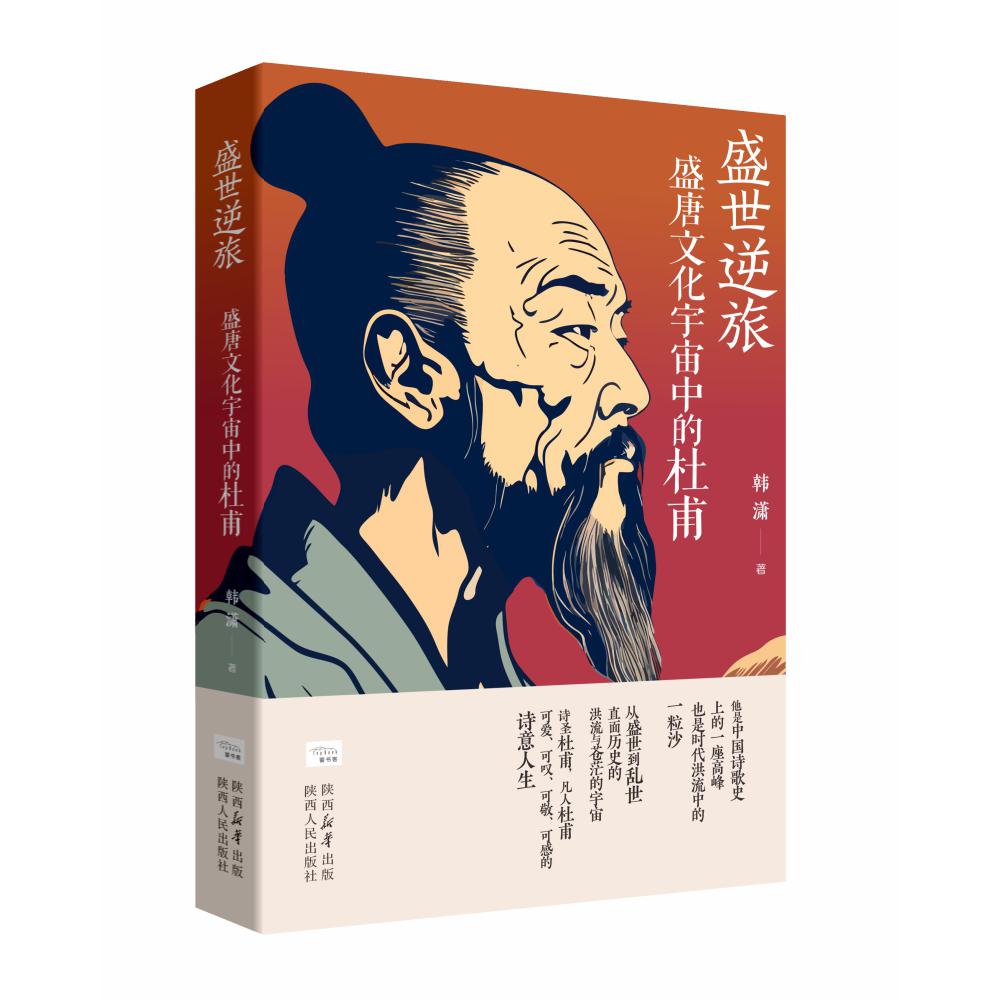
韩潇,1993年9月生,汉族,陕西安康人,文学博士,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研究方向为魏晋南北朝文学、隋唐五代文学、诗歌史、诗律学、文体学、文学与政治关系等,现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文学系讲师。?
第二十八讲 天地沙鸥 ——诗圣人生最后的岁月 一、“转作潇湘游” 大历三年(768)年初,杜甫一家辞别夔州,继续沿江东下,真正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生活。他先是来到江陵住了一段时间,但在那里生活得并不如意,不愿意也没有条件久住下去,又因为时局动荡、年老多病等种种原因,迟迟看不到北归的希望,于是只好权且先去他处了,按照杜甫的计划,备选目的地乃是吴越。 且看《第五弟丰独在江左,近三四载寂无消息,觅使寄此二首》其二: 闻汝依山寺,杭州定越州。 风尘淹别日,江汉失清秋。 影着啼猿树,魂飘结蜃楼。 明年下春水,东尽白云求。 题目中的“第五弟丰”是杜甫日思夜想的骨肉兄弟杜丰,与他已经三四年没有了联系,近来得知其在吴越的山寺中定居,便迫切地盼望着能与其相见。何况此时杜甫稽留江汉,过得并不顺心,中原故乡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加之早年漫游吴越又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顺江东下的决心便更坚定了。 事实上,杜甫根本没有耐心等到“明年下春水”,写完这首诗不久他就从江陵离开了,临行时,一位与杜甫交好的名叫郑审的江陵少尹前来送行,杜甫写下《舟出江陵南浦,奉寄郑少尹审》一诗作为留别: 更欲投何处,飘然去此都。 形骸元土木,舟楫复江湖。 社稷缠妖气,干戈送老儒。 百年同弃物,万国尽穷途。 离开江陵时,距离写下“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的大历二年重阳又过去了一年,此时的他——离家“万里”的距离没有缩短,又逢“悲秋”时节,“作客”仍是“常”态;“百年”人生的第五十七个年头也快走完,“多病”之躯更显沉重,虽不再“登台”,孤“独”却又更添几分。已经半截身躯入土的老儒,还借一叶小舟漂流在干戈不尽的天地之间,如同被世界所抛弃,处处都是走不通的穷途。开篇这八句道尽了诗圣晚景的凄惨和人生的悲情。接下来八句是对送别情景的描绘: 雨洗平沙净,天衔阔岸纡。 鸣螀随泛梗,别燕赴秋菰。 栖托难高卧,饥寒迫向隅。 寂寥相喣沫,浩荡报恩珠。 一场秋雨洗刷沙岸,平野格外清净,弯弯曲曲地与远方的长天衔接,显得无比广阔,增添了几分漂泊的寒意;江面的浮木上,寒蝉鸣叫,天空中南去的燕雀也掠过水草,原来万物也都居无定所。流寓他乡,本就难以安心高卧,饥寒交迫中伤心向隅恐怕才是常态。杜甫在江陵过得不顺心,郑审和前篇提到的李之芳是少有的对杜甫友善、关心的朋友,于是杜甫自比涸辙之鲋、伤路之蛇,临行之时,感激他们的“相濡以沫”。最后八句是对前路的畅想: 溟涨鲸波动,衡阳雁影徂。 南征问悬榻,东逝想乘桴。 滥窃商歌听,时忧卞泣诛。 经过忆郑驿,斟酌旅情孤。 秋季,百川灌河,江水上涨,如同鲸翻波动,气势磅礴,往衡阳飞去的大雁也迅捷无比,又一次激发了杜甫以一己之力搏击苍穹的豪情壮志! 这个老头还是那么不服老,还想要往南去,让太守为他下榻,往东边去,乘桴在海上漫游。他想到齐国的宁戚,能够因为一曲商歌被君主听到而得重用;又想起楚国的卞和怀玉,而不被楚王认可,反遭冤诬的结局。真诚地感慨己实在难逢,既是对郑审的认可与留别,也是对前路的深切忧虑。 离开江陵之后,杜甫沿江放船九十余里,来到了三国故城公安,当地姓颜的县尉和一位才学不俗的后生学子卫钧对杜甫十分礼遇,先后摆酒设宴款待,杜甫也一一写诗答谢。杜甫出峡后的诗作主要是这一类的赠答应酬作品,既没有时间深入命意和构思,也没有这种必要,因而也就缺乏现实针对性和艺术创造力,所以其成就很难再现夔州时期的辉煌,这是一种遗憾,也是不得不承认的事实。还值得一提的是,杜甫在公安见到了一位正要入蜀的年轻远亲,名叫李晋肃,也就是中唐大诗人李贺的父亲,杜甫留诗与之送别,虽然此时距李贺出生还有二十二年,但天意让唐诗的先锋火炬在不经意间完成了一次传承。 杜甫在公安写的一首比较好的作品是《公安县怀古》: 野旷吕蒙营,江深刘备城。 寒天催日短,风浪与云平。 洒落君臣契,飞腾战伐名。 维舟倚前浦,长啸一含情。 公安原本是刘备镇牧荆州的驻地,入蜀后交由关羽镇守,后被东吴袭取,又成为吕蒙的封地,四野开阔,江深浪险,控扼荆湘,古来英雄所必争。杜甫抱英雄之志,怀英雄之才,壮英雄之气,临英雄之地,却不能成英雄之业,故而怀古伤今,感兴颇深。杜甫在秋冬时节来到公安,天寒日短,更觉时间流逝;风吹浪涌,高入云天,使人豪气勃发——此情此景,他不禁更加感慨壮志难酬,英雄气短。刘备与关羽,名为君臣,情同手足;孙权与吕蒙,也是升堂拜母,约为兄弟。正是如此的“洒落君臣契”,成就了他们累世的“飞腾战伐名”! 杜甫心中的苦没有明说,但谁都明白,哀叹自己不得与君契合,难骋济世大志,于是只好满怀深情地长啸一声,而后轻移舟船,继续前进,离开这催人泪下的英雄城。 二、“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在公安居住没几日,一个清晨,杜甫再度起航,留下“舟楫眇然自此去,江湖远适无前期”的名句,向长江下游继续前进,朝洞庭湖边的重镇岳阳而去。这次跋涉的时间略长一点,途中经历了好几个夜晚。其中一天,杜甫听闻临近的舟船之中有人吹奏觱篥,凄厉的乐声弥漫江上,顿时生发旅愁,作下了《夜闻觱篥》一诗: 夜闻觱篥沧江上,衰年侧耳情所向。 邻舟一听多感伤,塞曲三更欻悲壮。 积雪飞霜此夜寒,孤灯急管复风湍。 君知天地干戈满,不见江湖行路难。 觱篥是西域传入的一种胡乐,形似喇叭,以芦苇做嘴,以竹做管,吹出的声音悲惨凄切,常常是旅人在客中所奏,催人泪下。衰暮之年的杜甫,在寒夜沧江之上听闻临舟用觱篥吹奏着塞上之曲,情感与之高度共鸣,更觉得天涯悲壮! 眼下这个夜晚,积雪飞霜,寒冷异常,对着孤灯,听闻急管,加之满耳的风涛振响,这景况又增添了几分凄凉。自古声能传情,杜甫是知音之人,从乐曲中听出了吹奏人表达的干戈离乱之苦,然而这种知音是单向的,吹奏之人却无从体察杜甫江湖行路的艰难。从这短短的一首诗中,我们便能体察到杜甫晚景的萧瑟凄惨。 大历三年年末,杜甫的小船终于抵达岳阳,比起在江陵和公安的待遇,杜甫在岳阳的生活境况更为凄凉,甚至没有像样的官员和士绅来主动接济他,他也因此深入体察了这里的民生疾苦,写下了晚年最具现实意义的一首诗《岁晏行》: 岁云暮矣多北风,潇湘洞庭白雪中。 渔父天寒网罟冻,莫徭射雁鸣桑弓。 去年米贵阙军食,今年米贱大伤农。 高马达官厌酒肉,此辈杼轴茅茨空。 楚人重鱼不重鸟,汝休枉杀南飞鸿。 况闻处处鬻男女,割慈忍爱还租庸。 往日用钱捉私铸,今许铅锡和青铜。 刻泥为之最易得,好恶不合长相蒙。 万国城头吹画角,此曲哀怨何时终? 岁暮的风雪带着北方的凛凛寒气,席卷了潇湘大地,整个浩荡的洞庭湖都被银白色覆盖,湖上的渔人、山林里的猎户都因为天寒地冻,难以生产,导致生计蹇迫;对于从事农桑的平民而言,无论收成是丰是歉,都将成为受害者,为了应对朝廷的租税,竟到了卖儿鬻女的地步;而达官贵人的生活却奢靡如故,甚至还通过私铸钱币,加大对百姓的剥削。这就是大历初年长江中游地区的社会现状,杜甫的痛惜之情犹如那城头的画角声,厚重绵长而又迟迟不尽。这首诗与《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北征》有相同的现实针对性,所不同的是,后两首诗发挥了五言古诗的叙述特长,以纪行为线索,通过具体情境的描绘和讲述,来表现国家离乱、人民疾苦和自己忧时伤世的思想;《岁晏行》则发挥了七言歌行自由洒脱、长于抒情议论的特点,以饱含感情的笔力纵论时事,表现对时衰世乱的思虑。 洞庭湖边有三国时期东吴鲁肃训练水师的阅兵高台,历经六朝增修,成为了一座可以俯瞰洞庭、极目潇湘的楼宇,人称岳阳楼,杜甫登临此处,作了《登岳阳楼》: 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 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 亲朋无一字,老病有孤舟。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 这首诗是杜甫出峡以后最有名、成就最高的作品,胜就胜在前四句的“境界阔大”、后四句的“生平落寞”以及前后八句之间“阔狭顿异”所形成的巨大反差。前四句中,有昔与今的对照、高与广的对照、水与山的对照、地与天的对照,所有一切关系都集合在一片洞庭烟波之中,冲突鲜明而又浑茫无间。“吴楚东南坼,乾坤日月浮”是千古名句,洞庭湖如同一个天然的裂口分离吴楚,也阻隔了在楚而思吴地的杜甫的去路,日月天地都如同在湖上运行,既让人感慨其壮阔,也对自己无论如何都走不出它的怀抱而感到悲壮。这一句像极了曹操在渤海之滨的高唱,“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虽然一是湖、一是海,但对于胸襟同样博大的两位旷世奇才而言,这种气吞斗牛、胸怀天地的境界是一致的。所不同的是二者的心态,曹操是开创时代的帝王,在平定北方之后登临沧海,挥鞭南下,眼里是雄途进取的英雄壮志;而杜甫眼下,亲朋无问、孤舟作伴、老病缠身、理想破灭,对天下兵戈只能徒然泪流,多的是英雄末路的悲哀与凄凉。 三、船儿悠悠 杜甫和他的小船,停泊在洞庭湖畔的岳阳度过了年关,开年便是大历四年(769),杜甫五十八岁了。原本想顺江东下直达吴越的杜甫,由于身体状态每况愈下,不得不搁置了之前的计划,转而前往衡州去投奔担任刺史的好友韦之晋,希望能在那里过上安定的生活,以卒余年。于是,他经由洞庭湖、青草湖,从长江驶入湘江,一路溯江南下,经过白沙驿、乔口、铜关渚、新康镇、双枫浦等地,虽然身体抱恙,但一颗创作的诗心却从未停歇,一路都留下了诗作,直到潭州,也就是如今的长沙。 杜甫到达潭州时,已时近清明,他写作了《清明二首》,是这一时期较有代表性的作品。其一: 朝来新火起新烟,湖色春光净客船。 绣羽衔花他自得,红颜骑竹我无缘。 胡童结束还难有,楚女腰肢亦可怜。 不见定王城旧处,长怀贾傅井依然。 虚沾周举为寒食,实藉严君卖卜钱。 钟鼎山林各天性,浊醪粗饭任吾年。 潭州春色正好,天气晴朗,春水荡漾,杜甫住在舟中,晨起做饭便清晰地看到小舟在明澈的湘江上飘荡。抬眼望去,美丽的飞鸟口衔着春花在天上自在飞翔,娇美的少年骑着竹马,无忧无虑地嬉戏打闹,只是这般快意美好都与自己这个衰病的老头子无缘。蜀地比起峡中,脱离了胡汉杂居的环境,这里的女孩腰肢纤细,惹人怜惜,使人不禁想起了春秋时好细腰的楚王和这里悠久的历史文化。汉代的长沙定王府而今已无踪迹,仅存的古井让人依稀想起太傅贾谊,他才华出众却被排挤出朝廷,贬谪至此,杜甫又从这位古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清明的前一天是寒食,按照习俗禁火不能烧饭,以杜甫如今的身体哪里承受得了,好在东汉有个叫周举的刺史怜惜百姓身体,曾经停罢了这一风俗,这让杜甫庆幸有据可依,时隔千载竟虚沾此番美意,得以将卖卜告讨祈求来的食物做成温热的饭菜,以之度日。杜甫感慨无论富足奢侈的生活,还是山林平淡的生活,这都是天意,不能过分渴求,晚年的他有浊酒一杯、粗茶淡饭,也就满足于此,了结余生了。然而事实上,即便是“浊醪粗饭”,对漂泊湖湘的杜甫而言,都已经成了一种得来不易的奢求。再来看其二: 此身飘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 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 十年蹴踘将雏远,万里秋千习俗同。 旅雁上云归紫塞,家人钻火用青枫。 秦城楼阁烟花里,汉主山河锦锈中。 春水春来洞庭阔,白苹愁杀白头翁。 杜甫的一生苦于东西漂泊,居无定所,然而奔波并没有换来功名,反让他落下一身的病根儿,他的右臂已经偏瘫,耳朵也一半变聋,还患有严重的消渴症。生涯寂寂,余年牵挂在一只小船上,想到这些,不禁使人双泪俱下;岁月悠悠,常年与病枕相伴,只能再用左手写出心中块垒,感怀世事多艰。安史之乱爆发十多年来,自己就像这清明节的蹴鞠一样被踢来踢去,携带着子女流落得越来越远,又好像他乡的秋千,虽然来回飘荡,却总也心向故乡。春回大地,眼望着空中的旅雁入云,便羡慕它们又将飞回北方的关塞,然而,舟中的家人取火,却仍然是要使用这江南的青枫。想象起清明佳节,长安城里的一些楼台殿阁都掩映在如烟的繁花丛里,而大唐的壮丽山河也闪耀在这片灿烂夺目的春光锦绣之中。而这一切,他都看不到,春水方生,洞庭潇湘都显得更加辽阔,但满满的白苹,却照应着满头的白发,打破了青春的美好,愁坏了杜甫这个多病思归的老翁! 在潭州,杜甫还游览了著名的岳麓山。这是长沙的地标之一,山上可以俯瞰全城,也有著名的佛教宝刹麓山寺,杜甫的故交、开元后期的文坛领袖李邕曾为之撰写碑文;山脚还有一座道林寺,北宋时期被拆掉改建成了岳麓书院。杜甫登岳麓山,顺便游览二寺,写下了一首长篇的《岳麓山道林二寺行》,以记录自己的游踪,这首诗从题目来看是歌行,从内容来看又颇为对仗,平仄严整,是唐诗中极为少见的七言排律。前面讲过,五言排律写作的难度很大,极能体现一个人的才气和学养,相对而言,长篇七言排律的难度就更大了,全唐都没有留下几首,就是杜甫这样的诗圣写出来也不能说是尽善尽美,主要还是由于这种体裁过于板滞凝重,加之格律的限制,就越发不能自由地写景叙事和议论抒情了。 四、第三首《望岳》 在长沙没有停留太久,杜甫接着沿湘江向南而去,经过凿石浦、津口、空灵岸、花石戍等地,便远远地望见了南岳衡山,也因而写下了人生中的第三首《望岳》。这是一首五言古诗: 南岳配朱鸟,秩礼自百王。 歘吸领地灵,鸿洞半炎方。 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 巡守何寂寥,有虞今则亡。 洎吾隘世网,行迈越潇湘。 渴日绝壁出,漾舟清光旁。 祝融五峰尊,峰峰次低昴。 紫盖独不朝,争长嶫相望。 恭闻魏夫人,群仙夹翱翔。 有时五峰气,散风如飞霜。 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 归来觊命驾,沐浴休玉堂。 三叹问府主,曷以赞我皇。 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朱鸟”即朱雀,是古代神话传说中镇守南方的神兽,与南岳相配,对它们祭祀由来已久。然而在唐代,南岳衡山在五岳中是相对落寞的:泰山“五岳之尊”的地位自不必说,合朝上下无不对泰山封禅趋之若鹜;华山与嵩山,一个靠近长安,一个毗邻洛阳,最方便天子驾幸;北岳恒山相对偏远,但也临近唐王朝的龙兴之地太原,依然有机会得到皇帝的眷顾;唯有南岳衡山,独处南国,寂寥久矣。在杜甫看来,大概自舜帝亡于潇湘,就断绝了后代帝王对这里的巡守。如今,杜甫这位伟大而又寂寞的诗人,来到了同样伟大而又寂寞的衡山脚下,渴望能够游走于山崖峻岭中追逐太阳,或泛舟于闪耀着清光的江上,去近距离感受它的伟大。祝融峰是南岳的主峰,极为高耸,山顶似乎直抵天上的昴星,诸峰皆朝于它;中唯有紫盖山势转东去,与之争高,不相上下。南岳流传着魏夫人的传说:她名叫华存,是晋司徒魏舒之女,幼好道术,得太极真人授《黄庭经》,得以托剑化形,登仙而去,成为南岳夫人。杜甫看见山头风吹云霞动,便想象这可能是群仙簇拥着魏夫人前来巡查了。杜甫远望南岳,限于前路漫漫,没有时间拄着杖爬上高崇的山岭,盼着归来之时能够登上庙堂,亲致祭祀,愿神灵赞助天子,降福人世,此心赤诚。 五岳之中,除了北岳恒山之外,杜甫应该都去过,其中在泰山、华山、南岳衡山先后写下了三首《望岳》,从青春壮志的“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到中年危机的“稍待秋风凉冷后,高寻白帝见真源”,再到垂暮之年的“牵迫限修途,未暇杖崇冈”,面对三座大山,他走出了他一生浮浮沉沉,背负着国家命运的沉重,不经意间登上了一座诗歌的高峰。 他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座高峰 也是时代洪流中的一粒沙 从盛世到乱世,直面历史的洪流与苍茫的宇宙 诗圣杜甫,凡人杜甫 可叹、可敬、可感的诗意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