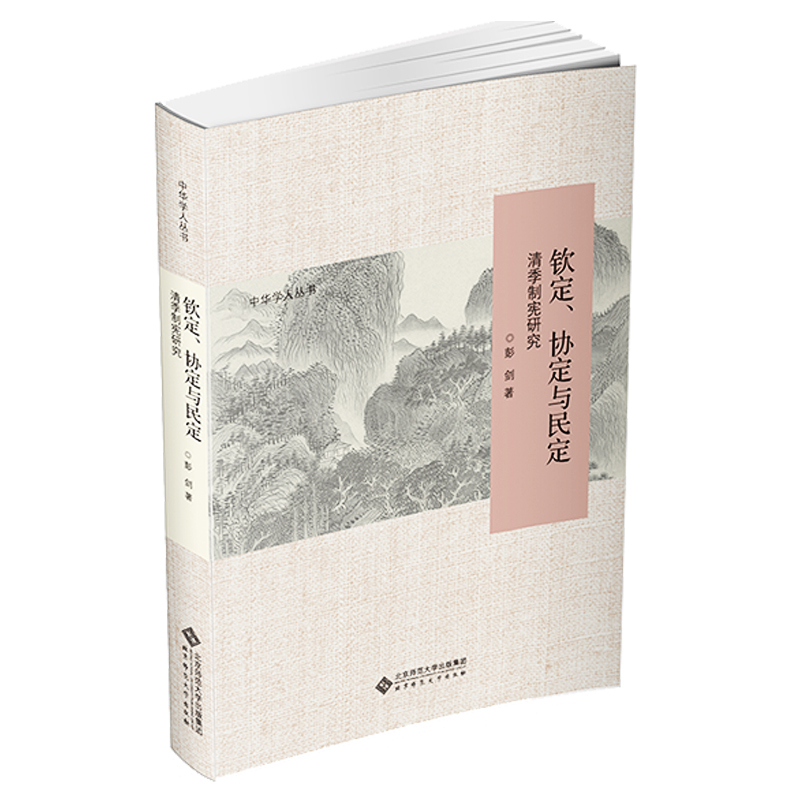
出版社: 北京师大
原售价: 79.00
折扣价: 53.80
折扣购买: 钦定协定与民定(清季制宪研究)/中华学人丛书
ISBN: 97873032639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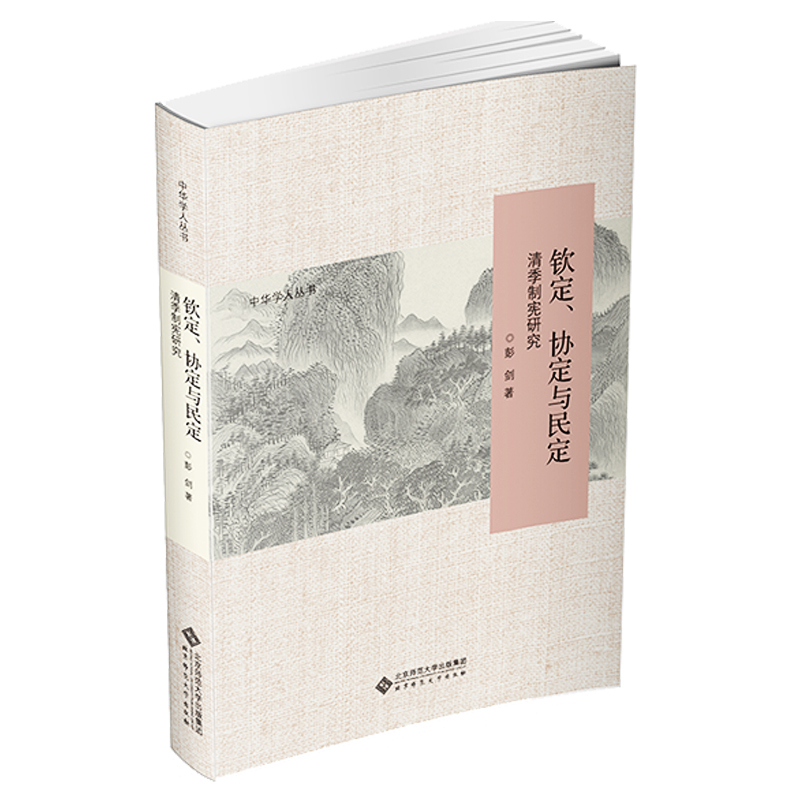
彭剑,1975年生,湖南宁乡人。1995年考入华中师范大学历史系,先后在此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2005年进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后流动站,2007年开始任教于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以辛亥前后史事为学术专攻。
"第十二章 制宪乃生死关头 一、生死关头 清廷宣布要迅速制定宪法之后,民间最初并不反对钦定。 比如,在派遣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的次日,《申报》就刊登了一篇文章,认为宪法既然冠以“钦定”名目,那就必然会“由朝廷订布”,不会允许臣下过问,且会在召开国会之前颁布,因此,在缩短开国会年限之后,派遣大臣制宪是合适的。该文还认为:“我国宪法,大纲早经先帝颁示,煌煌大典,已具雏形。”[ 醒:《读宣统五年开设国会上谕恭注》,载《申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五日。]该文对依照《宪法大纲》制定宪法持认可态度。而如我们所已知,《宪法大纲》确立的乃是钦定的制宪原则。 不过,很快,令人眼前一亮的一个词语出现了。 1910年11月8日,《申报》刊登的一篇《时评》对制宪问题发表意见,其中有如下一句: 记者敢为一班起草员告曰:编订法典为国会良楛、人民生死关头,不得视为过易,而率尔操觚,亦不可畏难,而迁延遗误。[ 《时评(其一)》,载《申报》,宣统二年十月初七日。] 制宪期间,民间发表了大量评论,堪称文山论海。但万语千言,都抵不上“生死关头”这四个字有分量。它的出现表明,在清廷派遣制宪大臣,起草宪法提上日程之后,民间很快看到了制宪一事的极端重要性。制定得好,人民权利有保障,人民才有生路;制定得不好,人民权利被剥夺,便只有死路一条。 既然制宪关系到人民生死,那就应该打破钦定,争取人民的制宪权。但是,该文作者没有提出这一主张,而是寄希望于制宪大臣。“不得视为过易”“亦不可畏难”云云,听起来振振有词,好像在对制宪大臣提出严格要求,但不争取制宪权,空言岂能有什么力量? 不过,当我们第二次在《申报》上看到“生死关头”一词的时候,该报已经极力主张打破钦定了。 这是该报于12月11日刊登的一篇时评。文章犀利地提出,派溥伦、载泽制宪的做法是不对的。因为宪法是“君民共守之法”,除了日本之外,其他各君主国制宪的时候,“皆有人民参预其间”,“断非一二亲贵所能独断独行,而拉杂纂拟”。 该怎么办?应该让资政院参与制宪。不过,《资政院章程》第十四条规定,资政院无权议决宪法。因此,人民要参与制宪,“首宜废去此条文”。若不如此,也该“别谋组织机关,以为要求参预之根据地”。总而言之,现在到了制宪的时刻,“生死关头,吾国民幸毋忽视之也”。[ 《时评(其一)》,载《申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十日。] 与“生死关头”类似的说法,是“生命关头”。 《申报》11月25日刊登的一则《时评》写道: 宪法为君民共守之法,尤为人民保障权利之法,生命关头,吾民断不可漠视也。今直隶谘议局有联合各省共同研究之举,而请愿代表团复有会集海内法政家纂拟成书呈备采择之通告,江苏人民权利思想素富,而上海又为法政发祥之地,其亦有名流巨彦同声相应,以襄此盛举乎。[ 《时评》,载《申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这一时评,号召江苏和上海精通法学的人们行动起来研究宪法,纂拟成书,因为制宪一事,乃是“生命关头”,国民不可漠视。 至于《时报》,则用了“万劫不复”一词表达“生死关头”的含义。该报11月21日所登《论宪法与权限》一文写道: 使当此政府纂拟宪法之时,而吾人民一若置诸不闻不问也,袖手以俟三年后之召集国会,罔或起而争之,则自今以往,万劫不复,又乌用是半面时装之立宪傀儡登场之国会为哉。[ 帝民:《论宪法与权限》,载《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 此文同样号召人民行动起来争取制宪权,否则会堕入万劫不复的境地。 正是因为意识到制宪一事是一个生死关头,若不争取制宪权,国民将万劫不复,在野的精英们采取了一些争取制宪权的行动。 二、国会请愿代表:争取参与 清廷在11月4日宣布将于宣统五年(1913)召开国会,并于此前设立内阁、颁布宪法的同时,要求各省请愿代表不再滞留京师,立即解散。[ “十月初三日内阁奉上谕,现经降旨,以宣统五年为开设国会之期,所有各省代表人等,著民政部及各省督抚剀切晓谕,令其即日散归,各安职业,静候朝廷详定一切,次第施行。钦此。”(《政治官报》,宣统二年十月初四日。)] 但是,在京的请愿代表们没有立即遵旨散归,而是向各省请愿同志会发出了一份通告,表示要先听父老们的意见,再决定是否继续请愿。 在此通告中,请愿代表向各省的请愿同志会提出了一系列问题,比如,离开国会还有三年,而三年中列强环视,“外交上有无变更与否”?现在财政竭蹶,国内“有无嚣暴与否”?在召开国会之前设立内阁,无人监督,“有无滥用权力与否”? 在众多问题中,有一问是针对制宪的:“宪法先颁而不经国会通过,有无权限失当与否?”[ 《同志会通告书》,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宣统二年。] 其实,对于这些问题,请愿代表心中并非没有答案。他们只是以提问的方式提醒读者,这些问题值得注意。聪明的读者看了他们所写的这些问题,自然都会选择“是”,而不会选择“否”:在未开国会的这三年之中,外患内忧,是会日益严重的;没有国会的内阁,是会有权力滥用的;不经国会通过的宪法,是会存在权限适当问题的。 当然,留京的请愿代表也并非时时都用这种迂回的宣传策略,他们有时也会用很直白的语言表明自己的观点。比如,在上述通告之后不久发布的另一份通告中,请愿代表就直接提出要设法参与制宪: 宪法、议院法、选举法及官制、内阁组织法,此数项为国会未开以前应行设备之事,自应要求赶早编订,并设法参预之。[ 《同志会通告书》,载《东方杂志》,第7年,第11期,宣统二年。] 那么,该如何参与制宪? 在一份通告书中,请愿代表们介绍,北京报界有人提出过一种设想,即在人民中推举代表,参与政府制宪。“未审海内政法家意见如何?”通告书虽这么问,但执笔者对这种做法显然并不欣赏,因为“允准与否尚难逆料”。他们提出了另一种参与方式:“私家纂拟成书,呈备采择。” 通告书继续写道,如果能将宪法等“代为编纂,克期告成”,也许开国会年限还能再缩短,国会请愿还能再继续。因为据其观察,“朝廷初无成见以靳国会”,之所以“迟迟不即举办”,就是因为宪法、议院法、选举法未起草好。如果能将它们“代为设备”,就可以使那些“持缓进主义者无所设辞”,“关其口而夺之气”。如此,“则异时请愿,度尚可再举”。[ 《国会代表团再通告书》,载《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八日。] 作为国会请愿代表,其关注制宪时总是与国会问题挂钩,本无可厚非。但是,换个角度来看,他们的观点就有些问题。此前,他们向人们暗示,宪法不经国会通过就颁布,会有权限适当的问题。按照这一思路,那就应该争取先开国会,后定宪法。但他们计不出此,而是提出由个人草拟,进呈给政府,供其参考,以便能尽快制定宪法等法典,然后再提出进一步缩短开国会年限的要求。若依此而行,即使遂愿,也还是先颁宪法后开国会,宪法还是没有经过国会通过就颁布了,还是难免“权限适当”。因为私拟的法典草案,进呈之后,采择与否,是全无把握的。尤其是宪法,如果不合清廷“巩固君权”的宗旨,那么私拟的草案陈义越高,束之高阁的可能性越大。 倒是12月初报刊披露的请愿代表团的一份最新通告书提出的参与制宪的方式,能够较好地打破钦定。 该通告书提出,目下应该重视的问题有四项,其中的第二项为制宪问题。[ 另三项分别为督促政府速立新内阁、请释党禁、灌输国民宪政之知识。参见《同志会通告海内外书》,载《申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从表面上看,这份最新通告书并不反对钦定,宣称“吾国宪法诚当然出于钦定”。但是,从其所谈的制宪方法来看,绝非钦定,而是协定。在支持钦定的名义下打破钦定,这是在野者打破钦定的一种方式。 通告书认为,溥伦、载泽两人虽奉命纂拟宪法,但他们所起的作用,不过是“名议上总其大成”,宪法条文肯定都“出于协纂之手”。有机会成为协纂的,肯定都是宪政编查馆的人。而宪政编查馆的官员,“灌输东学,浸淫日久”,必然会以日本宪法为模仿对象。若如此,“其危险不可思议”。因为每个国家的历史、地理、风俗、习惯都不相同,不可“强以相绳”。 制定宪法关系到“国家之存亡,人民之生死”。为了打破制定的宪法完全以日本为蓝本的局面,该通告书提出,要由各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直接给资政院打电报,请资政院具奏上请,待将来宪法起草好了,作为法典议案,由该院“协赞通过”后,再由“君上裁可颁行”。[ 《同志会通告海内外书》,载《申报》,宣统二年十一月初五日。] 资政院是为国会做预备的,其议员中有一半来自民选,另一半来自钦选。宪法若能由其议决,那就意味着人民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制宪,与由国会议决,具有相似的意义。 将争取人民的制宪权落实到争取资政院的“协赞”权,这是一个不错的主意。不过,这是马后炮。因为在请愿代表之前,早有人讨论这一主张,且资政院议员已采取过切实的措施,试图争取“协赞”权。 三、争取资政院的协赞权 (一)《申报》:资政院要争权 早在11月15日,《申报》就刊文提出,由专制政体进于立宪政体,必须有一个“最高之立法机关”,从事制定宪法等工作,这是“稍有政学者所同知”的。在共和国,立法权属于人民;在君主立宪国,裁可之权虽然属于君主,但立法之权则属于国会。我国的国会要等到宣统五年(1913)才召开,那么,要提前赶定的包括宪法在内的各种法典,当由什么机构负责? 该文作者注意到,此前,因无立法机关,法典都由宪政编查馆负责。但是,现在资政院已经成立,就不应该再由宪政编查馆负责,而应该由资政院负责,因为资政院被定位为上下议院的基础。该文作者推测,上谕在布置制宪事宜的时候,没有赋予资政院立法的权责,说明朝廷仍然有意继续以宪政编查馆为负责机关——这是该文作者的误会,其实,清廷的本意是要剥夺宪政编查馆的制宪权,宪法草案制定后,并不会交给该馆查核,而将直接钦定。 该文认为,宪政编查馆不应该享有立法权。而按照《资政院章程》,该院议员有立法权,这是“先朝设立资政院之本意”。如果还将立法权交给宪政编查馆,则是该馆侵权。文章明确提出,资政院要向政府提出质问案,争取参与制定宪法等立法权,不可放弃责任。末了,还加一句:“吾不知朝廷何故靳而不予也。”[ 嘉言:《再读十一日上谕谨注》,载《申报》,宣统二年十月十四日。]其矛头直指清廷,表达对清廷不让资政院参与制宪的不满。 《申报》11月20日刊登的一篇文章则写道,人们早就注意到,4日宣布缩短国会年限的上谕存在一个严重的问题:人民为了速开国会,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请愿运动,但是,上谕却说,之所以会缩短国会年限,“系采取各省督抚之奏章及王大臣之谋议”,完全不将人民放在眼里。因此有人大胆推测,将来制定出来的宪法,其内容“益可想见”,肯定摧抑民权。 作者继续以介绍他人观点的笔调写道,有人提出,要预防出现这种局面,必须争取资政院参与制宪的权力,“宪法非经资政院之协定,而议院、选举诸法非经资政院之协赞,吾民必不能承认之”。这里明确提到宪法要由资政院“协定”,否则,人民不予承认。并且,资政院议员也不能完全相信,人民应该“别设机关”,既作为资政院的后援,又监督资政院,如果发现了“不忠于民之议员”,这个机关要“设法对付之”。[ 樊:《论国会问题之一喜一惧》,载《申报》,宣统二年十月十九日。] (二)《宪法大纲》的表与里 11月21日,《时报》刊登的《论宪法与权限》一文,也明确反对清廷的钦定主张,不过,对于资政院的“协赞”,该文也不太看好。 该文作者注意到,《宪法大纲》(实则是宪政编查馆等上奏《宪法大纲》时的奏折)中有如下一句话:“宜使议院由宪法而生,不宜使宪法由议院而出。” 该文作者指出,对这句话,不能满足于表面含义,而要注意到它的深层含义,从表与里两方面入手,才能参透其真意。他的分析,可谓一针见血:“就表面观之,似为争立宪与议会之先后,而就里面观之,则在争宪法之成立于上而非成立于下也。”成立于上的宪法,即钦定宪法;成立于下的宪法,则是协定宪法或民定宪法。 在该文作者看来,宪法是不能成立于上的,因为“所谓宪法者,君与民均纳之于范围之中,而所当共同遵守者也”,因此,“宪法之发生,君与民共同制定而始成立,否则偏于独裁,仍未铲除专制之旧根性,非特效率无由生,而与宪法之原则相违背者也”。 但是,我国的宪法则明确规定要钦定。在该文作者看来,这“不啻明视宪法为在上者之专有物,而不容吾民之置喙”。并且,颁布宪法在先而召开国会在后,这是告诉臣民,大家只有“赐予闻政”的份儿。 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形?该文作者认为这是宪政编查馆的责任,因为宪政编查馆的人不懂三权分立是立宪的基本原则,议院拥有立法权更是各国的普遍做法。[ “三权鼎立之主义,昭然如日月同明,而议院操立法之权,尤如江海之导源于星宿,世界立宪各国固如出一辙。”(帝民:《论宪法与权限》,载《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日。)] 本来,资政院成立之后,应该享有立法权。但是,《资政院章程》却规定,宪法不交资政院核议。这说明资政院只是政府的附属机关,“弗克代表国民之公意”,即使让它参与制宪,给它“协赞”权,也未必能制定出一部好宪法来,何况还不让它参与呢?该文作者听说宪政编查馆将要改成“宪法局”了,并由此推测,将来协纂宪法,肯定都由该局来承担,资政院越发“处于退婴”,成为无用之物。 该文作者既然不看好资政院的协赞,乃号召人民起来争取制宪。在他看来,从来没有哪个国家有宪法而无国会,因为“稽宪法成立之源,可谓因有国会而起”。如果在制定宪法的时候没有国会参与、协赞,则宪法将毫无价值,“无异一纸之空文”。但是,我国国会还要等三年才会成立。因此,人民现在应该起来争取制宪权,不能袖手旁观,等待三年后的国会召开,否则,将有“万劫不复”之虞。 (三)吴赐龄等人:删除“但宪法不在此限”七字 在媒体热议是否可以通过争取资政院参与制宪以打破钦定期间,以吴赐龄为首的一些资政院议员,递交了一份《修改资政院章程提案》。其中,对于《资政院章程》第十四条的修改意见与制宪问题直接相关。 《资政院章程》第十四条关乎资政院可以讨论的事项的范围,涉及资政院的权限,内容如下: 资政院应行议决事件如左:一、国家岁出入豫算事件,二、国家岁出入决算事件,三、税法及公债事件,四、新定法典及嗣后修改事件,但宪法不在此限,五、其余奉特旨交议事件。[ 《资政院会奏续拟院章并将前奏各章改订折(附清单)》(宣统元年七月初八日),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下册,632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 提案关于此条的修改意见有两点,一是将“法典”改为“法律”,二是删去“但宪法不在此限”七字。 提案对将“法典”改为“法律”的理由说得很简单:“典字不如律字之赅括。”概括性强的法律所包含的内容,必然比概括性弱的法典要多。因此,一字之改,实有扩大资政院权限之意。 至于删除“但宪法不在此限”七字,则显然是为了争取资政院参与制宪的权力。为什么要删除这一句?提案做了详细说明。 从法理上说,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也是其他法律的渊源。“法政”有“三要件”:宪法、民法、刑法。民法是保护私益的,刑法是保护公益的,但要确定权利义务的界限、法律命令的范围,则要以宪法为标准。宪法如此重要,因此,要想宪法能够“垂之百世而无弊,推之天下而皆准”,就必须在“明乎立国之本”的基础上,“辨析至精,权衡至当”。要做好“辨析”“权衡”的工作,当然要扩大参与面,给资政院参与制宪之权。若不如此,万一稍有不慎,就会“酿成莫大之忧”。 从事实上讲,1908年的《宪法大纲》就由宪政编查馆和资政院会奏的,奏折内写得很清楚:“此折系宪政编查馆起草,会同资政院办理。”也就是说,“当时宪法大纲已由资政院参与会内(同)奏请钦定”。提案写道,“景庙”(光绪皇帝)那么“神圣”,都让资政院参与制定了《宪法大纲》,何况今上“尚在冲龄”,还是个小娃娃,当然更应该让资政院参与制宪了。并且,缩短开国会年限,钦派制宪大臣之后,“海内外人民希望参与宪法之热诚较之国会尤为殷切”,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只允许少数人参与,“不免起天下之争”,不如让资政院参与制宪,让较多人参与,“最足起臣民之望”。 提案还说,资政院参与制宪跟钦定的宗旨并不冲突,因为“经会场通过后,仍由议长会同军机大臣及编纂大臣奏请圣裁”,这完全是“恪遵钦定宪法之祖训”。[ 《修改资政院章程提议案》,载《顺天时报》,宣统二年十月二十四日。] 说宪法重要,因此需要多数人参与,这是多年来人们言之甚多的问题,并无新意。但是,以允许资政院参与制宪跟钦定不冲突为说辞,倒是一个创新。[ 很快就有人跟着这么说,并且有所发展。例如,1911年1月初徐敬熙在《申报》刊文,提出纂拟宪法大臣起草好宪法之后,在由君主钦定之前,应该先交资政院协赞,并论道:“若谓先经国民协赞有背于钦定名义,不知所谓国民协赞者,乃表示国民之意志,非谓国民协赞即定为法律。其裁可之权,仍上操于君主也。且正惟尊重主权之故,欲期推行于后,自当审慎于先。即以资政院之钦选议员为言,亦必先由各部院互选,后由朝廷钦选,未闻以互选之故,背于钦选。或又谓既有纂拟,又有协赞,不无抵触。然纂拟与协赞,权限分明,毫无顾虑。纂拟者纂拟未成之宪法,协赞者协赞已成之宪法。纂拟者为起草员之代名词,纂拟毕责亦毕。若协赞者,乃据其纂拟之结果,审其当否,而上诸君主,仰凭裁可者也。故析言之,纂拟自纂拟,协赞自协赞,钦定自钦定,界线严明,罔相逾越。而合言之,纂拟、协赞为一级,钦定为一级,上下贯通,互相结合。所谓钦定手续,固不得不如此也。”(徐敬熙:《钦定宪法义解》,载《申报》,宣统二年十二月初八日。)徐敬熙此文将纂拟、协赞、钦定分为制宪的三个不同阶段,是挺有意思的。并且,徐敬熙还以资政院中出自部院衙门的钦选议员,是先经部院互选,后面才有钦定为由,说明先有较多人参与并不违背钦定,进而提出经资政院“协赞”的宪法与“钦定”不违背,也是新信息。徐敬熙在1907年的时候就积极建言献策,推进宪政改革。时任两江总督的端方曾代递过他的一份呈文,颇能从三权分立的角度探讨立宪事宜。据此呈文,1907年时徐敬熙的身份是“候选内阁中书、江西副贡”[《两江总督端方代奏徐敬熙呈整饬行政立法司法机关折》(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八日),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册,261页,北京,中华书局,1979]。]并且,提案拿资政院与宪政编查馆会奏了《宪法大纲》说事,也有新意。虽然当时的资政院徒有其名,建制不全,人才匮乏,《宪法大纲》完全出自宪政编查馆之手,资政院只是列名而已,但是,奏折中确实写着“会同资政院办理”的字样,白纸黑字,谁也不能否定资政院参与了此事。既然资政院能参与《宪法大纲》的制定,为什么不能参与正式制宪的工作呢?提案的逻辑便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