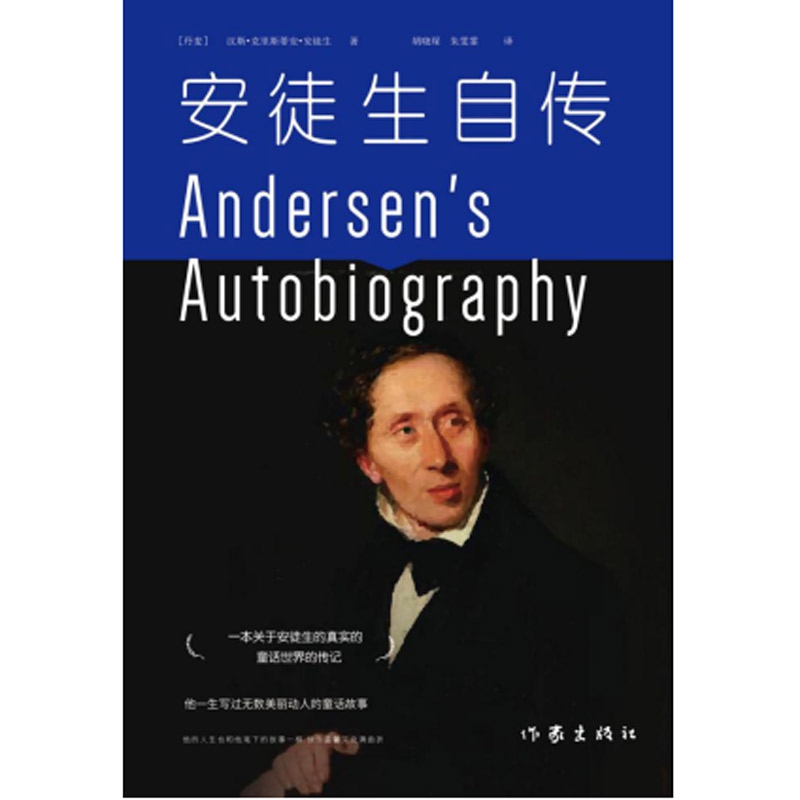
出版社: 作家
原售价: 28.00
折扣价: 18.00
折扣购买: 安徒生自传
ISBN: 9787506395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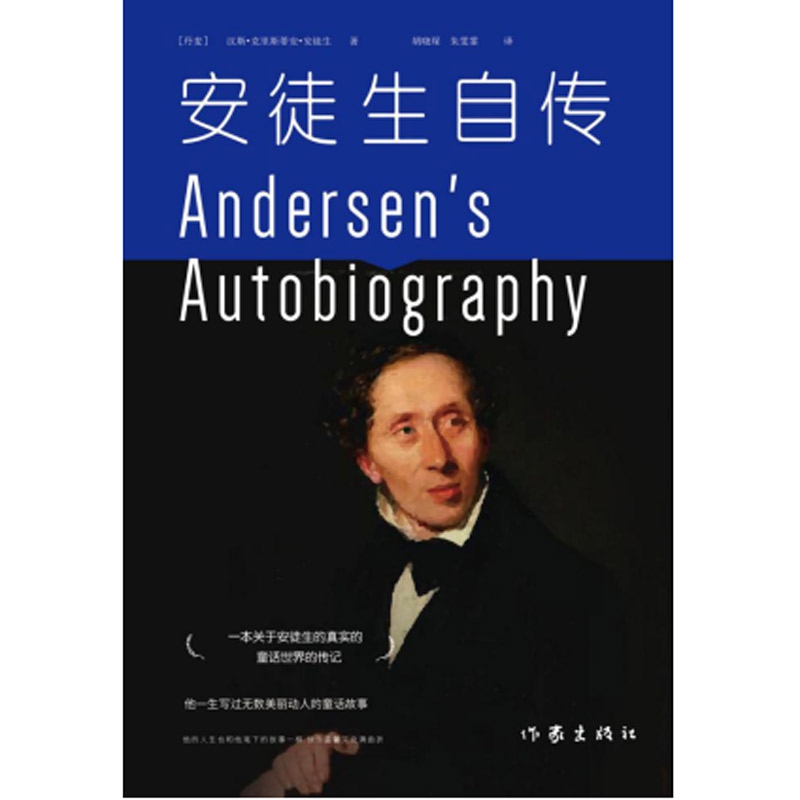
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1805—1875),19世纪丹麦著名的童话作家,同时又是诗人、旅行者及剧作家。安徒生写过诗集、小说、剧本、游记及童话,著有168篇童话和故事,被尊为现代童话之父。其著名的童话故事有《小锡兵》《海的女儿》《拇指姑娘》《卖火柴的小女孩》《丑小鸭》《皇帝的新装》等。安徒生生前曾得到皇家的致敬,并高度赞扬他给全欧洲的孩子带来了欢乐。《安徒生童话》已经被译为150多种语言,在全球出版发行。
我的早年生活 我的人生是一部美丽的童话,快乐温馨又充满曲折。少年时期, 我只身闯荡世界,一贫如洗,孤独无依,幸而遇见了一位善良的精灵,她对我说:“选择你自己的人生方向,并确定你为之奋斗的目标, 听从你的意愿和理智,我会给予你指引和保护,直到实现你的目标。” 这是命运对我最愉快,也是最为庄严郑重的启示。我的人生阅历告诉我,也将告诉世人:仁慈的上帝善意地主宰着世间万物。 我的祖国丹麦是一个诗意浪漫的国度,这里延续着广受喜爱的民间传统,古老的歌谣仍在传唱,丰富灿烂的历史与瑞典和挪威一脉相承。丹麦的岛屿上分布着茂密的山毛榉树林、绵延起伏的农田和三叶草地,放眼望去如同一座座巨大的花园。这些花园式的岛屿中有一座叫菲英岛(Funen),我出生的城市欧登塞(Odense)就坐落在这座岛上。欧登塞一名来源于异教的大神奥丁(Odin),传说这里是他的神殿。欧登塞是菲英岛的首府,距哥本哈根二十二英里(丹麦计量单位中的英里。——译者注)。 1805 年,欧登塞一间狭小简陋的小屋里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妇, 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丈夫是个鞋匠,尚不满二十二岁,却极具天赋和诗人的才智。妻子稍长几岁,对生活和世界一无所知,但心地十分善良。年轻人自己造了制鞋用的长凳和婚床。前不久,他用来制作床架的木架子上还停放着病逝的特兰珀(Trampe)伯爵的灵柩, 供人凭吊,木架子上残留的黑布记录着这件事实。 1805 年4 月2 日,这里躺着的就不再是黑纱和蜡烛环绕的贵族尸体了,而是一个活生生的高声啼哭的婴儿——那就是我,汉斯·克里斯蒂安·安徒生(Hans Christian Andersen)。据说,在我出生后的头几天里,父亲就坐在床边朗读霍尔堡(Holberg)的剧作,我却哭个不停。据说父亲会以玩笑的口吻命令我:“你能不能睡觉或者安静地听一会儿?”但我还是哭个没完没了。即便在教堂受礼时我也哭得惊天动地,以至于那位脾气暴躁的牧师说:“这孩子哭得简直像猫叫!”母亲对此事一直耿耿于怀。幸好当时我的教父戈马(Gomar),一位贫穷的外来移民,安慰母亲说,我在婴儿时期哭得越大声,将来长大后唱歌的嗓音就会越甜美。 我们的小屋几乎被鞋匠的长凳、大床和我睡的小床填满了,我的童年时光就是在这里度过的。好在墙上挂满了画,长凳上有一个小橱柜,里面放着一些书和歌本。小厨房里摆满了干净发亮的盘子和金属锅,通过梯子还可以到达屋顶,与邻居家屋檐之间的檐槽上有一个装满土的大箱子,这就是母亲种菜的后花园。在我的童话《冰雪皇后》中,那个花园仍然盛开着鲜花。 我是独子,因而备受宠爱。母亲时常对我说,我比她小时候幸福多了,简直像个贵族的孩子。她小时候被外公外婆逼着出去乞讨, 有时一无所获,就一整天坐在桥下哭泣。我在《即兴诗人》中的老多米妮卡(Dominica)和《只是一个小提琴手》中的克里斯蒂安(Christian)的母亲身上,分别表现出了母亲的两种不同性格。 父亲凡事都顺着我。我占据了他全部的心思,他是为我而活的。一到星期天,他就给我做透视镜、模型剧院和可以换页的图画,还会给我朗读霍尔堡的戏剧和阿拉伯传说。在我的记忆里,只有在这些时刻父亲才能真正快活起来,因为作为一个手艺人,他从未在生活中感到过快乐。祖父母曾在乡下,家境还不错,但不幸的事情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他们头上:牛死了,农场被烧毁了,最后祖父也疯了。于是,祖母带着他搬到了欧登塞,并把才智过人的儿子送去鞋匠那里当学徒。她别无选择,尽管儿子热切盼望着上文法学校学习拉丁文。有几个富人曾提到要凑些钱供他上学,让他开始新的生活,但从未兑现。我可怜的父亲眼见着心愿不能实现,却一直心念着无法忘却。记得小时候,有一次,一个文法学校的学生来定做一双长靴,他给我们看了他的课本,还讲述了他在学校学到的东西,我看见父亲的眼中闪烁着泪光。 “这才是我原本应该走的路!”父亲深情地亲着我说。然后一整夜他都沉默不语。 他很少和同行来往。每到星期天,他就会带我去林间散步。他不怎么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陷入沉思,而我会到处跑,把采来的草莓穿在草秆上,或者编织花环。每年只有两次,也就是在5 月的时候,当树木都披上了新绿,母亲才会和我们一道出游。那时她会穿一身棉布长裙,我记得那是她唯一的节日礼服,只有在领圣餐时才穿。每次散步时,她总要抱一大捆嫩绿的山毛榉树枝回家,移植到擦亮的炉子后面,随后又把代表圣约翰的箴言的枝条插在屋梁的缝隙里,我们相信,它们的生长预示着我们生命的长度。绿枝和图画点缀着小屋,母亲一贯把屋子收拾得整齐干净,床单和窗帘总是洁白如新,对于这一点她颇为自豪。 祖母每天都来看看她的小孙子,哪怕只是待上一小会儿,我是她的开心果。她是一个性情温和、安静慈祥的老太太,长着一双温柔的蓝眼睛,尽管生活百般摧残,她依然体态动人。她先是嫁给了一个家境宽裕的乡下人,现在却沦入了极度的贫困,和低能的丈夫住在用最后那点儿可怜的积蓄买来的小屋子里。我从未见过祖母落泪,但我印象极深的是,她有时轻声叹着气,给我讲她外婆的故事, 说她曾是卡塞尔(Cassel)城的贵族小姐,如何富有,又是如何嫁给了一个“喜剧演员”——她是这样说的,于是从父母家出逃,而如今她的后代就遭到了惩罚。我不记得她是否提到过她外婆那个家族的姓氏,我只知道她自己的娘家姓是诺姆森(Nommesen)。她受雇照看一所疯人院的花园,每到星期六的晚上,她就会给我们带些花来,这是医院允许她带回家的。这些鲜花装点了母亲的衣橱, 但这些花也是我的,我可以把它们插在装了水的玻璃瓶里。这是多么令人愉快啊!祖母把花全带给我,我知道,也懂得,她全心全意地爱着我。 每年两次,她要把花园里的枯枝败叶清理出来焚烧干净。那时, 她就会带我到疯人院,我躺在成堆的绿叶和豌豆秆上,在花丛中嬉戏。而这里最吸引我的一点是,能比在家里吃得好。 那些没有攻击性的病人可以在医院的庭院里自由活动,他们经常来花园。我既好奇又恐惧地听他们说话,悄悄地跟着他们,甚至跟着医护人员进入病情严重的疯人区。沿着长长的走廊可以到他们的小单间。一次,医护人员都走开了,我趴在地上,从一个房间的门缝往里看。只见一个几乎全身赤裸的女人躺在稻草床上,披头散发,唱着动人的歌。突然,她弹跳起来,向我所在的门边撞了过来, 把送饭用的小窗都撞开了。她两眼盯着我,伸出一只手臂要抓我, 我惊恐地尖叫起来,感觉她的指尖已经触到我的衣服了。医护人员赶来的时候,我已经吓得魂飞魄散了。过了很多年,这个场景和当时的感觉还记忆犹新。 紧挨着焚烧枯叶的地方有一间穷老太婆的纺纱房,我经常光顾那里,而且很快就成了最受欢迎的常客。和这些人相处,我发现自己能说会道,令人称奇。我偶然听到大夫讲关于人体内部结构的知识, 尽管我完全不懂,但这些神秘的事物令我着迷,于是,我就用粉笔在门板上画了一堆圈圈表示肠,又对心、肺做了一番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解。我被当作异常聪慧的孩子,但活不长久。为了犒赏我的伶俐口齿,她们给我讲故事,一个像《一千零一夜》一样丰富精彩的世界呈现在我眼前。在那段时间,这些老太太所讲的故事以及我在疯人院看到的那些病人的种种荒唐影像都深深地烙印在我脑海中, 夜幕降临时,我便不敢出门。因此,父母允许我在日落时就躺在他们的床上,因为我睡的折叠床不能这么早就放下来,我们的屋子太狭小了。我拉上长长的印花窗帘,躺在父母的床上神游,仿佛现实世界已经与我无关了。 我很害怕精神失常的祖父。他只跟我说过一次话,还正式地称呼我为“您”。他的“工作”就是用木头雕刻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 诸如兽头人和带翅膀的怪兽。他把这些玩意儿装在篮子里带到乡下, 那些地方的农妇们对他都很友善,因为他给她们和她们的孩子带去了这些怪异的玩具。一天,他回到欧登塞,我听见大街上有一群男孩在他身后喊叫,我赶紧躲在楼梯后面,因为我知道我是他的骨血。 似乎我身边每件事物都能激发我的想象力。我童年时代的欧登塞连一艘轮船都没有,与其他地区的交流也甚少,与如今完全不同。人们甚至可以幻想自己生活在一百年前,因为当地盛行着很多古代的风俗传统。比如行会的人列队在镇上穿行,一些滑稽的小丑拿着手杖和铃铛走在队伍前面;忏悔星期二那天,屠夫牵着一头头饰花冠的肥牛穿过街道,牛背上骑着一个身穿白衬衣,背上插着一对翅膀的小男孩;海员在城里游行,空中旗帜飘扬,还奏着乐,他们当中两个最勇敢的水手站在两条船之间的木板上摔跤,谁没有被扔进水里谁就是胜利者。 但真正给我留下深刻记忆的,是1808 年西班牙人驻扎菲英岛, 我对这一事件的记忆之后不断被人们的谈论唤醒。尽管当年我还不到三岁,但我清楚地记得那些身穿褐色军装的士兵在街道上乱成一片,炮火连天。我看见士兵躺在已经半毁的教堂的稻草堆上,那儿离疯人院不远。一天,一个西班牙士兵双手抱起我,把我的嘴唇压在他胸前佩戴的一枚银像上。我记得母亲对此很生气,她说这带有天主教的意味。我却很喜欢那枚银像和那个陌生的士兵,他围着我跳舞,亲了我,哭了。我想,他在西班牙的家乡一定也有孩子。他的一个战友被处决了, 因为他杀了一名法国人。多年以后,我记起这个情景,于是写了一首小诗《士兵》,由沙米索(Chamisso)译成德文后被收进了《士兵之歌》(安徒生曾将这首诗寄给本书英译者玛丽·霍伊特[Mary Howitt],她的译诗发表在《霍伊特杂志》第十九期)。 我很少同其他男孩玩耍,即使在学校,我对他们的游戏也几乎不感兴趣,只是在教室里坐着。在家里我有足够的玩具,全是父亲做的。我最大的乐趣就是给玩偶缝制衣服,或者在院子里我种的栗子树旁,用两根树枝撑起母亲的围裙,然后坐在下面凝视着阳光照耀下的树叶。我是一个极爱幻想的孩子,经常闭着眼睛行走,以至于给人留下了弱视的印象,其实我的视觉极为敏锐。 到了收获季节,母亲有时会去田里拾麦穗,我跟着她,感觉就像《圣经》里的路德在波阿斯富饶的田地里拾麦穗。一天,我们拾麦穗时遇上了一位远近闻名的性情暴躁的管家。只见他手里举着长长的鞭子赶来了,母亲和大伙赶紧跑开。我光脚穿着木鞋,匆忙间鞋子掉了,地上的麦秸扎脚,根本跑不动,我一个人落在了后面。他追上来,举起鞭子要打我,我盯着他的脸,不由自主地喊道: “你怎么敢打我?上帝能看见呢!” 这个严厉凶悍的男人看着我,竟然立刻变得和善起来,他拍拍我的脸颊,问了我的名字,还给了我钱。 我把钱拿给母亲看时,她对别人说:“我的汉斯·克里斯蒂安是个不寻常的孩子,人人都对他好,连这个坏蛋都给他钱。” 我的成长环境是虔诚而迷信的。我对贫困毫无概念,尽管父母挣的钱只够过日子,但至少我不愁吃穿,一位老婆婆会把父亲的衣服改给我穿。偶尔父母会带我去剧院,我看的第一场戏是德语剧目, 那时《多瑙河小女人》是全城最火的一部戏,但我看的是霍尔堡的《乡村政客》。 剧院和成群结队的观众给我的第一印象一点儿也没有显露出我有成为诗人的潜质,我感叹道:“如果我们有和这里的人一样多的黄油该多好啊!那我就能吃个够了!”不过,很快剧院就成了我最喜爱的地方,只是我偶尔才有机会去一次。我和剧院张贴海报的人成了朋友,他每天都会给我一张海报,我坐在家里的一角看着海报, 根据剧名和剧中人物想象整台戏剧的样子。这是我第一部无意识的文学作品。 父亲最爱读戏剧和故事,尽管他也读些历史和《圣经》。父亲看书时总爱陷入沉思,向母亲谈论,她却无法理解,父亲因而变得愈加沉默。一天,他读罢《圣经》说了一句:“耶稣是和我们一样的人,但他是非凡的!”母亲大惊失色,眼泪夺眶而出。我赶紧懊恼地祈祷上帝原谅父亲可怕的亵渎。“魔鬼只在我们心里。”一天, 我听到父亲这样说,内心便为他和他的灵魂忧心忡忡。一天早晨, 父亲发现他的胳膊上有三道划痕,可能是被钉子划到了,但我完全相信母亲和邻居们的说法,那是魔鬼在夜里造访了他,向父亲证明它们确实存在。父亲更频繁地去林间散步,从不停歇。他十分关注报纸上关于德国战事的报道,全部的心思都在这上面。拿破仑是他心目中的英雄,他从一个无名小卒发迹的历史是父亲最好的榜样。那时丹麦与法国结盟,战争成了人们谈论的唯一话题。父亲参了军, 希望能升个中尉荣归故里。母亲泪流满面,邻居们耸耸肩,说当兵去挨枪子儿太蠢了,没这个必要。 部队出发的那天早晨,我听见父亲兴奋地又说又唱,他告别时深情地吻了我,我能感觉到他内心焦虑不安。我在出麻疹,只能独自躺在屋里,这时军鼓敲响了,母亲一路哭着把父亲送到城门。他们走后不久,祖母就来了,她温柔地注视着我说,要是我现在就死了倒好,可上帝的意愿总是不可违背的。 那是我记忆中第一个真正悲伤的日子。 《安徒生自传》:安徒生于1847年亲笔所著的随笔体自传,讲述了安徒生如何从一个穷鞋匠的儿子成长为享誉世界的“童话大王”的人生经历。可以说,本书是深入了解和认识安徒生的一个窗口——在“童话大王”耀眼光环的背后,安徒生的身上也闪耀着一个出色的诗人和剧作家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