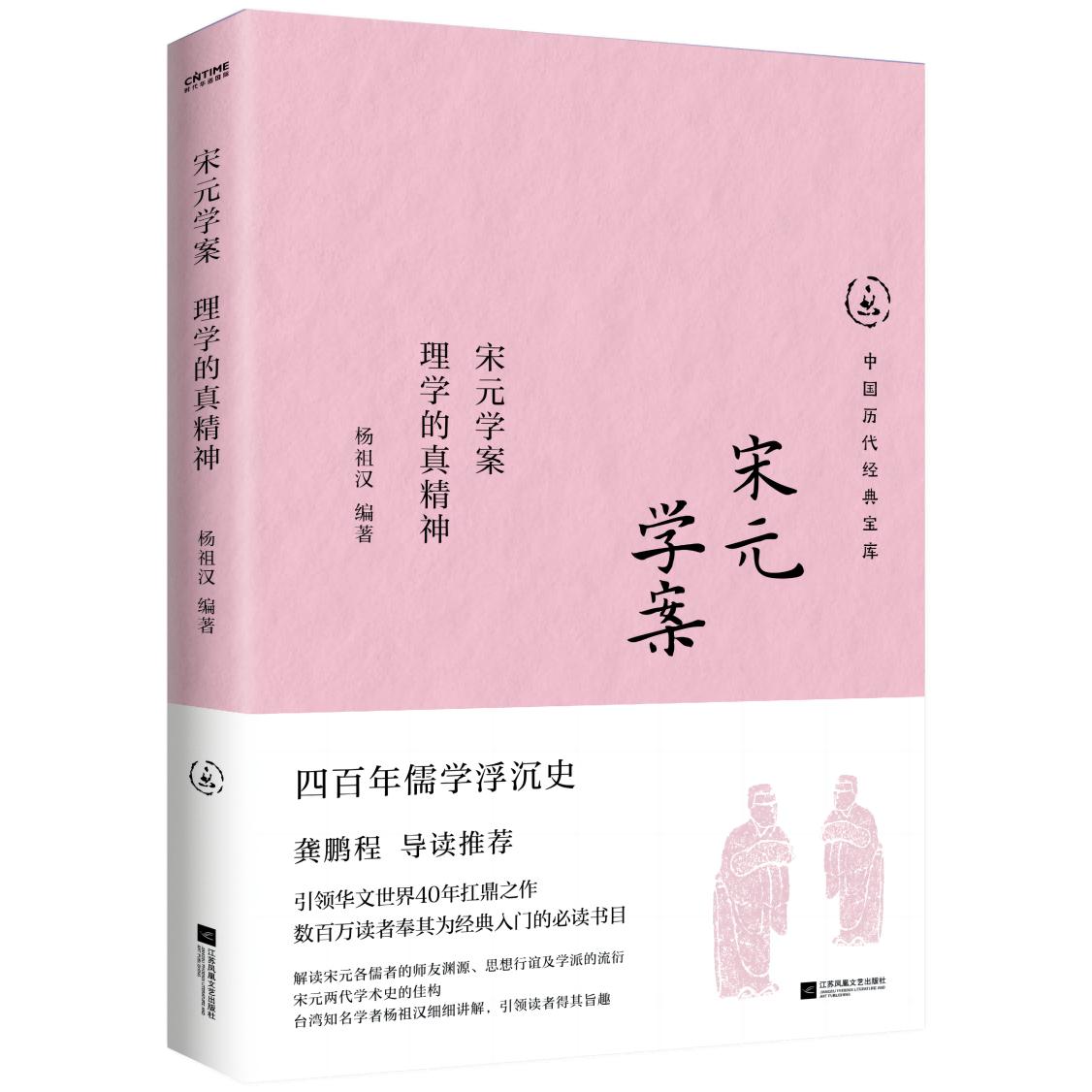
出版社: 江苏文艺
原售价: 58.00
折扣价: 34.30
折扣购买: 宋元学案:理学的真精神
ISBN: 978755948779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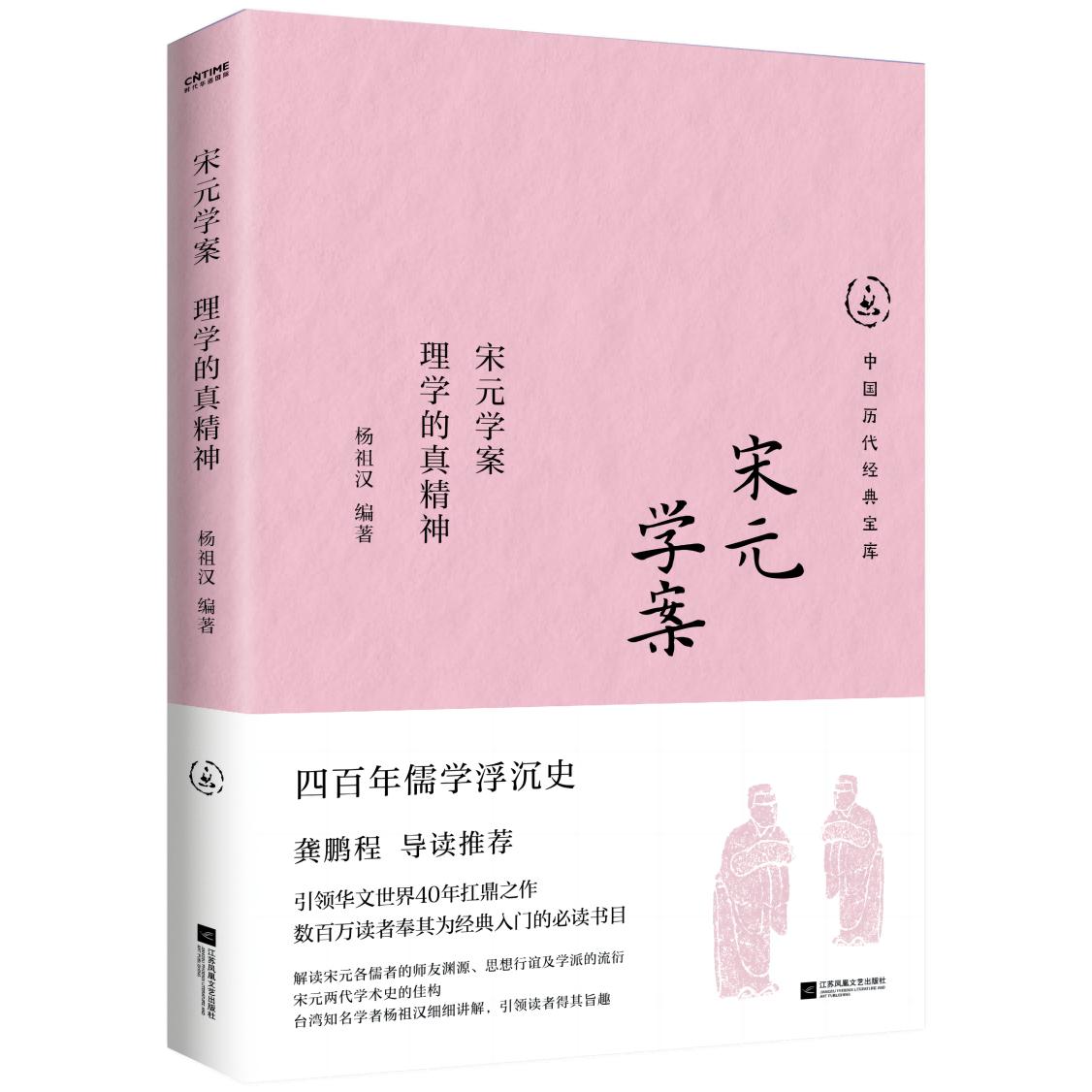
杨祖汉,原籍广东新会,出生于香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国文学系及香港新亚研究所哲学组硕士,曾任中国文化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任中央大学中文系教授。著有《儒学与康德的道德哲学》《中庸义理疏解》等。
《宋元学案》起初是由黄宗羲编纂的,后来经过好几位学者增补才完成。黄宗羲,字太冲,浙江余姚人,人称他为“梨洲先生”。他生于明朝神宗万历三十八年,卒于清朝圣祖康熙三十四年(1610─1695年)。他父亲黄尊素是明神宗和熹宗时的名臣,忠贞刚烈,不幸被奸臣魏忠贤陷害而死。这时黄宗羲才十六岁,已博览群书,学识超卓。他遵从父亲的遗命,拜父亲的至交好友刘宗周为师。刘宗周,字起东,学者称“蕺山先生”,是明末最有成就的儒学大师(他的生平及学术,请参阅《明儒学案》)。明思宗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入北京,思宗自缢,明福王即位于南京。这时清兵已入关。第二年,清兵破李自成,又攻陷南京,明朝亡,刘蕺山先生绝食殉国,黄宗羲则联络志士,从事反清复明的工作,可惜无功,后来便隐居家乡,专心从事著述。黄宗羲在学术上的成就很大,他和顾炎武、王夫之被后世称为“清初三先生”。后来清廷曾一再请他出来任官,他都不肯。他一生所著的书很多,有《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南雷文定》《明史案》等,都是很有价值的著作,其中的《明儒学案》及《宋元学案》,乃是宋元明三代最完整的学术史。 黄宗羲先写《明儒学案》,完成后再写《宋元学案》,但只写好一部分便去世了,由他的儿子黄百家继续撰写,但并未把这书完成。隔了许多年,这书的稿本为清儒全祖望得到,他便全力加以增补,费了十年的功夫,《宋元学案》才大致完稿。全祖望,字绍衣,号谢山,生于清康熙四十四年,卒于乾隆二十年(1705─1755年)。他虽未能见到黄宗羲,但对梨洲先生的学问很是景仰,可以算是黄梨洲的私淑弟子。在现在的《宋元学案》中,属于黄宗羲父子所写的部分只有十分之三四,其他大都是全祖望增补的,所以《宋元学案》可算是黄宗羲父子及全祖望合写的。全祖望在五十一岁时得病,在《宋元学案》还没有来得及付印时便去世了。稿本交由全祖望的学生卢月船保管,卢月船加以抄录誊正,又和黄梨洲的玄孙黄璋讨论商榷,但尚未抄录完毕而卢氏又卒,全氏原稿及卢氏抄本便藏在卢氏家中,子孙世代保存。另外黄璋又从卢月船处得到全祖望的底稿,黄璋和儿子黄征先后抄录誊正,补正许多缺漏。至清道光十八年(1838年),这书才由王梓材及冯云濠两学者根据卢氏及黄氏两稿本校刊出版,王梓材也做了许多校补工作,才成为现在的《宋元学案》一百卷,这时已是黄宗羲卒后的一百四十三年了,这书耗费了好几代人的精力才告完成,由此可见古人对学术的热爱及谨慎从事的精神。 在《宋元学案》一百卷中,属于两宋部分的有九十四卷,其中有好几卷分了上下,所以实数是八十二个学案,属于元朝部分的只有六个学案。每一个学案通常是代表一个学派,每一学案大部分以该学派的创始人或最重要的人的名号为名称,如卷一《安定学案》便以胡瑗(人称“安定先生”)为学案的名称,学案中除叙述了胡瑗的生平学术外,又叙述胡瑗的门人弟子及和他论学的朋友的生平学术。每一个比较重要的人物,都有传略、学说及附录三部分。传略是记载该位先生的生平及学问大概,学说是抄录他的著作中的重要部分,而附录则杂记他的遗事,以及当时的人或后人对他的评论。每学案前都有附表,用列表的方式表示出学案中各人相互间的关系,师友的渊源,非常清晰明白,也使人很容易便可以掌握当时的学术界的大概情形。这些表大部分是王梓材所补的。著录在学案的宋元儒者,共有千余人。 二 我国宋元明三代(960─1643年)六七百年间的思想学术界,是儒学在春秋战国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在春秋战国时,因为孔子孟子的兴起,而奠定了儒家学说的义理纲维。孔子一方面继承了古代传统的学术,整理了《诗》《书》《礼》《乐》等经书,保存了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他指点出人的真生命、真精神──仁,赋予了传统学术文化新的意义,豁醒了人的内在的精神生命,使人能在实践仁义时,了解到人生的真正意义。孟子则根据孔子所说的仁而说本心,指出恻隐、羞恶、恭敬、是非等心是人人都有的本心,亦即仁义礼智等理,因此仁义礼智等道德的理是在人的心中的。只要人时刻保存他的本心,不断地扩充,那么人人都可以成为一个最完美、最理想的圣人,而世间也会有最理想的政治。于是从人的有本心便肯定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那么人性当然是善的,人之所以为人的意义,人的可贵处,便是因为可以实践仁义礼智而成为圣人。孟子说本心、性善和保存扩充,便已将儒家学问的内容全部表明出来。人的保存涵养自己的本心善性,不断扩充,便可成为圣人,这是“内圣”(从自己的生命内部下功夫,不断提升自己的人格而成圣成贤)的学问;把本心善性推出去用于家国天下,便可以有理想的政治,那是“外王”(把理想实现在世界上,使一切人都过着合理的生活)的学问。这便是儒学的全部内容。儒家所说的学,是指示这“内圣外王”之学,并不只是读书求知识。 在孔孟之后的《易传》及《礼记·中庸》的不知名作者,顺着孔孟的义理推进一步,认为人的仁义礼智的本性,便是天理天道。所谓天理天道,即是使宇宙间的一切能存在的最高的法则。天理天道是无穷无尽的,能不断地创生一切,使一切能生生不息。《易传》及《中庸》的作者都认为,天理天道的内容便是仁义礼智。人性和天理在内容上是一样的,如果人能保存他的本心,又不断地扩充,便是把具有无限意义的天理天道实现在自己的生命中,于是自己便具有无限的意义和价值。只要人在日常生活中,本着本心本性去做,便会产生一切德行,成就种种该做的事情。人自然便会孝父母、爱兄弟、信朋友……当人在孝父母、信朋友时,内心不只是感觉到孝悌忠信是人所应做的,同时也会感到那便是天理所在,是人所绝对不能违反的,这时心中便会产生最大的快乐。而且这孝悌忠信的行为,是要不断推广的,人要用仁义之心来对一切人一切物,好像天地的包容一切、长养一切一样,人能够这样,便和天理天道合而为一,成为一个可和天地并立的有无限价值的人。于是人在实践道德的过程中,便可以体会到天理天道,而使自己的生命充满着无限的意义。 儒学这种义理、生命智慧,实在可以稳定住一切人间正常的生活,使人在伦常日用中体会到无限的意义和价值,而不必在人生之外另寻一个天国,也不必出家修行。这实在是人生的正道,大中至正之教。所以儒学后来便成了中国思想学术的主流,启发了所有中国人的道德理想,调护着每一个中国人的生命。 在孟子之后的荀子,也是儒学大师,很能道出礼乐教化的意义,但他并不能了解孟子的性善说,而认为人性是恶的,因而强调后天的学习教养,他对于道德心性、天理天道的了解便有了偏差,不能承接孔孟所创发的内圣学的真精神。秦代焚诗书、坑儒生,儒学的真面貌更黯然不彰。两汉四百年,大抵都以儒学作为政治教化的指导原则,但对于儒学的真精神,也是很少有人能了解的,这时期并没有一个能阐发真正的孔孟之学的纯粹儒者。这期间的儒者,大都用心在如何把儒学理想实现在政教及注释经书上,对于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善性,反求诸己以豁醒真生命,是没有相应的了解的。于是后来儒学便逐渐失去了活力,不能作为当时人生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所以到东汉末年,一方面是道家思想盛行,另一方面是佛教教义的逐渐传入。从东汉末年起,经历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共七百多年的时间,中国的思想界都是佛道的天下,其中以佛教的力量最大,大部分的聪明才智之士,都被佛门吸收了去。 佛教及道家(后来有人根据道家的修养方法而追求长生,成立了道教)两派,都有很高深的理论,而所面对、处理的,也是人生中的真实问题,所以很能吸引人。但佛道两教都是从人生负面的烦恼、执着入手,对于儒家所指出的人生的正常面、光明面,并不能正视,对于政治教化、伦理之道,并没有积极地肯定,于是就作为人生的指导原则来说,佛道都不免是偏颇的。若是有儒家思想做主,佛道都会是很好的辅助力量、很好的教路,但若要取代儒学的主流地位,以佛道做主,便会有很大的弊病。魏晋南北朝时中国大乱,佛道思想盛行,儒家思想则只保存在北方的一些士族中,凭着北方士族的家庭教育,保存了儒家的政教理想。隋唐两代能够重新统一中国,形成前所未有的昌盛局面,所凭借的正是北方士族所保存的儒家政教理想。 虽然说隋唐的统一的盛运,是儒家的政教理想所致,但在隋唐三百年间的思想界,儒学还是不能抬头,还是佛学的天下。因为经过了长期的吸收消化,佛教已经中国化,中国人在这时开始以自己本身的智慧,顺着原有的印度佛学的教义而往前推进,创立了中国佛学宗派,如天台宗、华严宗、禅宗等。这些宗派的教义,都不是印度原有的。其中的禅宗,后来更是风行天下。这是佛学在中国的黄金时代,一般读书人的注意力大都集中在佛教的教义理论上。这时候代表儒学出来和佛教相抗的,只有一个韩愈,而他是一位文学家,对于儒学的理论,并没有很深切的了解,因此他只能根据常识来反对佛学,这当然是不足的。韩愈也提倡师道,希望改变当时的读书人的浮夸而不切实的风气,但韩愈本身的学问人品,并不能达到足为世人所共仰的地步,因此韩愈只能成功地发起了一次古文运动,而不能使儒学复兴。在唐代中叶以后,武人割据,中央政府命令不能通达地方,政治愈来愈混乱,民变四起,在唐朝末年以至五代十国的几十年间,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黑暗时代,可以说已经不像是一个人间。在这大乱的时候,人便慢慢反省到,人要真正做一个人,人间要像一个人间,乃是最重要的事。人不像人,人间不像人间,一切都不能谈。于是儒学的重要性便逐渐为人了解,就是佛教的大师,在五代时也有劝人读韩愈的文章及儒家的经典的。可见他们也反省到,只有儒学才能稳定人间,而只有人间稳定了之后,才有佛教可讲。 三 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幸而被宋太祖结束了,但中原元气已大伤,许多疆土都被侵占了,宋代的立国实在十分艰苦。宋代的读书人眼见唐末五代的大乱,以及当时中国处境的艰苦,在内心中自然便产生出无比庄严的责任感,而要以天下为己任,加上宋太祖极力提倡文教,优礼读书人,儒学的复兴运动于是便逐渐展开。 宋代儒学最早的人物,是胡安定(瑗)孙泰山(复)两位先生,他们一同在泰山苦读,学成后便用经学来教育弟子,他们所教过的弟子有几千人,大都能成才,这对当时的学术风气有极大的影响。胡安定为人沉潜笃实,而孙泰山则高明刚正。徐积是安定最出色的弟子,所以有安定的风格,而石介的疾恶如仇,力攻佛道之学,便接近泰山。石介对孙泰山严执弟子的礼数,更对当时的风俗起了很大的改良作用,师道的尊严,在这时才真正再次建立起来。除这几位外,当时的几位著名大臣,如范仲淹、司马光、吕公著、欧阳修等,都能提倡儒学,奖励后进人才,而他们的人格,更是纯粹光明,最值得人效法。他们对当时的教育、政治,有莫大的影响。但以上诸位先生都未能对儒学的义理有深刻的体会,只能算宋儒中的先驱人物。 第一个能把握先秦儒学真精神的宋儒是周敦颐。周敦颐的学问没有明显的师承,大概是他自己体悟出来的,没有经过老师的传授。由于他曾和佛道的人来往,于是后来有些人便说他的学问夹杂有佛教道教的成分,其实这是很不负责任的言论,周敦颐的著作中所显示出的义理,纯粹是儒学的基本义理。他以《中庸》所说的诚来比配《易传》所说的乾元,体会到天理天道是最真实的,是生生不已的,而人的仁义礼智即是天道的呈现,于是人的成圣,便合于天道,这的确是地道的儒家式的智慧。从周敦颐开始,儒学的精义才重新为人所了解。周敦颐以后,大儒辈出,使当时的思想界显得极为热闹,在河南洛阳,有程颢程颐兄弟,在陕西,则有张载。程氏兄弟在少年时曾问学于周敦颐,但二程的学问并不是直接从周敦颐处承接而来,而是他们自己用了十多年的功夫研究体会而得的。程颢资性和粹,充养有道,最受当时人景仰,而他的学问更是圆融通透,境界最高。程颐性格刚严,不像程颢和粹,而学问见解和他哥哥也不太一样,但当时的程门弟子并不能觉察两位程先生学理上的不同。程颐比程颢晚死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他不断地讲学论道,使儒学达到了空前的昌盛。虽然在政治上他很不得意,晚年更被贬远方,但恶劣的环境却成了他修心养性的最佳场所,也激起当时百姓对儒者的崇敬,对儒学的重视。张载则是北宋各大儒中立说最有理论系统的一位,无论是对佛道的批评,或对儒家本身义理的阐明,都非常正确严谨。由于周、张、二程几位的努力,儒学的内容意义才真正为人所明白。当然他们也有新的思想,并不完全是墨守先秦儒家的说法,但他们的新义都是儒学的合理引申及发展。如张载便造了很多新名词,如太虚、气、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等,但名词虽新,所表示的都是儒学本有的义理。所谓儒学的本有的义理,是指前面所说的,孔子所说的仁,孟子所说的本心、性善,以及《易传》《中庸》所说的天理天道即是人的道德之性等。 因周敦颐号“濂溪先生”,后人便称他的学问为“濂学”:二程住在洛阳,于是被称作“洛学”;张载是关中(陕西地方又叫“关中”)人,所以被称为“关学”。当时有一位邵雍先生,和周、张、二程等同时,而年龄稍大,也是当时的著名儒者,但他的学问并不是纯粹的儒学,所以一般都不以他为北宋正统派的儒者。 濂、洛、关三派中,周敦颐没有正式的传人,张载的关学在当时和二程的洛学一样的兴盛,门人弟子很多。张载教人,以礼为先,关中风气因而变得像古代般淳厚,他的弟子吕大钧又推行“乡约”运动,教化地方,很有成效。可惜不久便是“靖康之难”,北宋亡,关中一带饱受战火的蹂躏,张载的门人弟子四散,关学便衰微不振了。 二程的洛学则是一直绵延不断,弟子散布各地,都能谨守师说。其中以谢良佐、杨时、尹焞最有成就。谢良佐气质刚毅高明,议论横厉风发,他很能把握程颢的学说要点,他说仁是觉,是生意,说得很是具体活泼,后来胡安国便由于得他的指引而了解洛学精义,胡安国的小儿子胡宏更能将北宋周、张、大程的学问消化融会,开出湖湘一派的学术。杨时的气质和平,议论平缓优游。他很得程颢的喜爱,当杨时辞别程颢而南归时,程颢目送他,说:“我的道将传到南方去了。”所以杨时这一系统,被称作“道南系”(又因杨时是南剑人,故又称“南剑系”)。杨时的寿命长,“靖康之难”宋室南渡后,他便在南方努力传扬儒学,弟子非常多。其中最得杨时真传的,是罗从彦。罗从彦传李侗,而李侗则是南宋大儒朱熹的老师。尹焞的年辈较少,他未见过程颢,追随程颐十多年,专心从事于持敬涵养的功夫,学问品行极为醇正,宋高宗曾说他的行为便是一部活的《论语》。 以上是北宋儒学的大概。南宋儒学并不因“靖康之难”而中断,而且更为昌盛,但当然儒者的活动范围要往南移了。胡宏是宋室南渡第一个儒学大师,他所著的《知言》,后来的吕祖谦说胜过张载的《正蒙》,虽未必是这样,但《知言》的义理的确很是精微,足以承接北宋诸儒的学统。因为当时秦桧当政,胡宏和他的兄弟都隐居在湖南衡山湘水一带,不肯出仕,于是他们便被称为“湖湘学派”。胡宏的弟子最著名的是张栻,但张栻在胡宏的门下日子不长,对胡宏的学问未能有深切的了解。所以后来当朱熹因对胡宏的说法有所怀疑,而和张栻讨论时,张栻便不能稳守胡宏的说法。胡宏的其他弟子虽多能谨守师说,但因都处在湖湘一带,稍微偏僻,不能产生大的影响,而且大都短命,于是湖湘学统便不能延续下去了。 朱子(熹)是南宋以来最受尊重的大儒,一般人都认为他是宋代儒学的集大成的人,他一生不断讲学著书,他的理论及著作都有很大的权威性,是被南宋以后大多数的读书人所遵从的。但朱子其实只继承了小程子(程颐)的学问,主张先要以敬来涵养内心,心涵养久了,便会清明,便能明理,但明理非要通过格物(研究事事物物)不可,把心知的灵明运用在事事物物上,便能明理,能明理,人的行为便有可依循的法则,便能使行为合理而无差错。朱子这样的理论,并不同于孟子所说的本心的意义。本心本身便是仁义礼智等理,理是本来就具备在本心中的,只要人能反省自觉,便可觉察这理,所以道德实践的最切要的功夫,是反省自觉,而不是格物穷理。当然朱子所要明的理也是道德的理,而不是科学的理,我们不能混乱。朱子这说法不同于先秦的孔孟,也不同于北宋的周、张、大程,他是承继小程子的学理而发扬光大,成为另一套大系统。因此他对谢良佐的以觉说仁的说法,对胡宏的知言,都深表不满。 朱子是福建人,后来的人便称他的学问为“闽学”,而濂、洛、关、闽后被称为“宋代儒学四大派”。 和朱子同时,江西的陆九渊是南宋另一位儒学大师。他的学问并没有师承,他自己说是“读《孟子》而自得之”,他不满意朱子所说的持敬穷理的说法,认为朱子学不见道。他教人在心上作明辨义利的功夫,只要义利辨明,人的本心便自然呈现,本心一呈现,理便在其中,顺着这本心,便自然能孝悌忠信,不需要往外面格物穷理。陆九渊的学问完全是根据孟子而来的,但朱子却说他是禅学,两家的门人后来便争论不已,朱陆异同,便成为南宋最重大的学理争论。 和朱子及陆九渊同时,在浙江东部有一群重视实际的功效,而不喜欢谈高深理论的学者,他们的代表人物有吕祖谦、陈傅良、陈亮、叶适等,其中以陈亮和叶适较为激烈,陈亮认为有了实际上的事功,便即是有道德。叶适则认为曾子、子思、孟子以至二程的洛学,都不是道的原本传统,因他们都是不切实用的空谈理论,而没有客观面的事功上的成就。陈、叶二人这些说法,都未免有偏差,在学理上是不大说得通的。而他们之所以会有这些说法,是因有感于那时南宋国势愈益危弱,于是便把注意力集中在实际的事务上,希望通经术以致用,但他们实际上并未有重要的事功表现,却以重视事功为理由来反对心性之学,这未免是本末倒置。 朱子的门人弟子是两宋儒者中最多的,但大多死守朱子的说法,能有创发性见解的人很少,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蔡沈父子、黄干及陈淳等。稍后有魏了翁及真德秀,虽未曾及于朱子之门,但都宗朱子之学,成就则比朱子的门人弟子有过之而无不及。其中魏了翁的学问见解更是卓越不凡,并不为朱子见解所限。 陆九渊的门人也很多,当他在象山讲学时,来问学的学者共千余人,极一时之盛,但后来卓越有成的并不多,其中以杨简、袁燮、舒璘的成就较大。杨简天资高,最得陆九渊的真传,所以陆门弟子以他最有影响力。 朱陆的门人弟子一传再传,直到宋亡元兴的时候,固有文化受到战火摧残,儒学一落千丈。其中虽然有几位儒者在艰苦支撑,竭力维持学脉道统,他们的精神固然可敬,但在学理上并没有什么发展。儒学要到明代的王守仁起来,才有另外一番新面目。 四 原本《宋元学案》的篇幅很多,所叙述的人物共有一千多人,学派亦很繁杂,我们现在只能选择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来叙述。比起原书来,分量实在太轻,遗漏太多。而且这些儒者所说的学理,都不是简单几句话所能够解释清楚的,所以在语译出来的各段落之后,常要详加解,既要解释,便一定有编者的意见在,不能完全客观,亦不能完全采取原来的编著者(黄宗羲、黄百家及全祖望等)的意见。 我们现在不按照原著的以学案为主体的体例,而以人物为主,大体上每一个人物在原著中都占一个学案。其中周濂溪、张横渠、程明道、程伊川、胡五峰、朱子、陆象山等是两宋最重要的儒学大师,所占的篇幅较多,解释亦较为详细。其中朱子及陆象山两章的材料有些是在原本《宋元学案》之外的。关于各家的学问理论的解说,主要参考牟宗三先生的《心体与性体》(台湾正中书局)、《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台湾学生书局)及蔡仁厚先生的《宋明理学·北宋篇》《宋明理学·南宋篇》各书。所用的《宋元学案》是台湾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版,又曾参考陈叔谅、李心庄《重编宋元学案》(台湾正中书局)及缪天绶《选注宋元学案》(台湾商务印书馆)。 一、胡安定先生瑗(993─1059年) 胡瑗,字翼之,泰州如皋(今属江苏省)人。他的先世原居陕西安定,所以学者称他为“安定先生”。胡安定七岁便能作文,十三岁时便读通五经。家贫,不能自给,他便往泰山(在山东省)和孙复、石介二人一起读书,生活很刻苦,常整夜不睡觉。他在泰山一住便是十年,中间未曾回家一次。每有家信来,他拆开看时,只要看到信上有“平安”两字,便不再看下去,立刻把信抛下山涧中,他是恐怕把信看完会扰乱自己切志求学的心志。今日泰山南麓有一座栖真观,便是他们当年苦学用功的地方,栖真观旁有一条投书涧,便是因为胡安定的投书而命名。他自信已学有所成后才下山。初时在吴中(今江苏苏州吴中区)教授经学,后来名臣范仲淹知道他是有学有德的大儒,于是便聘请他做苏州州学教授。范仲淹的儿子亦向胡安定问学。后改任湖州(属浙江省)教授,他在苏湖地区任教共二十年,他的教法,后来被政府采用于京城的太学。后来他被召入京管理太学,四方学者蜂拥而来,使馆舍不能容纳。他一生教过的弟子共有一千七百余人,大都是有用的人才。他教学生,能以身作则,虽是大热天,也一定穿着整齐,严格执行师生的礼仪。他视学生如自己的子弟一般,学生亦爱他如父兄。他教学的内容非常详备,分经义、治事两门。凡是志气远大,聪明通达,可当大任的,便使他们明六经义理。治事则一人各专攻一科,又兼修另一科,有政治、军事、水利、历算等科,很像现代的分科教育。他要学生住在一起,使他们常常互相讨论,亦常召见学生,要学生说心得,而亲自裁定对错。他能顺各学生的禀性高下、兴趣所近来教导,所以他的学生大多成材。当时主管考试的礼部所录取的人才,十之四五都是他的学生。他的学生都有一种特别的风格和气度,当他们走在街上,别人一看,便知道是胡先生的学生,可见他的感化力的伟大。闽县(在福建省)刘彝是安定的高弟(出色的弟子),后来宋神宗问刘彝:“胡瑗和王安石(神宗时的宰相)两人,哪一个比较好呢?”刘彝答道:“我的老师胡瑗以道德仁义来教东南诸生时,王安石还在为科举考试而努力读书。我听说过,圣人的道,有体(根本),有用(作用),有文(显现于外的条理仪文)。君臣、父子、仁义礼乐,是永不改变的,所以是体;《诗》《书》、史传,可做后世的典范,乃是文;而将这些道理典范运用到天下国家上,使百姓都能安居乐业,便是用。我朝(宋朝)几代以来的开科取士,都不以体用为主,而只崇尚浮华的辞章,所以社会风俗愈来愈浇薄。我的老师深切了解这毛病,于是以明体达用的学问来教授学生,辛勤二十多年,从苏湖地方而至太学,经过他教导的学生不下数千人,今天学者之所以能明白圣人之道,都是胡先生的功劳,王安石哪能比得上呢?” 刘彝虽是胡安定的学生,但这段话说得十分公允,并无半点溢美,由此我们也可以知道教育的重要性。胡安定先生首先是苦学十年,然后是献身教育二十多年,终于为国家培养出许多的人才,而且也扭转了当时的学术风气,以至社会风俗,他实在是一位伟大的教育家。从胡瑗开始,儒学才真正在宋代复兴。 胡安定的著作有《周易口义》及《论语说》等。下面选录几条胡安定的《论语说》: “子贡之所以说孔子是没有人能及得上的(好像天不能用梯子爬上去一样),是要特别强调孔子的伟大。但其实孔子也是经过多方的学习,以及向许多人请教,才成为圣人的。” “朋友是辅助自己向上,使自己养成良好品格的,因此,不能交不能使自己向上的朋友。孔子曾说,我死后,子夏会日益进步,子贡则会日益退步。因为子夏喜欢和比他好的人相处,子贡则相反。” “子路每次听到了孔子的教诲,便一定要实行出来,如果他一时还未能实行,便害怕再听到孔子的教诲。其实不只是听到孔子的教诲要这样,听到或看到任何好的言语、好的行为,都要这样,马上实行。” 在胡安定众多的弟子中,最能承继他的学问和志业的是徐积。 引领华文世界40年扛鼎之作 数百万读者奉其为经典入门的必读书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