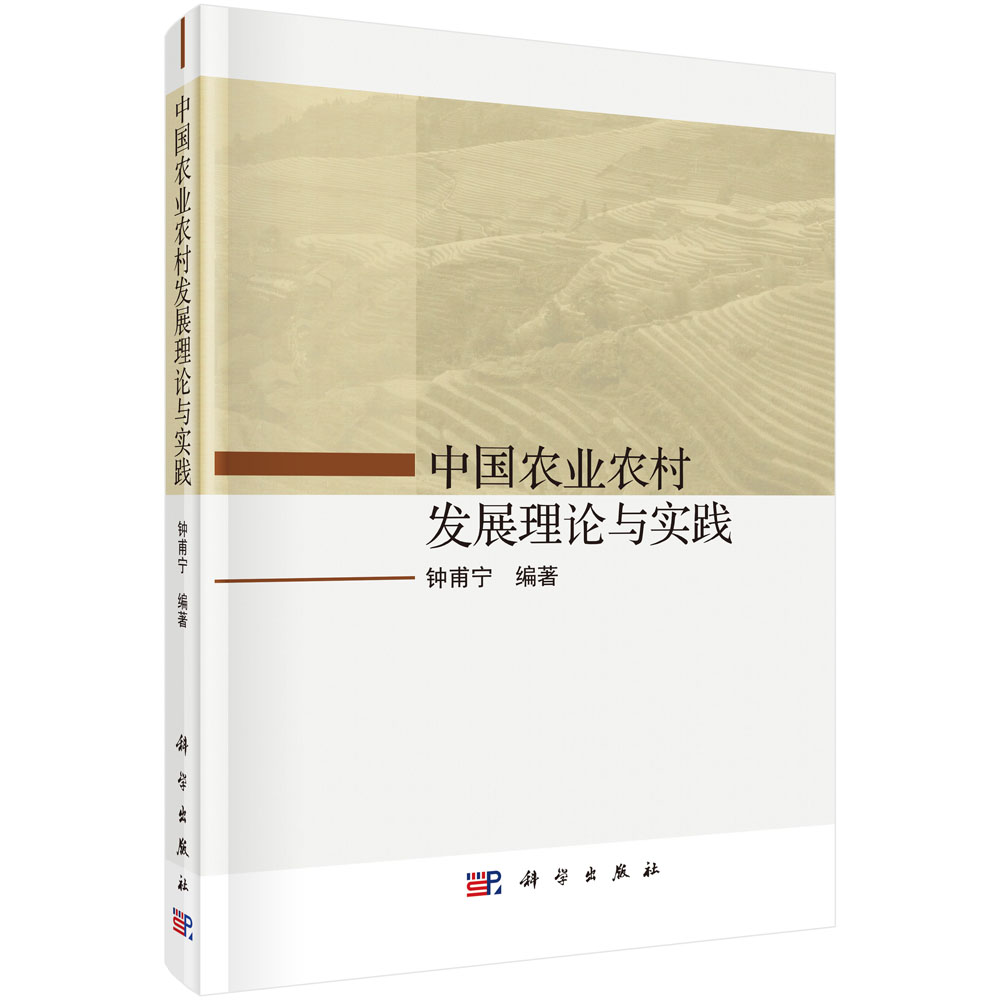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186.00
折扣价: 147.00
折扣购买: 中国农业农村发展理论与实践(精)
ISBN: 97870306894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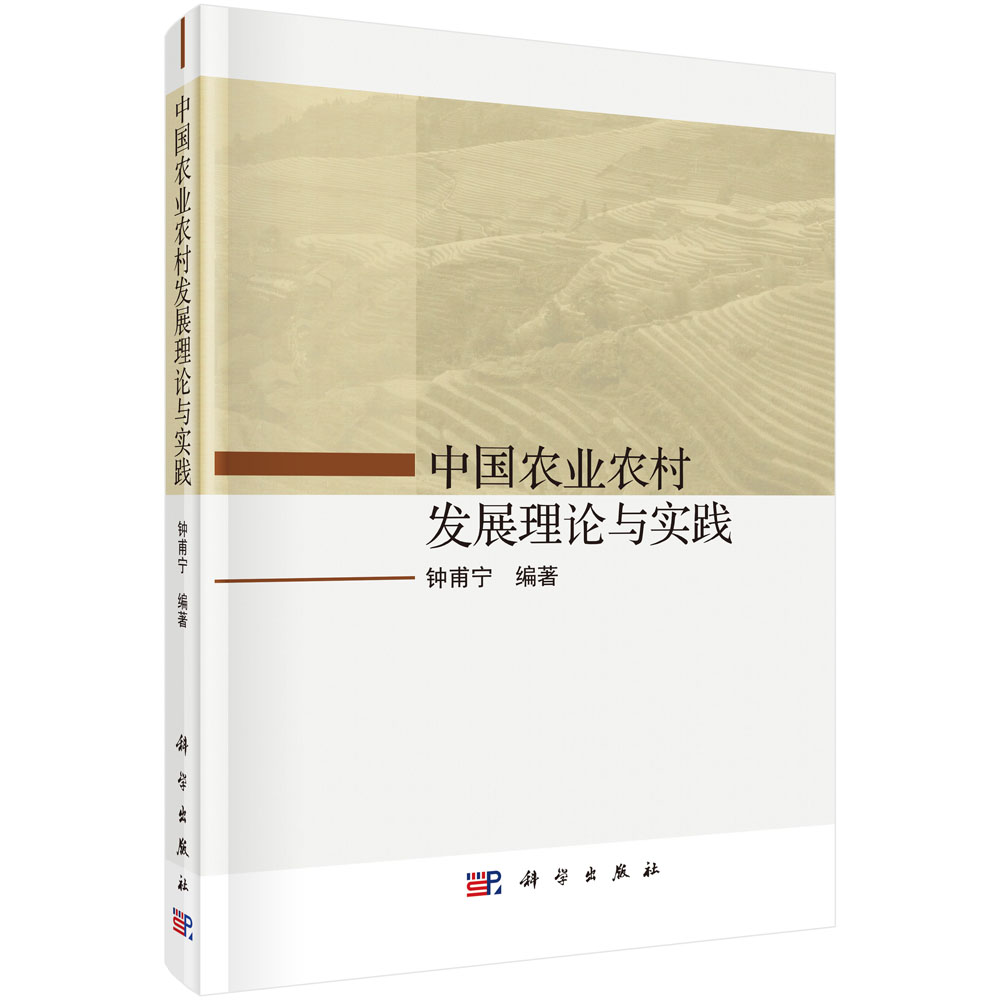
第一篇 农村人口与城市迁移
第1章 对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
在20世纪90年代大多数农业经济学家和政府有关官员一致认为,庞大的农村人口和隐性失业大军是我国农业与整个国民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无论是农业生产比较利益、农民收入、农产品供应,还是地区与部门的平衡发展,都受到几十年积累下来的人口问题的困扰。对农业和农村经济来说,人口和劳动力的压力更大,因为实行了几十年的户籍制度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其他部门转移。所以当时这一领域所有的研究几乎都涉及对农村人口和剩余劳动力数量的估计。从当时的研究来看,所有的计算都以《中国统计年鉴》或《中国农业年鉴》上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根据各自对农村和农业劳动力实际需求的计算,大多数研究估计1990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在 1 亿人左右。然而,有证据表明实际过剩的数量远远大于通常的估计。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与统计年鉴资料相比较,当年全国就业总人数多出8 000万人,主要差别就在于农村和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数字不一致。
1.1 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
农村人口和农业人口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理论上讲,前者指居住在农村地区的人口,与地域相联系,而后者指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包括家庭成员),与职业相联系。两者密切相关,但又有区别,其一致程度主要取决于划分市镇的标准和农村非农化的程度。如果降低市镇建制标准,农村人口就会减少,但农业人口不变。如果市镇建制不变而农村非农化程度提高,农业人口就会降低而农村人口不变。在我国的统计实践中,农业人口可能有另一种含义,即特指持农业户口的人口。从这个意义上来看,农村人口可能与农村劳动力有密切的对应关系,而农业人口与农业劳动力的关系就不一定很强。
1990年人口普查得到的农村人口总数与年鉴上的统计数字基本一致,即按照第二种口径统计的县人口与乡村总人口相对应,约8.4亿人(如果按照1964年建镇标准则为8.96亿人),而市镇总人口为3亿人左右(表1-1)。此外,人口普查指出当年农业户口总数为9.02亿人,同时表明,市人口和镇人口中分别有38.1%和32.4%属于农业户口。这部分具有农业户口的城镇人口大多为建制市镇的郊区人口,并且有相当一部分从事农业生产活动。我们有理由设想,市镇人口总数,特别是其中具有农业户口的人数,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建镇标准。
表1-1 全国人口及其构成比较(单位:万人)
表面上看,表1-1中人口普查与统计年鉴在农村人口方面基本一致,细微的差别大致缘于1990年下半年人口的自然增长。不过,更深入的分析提示我们,在计算农村劳动力平衡表时,市镇人口中的农业户口不能简单地算作城镇人口。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能就业于乡镇企业,因此,乡镇企业劳动力并不全是农村劳动力。换句话说,即使农村各业实际就业人数加上乡镇企业就业人数等于农村劳动力总数,农村仍然可能存在失业人口,其数量等于市镇人口,更准确地说是其中的农业户口在乡镇企业中就业的人数。不仅如此,郊区农业生产活动也是由当地居民(即统计意义上的城镇人口)来从事的,因而实际农业劳动力需求中的一部分也是由城镇劳动力来满足的。
1.2 农村和农业劳动力
1990年人口普查资料和统计年鉴资料在劳动力方面的数字有很大差别。普查资料表明全国在业人口总计为6.47亿人,但统计年鉴上汇总的全国从业人员总计只有5.67亿人,两者相差0.8亿人(表1-2)。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差别主要在于农业劳动力的统计不一致。例如,人口普查的在业人口中有4.68亿人从事农林牧渔水利业,其中农业占4.58亿人。统计年鉴中全国农林牧渔从业人员仅3.41亿人,加上地质水利从业人员197万人也不过3.43亿人,比人口普查中的数字少了1.25亿人。农村劳动力的统计也不一致,人口普查中全国县在业人口总计为4.81亿人,其中农业为4.21亿人,而统计年鉴中乡村从业人员总计为4.20亿人,其中农林牧渔仅3.33亿人,分别相差0.61亿人和0.88亿人,值得一提的是,农业劳动力的划分标准在这里仅指就业部门,与户口无关。
表1-2 农村劳动力及有关统计比较(单位:万人)
一般来说,人口普查的精度要高于年终报表。因此,农村总劳动力的数量更接近4.81亿人而不是4.20人,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可能比通常认为的数字多0.61亿人。这一估计可以从农村住户抽样调查的资料得到证实。根据统计年鉴上提供的资料,1990年抽样调查了66 960户,常住人口共有321 429人,平均每户4.80人,整半劳力2.92人,平均每个劳力负担1.64人(包括自己)。按照1.64的比例,8.41亿农村人口应当有5.13亿劳力,而8.96亿农村人口(1964年建镇标准)则应当有5.46亿劳力。如果认定农村劳动力总数为4.20亿,赡养系数就上升为2.00,甚至2.13,这显然是不大可信的。
更进一步的分析表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被低估的可能还不止0.61亿人。从表1-2中可以看出,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全国县在业人口总数与农业在业人口数之差为5 940万人,即县在业人口中有近6 000万人从事非农行业的经济活动,而统计年鉴上的数字则表明乡村从业人员中有8 686万人从事非农行业。造成这一差别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是兼业劳动力的分类标准也许不一致,以致同一个人有时被统计为农业劳动力,有时又被统计为非农业劳动力。另一个原因与农业劳动力的统计方法有关。如果统计年鉴中采用乡村总劳动力减去其他各业劳力数的方法来计算农业劳力,则有可能多减去了城镇劳力中就业于乡镇企业的那部分人数。当反过来再用乡村从业人数与农业劳力数计算非农业劳力时,从事非农行业的乡村从业人数就被夸大了。因此,与农村劳动力总数相比,被迫留在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被低估的幅度很可能更高。如果这一推测是正确的,我们大致可以接受人口普查提供的数字,即农村劳动力留在农业部门的人数为4.21亿人,比统计年鉴上的数字大0.88亿人,也就是说,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总数也比通常认为的大0.88亿人。此外,市镇在业人口中有3 671万人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其中一部分郊区人口直接从事田间作业。因此计算农业劳动力实际需求量时应当把他们也考虑在内。这样一来,农村剩余劳动力总数被低估的幅度就更大了,很可能超过1亿人。
1.3 结 论
以上分析表明,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远远大于通常人们认为的数字,因此隐性失业的压力也比我们认识到的程度更严重。如果按照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以调整,农村剩余劳动力可能是两亿以上而不是一亿。当然,实际问题的严重性并不因计算方法或人们的认识而变化,这里所说的剩余劳动力也不是绝对失业人口,其中相当一部分已经转移到其他地区从事非农行业生产活动。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更清醒地认识这一问题的严重性,就有助于制定更有效的政策来减轻它的不利影响。
从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到,农村劳动力就业的分类标准和市镇建制标准直接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计算。如果不用平衡表的方式进行统计,或者不考虑城镇郊区从事农业和乡镇企业生产的城镇劳动力,一部分劳动力就有可能重复计算。当涉及非农产业(如乡镇企业)时,还可能将部分城镇劳动力错误地计算为农村实际就业人数。因此,使用各业分别统计再汇总的方法一定会夸大实际就业人数,从而低估农村隐性失业的人数。为了更准确地分析问题与制定政策,我们希望统计部门提出更可靠、更合理的统计方法与指标体系,也希望研究人员和有关部门更多地利用人口普查的成果来核对与校正现有的统计数据,在可能的条件下尽量把数字搞清楚。
第2章 中国城乡迁移和流动人口规模重新估计
农村人口迁移和流动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研究利用事件史分析法对城乡分年龄和性别的人口迁移率和流动率进行测算,并利用年龄推移法对1991~2010年的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农村户籍人口和农村流动人口进行重新估计。研究发现,首先,利用事件史分析法,采用整村调查数据能够较好地模拟中国农村人口的流动和迁移过程;其次,利用年龄推移法对农村常住人口的结构进行修正后发现,2015年农村65岁及以上常住老年人的比重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4.1个百分点;再次,不仅农村常住人口老龄化程度较高,在城乡间流动的人口中,50岁及以上的劳动力占比也呈上升态势,农民工群体的老龄化趋势非常明显;最后,虽然从时间序列上来看,农村留守儿童规模整体呈下降态势,但学龄前儿童留守的比例从2010年的43.3%上升到2015年的45.88%,提高了2.58个百分点。
2.1 引 言
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是政府和国内外学者关注的重点(农业部课题组,2000;宋洪远等,2002;蔡昉和王德文,2003;李仙娥和王春艳,2004)。由于城乡经济社会差距的扩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进程缓慢,中国城乡人口结构出现倒置,昔日年轻的农村人口以较快的速度步入老龄化,城市则因大量的农村青壮年劳动力流入而保持活力。以人口特征为主题的中国城乡经济社会问题研究越来越多(蔡昉和王美艳,2007;段成荣和杨舸,2009;段成荣等,2014;郭志刚,2014)。当前,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问题是经济转型阶段的重大现实问题,也是未来一段时间内深化城乡一体化改革,实现人民安居乐业的重要内容之一。
中国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统计数据及统计口径差异较大,不仅长期困扰着有关全社会人口流动、城乡人口流动强度等研究的深入(杨云彦,2003;韦艳和张力,2013),也导致根据不同数据来源计算的流动人口规模和留守儿童规模等数据存在很大差异。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以下简称“六普”)数据显示,农村户籍人口与农村常住人口分别为8.83亿人和6.71亿人,这意味着有2.12亿农村人口在户籍地以外的地方常住。按照人户分离口径统计,扣除市辖区的人户分离人口,2010年全国非市辖区的人户分离人口有2.21亿人。由此可推算,人户分离人口中农村人口占96%,剩下的4%(约900万人)是非农户籍非市辖区的流动人口。有研究发现,2010年全国流动人口中有1.5亿人来自农村(郑真真,2013),远低于根据“六普”数据计算得到的农村流动人口数。同时,该研究指出,2010年非农流动人口约为7 000万人,其中,非农跨省迁移人口就达1 980万人,远高于根据“六普”数据计算得到的900万人。
此外,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提供的外出农村劳动力数据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供的流动人口数据,均以在外地居住(人户分离)时间超过1个月为时限,这与国家统计局常住人口登记以6个月为时限的统计口径不同,且无论是流动人口监测调查,还是农民工监测调查,调查对象均为劳动年龄人口,缺乏农村未成年流动人口的信息,而通过不同渠道获得的留守儿童数据存在很大的争议。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简称全国妇联)发布的报告显示,“六普”时期农村留守儿童有6 102.55万人,而民政部2016年发布的农村留守儿童排查结果显示,农村留守儿童仅有902万人。6年时间里,农村留守儿童减少了约5 200万人引起了很多人的质疑。研究人口的迁移和流动所带来的农民工结构变化、农村留守儿童的规模和结构变化等问题,都需要利用有效的数据和方法进行分析、对比和预测,从而就人口变迁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做出准确的判断。
本章拟从人口流出地(即农村)角度出发,通过整村调查法重塑过去20多年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过程,并根据年龄推移法对中国农村常住人口和城乡流动人口的年龄结构进行修正。一方面,能够对有关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研究进行补充;另一方面,可以获取中国城乡迁移和流动人口的时间序列信息,并对不同类别人口进行预测。这不仅有助于量化户籍制度等对中国城乡人口迁移和流动的影响,还有助于对中国城乡一体化过程中的人口结构和劳动力变化做出预判。
2.2 分 析 框 架
研究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文献很多,有关人口迁移和流动的概念也纷繁复杂,如永久性迁移、非正规迁移、暂时性迁移、暂住人口和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