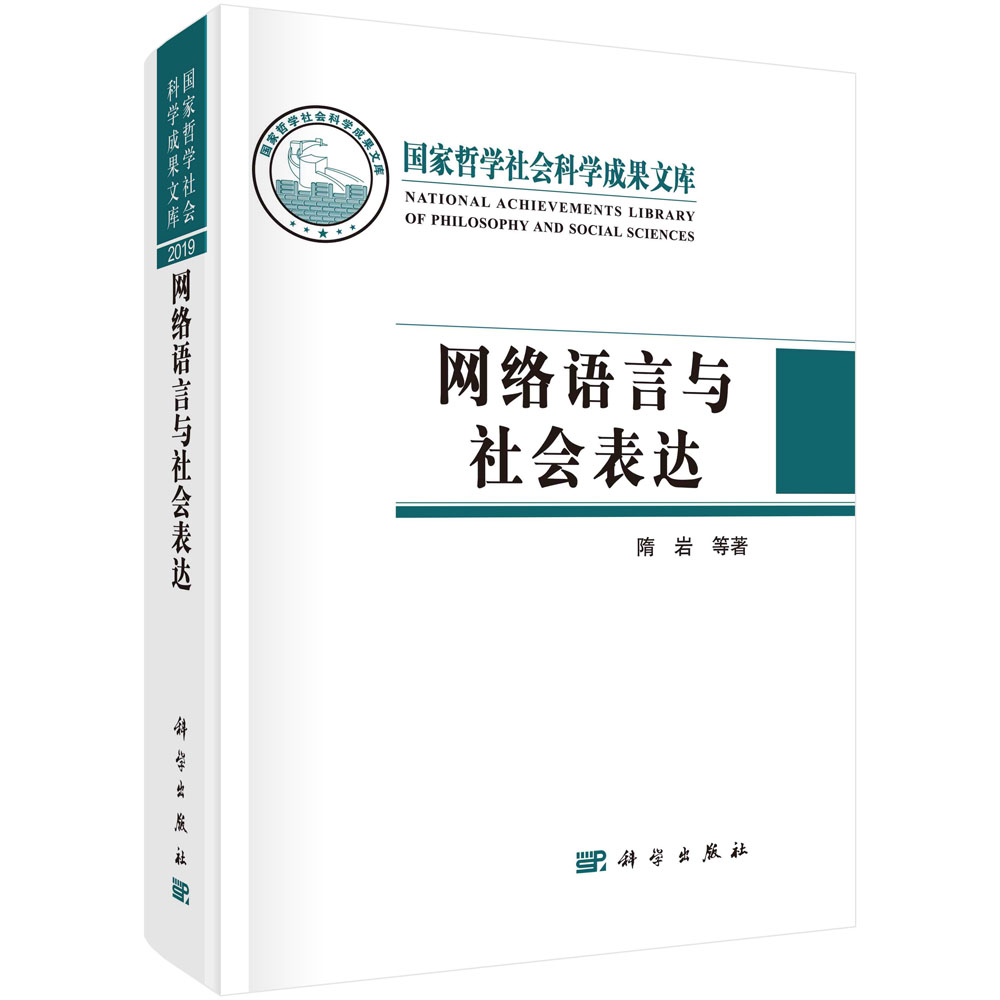
出版社: 科学
原售价: 99.00
折扣价: 78.21
折扣购买: 网络语言与社会表达/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
ISBN: 97870306816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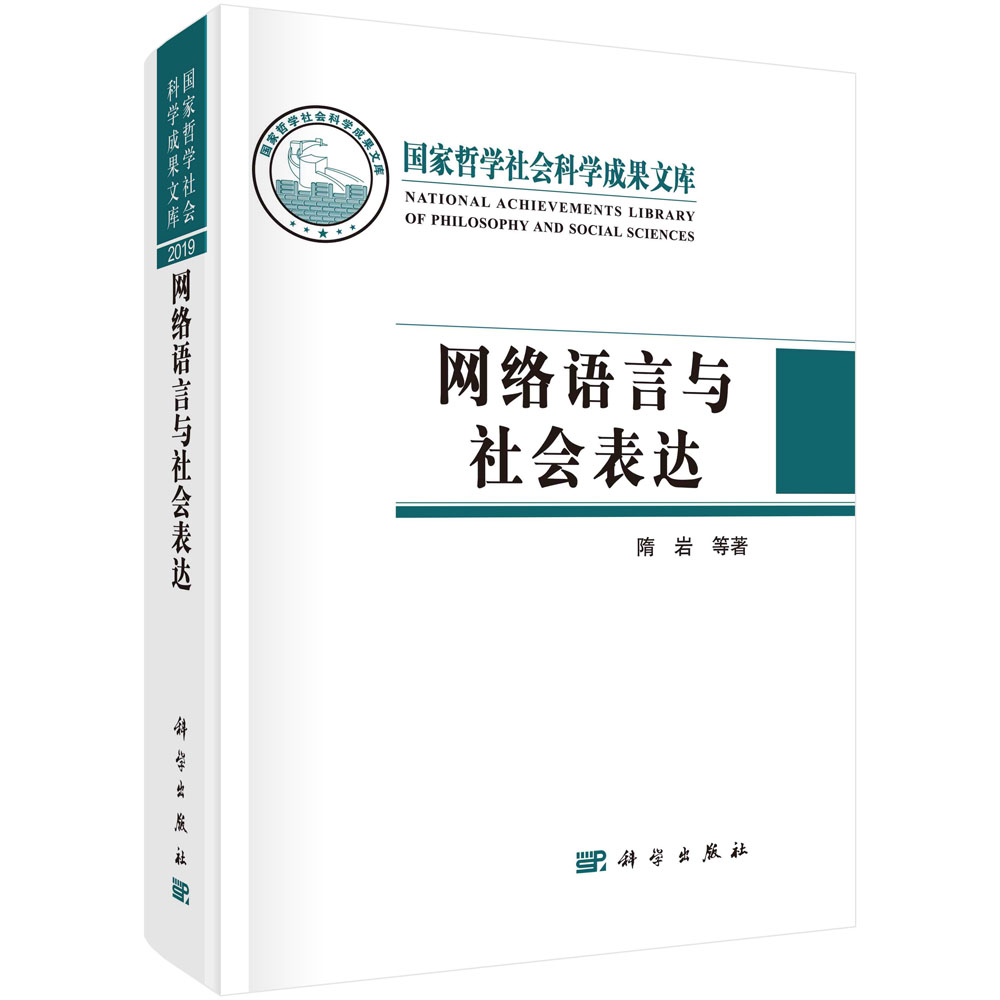
绪论
作为社会表达的网络语言
一、社会表达及其主体、形态在媒介发展视域中的流变
法国心理学家 Moscovici 在 1961年指出,社会表达“是关于社会思考和交流的理论。社会表达是日常生活中个体交流过程产生的一系列的概念、陈述及解释,是包括了概念和意象的一系列环境,如同普通意义的环境一样,社会表达既影响人群也被人群影响,且是历史的产物,详尽记录了历史发展的完整顺序及变化,并在历史过程中成功转化” ①。社会表达的历史流变依附于媒介域的历史分期。“媒介域”是由法国思想家雷吉斯 德布雷提出的媒介学概念,它是指“以信息传播的媒体化配置(包括技术平台、时空组合、游戏规制等)所形成的包含社会制度和政治权力的一个文明史分期” ②。从媒介史学观出发,德布雷将媒介域划分为以口语、文字为表达形态的逻各斯域;以活字印刷为表达逻辑的书写域;以视听感官为主,“将书籍从其象征底座赶下台”的电子图像域。 ③此后,接踵而至的技术繁殖又将媒介域延拓到集多种传播形态于一身的数字域。在线性的历史流变中,媒介域的发展不断影响着社会表达的转化;基于人类交流互通需求的社会表达也在所处媒介域的不断更替和叠加中,实现着从媒介形态的表层改变到质变的历史性变革。
由此,笔者从媒介学研究范式出发,结合社会表达形态与媒介域的依附关系,突出以人为核心的主体地位及其表达形态的演变,来探讨社会表达的变革律动。需要说明的是,印刷技术的诞生使社会进入大众传播时代早期,而后期出现的以广播、电视为代表的图像视听媒介则在大众传播时代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在以印刷为技术特征的书写域和以视听为感官特征的图像域中,社会表达所使用的表达形态与表达主体的性质密切相关,因此,本书在论述中将“书写域”和“图像域”统归于“大众传播时代”,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域归为“群体传播时代”,以更好地划分媒介和表达的疆界。
通过梳理可以发现,社会表达经历了三个重要时段:①在囿于地缘的社会发展早期,社会表达经历了小范围、封闭式人际表达的“前大众传播时代”;②基于工业化的物质生产能力,社会表达进入了“渠道霸权时代” ①,以及由传统媒体控制表达渠道的“大众传播时代”;③ 20世纪末,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带领社会表达走进了以社交媒体为平台、以网络语言为主要表达形态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这一系列的时代迁移逐步消解了媒介的时空偏倚与主体的阶层制约,使社会表达的主体、形态与效果都在历史的研判中或改变,或创新,或凸显。
(一)前大众传播时代
此时由于物理空间的褊狭和技术的落后,社会表达的特征主要表现为主体单一、渠道单向、形态单薄。初民社会的原始表达是缔造以人的身体为媒介、以口头语言和表情动作为手段的“亲身传播” ②,例如,原始赞歌、神话、教义的传颂和舞蹈的形体表达。在我国上古时期,“乐”是重要的社会表达形式,它“是一种集诗歌、音乐及舞蹈为一体的复杂的艺术形式,在当时的政治生活中具有表达政治意见的重要功能,是其时重要的政治语言之一” ①。“乐”并不局限于政治表达,如农事祭祀乐舞的“葛天氏之乐” ②则是人们寻求精神寄托的民意表达。“正因为集音乐、舞蹈及诗歌为一体的‘乐’,是反映民风、民情的重要载体,所以早在夏代,王朝中就设有遒人一职,负责到各地采集诗歌,以了解民风民情。例如,《夏书》中就记载:‘遒人以木铎徇于路。’晋杜预注云:‘求歌谣之言。’又《礼记 王制》记载古制也说:‘命大师陈诗,以观民风。’” ③然而,当时的社会处于发展早期,囿于逻各斯域的技术,文明曙光初显且稚嫩无比,历史发展的轨迹变幻莫测,即使“遒人”一职的设置有利于民意的采集,媒介的单一仍使得话语权及话语传播效度局限于极少数的社会精英。随着文明羽翼的不断丰满,文字符号开始出现并丰富了人类的表达形态,然而行为活动场域和传播技术的拘囿仍使得普罗大众的社会表达长期局限于邻里亲友间,其对外传播用时较长、传播范围狭窄,有效性颇为微弱。
(二)大众传播时代
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使得前大众传播时代得以落下帷幕。机械复制急剧增加、电子媒介平台开始出现,社会表达渠道和传播疆界均有所突破。19世纪 30年代,以《太阳报》为代表的廉价报刊依托于蒸汽驱动印刷技术,大大削减了生产成本、降低了售价。加之以本杰明 戴为代表的创刊人在报刊内容方面的通俗化改造和经营运作的市场化转向,极大地扩大了报纸的消费群,报刊发行量呈指数级增长,标志着真正意义上大众传播时代的到来。基于工业革命的红利,西方资本规模急剧扩大,并形成霸权态势向海外扩张,也向中国蔓延。 19世纪末至 20世纪初,中国在政治、经济、思想上面临极大的内忧外患,民族危机空前。时处书写域的国内有识之士和先进知识分子救亡心切,他们深感群众思想觉醒的重要性和运用报刊宣传中国思想大变局的必要性,积极投入办报事业中。其中,以《循环日报》《时务报》为代表的政论体报刊开启了我国政治家办报的先河,为变法强国制造舆论,突破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言禁。“如果说印刷传播实现了文字信息的大量生产和大量复制,那么电子传播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①从 1837年大西洋西海岸的美国“电报之父”塞缪尔 莫尔斯发明电报机,到 20世纪 20年代太平洋西海岸的中国**批自办的广播电台开始在混沌的社会秩序中发声,再到 1930年无线广播几乎遍及全世界,电子媒介的逐步应用使基于书写域的社会表达畛域有了进一步突破,以“听”为新型表征的电波渗透无孔不入,使远隔重洋不再成为人类沟通的阻碍,进而实现了从传声渠道进行宣传和传播。电子图像域的电视则诞生于 20世纪 20年代;中国电视机构较之则晚,诞生于 1958年,而快速发展于改革开放以后,新闻、节庆、仪式、娱乐、故事、生活等多种类型的电视影像内容走上改革开放后的中国荧屏。集声音和影像信息于一身的体外传播给予受众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现场感,作为一件家用电器,电视所提供的新兴时尚、直观易懂、形象生动的文娱内容建构了重要的家庭社交场景,为大众传播奠定了广博的受众基础。
由此可知,大众传播时代书写域和电子图像域的大规模覆盖,打开了受众知悉社会的窗口,从理论上来说,越来越多的报纸、广播电视媒体出现,使社会表达变得更加便捷和可行。然而,获取信息的便利不代表社会表达的便利,传播媒介的更迭未能使民众获得更多的社会表达契机,媒介组织仍然是大众传播时代占据社会的表达主体。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大众媒介建构一系列的社会议程,将受众置于“拟态环境”之中。普通群众有部分发声渠道,但由于对社会的经验性触达范围狭小,发声内容往往也只是对拟态环境的反馈,在媒介组织的把关后,产生微弱的影响抑或不产生影响。这种传播路径的成熟实际上引致了社会表达的两极化趋势,即精英话语权的垄断和个体话语表达的微弱。另一方面,以印刷、电子媒介为代表的文化工业的批量生产和机械复制,使受众通过大众媒介接收到的信息趋于一致或完全一致。长此以往,在不断大众化、城市化的社会发展中,语言也在不断地标准化和规范化,语言的丰富性和话语活力难以得到增强,这也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个体进行社会表达的内涵与外延。因此,大众传播时代,媒介组织成为社会表达的主体,普通受众的社会表达在大众媒体上无法集中实现,也很少受到鼓励,对社会产生的影响、发挥的作用有限。
(三)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
20世纪末,随着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信息总量的扩大、抵达人群的广度及信息传播速率的增长,都在呼唤一种与此相应的媒介” ①,基于此,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数字媒体开始普及,为人类的社会表达建构了另类的公共场域。互联网的社交性、共享性及草根性在本质上培育了新兴的网络群体,即网民。互联网数据研究机构 We Are Social和 Hootsuite 于 2019年发布的报告显示,全球人口总数为 76.76亿,随着互联网技术的普及和深耕,网民人数已达 43.88亿,同比增长 3.67亿人,其中有 34.84亿人活跃在社交媒体上;从网络使用时长来看,全球互联网用户平均每天上网时间为 6小时 42分钟,也就是说人们生活中的 1/4的时间在上网。②由此可见,新时代的数字土著(数字原住民)以及在新技术的流布中持续黏附的数字移民为互联网群体传播提供了庞大、多元、广阔的传播源。“所谓群体传播,是群体进行的非制度化的、非中心化、缺乏管理主体的传播行为。” ③依托于不被约束、自发、平等的特征,群体传播所积聚的力量在自觉中产生新的社会意识和媒介感知,改变了传统精英阶层垄断社会表达路径的局面,重组了社会表达结构,使多元、异质的互联网群体的自由社会表达在技术上得以成立。“新信息更接近新技术,二者黏合在一起,就形成新的话语方式或舆论形态” ④,只要具有互联网或移动互联网终端,凭借具体的社交平台,任何网民均可以在“观点的自由市场”中投入社会表达的生产,进而输出多元话语,展现主体性地位的提升。在此过程中,新媒介的传播格局加速了网民社会表达的多样性与变异性传播,形成网络体系中新兴且不可分割的社会表达形态,网络语言就此诞生。
二、精练与多元:群体传播中网络语言表达的特性
Moscovici认为,“我们的现实是建立在社会表达的基础上,对表达的认知与对客体的认知同样重要,所有的客体都包括一个社会表达,社会表达是认知、态度及观点链中我们**能看到的一环” ①。社会表达输出的主要表征为语言形态,语言是人类社会所独有的符号系统。在基于虚拟空间的互联网群体传播时代,携带亚文化社交属性并集认知、态度、观念于一身的网络语言,是呈现网民社会表达非常重要的符码。网络语言是指产生并运用于网络的语言,狭义的网络语言一般只包括网民创造的、用于网络交流互动和信息传播的语言,它是通过互联网群体的社会表达而呈现出来的新兴语言形态,它把人们编织进整个网络的社会。因此,网络语言与网民及其社会表达共存共生、彼此依存。伴随互联网的更新换代和网民人数的不断激增,注重个人体验、具备自由感知的网络语言为互联网单元群体传情达意、交流互动、实现社会参与提供了新锐的手法,增强了语言的活跃性,传播力、影响力越来越大。语言永远是现实生活的一面镜子,网络语言主体特征的草根性、犀利机智的表达风格、多样化的传播介质表现出的话语权逆转趋势,使其不断从虚拟走进现实,并在很大程度上融入社会之中。
(一)网络语言分类多样化
从梵 迪克关于话语分析的语境视角出发可知,语言的产生、传播、更迭与其所对应的时代特征、社会文化和物质生产力水平存在“共变”关系。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互联网平台的兴起伴随着社会发展的进程,经济体制转轨、社会结构转型、传播资源盈余引致了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变化。“新的规则、观念的输入敦促人们对既有的社会实施改造。同时,已有的语言系统无法表述新的社会情境,面临‘莫可名状’抑或‘失语’的状态时,就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