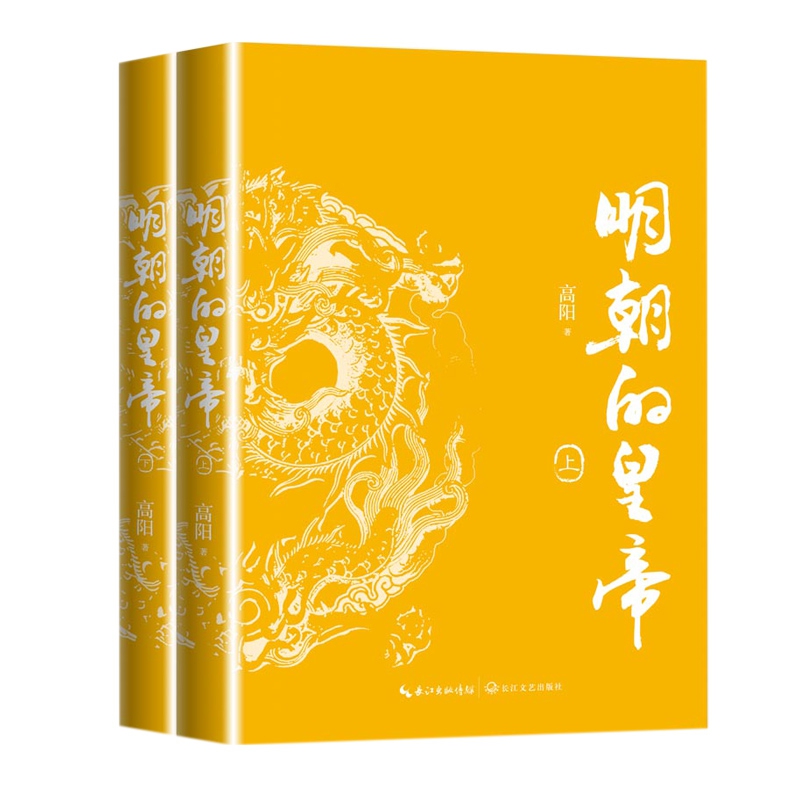
出版社: 长江文艺
原售价: 78.00
折扣价: 49.20
折扣购买: 明朝的皇帝:全二册
ISBN: 978757020986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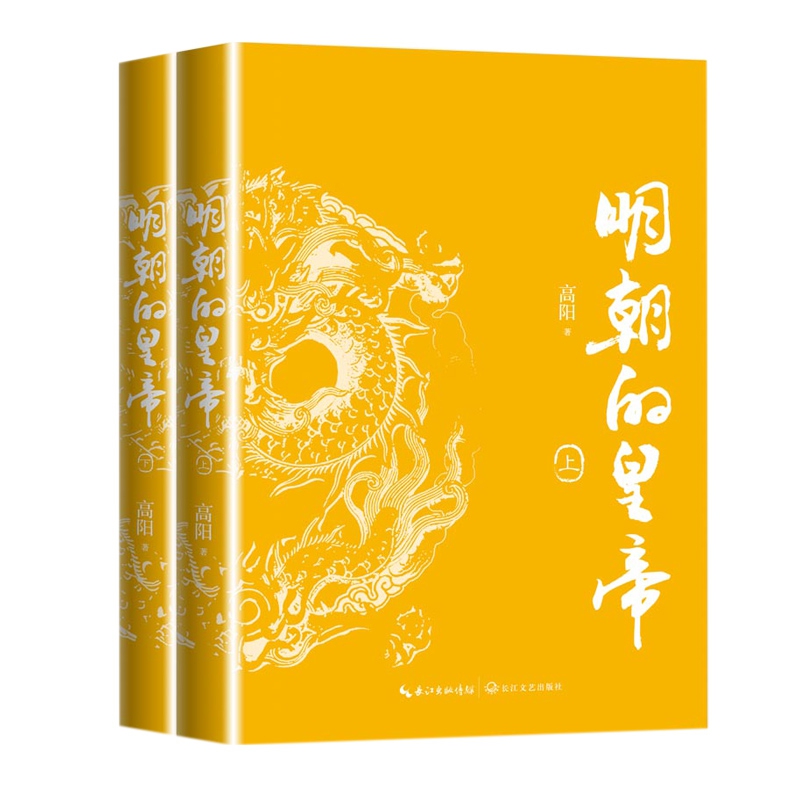
高阳(1922—1992),著名历史小说家,代表作有《李娃》《明朝的皇帝》《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等。高阳注重历史考证,文字冷静生动,读起来轻松畅快,读者仿佛身临历史现场,其作品被评为“华语历史小说不可逾越的高峰”。
第二章 夺门之变 一 宣德年间民生乐业 明朝有个很够格的皇帝,那就是宣宗。自燕王以“靖难”之名,夺了他侄子建文帝的皇位,帝系即由长房移转到四房,燕王即位为成祖,在位二十二年传仁宗;仁宗在位未一年而崩,传位宣宗,年号“宣德”。 《明史?宣宗赞》说,宣德年间:“吏称其职,政得其平,纲纪修明,仓庾充羡,闾阎乐业,岁不能灾。盖明兴至是,历年六十,民气渐舒,蒸然有治平之象矣。”又说宣宗“英姿睿略,庶几克绳祖武”。大致一个皇朝在统一四海、与民休息之际,能出一个好皇帝,就必有一段太平盛世出现;而此皇朝,亦就靠此造成太平盛世的深仁厚泽站住脚,享国至数百年之久。汉朝的文、景,唐朝的贞观、开元,宋朝真宗、仁宗之治,以及明朝的仁宗、宣宗都是如此。 可惜,明宣宗与宋神宗一样,都只活到三十八岁;英年早崩,社稷苍生的大不幸。在宣德享祚的十年中,朝势之美,史不胜书,唯一的缺失,就是纵容内监,设“内书堂”,简文学之臣教太监读书,并使太监“秉笔”批本。太祖定制,内侍干预政务者斩;既令秉笔,则太监不得不与内阁打交道,因而逐渐与外廷交结,太祖的遗命至此不行,遂启一代宦官之祸。就此层而论,不能不说宣宗不肖;而纵容宦官的结果,就在他儿子身上便生巨祸。得失兴亡,因果历历,只是种因者往往不及亲见,此所以一部“二十四史”,充满了荒谬。 宣宗崩后,皇太子祁镇即位,时年九岁,是为英宗。宣宗在位时,孙贵妃以殊色得宠,胡皇后无故被废,孙贵妃被册为皇后。但孙贵妃得以正位中宫,虽说出于恩宠,也因为她“生”了皇长子,而此皇长子实在是宫女所生,为孙贵妃假装怀孕,取而为子。及至继位为君,当然没有人再敢提他的生母了。 明朝的年号,都是“从一而终”,唯一的例外就是英宗,第一个年号定为“正统”;内阁拟此二字,是不是要特意表明他为“嫡出”之子,很值得玩味。但当宣宗初崩时,外间有召襄王入承大统的传说。襄王名瞻墡,仁宗第五子,与宣宗同为张皇后所出,封在长沙,颇有贤声,在“国赖长君”的原则下,兄终弟及,亦非无此可能。 二 委任股肱四海大治 这时的决定权操在张太后手里。明朝多贤后,高祖马皇后、成祖徐皇后、仁宗张皇后,三代均有懿德。这位宣德朝的张太后,为她本身着想,应该立襄王,因为这一来,她的身份不变,仍为太后;而立皇太子祁镇为帝,她就成了太皇太后,祖母与孙子,关系到底隔了一层。但是张太后选择了孙子,《明史?后妃传》记: 宣宗崩,英宗方九岁,宫中讹言,将召立襄王矣。太后趣召诸大臣至乾清宫,指太子泣曰:“此新天子也。”群臣呼万岁,浮言乃息。 由此可见,她的措施是很贤明的。大致皇位的继承,以父子递嬗为正格;兄终弟及,会发生三种弊病:第一,一弟继则另一弟亦可继,因而遭致骨肉间觊觎皇位的奇祸;第二,一朝天子一朝臣,藩王入承大统,则王府僚属即为从龙之臣,与先朝旧臣争夺权势,必致引起大局的不稳;第三,继统不继嗣,宗庙的祭典发生麻烦,如世宗的“大礼议”,就是最明显的例子。 因此,以社稷为重的太后,如宋朝的宣仁太后和这位张皇后,都依正规行事。而反面的例子,则是慈禧太后,同治崩后无子,应择“溥”字辈近支皇裔继统继嗣,而慈禧为求复得长期垂帘听政,召载湉入宫,私心自用,终于覆清。相形之下,张太后又有可称。当时群臣请她垂帘听政,她说:“毋坏祖宗法。”只传懿旨罢一切不急之务,尽心勉励幼帝向学,委任股肱,四海大治。 “股肱”者:杨士奇、杨荣、杨溥,史称“三杨”。执政都是二三十年,都享大年,缔造太平而享太平之福,真正是所谓“太平宰相”。《明史?三杨传赞》: 成祖时,士奇、荣与解缙等同直内阁。溥亦同为仁宗宫僚,而三人逮事四朝,为时耆硕,入阁虽后,德望相亚。是以明称“贤相”,必首“三杨”。均能原本儒术,通达事几,协力相资,靖共匪懈。史称“房杜”持众关效之君,辅赞弥缝而藏诸用;又称姚崇善应变,以成天下之务;宋璟善守文,以持天下之正,三杨其庶几乎。 正统初年,内有贤后,外有“三杨”,在明朝历史上,是为全盛时期。 三 太监王振擅作威福 不幸的是,“三杨”也犯了很大的一个错误。这要从王振谈起。王振是个太监,他的出身很奇特,可能是自有太监以来独一无二的。据孟森《明代史》考出明朝严从简的《殊惑周咨录》中,有这样一条记载: 王振,山西大同人。永乐末,诏许学官考满乏功绩者,审有子嗣,愿自净身,令入宫中训女官辈。时有十余人,后独王振官至太监。世莫知其由教职也! 所谓“学官”就是地方教育官员,其首长在府为“教授”,在州为“学正”,在县为“教谕”,以下都有“训导”为佐理,“月课士子之艺业而奖励之”,向来是极清高的官职,想不到会净身去做太监。 就因为王振的出身“不凡”,所以在宣德年间被选入侍东宫。英宗一直称他“先生”,则可知曾为教英宗认方块字的启蒙老师。英宗对他极其信任,即位以后,授为“司礼监”。而王振可能颇为向往永乐的武功,所以从小就鼓励英宗“阅武”,“北狩”之祸,种因于此。 王振的擅作威福早见端倪。张太后一死,更无忌惮,秉笔批本,大权独揽。而在张太后生前,大约是正统二年正月,张太后曾经要杀王振,《明史纪事本末》叙其事如下: 太皇太后张氏尝御便殿,英国公张辅,大学士杨士奇、杨荣、杨溥,尚书胡被旨入朝,上东立,太皇太后顾上曰:“此五人,先朝所简贻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计。非五人赞成,不可行也。”上受命。有顷,宣太监王振。振至俯伏,太皇太后颜色顿异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当赐汝死。”女官遂加刃振颈,英宗跪为之请,诸大臣皆跪。太皇太后曰:“皇帝年少,岂知此辈祸人家国,我听皇帝暨诸大臣贷振,此后不可令干国事也。” 张辅是武人,胡以周游天下访知建文帝的踪迹受知于成祖,才具不及“三杨”。君子责备贤者,后世多以“三杨”不乘时机诛王振为可惜。而以后数年,“三杨”竟不能不敷衍王振。 四 禁宦官干政的铁碑 王振只有张太后能约束他。张太后的方法是,每隔几天,遣太监到内阁问“三杨”近日施行何事,如果其中有出于王振独断而未经内阁会议的,张太后一定会把王振找来骂一顿。这样骂到正统七年十月,太皇太后驾崩了。 当大渐之际,“三杨”只剩了“二杨”——杨荣已死,杨士奇和杨溥被召至寝宫门外,张太后命太监问“二杨”国家还有什么大事未办。杨士奇举了三件事:第一件,“建庶人”——当时对建文帝的官式称呼——虽亡,应该修他的实录;第二件,成祖曾有诏令,谁收藏方孝孺等人遗著的,处死,这条禁令应该取消;第三件未及奏上,张太后已崩,因而史书没有记载,但可以断言的是,决非裁抑宦官的权势。 老太后一死,王振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盗碑”。太祖年间,鉴于前代宦官之祸,特意造一面三尺高的铁碑,立于宫门口,上铸八个大字:“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王振进进出出,看得刺心,把这面碑悄悄移走。照律例言,这是死罪,但没有人讲话。 到了正统十一年七月,“三杨”均已下世,阁臣的次序为曹鼐、陈循、马愉、苗衷、高穀,除了马愉以外,其余四人都是“三杨”在日王振所荐。曹鼐、陈循都是状元,但亦都是庸才,加以举荐之恩,因而王振得以肆无忌惮。当然,主要的是他能得到皇帝的宠信。 英宗对王振,不仅宠信,实为敬惮,此亦是不可解之事。正统六年九月,明朝称为奉天、华盖、谨身的“三大殿”及乾清、坤宁两宫落成,大宴百官。照规矩,宦官不得参加外廷的大宴,王振自然很不高兴。等皇帝派人来问“王先生”在干些什么时,王振正大发脾气,他说:“周公辅成王,我就不能在那里坐一坐?”皇帝听得这话,皱了半天的眉,下令开东华中门召王振,百官都在门外迎拜,王振才转怒为喜。 这时张太后还在,王振已经如此,于此可见,张太后左右早已为王振威胁利诱,控制在手下,他的作威作福,根本就没有人敢去告诉卧病深宫的张太后。 这样到了正统十四年,终于激出“土木之变”。 当代历史小说家高阳力作!风云起伏的明代历史,写尽众生百态。好读好看,装帧精美,大气双封。